
8月20日,由文艺报社、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邵璞诗选》新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郭运德出席研讨会,来自文学界、艺术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对邵璞诗歌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主持。
王祥夫:作家、画家
邵 璞:诗人、画家
王祥夫:焦墨山水可以肯定一点的它是就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能够领略和欣赏焦墨的到最后还应该是文人群体。你让工人和农民来对着焦墨山水鼓掌,这不太有可能。
邵 璞:在2013年《邵璞焦墨艺术研讨会》上,荣宝斋常务副总经理、画家唐辉先生、《美术》执行主编尚辉先生等都谈到了我的焦墨中国画创作与“文人画"的相关性,这个话题的提出,本身反映的一是我不是美术科班出身,二是诗人出身,二是我的焦墨创作与其他一般的美术作品有一个一看就跳出来的区别,即不像一般的美术作品,一般的美术作品,可能通常都强烈表现的是书画本身的技巧、颜色、笔墨、深入与否、纯熟与否等,未强烈反映出"格调、情绪、意境,三是肯定我创作里有中国画追求的最高 价值。焦墨山水,作为中国画正在探索前行的一个流变,因为选择了排除颜色和水,选择减去中国画构成要素本身是为了能更出色达到中国画的独特表现。我本身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地道的诗人,所以我的焦墨中国画毫无疑问属于"文人画”的代表。书画艺术收藏者、爱好者追捧程度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还是艺术家、作家对我焦墨中国画的认可程度。中国画作品在不同人、不同时期的辨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文物、可能是灵魂的通道、可能是战斗的武器、可能是时代的标志,对此重要在画家自己内心追求什么。
[详细]
诗人邵璞坚持业余写作三十余年,诗不多,但很精。他的诗作表面上不涉及政治、历史和人文,基本上都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以此表达自己独特的心灵感受。这个以抒情诗为主的诗人更擅长写情诗,可见邵璞是个多情的种子。
多情的种子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在邵璞身上,男孩般的羞涩与东北汉子的豪放、细腻的内心与爽朗的行为、天真的罗曼蒂克与老练的江湖气息那么矛盾而又谐和地融合在一起,多重的性格也是造就了他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风格。粗略概括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给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诗人》《火山》《夏天,我们从黄土高原经过》等,属于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的诗风;一类如《致地中海》《囚鸟》《鸽栖》《透明的第三只手》等,属于是隐晦曲折、含蓄蕴藉的风格。
邵璞诗最突出的成就是表现他直抒胸臆的部分,这些诗一泻千里地渲染着青年一代的青春激情和心理渴求。通常而言,青春激情的表达容易直露,懵懂的异性饥渴有时不免带着几分情色因素,但邵璞的诗没有这些毛病,从青春期开始他的诗就是老道的。他善于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捕捉诗意,有独到的观察视角和充满激情的叙事,虽然受传统诗歌影响很深,但艺术表达却十分现代,所以特别受当时大学生们的追捧。他的成名诗《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写尽了小男生们羞涩的情感、渴望的心理和青春的骚动,浓而不艳,烈而不炽,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在一个无名的小站》多少天、多少年, [详细]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的宿舍
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借口
就是想去坐坐
那天大家说了很多很多
尤其那位玻璃似的女同学
平时她老像一股羞涩的风
匆匆地一闪而过
那天却仿佛仲夏的雷阵雨哗啦啦
打湿了手心,打湿了外套,也打湿了前额
那天,开始我们找老乡,找“本家”
谈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来扯到太阳岛
扯到“飞碟”一般的世界
谈到一种种别扭又时时都有的感觉
紧张严肃却不够团结活泼的
学习和生活
黏液质、胆汁质、多血质和神经质四种
性格 [详细]

邵璞
 《邵璞诗选》研讨会现在开始,欢迎大家的到来。本次研讨会由文艺报社和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各位来宾。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仲呈祥,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郭运德。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公安部宣传局局长、诗人杨锦,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诗刊》原主编叶延滨,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部学部长李怀亮,《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赵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彭学明、何向阳,《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邱华栋,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空军文艺创作室副主任王界山,野战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诗人刘立云,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张力奋,广州中懋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彤,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宾堂,《作家通讯》主编高伟,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作家寒小风、徐永,《诗刊》编辑、诗人蓝野。主办方的同志:《文艺报》的新闻部主任颜慧,以及陈新民等。还有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中新社、新浪网、中国作家网等媒体的朋友……
《邵璞诗选》研讨会现在开始,欢迎大家的到来。本次研讨会由文艺报社和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各位来宾。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仲呈祥,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郭运德。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公安部宣传局局长、诗人杨锦,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诗刊》原主编叶延滨,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部学部长李怀亮,《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赵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彭学明、何向阳,《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邱华栋,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空军文艺创作室副主任王界山,野战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诗人刘立云,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张力奋,广州中懋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彤,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宾堂,《作家通讯》主编高伟,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作家寒小风、徐永,《诗刊》编辑、诗人蓝野。主办方的同志:《文艺报》的新闻部主任颜慧,以及陈新民等。还有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中新社、新浪网、中国作家网等媒体的朋友…… 诗书画是中国艺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邵璞在这三方面的成就是独树一帜的。我读了他的诗,欣赏了他的书法,又看了他的焦墨画之后,感到眼前一亮。这是一种极具个性、极具创造力,在中国文坛值得关注的一位艺术家。首先,我从邵璞的诗书画作品里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文化底蕴,而文化底蕴里最核心的部分又是他的文化自觉。我读他的诗《周末我们去女生宿舍》是很早之前,发现诗里有一种意境,有一种精神追求,和当年其他人写的小说相比,反映出来的境界不一样,艺术家的哲学思维主要体现在境界上。他的书法更是独具个性,尤其他的焦墨画,我从邵璞的焦墨画里悟出来了诗心,所以他的诗书画一体,都是从他艺术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这对整个艺术创作和艺术规律的把握,对艺术家的培养和造就都是极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这样一位有个性、有成就的艺术家,进一步探索新的方向,这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诗书画是中国艺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邵璞在这三方面的成就是独树一帜的。我读了他的诗,欣赏了他的书法,又看了他的焦墨画之后,感到眼前一亮。这是一种极具个性、极具创造力,在中国文坛值得关注的一位艺术家。首先,我从邵璞的诗书画作品里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文化底蕴,而文化底蕴里最核心的部分又是他的文化自觉。我读他的诗《周末我们去女生宿舍》是很早之前,发现诗里有一种意境,有一种精神追求,和当年其他人写的小说相比,反映出来的境界不一样,艺术家的哲学思维主要体现在境界上。他的书法更是独具个性,尤其他的焦墨画,我从邵璞的焦墨画里悟出来了诗心,所以他的诗书画一体,都是从他艺术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这对整个艺术创作和艺术规律的把握,对艺术家的培养和造就都是极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这样一位有个性、有成就的艺术家,进一步探索新的方向,这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我和邵璞基本上是同代人,进作协我是1984年,他是1985年,当时办公室不在一块,好像当时也不认识,上大学他是1979年我是1980年,所以读这本书一下让我想到很悲催的大学时代。我看《周末我们去女生宿舍》,不是我们,是他们,不包括我,我那时年龄太小,女生宿舍不是没去过,但是去女生宿舍的时候,没有怀着那么复杂的心思。当时读时就觉得他们心思太复杂,想法太多。现在看,我觉得真是能够感到时光的流逝,也能感到时代的变化。从诗歌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80年代的气氛,80年代的精神气质。《邵璞诗选》第二部分没有明确标年月日,我看大部分是写于80年代,使我们能够非常鲜明的感受到80年代的气质。我们这些从80年代过来的人,都会依然为之感动,依然觉得他把那个时代的气氛,把那个时代人们隐秘的心声表达出来了。
我和邵璞基本上是同代人,进作协我是1984年,他是1985年,当时办公室不在一块,好像当时也不认识,上大学他是1979年我是1980年,所以读这本书一下让我想到很悲催的大学时代。我看《周末我们去女生宿舍》,不是我们,是他们,不包括我,我那时年龄太小,女生宿舍不是没去过,但是去女生宿舍的时候,没有怀着那么复杂的心思。当时读时就觉得他们心思太复杂,想法太多。现在看,我觉得真是能够感到时光的流逝,也能感到时代的变化。从诗歌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80年代的气氛,80年代的精神气质。《邵璞诗选》第二部分没有明确标年月日,我看大部分是写于80年代,使我们能够非常鲜明的感受到80年代的气质。我们这些从80年代过来的人,都会依然为之感动,依然觉得他把那个时代的气氛,把那个时代人们隐秘的心声表达出来了。 邵璞是个有故事的人,我们打交道30多年,他是一个充满着激情,但是也是充满着矛盾复杂的个体,是天真烂漫的,也有老练的,既是细腻的、内向的,也有东北汉子豪爽的成分,既有孩子般的羞涩,也有北方人的狂野,既有商人的精明,也有诗人的细腻。他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邵璞的诗很精炼,但是所有诗读下来,能发现他是个多情的种子,都是情诗。他表面上不涉及社会的政治、人文、历史,实际上都是在借景生情、借物言志,表达的都是自己独特的心灵感受。他的诗歌,一类是比较直白,比较直抒胸怀的,比如像《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这样的诗;再就是比较隐讳一点的,含蓄蕴藉的,《求鸟》《透明的三只手》都是曲折的,但是也有自己心灵的表达。当年读这些诗是在认识邵璞之前,最早的时候是本朦胧诗选,朦胧诗选有他的四五首诗。读过诗再见到本人,就有全新的心理感受。
邵璞是个有故事的人,我们打交道30多年,他是一个充满着激情,但是也是充满着矛盾复杂的个体,是天真烂漫的,也有老练的,既是细腻的、内向的,也有东北汉子豪爽的成分,既有孩子般的羞涩,也有北方人的狂野,既有商人的精明,也有诗人的细腻。他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邵璞的诗很精炼,但是所有诗读下来,能发现他是个多情的种子,都是情诗。他表面上不涉及社会的政治、人文、历史,实际上都是在借景生情、借物言志,表达的都是自己独特的心灵感受。他的诗歌,一类是比较直白,比较直抒胸怀的,比如像《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这样的诗;再就是比较隐讳一点的,含蓄蕴藉的,《求鸟》《透明的三只手》都是曲折的,但是也有自己心灵的表达。当年读这些诗是在认识邵璞之前,最早的时候是本朦胧诗选,朦胧诗选有他的四五首诗。读过诗再见到本人,就有全新的心理感受。 邵璞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画家,简单说一下我对他诗歌的印象。我跟他的年龄是最接近的,我也是1979年的学生,所以他诗歌中表达的很多东西跟我非常接近,我尽管自己没能成为诗人,但是很喜欢诗,看他的诗特别能回到从前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诗确实跟朦胧诗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像朦胧诗选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持续阅读的一本,还有新诗潮诗集。他的诗能让人想起那个时代,那时候写诗都讲究押韵,朦胧诗实际上跟邓丽君的歌曲一样,在80年代有点“靡靡之音”,但过了30年后再看那些诗,读者会觉得非常传统,真的是古典的一部分。其次是意象,邵璞的意象跟北岛的意象不太一样,北岛他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用几十个意象来描述。邵璞的诗要稍微舒缓一点,所以他的意象没那么密集,但他在意象和押韵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所以他的诗读起来有种舒缓的、绵延的、更加古典的感觉。
邵璞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画家,简单说一下我对他诗歌的印象。我跟他的年龄是最接近的,我也是1979年的学生,所以他诗歌中表达的很多东西跟我非常接近,我尽管自己没能成为诗人,但是很喜欢诗,看他的诗特别能回到从前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诗确实跟朦胧诗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像朦胧诗选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持续阅读的一本,还有新诗潮诗集。他的诗能让人想起那个时代,那时候写诗都讲究押韵,朦胧诗实际上跟邓丽君的歌曲一样,在80年代有点“靡靡之音”,但过了30年后再看那些诗,读者会觉得非常传统,真的是古典的一部分。其次是意象,邵璞的意象跟北岛的意象不太一样,北岛他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用几十个意象来描述。邵璞的诗要稍微舒缓一点,所以他的意象没那么密集,但他在意象和押韵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所以他的诗读起来有种舒缓的、绵延的、更加古典的感觉。 邵璞是中国80年代诗歌运动的参与者,他是大学生诗歌运动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邵璞诗选》,实际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一个样本。因为邵璞80年代在学校开始写作到90年代封笔,这本诗集为80年代的思想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样本。邵璞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他的《周末去了女生宿舍》,对还没进过女生宿舍大学生们,其实很重要,题目本身就是朦胧的,因为大学宿舍是个很敏感的地方,如果大学是一个游泳池的话,那么女生宿舍就是比基尼遮住的地方。这首诗实际上进入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和青春萌动的证据。
邵璞是中国80年代诗歌运动的参与者,他是大学生诗歌运动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邵璞诗选》,实际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一个样本。因为邵璞80年代在学校开始写作到90年代封笔,这本诗集为80年代的思想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样本。邵璞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他的《周末去了女生宿舍》,对还没进过女生宿舍大学生们,其实很重要,题目本身就是朦胧的,因为大学宿舍是个很敏感的地方,如果大学是一个游泳池的话,那么女生宿舍就是比基尼遮住的地方。这首诗实际上进入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和青春萌动的证据。 读邵璞的诗是一次怀旧,我们聚在一起,向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致敬。时间走得确实非常快,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创作的那种明朗、沉静、理想、真挚,在他诗里有了充分的反应。他说“我们真挚,我们热爱生活”。他的这些诗,视野非常开阔,题材也非常广泛,感情很有质感,让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年代,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了,域外的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但是人这个时候反而是沉静的,他是安静的,没有名利的困扰,也没有分散人精力的手段。就是那时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他写到人和人一起散步、见面,他还原了那个时候特有的氛围。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诗里边的一些句子,是非常美好精巧的,比如“像盲人的眼睛一样被锁上”,“四季一般的情不自禁的信念”,“墙一样的河水里乘船”,“年轻不能以年龄来算,应该以心理”,这些说法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明练。
读邵璞的诗是一次怀旧,我们聚在一起,向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致敬。时间走得确实非常快,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创作的那种明朗、沉静、理想、真挚,在他诗里有了充分的反应。他说“我们真挚,我们热爱生活”。他的这些诗,视野非常开阔,题材也非常广泛,感情很有质感,让我们突然回到那个年代,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了,域外的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但是人这个时候反而是沉静的,他是安静的,没有名利的困扰,也没有分散人精力的手段。就是那时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他写到人和人一起散步、见面,他还原了那个时候特有的氛围。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诗里边的一些句子,是非常美好精巧的,比如“像盲人的眼睛一样被锁上”,“四季一般的情不自禁的信念”,“墙一样的河水里乘船”,“年轻不能以年龄来算,应该以心理”,这些说法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明练。 我是邵璞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可能是我的学长,但是不是一个系。邵璞当年写了那首《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正好是我进大学的第一年,在复旦屈原诗会上,当时邵璞在复旦的大礼堂朗诵了这首诗。当时的女生宿舍我们都很想去,但是可能去不了,邵璞当时能够去,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把钥匙,就是他的诗。我记得当时在复旦的时候,诗人和哲学系的同学身边都围着许多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1988年以后我离开中国去了英国,其实我当时跟邵璞结识,第一是因为他的诗歌,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去女生宿舍,还能写女生宿舍,当时在我看来是一个特权。后来跟邵璞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个诗人,有自己的想象,他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行动者。
我是邵璞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可能是我的学长,但是不是一个系。邵璞当年写了那首《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正好是我进大学的第一年,在复旦屈原诗会上,当时邵璞在复旦的大礼堂朗诵了这首诗。当时的女生宿舍我们都很想去,但是可能去不了,邵璞当时能够去,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把钥匙,就是他的诗。我记得当时在复旦的时候,诗人和哲学系的同学身边都围着许多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1988年以后我离开中国去了英国,其实我当时跟邵璞结识,第一是因为他的诗歌,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去女生宿舍,还能写女生宿舍,当时在我看来是一个特权。后来跟邵璞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个诗人,有自己的想象,他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行动者。 第一次看到邵璞的名字是在80年代读朦胧诗的时候,读到了《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最近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去年,大约是夏秋之际的时候。邵璞的诗在朦胧诗里是别具特色的,他不像当时舒婷、北岛、顾城的诗歌,他的诗有些委婉,但不艰涩,喜欢叙事和白描。刚才说的《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题目本身就是叙事的,而且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完全是白描的写法,但是里边存了一些东西,构成了当时朦胧的元素。他的诗是平白的,八九十年代我们看他写的这些诗,包括刚才举的一些例子,包括他写老人、车站的诗,其中都有叙事的成分。他在非常平实地说着一件事,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如果只用平实、朴素来评价他的诗,又走入了一个误区。他的诗里还有80年代的雄辩,一种雄辩的东西要突破白描。比如有的诗一开头六个“但见”,其实在写诗里是大忌,但是他就反其道而行之,构成一种气势。
第一次看到邵璞的名字是在80年代读朦胧诗的时候,读到了《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最近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去年,大约是夏秋之际的时候。邵璞的诗在朦胧诗里是别具特色的,他不像当时舒婷、北岛、顾城的诗歌,他的诗有些委婉,但不艰涩,喜欢叙事和白描。刚才说的《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题目本身就是叙事的,而且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完全是白描的写法,但是里边存了一些东西,构成了当时朦胧的元素。他的诗是平白的,八九十年代我们看他写的这些诗,包括刚才举的一些例子,包括他写老人、车站的诗,其中都有叙事的成分。他在非常平实地说着一件事,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如果只用平实、朴素来评价他的诗,又走入了一个误区。他的诗里还有80年代的雄辩,一种雄辩的东西要突破白描。比如有的诗一开头六个“但见”,其实在写诗里是大忌,但是他就反其道而行之,构成一种气势。 我读过邵璞的诗作,他最大的优势,一是本身在写诗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来画画,他把诗人与画家的身份相结合,通过文字打通了文学与艺术的通道,所以他的作品既有诗情也有画意,诗情与画意结合得比较完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白描似的诗句,比如《小巷里的女孩子》就是白描的,讲的是大白话,但是寥寥几笔,就把孩子那种阳光、沉静、艰辛、乐观描写得跃然纸上。诗集的第75页完全是写意的,第39页完全是工笔画,把一个男生朦胧的情感,想见女孩不敢见的那种羞怯与闷骚,写到了极致。他的诗也有一种雕刻的感觉,比如《鲁迅故居》,他从6个角度去写鲁迅故居,诗情画意结合得非常好,使人感觉很柔美。
我读过邵璞的诗作,他最大的优势,一是本身在写诗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来画画,他把诗人与画家的身份相结合,通过文字打通了文学与艺术的通道,所以他的作品既有诗情也有画意,诗情与画意结合得比较完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白描似的诗句,比如《小巷里的女孩子》就是白描的,讲的是大白话,但是寥寥几笔,就把孩子那种阳光、沉静、艰辛、乐观描写得跃然纸上。诗集的第75页完全是写意的,第39页完全是工笔画,把一个男生朦胧的情感,想见女孩不敢见的那种羞怯与闷骚,写到了极致。他的诗也有一种雕刻的感觉,比如《鲁迅故居》,他从6个角度去写鲁迅故居,诗情画意结合得非常好,使人感觉很柔美。 对于邵璞的诗,我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我翻开书柜,找到当年的那本《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一看才知道他那时写过一首诗叫《火山》,曾经烫过我一次。我是78届的大学生,我是从边缘参加诗歌运动的。当时学习成绩好的都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了,学习一般的则大都在省里读大学,我则留在省里。我们班里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班里要设计划生育委员,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为什么说特殊呢?我是24岁进大学的,我们班大的有30多岁,有一些人完全可以当父亲了。邵璞在诗中写到周末去女生宿舍,但对于我们这些年纪相对比较大的学生来说,进女生宿舍已经没有那种青春期的躁动。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有男朋友、女朋友了,或者已经结婚了。但是,从《火山》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人的共同性——那种对于国家的担当。
对于邵璞的诗,我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我翻开书柜,找到当年的那本《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一看才知道他那时写过一首诗叫《火山》,曾经烫过我一次。我是78届的大学生,我是从边缘参加诗歌运动的。当时学习成绩好的都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了,学习一般的则大都在省里读大学,我则留在省里。我们班里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班里要设计划生育委员,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为什么说特殊呢?我是24岁进大学的,我们班大的有30多岁,有一些人完全可以当父亲了。邵璞在诗中写到周末去女生宿舍,但对于我们这些年纪相对比较大的学生来说,进女生宿舍已经没有那种青春期的躁动。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有男朋友、女朋友了,或者已经结婚了。但是,从《火山》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人的共同性——那种对于国家的担当。 上世纪80年代,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非常热闹。我们从《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复旦大学是多么洋气,而且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那种自信。我是认认真真读了邵璞的诗,我发现了三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点。
上世纪80年代,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非常热闹。我们从《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复旦大学是多么洋气,而且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那种自信。我是认认真真读了邵璞的诗,我发现了三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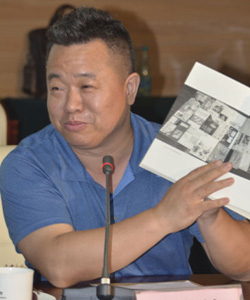 我写诗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当时写诗参考的教材就是《朦胧诗选》。那本诗选中就收有邵璞的诗,所以现在看到邵璞的诗集,首先唤起的是我对最开始写诗的感觉、感情,很多具体的事想起来了。邵璞收在《朦胧诗选》里面的那几首诗,我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有感触。当今天再看这些诗时,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仿佛一个时光的容器放在那儿,把某种东西给定住了,让我们重新打量1980年代启蒙文化背景下文学写作的价值。
我写诗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当时写诗参考的教材就是《朦胧诗选》。那本诗选中就收有邵璞的诗,所以现在看到邵璞的诗集,首先唤起的是我对最开始写诗的感觉、感情,很多具体的事想起来了。邵璞收在《朦胧诗选》里面的那几首诗,我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有感触。当今天再看这些诗时,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仿佛一个时光的容器放在那儿,把某种东西给定住了,让我们重新打量1980年代启蒙文化背景下文学写作的价值。 邵璞的诗,我以前读过一些,这次又读了一些。我更加体会到邵璞诗歌中的那种律动,其中的的感情线索、丰富意象都非常精彩。我读起来,对这些作品感到特别亲切。我也是78届的学生,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精神状态与现在的是不一样的。读邵璞的诗歌,我能感受到那一代人的精神共同性。《邵璞诗选》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典型的80年代的声音,读了之后,又勾起来一种思绪和情怀,感觉到这是一种精神上、血脉上的相通感。这种精神也许是现代诗歌中最需要的。
邵璞的诗,我以前读过一些,这次又读了一些。我更加体会到邵璞诗歌中的那种律动,其中的的感情线索、丰富意象都非常精彩。我读起来,对这些作品感到特别亲切。我也是78届的学生,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精神状态与现在的是不一样的。读邵璞的诗歌,我能感受到那一代人的精神共同性。《邵璞诗选》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典型的80年代的声音,读了之后,又勾起来一种思绪和情怀,感觉到这是一种精神上、血脉上的相通感。这种精神也许是现代诗歌中最需要的。 我以前看过邵璞的画,现在又读到了他的诗。我觉得,邵璞虽然是一个画家,但是他的画中有一种诗意的表达,有一种对生活的温情。我觉得邵璞搞艺术创作,没有太直接的目的性,他很洒脱。我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去采风,大家都抢着画达官贵人,而邵璞却将笔触锁定在一个基层的战士身上。这么多年来,虽然职业不断变化,但邵璞依然在内心保持着对文学、诗歌、美术的热爱。
我以前看过邵璞的画,现在又读到了他的诗。我觉得,邵璞虽然是一个画家,但是他的画中有一种诗意的表达,有一种对生活的温情。我觉得邵璞搞艺术创作,没有太直接的目的性,他很洒脱。我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去采风,大家都抢着画达官贵人,而邵璞却将笔触锁定在一个基层的战士身上。这么多年来,虽然职业不断变化,但邵璞依然在内心保持着对文学、诗歌、美术的热爱。 我喜欢邵璞的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里,我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去阅读朦胧诗。现在读邵璞的诗,仿佛跟着他的诗句重新回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古代的文人经常如此,但现在却“画家就是画家,诗人就是诗人”,很多都是为了钱而画,没有变成自身的一种修养方式。邵璞兼修诗书画,很是难得。
我喜欢邵璞的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里,我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去阅读朦胧诗。现在读邵璞的诗,仿佛跟着他的诗句重新回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古代的文人经常如此,但现在却“画家就是画家,诗人就是诗人”,很多都是为了钱而画,没有变成自身的一种修养方式。邵璞兼修诗书画,很是难得。 我跟邵璞也是同时代的人,我1980年进黑龙江大学,我们当时也创立了诗社,跟各地学校联系也比较多。研讨邵璞的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对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生活和当时的诗歌运动进行一次回顾。
邵璞的诗非常有个性,也非常有特点。他的代表作《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描述的应该是一代年轻人的记忆。到今天,30年以后,我们再重读这些作品,感到非常的亲切。可能邵璞根本没去过女生宿舍,但是他捕捉了一种意象。
我跟邵璞也是同时代的人,我1980年进黑龙江大学,我们当时也创立了诗社,跟各地学校联系也比较多。研讨邵璞的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对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生活和当时的诗歌运动进行一次回顾。
邵璞的诗非常有个性,也非常有特点。他的代表作《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描述的应该是一代年轻人的记忆。到今天,30年以后,我们再重读这些作品,感到非常的亲切。可能邵璞根本没去过女生宿舍,但是他捕捉了一种意象。 邵璞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到今天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实际上把邵璞再归为朦胧诗肯定是不对的,他还是处在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背景之下。读了邵璞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诗作,我感觉他的诗歌变化并不是很大。读他的诗歌,我首先想到关于诗歌声音的说法。邵璞的诗肯定是面向自我,但是这种自我又是敞开的。为什么他的作品读起来,读者会有同感?这是因为他的自我还是面向公众的,邵璞诗歌的声音恰恰是一种宣告性的。
这种宣告性的声音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带有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符号,其一项都比较公共化,比如江河、大山、旭日、路灯等。在邵璞的诗歌中,一种公共的、外在的声音比较明显,它跟歌词好像区别不是很大,甚至有的诗歌押韵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他的声音决定他的公共性。同时,他的诗歌中有很多箴言警句,这也是当时大学生写作的特点。在诗选中,有一些关于城市的诗歌,对城市肯定的比较多,有对科技城市的赞颂。但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当下诗人对城市更多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感悟诗歌主题与时代语境之辩证关系。
邵璞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到今天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实际上把邵璞再归为朦胧诗肯定是不对的,他还是处在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背景之下。读了邵璞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诗作,我感觉他的诗歌变化并不是很大。读他的诗歌,我首先想到关于诗歌声音的说法。邵璞的诗肯定是面向自我,但是这种自我又是敞开的。为什么他的作品读起来,读者会有同感?这是因为他的自我还是面向公众的,邵璞诗歌的声音恰恰是一种宣告性的。
这种宣告性的声音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带有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符号,其一项都比较公共化,比如江河、大山、旭日、路灯等。在邵璞的诗歌中,一种公共的、外在的声音比较明显,它跟歌词好像区别不是很大,甚至有的诗歌押韵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他的声音决定他的公共性。同时,他的诗歌中有很多箴言警句,这也是当时大学生写作的特点。在诗选中,有一些关于城市的诗歌,对城市肯定的比较多,有对科技城市的赞颂。但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当下诗人对城市更多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感悟诗歌主题与时代语境之辩证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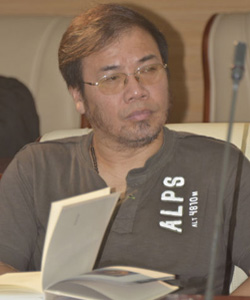 我曾读过《朦胧诗选》,由此知道邵璞的诗歌。但现在读到《邵璞诗选》,更加全面地了解邵璞的为人与为文。邵璞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有一颗多情自由的心。惟有这样一个多情、自由的心,才有他的诗和画。他诗歌里边有一种诗、音、画三位一体的感觉,真正能把这些打通的人非常非常少。他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音律性,我在读诗过程中也发现,他的诗歌里边居然有那么多押韵的地方,有的诗歌甚至就是非常好的歌词。由此我想到,邵璞除了有自由的心,还有一颗笃定的心,对艺术抱有非常笃定的态度。虽然这么多年,像他这么押韵的诗不是一种时尚的诗,还是在继续他的追求。我觉得表现出他的一种笃定、沉静的态度。《邵璞诗选》记录了80年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迹,而且也是见证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我们可以借助这本诗选,向更年轻一代说明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的青春。
我曾读过《朦胧诗选》,由此知道邵璞的诗歌。但现在读到《邵璞诗选》,更加全面地了解邵璞的为人与为文。邵璞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有一颗多情自由的心。惟有这样一个多情、自由的心,才有他的诗和画。他诗歌里边有一种诗、音、画三位一体的感觉,真正能把这些打通的人非常非常少。他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音律性,我在读诗过程中也发现,他的诗歌里边居然有那么多押韵的地方,有的诗歌甚至就是非常好的歌词。由此我想到,邵璞除了有自由的心,还有一颗笃定的心,对艺术抱有非常笃定的态度。虽然这么多年,像他这么押韵的诗不是一种时尚的诗,还是在继续他的追求。我觉得表现出他的一种笃定、沉静的态度。《邵璞诗选》记录了80年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迹,而且也是见证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我们可以借助这本诗选,向更年轻一代说明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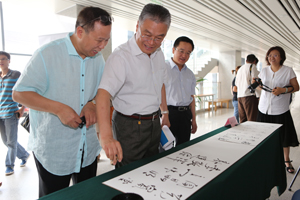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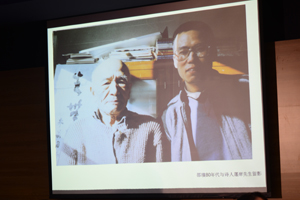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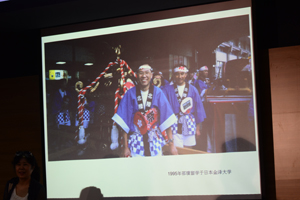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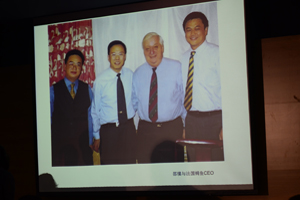

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