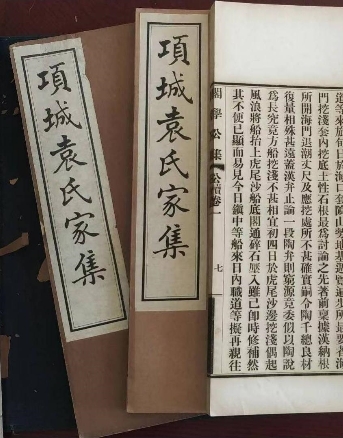还需要一个“80后文学”的概念为我们加冕吗?
主持人
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诗人,批评家)
观察者
黄 平(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批评家)
林 森(作家、诗人)
李 峥(专栏作家,“听筝读诗”创始人)
金 理(复旦大学副教授,批评家)
蔡 东(作家)
宝 树(科幻作家)
戴潍娜(诗人、译者)
罗皓菱(记者、作家)
最近几年,80后在多重意义上得到关注和讨论,在社会学的层面,这一代的长大成人构成了历史事件,并必将在整体上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在文学或者文化的层面,这一代人创造的精神产品也将接受更多的质疑、挑战和反思。强调原创性和个人风格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在瓦解固有的“80后文学”概念。“80后文学”这一命名还有意义吗?它已经并将继续呈现何种变化?本期非常观察栏目邀请80后的作家、批评家、媒体人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1
杨庆祥:“80后文学”这个概念,讲了很多年,其起源和外延都变得非常含糊不清,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认可这个概念?或者说,如果认可,是在什么意义上?如果不认可,又是在什么意义上?
黄 平:我还是认可的,“80后”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代是有高度历史性的一代,并在这种历史时间中形成了有独特特征的美学,尽管这种美学往往以脱历史的面目呈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以“80后”为窗口倒推回去,是一种可能。
林 森:有保留的认可,认可的这部分,只是因为我没办法让自己不出生在1982年。“80后文学”作为早先有某种市场期待的提法,是成立的,但在这个提法内,并没有提出多少和文学审美有关的内容,以至于到了最后,只要是年龄出生在1980年代,就全被这个筐子装进去了。现在,谈论任何一个作家,好像不先提一个“几零后”就没法谈,韩少功出《日夜书》的时候,还被说成50后;格非会被说成60后。没办法,对很多人来讲,先装筐才好讨论。
李 峥:简单用代际、民族、性别、地域等来区分人,是很愚蠢的;同样,简单用“80后”来看待作家与作品也很愚蠢。文学气脉的差距,不能简单按照年代来区别。真正的文学杰作会穿越历史语境,跨越一时、一地、一代的局限。“80后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裹挟了太多的设计,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80后文学”这个新概念也在很大范围内博取了人们的眼球,它并不能涵盖这一代人写作的复杂性。所以,今天,我不愿认可这个概念。
金 理:我只能这样回答:目前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依然还在使用“80后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我们承认这个概念在学理上并不具备太充分的正当性。它最早的出场,和商业炒作、文学批评命名的无力、对于“断裂”的渴求等密切相关。其次,之所以不具备充分的学理性却依然还在使用,不过就是视之为“方便法门”罢了,就好像翻开文学史著作,“建安文学”“南唐词人”“大历十才子”“知青一代”等比比皆是。所以第三,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并不是说放弃概念,而是如何找到有说服力的概念。我知道不少同代人不屑于此,尽管他们几乎都通过这个概念有所获益过,尤其不少创作者很反感被捆绑在一起来讨论,他们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单打独斗的,伟大的作品从不在一面旗帜下拉帮结派。但是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能够以个体的面貌最终在文学史上占据单独章节的,往往是极少数;而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指认,往往都是通过一两个精简而有效的关键词来“落实”的。前些年看到过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对话围绕的主题就是他们这代“60后”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比如“日常生活”,从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反观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因为创作所呈现的美学面貌的模糊,也许是因为评论的阐释力不够,今天讨论“80后”,我就觉得很难提炼出前人那样的关键词。顺便一说,“80后”这个概念已开始进入文学史。藤井省三先生在《华语圈文学史》中的“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和文学”这章最后特列“‘80后’作家韩寒和郭敬明”一节。孟繁华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下编中设了一节“网络文学与80后、90后文学”,在韩寒、郭敬明之外,提到的作家还有春树、李傻傻、张悦然等。尽管篇幅简短且仅止于现象描述,但以上专家显然已经开始意识到进而尝试处理“80后”的“文学史化”。
蔡 东:即使生活经历相似或年龄接近,写作依然是很个体的事情。这个概念最好只是基于指代的方便,而不是因为作品有太多共性。
宝 树:对“80后文学”没什么研究,但我个人感觉,大体而言85年前后有一个断裂。一般如果说80后文学应该是80-85年生人,其实往往也包括70年代末的人。这一代人,塑造其世界观人生观的青春期大概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时候社会已经全面开始市场经济转型,意识形态退潮,对外开放程度也比之前提高很多,但是电脑网络和手机等还没有普及,社会的阶层分化也不显著。所以这一代人是有某些不同于此前此后的共性的。但是也可以说是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点上,而且这种共性也正在迅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分化瓦解,最后或许只剩下一些怀旧的残留。文学是社会的折射,所以也许根本问题在于这一代人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或者说,能不能创造出一个普遍认同的东西来,这是一个尚未决定的事件,但随着80后普遍跨入中年,留给我们的时间是不多了。
戴潍娜:70后,80后,90后这样的概念,总让我不禁联想到iphone5,iphone5s,iphone6,其本身是一种非常工具化的流水线式的划分。而众多粗暴的标签当中,以年龄作为区分则是最为含混的一种。何况,诗人没有年龄。“80后文学”这个概念最初被运用在一批年轻的文学偶像身上,可以说,这个狡猾的概念本身,就是反智的时代映射。
罗皓菱:代际也是我们认识文学的一种方式,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偷懒的方式,通常在我们对一种复杂的事物缺乏认识能力的时候,时间则是一种最为方便的坐标,仿佛只要装进这些时间的抽屉里,混乱的世界马上就变得拥有秩序了。对于时间的这种敏感,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中,以至于我们要以十年,甚至五年或更短时间去标识一代人的写作,在欧洲或者美国的文学界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概念的,六十年代可能是一个标识。但是在我看来,80后现在仅仅是具有一种时间上的意义,而它最初出现的那些文化意义已经消失殆尽了。
2
杨庆祥:如果从起源上看,所谓的“80后文学”从一开始其实带有加冕的性质,也就是认为这一代写作者可以开创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文学时代”。今天看来,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了?
黄 平:目标尚未实现,“80后”的大作家与大作品还没有出现。一开始是市场写作对于文学的戕害,郭敬明最为典型。现在是职业写作的拖累,这方面杀伤面更大,学美国这个作家日本那个作家,是一条文学的死胡同。写作不是木匠活,从来没有普遍规律这回事。一个市场化,一个职业化,把文学应该有的历史能量消耗殆尽。坦率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作家不是越写越好,是越写越差。当一本中国小说读起来像翻译小说,这本小说就失败了。
林 森:没实现。“加冕”说不上,但起先的时候,“80后作家”这一称呼如果临幸在哪个写作者身上,代表着他被市场认可了,回报是很可观的。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都是最早有资格拥有这个名号的人。在那时,“80后作家”不是谁想自称就可以的,等到这个说法变成了只是用来提醒写作者年龄的时候,它就已经“贬值”了。现在我们失望的是,这些出生在1980年代的写作者,不但没有开创某种新时代,比文学前辈都要晚熟得多,莫言、韩少功、余华、马原、铁凝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重要的作品都出来了,可当前这批人呢,哪部作品可以说是一旦不出现就让人觉得天空缺了一角的?
李 峥:举个例子,跑过接力赛的人都知道,接过接力棒后你只需要在既定轨道之上奋力奔跑。我从没见过接手接力棒后开始跳啦啦操的选手。倘使有这样的选手出现,我一定不会认为他/她是开创一种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接力赛时代”。
“80后文学”从一开始“接棒”之日,就被万千吃瓜群众瞩目,似乎要开始挥动“接力棒”肆意狂欢跳舞,开始不必接受既定赛道的限制。故而,有今日群魔乱舞的“盛况”。文学与文化,有其自身的命运,不需要被热闹加冕。相反,这个喧哗的时代里,文学的加冕或许该是寂静的。
金 理:“加冕”在我的理解中,应当是在有了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再给予认可。但是从“80后”这个概念的初起来看,更多是为了吸引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的注意,当时的“80后”作家还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作品,与其说加冕,还不如说是“无中生有”的召唤。如果以传统与变新的辩证关系来看,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写作代际群体可以称得上“开创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文学时代’”。从目前来看,“80后”这一代迄今依然没有在清晰而有效的美学经验上,落实其文学贡献。这就需要同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从创作与阐释这两方面来共同努力。不过这也不用心急,前几年有次和编辑朋友聊天,她问我“‘80后’作家是否给出了属于他们的文学书写?”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作总结或画蓝图,怎么回答都不太明智。尤其“80后”写作目前还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中。说得再极端一些,在后世的文学史上留名的“80后”作家,或许现在还处于隐秘修炼中不为人知,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形,也一点不用奇怪。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双雪涛就横空出世了。所以大家心态放平,不用着急,文学事业更像是一场马拉松。
蔡 东:风格和关注点各有不同,但暂时还看不到太多的新质和异质。也许,不是一代人能开创的,不知道多少代人才能出一个石破天惊,出一个意外,或许是单个的写作者,未必以集群形式出现。
宝 树:在纯文学领域里,应该说没有实现。现在这个时代,更年长的作家仍然非常活跃,80后并不是创作的主体。但在类型文学,比如科幻奇幻里有部分的实现。当然也有很多年纪较长成就卓著的科幻奇幻作家,佼佼者如刘慈欣、王晋康、燕垒生等,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五〇后、六〇后传统,也没有形成足以主宰相关领域的普遍范式,现在主要的写作者是70末到80后的一代人,而主要写作的方式也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形成的。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有一个类型化、商业化的新方向,科幻、奇幻、悬疑、青春文学等都大体发轫于那个时代,这里有国外和港台的影响,也有网络的传播效应,反而传统文学的影响是比较弱的。这些东西抓住了当时还是少年人的70末到80后一代,也让他们开始创作的尝试,很快推出第一批作家。这些领域没有父亲一代的权威,可以让80后作家尽情地发挥。
戴潍娜: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80后文学”的主体到底是谁,谁又能真的代表80后?早先常提的“80后文学”明星像韩寒、郭敬明,其实他们都是60后50后塑造出来的,80后始终缺乏自己选举出来的文学代言和精神领袖。80后的知识青年属于80后的群体,80后的打工者是另一个群体,80后的海归青年又有所不同。眼下这个复杂的群体,跟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小说描述的青年男女的状态有些接近。要真正开创一个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文学时代”,恐怕还要更多的依赖于大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革。
罗皓菱: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成名于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所确立的标准至今仍未打破,曾经我们希望80后这批作家能够成为新的“立法者”,但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完成。
3
杨庆祥:80后写作长期处理的主题是自我的成长,最近这些年,随着一些作品的出现,80后写作又开始处理历史社会等相对宏观的主题。这种转变当然在意料之中,我的问题是,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80后文学”真正变得成熟了?或者说,80后真正长大成人了?我自己的观点是,这种转变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同时有外在化的倾向,在精神的质地上,依然比较纤弱。
黄 平:我也觉得这种转变值得肯定,但从“自我”进入“历史”,需要极其艰苦的准备。比如“文革史”,不去读红卫兵小报,不从那些好像是革命套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别一种青春的焦虑,而是以我们熟悉的青春去覆盖当代中国一处处惊心动魄的断裂,那这种进入似乎也太容易了。而且在以往历史写作的形式都变得可疑的当下,如何重新发明历史叙述的形式,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代人恐怕暂时还无法应对。
林 森:这种所谓的“成熟”,其实并不来自自身,而来自外在的“期待”,来自评论界失望后的某种迎合。也就是说,有些人在处理所谓的历史、社会题材的时候,并非他觉得自己对此不得不说,而是规划好了,一旦他这么写,就会得到某种来自“专业”领域内的掌声。当这些人不再仅仅依靠技巧、题材来讨巧,而是真正把自己的生命全盘托出时,才是他们真正成熟之时。
李 峥:80后写作开始“走出闺房”固然重要。但是“走出闺房”,并不是成熟的指标。其实,只处理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只书写爱恨情仇与饮食男女,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而与之相反,一味地外在化关心宏观命题而不唤起更多人的共鸣、不给人以切肤之感、不直抵人心地叩问命运与灵魂,这样的作品也无非是隔靴搔痒的文字抚慰,寡淡无味。
金 理:我很怀疑主题的转变能成为文学成熟的判断标准。卡夫卡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大多数作家都卷入了社会事件之中,卷入了外部世界的活动。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为见证,……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这种东西”(克里玛:《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写作的成熟、作品的优秀,和题材选择没有关系。你看周嘉宁和张悦然近期的长篇《密林中》和《茧》,从题材而言恰好是两个方向,私密经验和历史记忆,但这并不成为评价何者优秀的标准。将创作视野转向历史纵深或宏观主题,未必就会自动给作品加分。以张悦然的《茧》为例,如果以历史认识论来说,这部长篇并没有提供对“文革”独到的认知,张悦然的长处不在这里。但是因为倚靠“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空间,作家对人性的洞察能够抵达更加饱满而幽微的地方。从先前的“生冷怪酷”(邵燕君教授语),走到今天对人性幽微的皱褶有更温厚的体贴、对生活中的款曲委婉有更复杂的理解,我更愿意将此视作一种“成熟”。
蔡 东:我没有经历青春写作的阶段,没有过什么浪漫和激情,甚至连爱情小说都没写过。从一开始写,就只对生老病死感兴趣,挺沉重的,挺痛苦压抑的。从精神质地上说,我觉得自己的确不够强韧,或者从心理学意义上说,不是成熟强健的主体,恐惧让我逃避又懦弱,但我从来没有放弃改变,总归是个有生活热情的人,有时候这热情还非常汹涌,只要还能心血来潮,还能读书写作,就有希望吧。随着年龄增长,我倒比以前多了些少年意气和涉险的意愿,生长性对作家来说挺重要的。关于写作的主题,处理成长的经验,或处理历史社会等宏大题材,并非前者就一定是稚嫩轻浅的,后者如果刻意为之,也可能写得生硬又孱弱,缺乏力量和根本的支撑。
戴潍娜:作家的成长,一定是会渐渐走出狭窄的自我,去知觉他者和世界。80后有意识地处理历史社会等相对宏观的主题,当然值得肯定,但我担心的是,这种“意识”是否刻意,是否出于对各种评奖委员会的揣度,或者更直接地说,这些“宏大关怀”究竟有几分真诚?文学里最可怕的就是鹦鹉学舌的反抗和虚情假意的关怀。80后早就不再新鲜了,他们开始普遍分享一种令人担忧的早熟,毕竟没人愿意看到一群面孔年轻的老年人。这也不仅是中国文学独有的问题,事实上全球都在历经这种“无谓的早熟”和“艰难的成熟”。随着医学水平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人口平均年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青年一代更多地暴露在了相对稳妥的老年生活的威慑之下。因而,这一代年轻人肯定跟上一个世纪的年轻人有着深层的生理和心理结构上的不同。缩小到亚洲范围来说,整个亚洲的青年一代都有内卷化的趋势,日本近几年有很多“宅男文化”的研究,青年一代被称之为消失的一代。诚如主持人所言,“80后文学”的精神质地依然比较纤弱。这一代的贫困,不在于买不起房,而在于我们和历史、传统、现实政治之间淡漠的关系。
罗皓菱:在我看来,很多80后作家因为受到批评家的批评所以转而去写一些他们不那么擅长的更为宏大的主题。每个作家还是要去写自己最有感受力的生活,那一定是从个人出发的,而不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我想你说的真正的成熟,大概是指一个作家对于时代和历史的精神有了真正的感受力,当他从个人出发,同时恰恰也和时代情绪合拍,这样大概就能诞生比较好的作品了。作为一个作家,不要去图解社会问题,而是让自己内部成为一个“丰饶的共和国”,当这个小的共和国和大的共和国之间能产生某种共振,离你说的“成熟”可能就不远了。
4
杨庆祥:长期以来,对于“80后文学”的关注集中于叙事文学,而对于80后的诗歌写作似乎谈论得不多,这当然与当代诗歌越来越圈子化有关系。我想了解各位对80后诗歌的观感。也可以延伸一个问题,不同文体之间的互动是否能提供更多写作的路径?
林 森:我自己写诗歌,也编诗歌,我自己对诗人的态度是:敬,而远之。讨论80后的诗歌很困难,除了你提到的圈子化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没法把握、没法谈。诗歌内部的千差万别已经是现实,要说到点子上,哪有那么容易?在我有限的80后诗歌阅读观感中,我觉得,这代人的诗歌平均水平远比前几代人要高,但诗歌却最不讲平均值,只讲“孤峰”,谁上去了,就上去了,可以孤零零地俯视。我们很遗憾没有看到80后诗人里的“孤峰”。不同文体间的互动,当然会带来很多新的思考。比如说,我选择当一个小说家而不是诗人,其实是来自某种自知,自己没有那种成为“孤峰”的天才。但我一直保持着诗歌写作,以此锤炼对万物的敏感和语言的洁净,这让我在小说写作时获益良多。说老实话,很多80后小说家的语言太泛滥、太糟糕了,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诗歌锤炼而造成的恶果。
李 峥:不同文体之间的互动会更能成就一个作家。由于我自2015年开始发起“听筝读诗”文化沙龙,持续关注当下诗歌圈的动态,所以对诗人与当下诗歌相对熟悉。诗人,往往是一个人生命元素当中的一部分,不能成为其写作的全部。很多杰出的诗人,除却诗歌之外的文体也是写得很好的。在这点上,相信主持人杨庆祥也很有发言权。
蔡 东:对80后诗歌了解有限,50后和60后的诗人有不少喜欢的。我不太敢写诗,我心里,对能称得上是“诗”的东西要求很高,有些文字,我觉得,还是不名之为诗的好。而废名和沈从文的一些小说,读起来分明就是好诗,从美学标准上说,亦是好诗,寥廓,又晶莹;读完了,说不出话来,只能默然,唯有默然。鲁迅的《故事新编》,我也是当诗去读的,冷峭的诗,气息非常复杂,有的地方透出世故,透出鲁迅特有的酷烈,有的地方,透出的是孩子气。在几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刻意追求的是诗的味道,语言上,造境上,余韵上。那几篇小说是我珍爱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一种无限接近平静的喜悦。
戴潍娜:过去二十年中国诗歌的“边缘化”和小圈子的“亚狂欢”,某种意义上恰恰让诗歌成为了最纯粹的艺术存在,很多年来,诗歌换不来一分钱。这种糟糕的生存处境,反倒令诗人有了暗自磨砺的潜伏时间,诗歌技艺不断精进,引领了白话文的成长。如今一个二流诗人都可以写出当年朦胧诗大师的水准。诗歌圈普遍认为,当下中国诗歌的水准,放到国际诗坛毫不逊色。问题出在,中国诗歌教育的缺乏,使得大众审美跟语言的进化严重脱节,口味仍停留在朦胧诗阶段。80后诗歌有好的技艺传承,但无法概论,诗人永远都是个体的存在。一位前辈曾对我说,跟诗歌圈还是保持些距离,你会感到很失望的,因为诗与任何群体无关,它是个人的和人类的。未来的文学,也许不再有严厉的文体区分,会有一种打破一切界线的令人兴奋的文化气质。
罗皓菱:相对于80后叙事文学,80后诗歌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群体,在公众话语领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声音,倒是70后的一批诗人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在新媒体时代,大家对于诗歌本身的关注常常多于诗人,我们经常读到一个漂亮的句子,但是并不知道作者是谁,这种碎片化的方式很难让人对某个群体的诗人形成某种关注吧,除非他们以某种独特的美学趣味形成某种运动,但是在80后的一群诗人中几乎没有这样的自觉。
5
杨庆祥:80后的写作其实有多种的路径。比如科幻写作,有一批优秀的作家正在从事相关的书写。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不知道各位有何想法?
林 森:拓展新的领域是必然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看科幻片,如果里面是说英文的西方人,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如果变成讲中文的中国人,就很怪异。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识里还没达到很自然地接受这么一种东西的程度。近些年来,网络技术让全世界拉平了,我们可以最快的速度,享受最先进的数码产品和移动互联网,大家的意识提升上去了,中国人在科幻里出现,变得可以接受了。我自己其实很关注数码和科技新闻,知道这些技术的发展,最后一定会对社会伦理造成冲击,而提前把这些可能会造成的冲击写下来,不就是科幻吗?前些时候发现引力波的新闻出来后,我一看引力波的图片,吓一跳,那不就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太极图吗?最古老的东西里面,藏着最前沿的科技,这要是以丹布朗的方式,写一本类似《太极密码》之类的科幻小说,会不会很有意思?
李 峥:当然重要。科幻能让人插上想象力的翅膀,文学使想象力的羽翼更加丰满。《三体》一出,让多少科技少男少女拥抱了文学呀!科技与文学所抵达的远方,在我看来,是一致的。二者都是超离现实的一种力量。
金 理:很认同这个看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方向”。近年来我也补课读一些青年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经常会有震撼,比如在其中看到目前一般主流文学刊物中已经很少看到的对于人类社会“远景”的想象。我们经常喜欢把文学分类,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学……其实重要的是,这些板块的缝隙间,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而科幻文学其实就处于这种交界处。尤其当那些写作科幻的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一块回旋的余地的时候,能否感知到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另外,我读一些关于科幻文学的评论,也受到启发,不过感觉这样的评论长期以来有自己的规范和传统,并不和主流文坛以及“80后写作”有积极的交融,如何产生整合而又不削弱其自身独特性的视野,也值得思考。
蔡 东:说到科幻文学,在我看来,刘慈欣是和奥斯汀、布尔加科夫、阿西莫夫一样伟大和经典的作家,突破了类型的局限。阅读他的作品时,就像在过节,过很盛大的节日,整个人都沉浸在他虚构的世界中,那种阅读体验太震撼了。对于想象性的作家来说,科幻写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向,或者说,在科技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今天,写科幻,某种意义上也是写现实。除了绚烂激扬的幻想,打动我的科幻作品都是有根底的,有对终极问题的思考,比如说《黑镜》第一季,有一层不太华丽的科幻的壳子,内核是极其人文的、老派的、知识分子的。
宝 树:有一定道理,这个时代有很多随着新发明、新技术涌现的问题,传统的文学可能处理起来不好把握。比如传统上写一个围棋棋手的生活和技艺可以驾轻就熟,甚至描绘出玄妙深奥的意境,但现在出现了阿尔法狗这样的全新事物,深刻影响了围棋本身。对这种现象,首先不是支持或者反对,而是常常令人感到眩晕,不知如何把握。所以传统文学的写法,也许难以找到其中的意义。但是,科幻小说也许就可以用更幻想性的方式把这里的问题表达出来。这并不是说科幻如何高明,恰恰是因为科幻比较幼稚,它好奇的只是这个问题本身而不是人性的很多细微微妙之处,才有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去写。
戴潍娜:我在留学期间也曾半途而废,偷尝过科幻长篇。那会儿有机会和各个学科最尖端的实验室同学打交道,听他们侃侃而谈谈生物科技、天体物理、化学材料等的前沿进展,就忍不住手痒积累了些科幻素材,参照牛津大学的历史背景编织了一些故事情节。可惜没完成,存了十来万字的废稿。
罗皓菱:未来文学的可能性的空间肯定是在所谓的纯文学之外打开的,科幻写作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可能还有别的分支。我最近在看一个德国的短篇小说家的集子《背对世界》,这个小说家以前也是记者,她写的那些很多生活都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比如一个广播电台的庆典,那些人物改头换面几乎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我就在想这也是小说呀,写出来还这么好看。当各个行业的人有了某种写作的自觉,我觉得会为我们的文学写作提供很多有意思的经验。
6
杨庆祥:各位或者是作家,或者是批评家,对于未来的写作有什么规划?在我看来,个人的写作规划以及个人的美学趣味可能才是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东西。现在看来,“80后文学”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概念已经无法为我们的写作加冕了,当然,更不能为我们的写作进行辩护。
黄 平:在2017年我会出版两本小书,目前都处在修改阶段:一本是文学史,《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回到改革时代的源头理解我们这一代情感结构的由来;一本是文学批评,《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主要借三位作家作品,讨论两个关键词:价值上的“虚无”和形式上的“反讽”。
林 森:规划有长期的,也有近期的。长期的规划里,有一个大的东西,还需要时间去沉淀;短期的规划里,除了一些中短篇,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长篇正在进行。有生命力的,只能是好作品本身,而不是某种概念下的产物,当然希望看到这一代人里的重要作品早点出现。
李 峥:在展望未来之前,我想先梳理一下自己过去的写作。由于供职于央媒的缘由,很多时候作品是为了完成一些新闻任务。2017年,我会整理出版文稿,也想把打动我内心的一些故事、思考与观察分享给更多的人,可能是通过诗歌、小说、散文……我期待未来我在文字里与更多的人心意相通。只要坦诚地面对写作与内心就好,不论是否“加冕”。
蔡 东:用写作来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做不到”和“完不成”,时代有格律,但写作可以参差多态地瓦解时代的格律,在扭曲板结的价值体系上撕开一道缝隙。短期来说,先把手头的中篇写完,一篇一篇来,尽量从容些。
宝 树:我个人的写作并没有太考虑80后与否的问题。作为科幻作家,写作的题材往往以广袤时空为背景,也需要尽量超越个人的时代背景,去拥抱更广大,更奇异的存在可能。当然作为80后生人,也一定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这也是不可摆脱的宿命。比如我感兴趣的题材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物在遥远时空下的陌生和怪异化。在一篇小说里,我写到日本AV出现在几千年后人类灭绝以后的星际博物馆里,另一篇小说里,写红歌传播到几百光年外的星系里……这也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观照吧。未来的写作规划包括的范围很广,有纯架空的世界,也有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也有和当代生活联系密切的故事……无论如何,每一部作品我希望都能展现一些没有人写过的独特的意境。
戴潍娜:我常常想,这一生可以辜负人,可以辜负事,可以辜负自己,但不能辜负诗歌。未来,诗歌依然会是我随时随地的生活方式和猝不及防的神秘体验。因此我大概会一直写诗,也会写一些思想随笔,另外希望每两年翻译一本值得译介的好书,晚饭后坚持译上一两页,就跟帅哥靓女天天去健身房练会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