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增订版):“美”是人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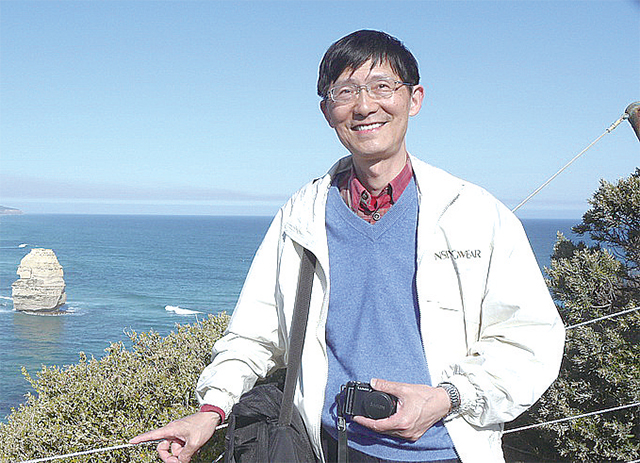
刘绪源

刘绪源的《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增订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是一部从审美视角探究儿童身心与文化发展的童年学著作,也是一部从童年视角探询人的审美发生奥秘的美学著作。
很难说童年学和美学的关切在刘绪源的论说里到底孰轻孰重。有时候,你觉得他之所以谈审美,为的即是提出关于儿童和儿童蒙养的新论见。可你又觉得他谈儿童,谈儿童的成长,无不意在阐明美与我们的存在之间最本质、最深切的关联。这部著作的笔墨格调朴白可亲,但它的思想浓度又是如此之重,密布文本的那些富于创造力、洞见力的思考、探求、发现和阐说,令人深感学术的研究若有真义,非此而何在?
儿童审美发生学:一个学科的可能
《美与幼童》谈儿童审美的发生,却是从儿童发生认识论的鼻祖皮亚杰说起。我以为,这其中除了理论和方法的扎实借鉴,亦包含了一种探索与研究的远大宏图。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相隔近半个世纪出版的《美与幼童》,实在是一部与“发生认识论”遥相呼应的“审美发生论”。它所着意探讨的,是与“认识”相对应的人的另一种根本能力的源起,更进一步说,是传统哲学范畴里与“理性”相对应的人的另一半存在本质的内容。以这一审美能力和审美本质为对象的审美发生学研究,在美学研究的传统中向来占有一席之地,但《美与幼童》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在于从个体身心的发生学视角,来整体探讨这一审美能力的发展和审美本质的展露。
正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并非探讨作为一个群体的人的认识力究竟从何而来,而是揭示个体层面人的认识力如何具体地发生演进,刘绪源的审美发生论同样并不以人类群体审美经验的发生学考察为主旨,而是重在探究作为一种人性维度的审美力如何在个体身上潜伏、萌芽、生长、显露。这是一种朝向每一个体的存在体验和生活实践直接打开的研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发生期演进而来的个体,这一个“儿童”将有可能揭示与人的成长、实现有关的重要奥秘。所以刘绪源谈皮亚杰,“理路清通”之外,亦且心有戚戚。
《美与幼童》一书,在高度浓缩的思想演绎中,遍布着可供有心者发现、点燃、引爆的理论生发的信子。比如作者谈到婴幼儿时代“对于快乐的追求和记忆”乃是最初的审美情感,以此回观王阳明“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瘘”的教育观,这里的“嬉游”之乐非是劝人暂予忍耐的某种粗陋欲望,实是儿童胸中审美本能的自然抒发,所谓“舒畅之”的“条达”之法,在肯定、顺应这种初级审美之“乐”的前提下,使之朝着更为丰富深厚的审美愉悦成长和升华,以此惠及个体的全部生存。此即儿童美育的一大课题。又如书中大量援引儿童文学作品做幼年审美心理的精微分析,往往显出实证研究常不能及的生动、精准与深透。由这一特殊文类寻索儿童审美活动的特征、规律等,乃是审美发生研究的一大要径,是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可有作为的另一广域。
我甚至认为,未来的儿童研究若能循着《美与幼童》开辟的疆场和路径,从保育学、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儿童艺术等各个学科方向,结合思辨、实证、经验等多种研究方法,将这一特殊的“审美发生论”话题持续推进下去,极有可能促成一个在研究价值、学术影响上均可比肩“发生认识论”的新学科的诞生。
节奏、想象、情感的再认识
《美与幼童》虽由皮亚杰的立点启步,并在论说中援引、运用了“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等发生认识论的重要概念,却是借此在审美的地界里另辟理路,另立新说。在哲学领域,“图式”一词绝非陌生的范畴,然而作者从传统认知图式的旧入口而进,却由婴儿审美图式的新出口而来,竟把我们带入“图式”之说的又一片开朗之地。这个初始阶段的审美图式,也就是个体审美力的起点,刘绪源以再朴素不过的“节奏”一词来概括它的基本内涵。现代儿童研究对这个词无疑太熟悉了。皮亚杰曾谈及幼儿的节奏感,蒙台梭利也详究过儿童期的节奏,但当刘绪源用节奏的“松开”和“分化”——亦即人的审美感受力、理解力的“由简到繁”、“由显入隐”——来解释个体审美成长的秘密,在儿童研究的语境里,这个看似普通的语词骤然获得了一种充满穿透力、诠释力、生长力的思想能量。节奏感的“由简到繁”所指向的个体审美图式的扩充复化,以及其“由显入隐”所指向的个体审美能力的内化创生,在发生学的视野下得到清晰的呈示,我们于此似乎窥见了人的丰繁复杂的审美经验世界以及独特幽深的审美存在感受的根本源头。
事实上,整部《美与幼童》的理论展开,所用多为学界熟悉的儿童发展理论、概念、术语等,却就此发掘出诸多充满新意的阐说。作为这部著作论说核心的“想象”与“情感”范畴,在儿童心理学领域亦非新词。但刘绪源谈“想象”,不独将其作为一种由旧材料创编新形象的心理机制,更是一种促成人的智性的各个方面在自由舒展的运行中达到“默会整合”的特殊精神能力,它有形式、有内容,还有丰沛的主体情感的介入和渗透。伴随着这一“想象”的精神活动而兴起的“情感”,同样不仅是指具有特定内容的情绪感受,更是一种经由想象推动催生、同时又反过来导引想象并与之融会一体的感性体验,是“人”与世界、“我”与他物在“想象”的水流中自在相遇而激起的精神感兴。它是将人的身体由动物性进一步导向人性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熟悉的想象、情感等范畴由实验心理学层面被进一步推至更阔大深远的哲学、美学视野中,而其哲学和美学的蕴涵则在儿童发生学的方法下得到独特的探询和揭示。
童年日常背后的理论深度
《美与幼童》中许多极广而深的剖析解说,皆由常理、常见起笔,毫无玄虚,却又步步生景,曲径通幽,最后把我们带进别开生面的思想洞天。这大概是刘绪源为文一贯的风格,但或许还因为他谈论这些,心中无时不怀着一个孩子的生动形象。这个形象,既是叠合了一切儿童特性的那个最普遍的孩子,也是他膝头从婴孩渐渐长大为幼童的那个最具体的“娃娃”。可以说,《美与幼童》的一切理论演绎与发明,都是从这个孩子的最具象的生命情状和最切实的生活展开出发,并以他(她)的完整的精神发展和生命实现为最终的旨归。为什么要向幼童提起美的话题?婴幼儿时期有真正的审美吗?这种审美活动的表现为何?如何理解它在幼童生命结构及其发育过程中的位置?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论证,首先不是出于任何寻求“新见”的理论探险,而是为了一窥儿童生命的真实奥秘,并由这个奥秘的揭示,来为儿童的发展、成长、教育等提供真有助益的指南和建议。所以,尽管全书博采心理学、哲学、美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学、自然科学等众学科的丰富理论资源来支撑论证,却从不让我们觉得这些理论的探讨越出了儿童生活的日常边界。在述说儿童的问题时,《美与幼童》的“理路”一如作者介绍皮亚杰时所言,始终是“清纯的、清晰的”。我相信,任何留心与孩子相处的成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所相识的那个孩子的亲切身形与面目,亦会感到书中理论的关切、阐说与儿童生活现实的时刻契合。
这种“清纯”和“清晰”反过来烛照理论本身,使之显出当代学术生产机制下久违的那种素朴的智慧与清明的深刻。例如,书中富于创见的“二元阶段”说,探讨特定幼儿时期的秩序感与反秩序冲动的根本源头及彼此关联,其发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幼儿阶段最常见的“遵循秩序”与“破坏规则”的二元行为趋向,尤其是理解幼儿“反秩序”冲动的审美本质与文化价值,并将它恰当落实于儿童教育的实践,具有直接的指点和导引作用。此一“二元阶段”说,表面的通透敞亮背后,其实包含了贯穿人类哲学史、美学史的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那场聚讼公案:如何看待理性和感性在人的完整存在与自我实现中的各自地位;如何从这两者的“各司其职”中,判定它们之间复杂、深入、微妙的相互交缠;以及,如何通过理性与感性之间恰到好处的分工协作,寻求人的充分发展的更高可能。这其中的每一点都足以构成一个体量庞大的美学研究课题。《美与幼童》本身从发生学的独特视角探问着这些人类精神的宏大之问,但从它的论说内容和姿态里却不见丝毫宏大理论的傲气。相反,透过它所关切的那些具体无比的儿童话题,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真正的哲学、美学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深切关联。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背后宏大的理论思想的照耀,作者笔下看似寻常的那些儿童心理和文化范畴才焕然而发出更为迷人的理论光彩;但也正是经由这个小之又小的幼童身影的投射,那看似宏伟高远的理论之母,才充分显出它与普通生命和寻常生活贴肤相关的本真价值与魅力。
从儿童的发展到人的实现
于此,刘绪源把他研究视野里的这一个“幼童”,既描画得极亲切寻常,也洞穿得极深刻精微。“在这个小小的童年奥秘中,其实是隐藏着非常巨大的人生奥秘的。这里隐寓着一些十分积极的规律性的东西:小而方之,孩子正是在这种求新求奇中成长的;大而方之,整个人类正是在这种求新求奇中发展的。”《美与幼童》让我们看到,如何经由童年的审美之钥,为人类个体和群体打开通往更好未来的那扇门扉。书中一再谈到对于个体成长和人类发展至为重要的“创造性思维”“创新型人才”等概念——从审美的视角、原理、方法提出陶育这种思维和这类人才的恰当之径,应是《美与幼童》为儿童发展理论所奉上的一个充满价值的贡献。书中大量有关幼儿审美现象的见解,包括婴儿审美图式的初现、幼儿审美能力的演进、审美想象在幼年阶段的重要性及其原因、审美想象与人的创造力的关联、人的审美力与理性之间的转化互推等,对于当代儿童的家庭蒙养、学校教育乃至与孩子有关的一切文化事业,无不有着基础理论和操作实践上的大用。
但我也以为,刘绪源在《美与幼童》中辩说、揭示的“童年奥秘”,远不只是为了满足人及人类未来发展的某个功利需求。在追寻“成长”和“发展”之前,它的更重大、更基础、也更深远的意义,应在于借助普遍而永恒的童年经验的指引,带我们进入关于人的审美本质的慧性识判和深刻体悟中。从这个审美的幼童身上,我们或许空前透彻地体认到,人是一种审美的存在,这个审美之维不是旁列于人的其他存在维度的一种补充内涵,而是渗透于人之为人的一切方面实践,包括人的认知的建立、理性的发展、身体的塑造、精神的成型,直至日常生活幸福感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刘绪源说审美是“调动完整的人,是对人的整个生命的冲击”。
《美与幼童》绝不是一部泛审美主义的著作,作者在谈论审美的问题时,始终审慎地辨析、厘定着审美与认知、理性等精神范畴之间的边界:“在婴幼儿的审美走向成熟后,认知的成分会渗入其中,审美本身也会成为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但审美与认知的差别将永久存在,永不可能消弭”;“理性思维将走向抽象的结论,将走向清晰,审美则走向模糊……”正因如此,当人的审美性从这样的审慎论证中鲜明地显影而出,当刘绪源说“审美……应是与认知相并列的、相辅相成的、居于同等地位的精神方式,如果不说它是一种更根本、也更重要的方式的话”,他恰恰是为审美之于人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做了最充分的注解。
我想起那个著名的关于美的命题:“美是上帝的名字”。在辨美的语境里,《美与幼童》以其独特的发生学方法与发现,汇入到了关于美的现代诠释的传统中。这个传统致力于揭示和证明,“美”是人的名字,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舒展与完整实现的必要精神基底。它使生命不但是丰富的,而且是生动的;不但是紧要的,而且是美妙的。《美与幼童》指示给我们,如何由孩提时代的审美图式和审美经验启程,踏上那通往更丰厚的生动和更深切的美妙的成“人”之途。
 更多
更多

王朔:真实生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来
“特别残酷的东西,我不愿意看,我自己也不愿意写。我也认为事情不是那样的,或者我宁肯事情不是那样的。”
 更多
更多

重读《鼓书艺人》:生计、尊严与幸福的难题
“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