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1917年,26岁的胡适留美归来,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当他踌躇满志在北大讲台用英文朗诵荷马史诗时,辜鸿铭毫不留情地予以嘲讽,说胡适的英文是英国下等人的口音。他对胡适倡导的新诗和白话文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
胡适于1919年8月3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以笔名“天风”发表一篇《随感录》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当胡适把《每周评论》给辜鸿铭看时,辜鸿铭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装在衣袋里,郑重其事地向胡适说,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1935年8月1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记辜鸿铭》,回忆了辜鸿铭的两件趣事。1922年10月13日夜,胡适在老同学王彦祖的家宴上与辜鸿铭相遇,辜鸿铭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胡一时想不出来,问道:“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辜鸿铭自豪地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接着他又考胡适:“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辜鸿铭说:“是清朝的大帽。”引得哄堂大笑。
辜鸿铭和胡适常常因为思想、学术争得面红耳赤,针锋相对,但是却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胡适曾在《每周评论》发表的《随感录》中说:“我看了这篇妙文,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说老实话,他真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辜鸿铭去世后,胡适多次写文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在《记辜鸿铭》中说:“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更多
更多

苏童:写作服从于隐蔽的“文本暗磁场”
“文本是暗磁场,隐蔽的磁力引导你的叙事方式,故事的走向,甚至决定你每一个句子。其实我的写作从未刻意要关注什么,舍弃什么,只是服从那个磁场而已。”
 更多
更多

李渔:另一面“帮闲”
李渔的“帮闲”却又不是简单的“帮闲”;他有的也不只是文采,还有不同寻常的思想与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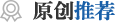 更多
更多

散文 | 夕潮心海
文章回忆初遇海边夕阳的狂喜与七年后的沉静,及如今对黑夜微光的凝望,反思现代生活中心灵与自然的疏离,感悟微光的价值。

散文 | 泥泞里的晴空
《泥泞里的晴空》以雨为引,书写异乡泥泞中的挣扎与成长。从初入社会的窘迫到扎根立足的坚定,在冷雨与暖意交织间,于艰辛泥泞里望见希望晴空,藏着对故乡的眷恋与对未来的笃定。

散文 | 古桑洲记
描绘湘江绿洲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变迁,记录探访株洲古桑洲的见闻,展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态思考。文中“飞鸟如信使丈量传统与现代的距离”等意象,凸显文学性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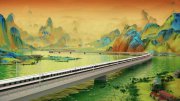
散文 | 整个夏天试图去寻找呼伦贝尔草原的风
风裹挟着草种、尘土、羊群的碎语、马匹的汗息,甚至还有远方朋友零落的名字,浩荡地穿过我,穿过我的眼眸,穿过我的胸膛,穿过我浩大的寻找和相认,又奔涌向天边

诗歌 | 我们讨论了话题(外三首)
刀锋或者囚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