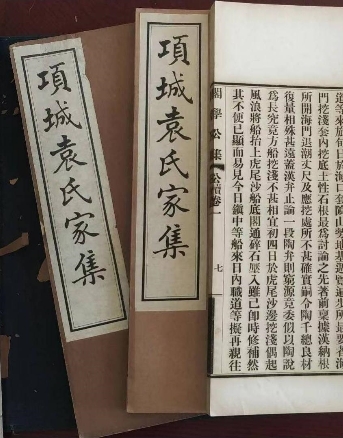人生最美是转弯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陕西人习惯把秦岭以南的地方,叫陕南,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川湘意味。安康,是陕南地区的一颗明珠,“长得最像四川、湖南”,是一座“南腔北调”的城市。
此次,我是经朋友阿敏介绍,从西安来安康采风的,目的地是距离安康市两个小时车程的汉阴县。那里有明清时期的1.2万亩古梯田。
秦岭以北地区,多是旱地,那里的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几乎没有水田。在做采风功课时,我盯着一张张梯田照片,感叹着这“鱼鳞”一样会忽闪忽闪的大面积田地,就像是大地的曲线。
囫囵睡了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向着汉阴出发了。阿敏执意要陪着我们去汉阴。她在安康地区做了20多年的基层民警,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片褶皱,她都如数家珍,热情地说要完成采访,非得她“出马”。
就这样,一行人便向汉阴而去。
凤堰古梯田,并不在汉阴城内,我们沿着省道足足开了两个小时的车,终于到达海拔2000米的凤凰山山顶。
举目远眺,麦野阡陌,水田相连,山岭沟坡,成片成片粼粼波光,把青山、白云和蓝天都倾倒在里面了。
像破碎的镜面,像巨大的霓裳与珠衣。
时值插秧季节。高低错落的梯田里,活跃着农民们的身影。站在山顶远眺,人影星星点点,和绿水青山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你们明年三四月间再来,那时候,梯田的油菜花会开,都是一格一格黄澄澄的,好看得很。”阿敏操着当地方言满怀热情地向我们说着。
其实,来之前,我翻阅过大量梯田的四时照片。
我看到初春时,形状各异的大小梯田还没有苏醒,只盛满清泉,阳光招摇得明光闪闪的,春风拂过,波光粼粼,似乎整座凤凰山都动了起来。
三四月间,油菜花次第开放,荷花、秧苗交相辉映,一块块绿的、黄的“毯子”,铺满了凤凰山,像披着彩衣的仙子。夏末秋初,稻谷成熟,放眼望去,一片金黄。
此时正值六月,山田间的水稻刚刚伸展开了腰肢,一束束排列开来,傲挺挺得像不屈的小将。青绿色的田地和大地本来的土黄色、周围的村庄、远方的青山相映成趣,横竖交错,织成了不知哪位仙子的百褶裙衣。
这里的地理形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些随山就势开垦的梯田,虽然经过百年风云,土地依然肥沃,依然是后世儿孙们最重要的粮食来源。
此时的梯田还未到葱茏时分,但只这水光山色,已足以让我欣喜。梯田的最高处,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那里是梯田的“泉眼”之处,全靠森林雨水给这些梯田蓄水。远处古朴的村庄或散或聚,一团团点缀其间,间或升起的袅袅炊烟让这山间小村更加灵动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下山去,沿着田埂与水田相拥,此时,我也是这画中人了。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绿油油的稻苗奋发向上,舒展身姿,长势喜人,微风拂过,此起彼伏,满目翠绿。随处可见农民们挽起袖子、卷起裤腿,有的在运苗,有的低着头、弓着腰,将嫩绿的秧苗插至田间,为农田“换新衣”,披上新“绿装”。
“草帽子儿楼上楼/ 狂风吹到河里头/ 你要沉来沉下底/你要流来你就流/你莫给奴家丢想头……”
隐隐约约的歌声传来,我听不太懂安康方言,只大概搞明白了这几句,简单的曲调却是朗朗上口,我跟着哼哼起来。下山风冲下来,一个猛子,掀起我的草帽。
“这边这边,全是我们吴家人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垦的。从湖南过来的。”如今的吴家第20代孙,向导吴明老先生也已年近古稀,但到底汉江水养人,我没有在他脸上找到过多的岁月痕迹。老爷子中气十足,走在这缓坡上,脸不红、气不喘。
据考证,凤堰古梯田是清朝中叶由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移居当地后,以吴氏族人为主修建的,距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秦巴山区考古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梯田,是中国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山区农业知识技术体系的集成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据吴老讲,明清年间,除了吴氏,还有鄢、蓝、刘、石、张、李、王、屠、冯等姓氏也先后从外地迁入汉阴境内的汉江两岸,开山垦荒,前后一百余年,把山坡开垦成层层叠叠、旱涝保收的稻田。
“这儿是吴家的,那儿是张家的,这个还是你们西安人在清末过来修的……”吴老指着一片一片的水田,兴致勃勃地讲着。
从讲述中我们得知,凤堰古梯田主要利用凤凰山溪进行自流灌溉,再加上当地人开挖的沟渠与堰塘,接住了从高山森林自上而下的水流与渗出的泉水,丰沛的自然水源使得梯田内部沟渠纵横,灌溉系统完备。人们在建设、改造和利用梯田时,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山顶原始森林涵养水源,塘、窖蓄水沉沙,田间采用自流方式调配水资源。“田、渠、塘、溪”组成的灌溉体系,与“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建设理念完美契合,是因地制宜的低影响开发方式。
我越行走,越觉得梯田隐蔽而科学的灌溉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每一处梯田,都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只要灌溉满了,水自动流到下一层……同时,还有大大小小40余处堰塘,用于储水,以备天旱。
一阵夏风吹过,似是给我们翻开了历史的书页。
人类文明,沿河而生。汉水之南,虽有充沛的阳光雨露,却并非历史一开始就划定的“乐园”。
梯田,让移民而来的老吴家人打了一场漂亮的逆袭仗,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创业史”。梯田边上的吴家花屋,正是移民后的第三代吴敦伍修建的。据说,当年因地处深山僻壤,周围建筑房屋多为茅芦草舍,而吴家的府邸青砖灰瓦、雕梁画栋、楼阁亭榭、青山作屏、花草相映,甚是好看,大家便把它叫做“吴家花屋”,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江东去,不知带走了多少治乱更迭的王朝遗梦,留青山斜照,暧暧人烟。在中国历史上五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中,迁徙汉阴的外地后裔占总人口十之八九。
今天,当我们行走于交通阡陌,似乎仍能闻到先民烧山垦荒的烟味。
“哞——”一阵低沉粗犷的牛叫声,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拉了出来,循声望去,一头油光水滑的老黄牛在一处农舍边吃草,竟还有一头小牛依偎在旁。
走在田埂上,有人闲散地放着黄牛,有人唱起了歌谣,阿敏两岁的儿子虎虎一路小跑追着路边一只柯基犬把我们甩开,又在不远处停留下来等待。
阿敏一路上,都在刷新着自己的惊喜程度。
离开汉阴的时候,阿敏才吐露,自己平时工作忙碌,疏于对孩子陪伴。这半年来,阿敏把注意力转向虎虎,每逢周末就带他去亲近自然,但效果并不明显。
这次到了梯田,追着风,追着狗,追着蝶,追着他喜欢的,虎虎终于开口了,会和大家互动了,更学会了等待。
阿敏的激动,可想而知。
我鼓励她:“你就当虎虎的成长,是因为多转了几道弯,所以迟了一些,人生不就贵在转弯吗?”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行人。即便水穷处,不是还有云起时吗?
汉阴无疑是柔美的,比如那雾里花溪、雨中小筑;但也是坚毅的,树挪死,人挪活!吴老说,梯田之美,在于它修建时是按照凤凰山的等高线,逐级而上。
然我所眼见,觉得正是美在它的“弯”度。
【作者简介:王洁,作家、编剧。西安市文艺两新联合会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