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2024年第4期|林为攀:胡不归(中篇小说 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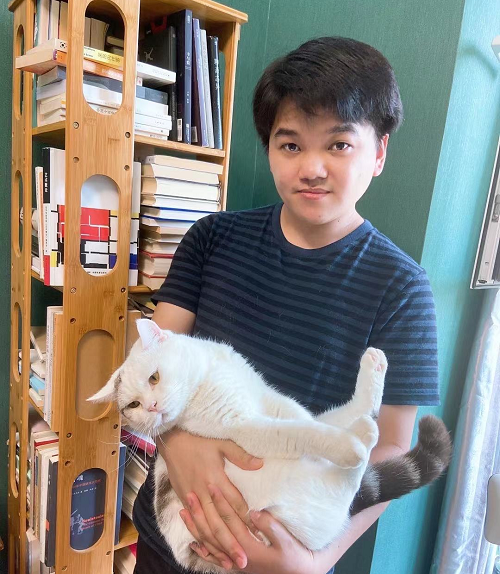
林为攀,90后青年作家,福建上杭人,现居北京。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花城》《中国作家》《福建文学》等刊物;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追随他的记忆》《万物春生》和小说集《驯小说的人》《偶和家庭》等。
一
安邦国和安育民是双胞胎。他们诞生于同一个子宫,长大后分道扬镳,一个生活在华北平原,一个定居在闽西丘陵。每年夏天,安邦国都会提醒安育民注意台风动向,安育民则在电话里回道:“瞎操心,台风吹不到这么远。”
然而今年,一直止步于沿海的台风却吹到了丘陵地带,当安邦国再次打电话提醒安育民时,后者的房屋已被台风洗劫过一遍了。当时安育民正在楼上晒谷子,眼瞅着天边乌云密布,丘陵上的树木大都被吹倒,只剩几棵盘根错节的老树挺了下来,但他却不以为意,只是抓紧收谷子,然后回到客厅静候台风上门。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房子背面的门窗都在晃,遂用扫帚顶住门,用胶带粘住窗,刚想坐下来,便听到门窗被风撕裂,正要回头查看,就被溜进屋里的台风偷袭了。
“好险,如果我不是被挂在了树上,早就没命了。”安育民在电话里说。安邦国担心他的安危,让他抓紧时间转移。“没事,台风走了。”安育民说。让安邦国没想到的是,安育民接他电话的时候还没从树上下来,此刻正卡在树上兴致勃勃地跟他描述台风:“你是不知道,台风冲破门窗把我吹出去后,我刚置办的家具也全被吹走了,就像一张装米的编织袋那样被吹走了。”安邦国让他别管那些家具,保命要紧。安育民说:“那些家具就是我的命,我要赶紧去找回来,否则就被别人顺走了。”话虽如此,但安育民却无法下来。安邦国在电话里听到他哎哟哎哟的声音,还想开口,电话就挂断了,拨回去已显示占线。
安育民发现信号中断后,小心地把手机揣回口袋,继续尝试下树,仍然动弹不得。他见到许多人都探头探头地从屋里出来了,立即开口呼救,但他们都忙于检查房子的毁坏程度,无暇回应安育民的求救。安育民更着急了,不是为自己的现状着急,而是担心那些家具被他们捡走。摆在安育民客厅的沙发、桌椅都被台风搬到了这些人的大门前,假如是别人的家具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前,安育民二话不说就会埋头搬回家,所以他觉得别人也会这么做。现在虽然行动不便,幸好他还能开口说话:“喂,姓陆的,千万别打我沙发的主意,姓李的,看什么看?那不是你家沙发。”他的话吸引了陆李二人的注意,这两家的屋子挨得很近。他们先后从屋里出来,同时看到了门前的沙发和桌椅,都说谁先看到的就归谁。二人相持不下,准备去找人评理,可还没挪动脚步,就听到了安育民的声音。他们下意识地往安家看去,但在安家门前并未看到安育民,以为他在楼顶说话,又不禁仰脖往上看,还是没有。他们都觉得奇怪,难不成安育民那只铁公鸡被台风刮跑了?
他们跑到安家门前,这一看就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安育民整齐干净的房子不复存在,代之以污水横流,地板上还有来自沿海地区的贝类、鱼虾和海藻,墙上挂的日历、年画也全都不见了。他们争相喊起了安育民的名字:“安育民,安育民……”见无人回应,他们相互看了一眼,都在彼此的眼神里看出安育民已不在人世的信号。
他们径直往回走,走了几步,陆旭阳跟李星辉说:“你听。”李星辉什么也没听见,继续往回走,陆旭阳拉住他说:“是安育民的声音。”声音从前方传来,他们却往后看去,照样什么都没看到,不过随着他们离那棵枇杷树越近,安育民的声音便越清晰。他们终于抬头发现安育民被夹在枇杷树上,活像被一只佘氏蟹夹住的新米虾,不禁捧腹大笑,笑够了才想起去救他。
他们够不到树杈,跟安育民的交情又还没到可以为他上树的地步。安育民深知这点,知道此刻不把大哥安邦国搬出来,他就永远没机会下地。“只要你们把我弄下来,将来你们去北京就让我大哥免费当你们导游。”陆旭阳和李星辉思考了一会儿,看看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一趟北京,但想了半天都没找到去北京的理由,便打算撒手不管。安育民在树上看出了他们的犹豫,决定把价码往上涨一点:“到时就让我大哥给你们买机票,你们不用花一分钱。”安育民的话打动了陆旭阳,但李星辉还在纠结。陆旭阳便坐地起价:“听说北京吃住都很贵?”羊毛没出在安育民身上,所以他乐于大方:“我保证让他到时负责二位的一切衣食住行。”李星辉也被说动了,第一个爬上树准备把安育民拽下来。
“痛,痛,别硬拽。”安育民又像回到了娘胎里,当时因为跟安邦国共住一个子宫,所以那十个月里都快被挤死了,当然他无从知晓这点,还是长大后见自己的后脑勺比安邦国的扁,从而得出的这个结论。原以为安邦国离家后,他能住得宽敞一点,没想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台风让他又“挪不了身”。安育民让他们去架梯子,拿锯子,锯掉树杈救他下来。陆旭阳表示锯树可以,但要先签字。安育民还没明白过来签什么字,李星辉已经扬手把写好的保证书递到他跟前了。
安育民在树上签完字后,陆旭阳跟李星辉两人又出现了问题,他们对谁上去锯树,谁在下面扶梯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在他们看来,上去锯树的总归比下面扶梯的出力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两人以后去北京还享受同等待遇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陆旭阳最后让出将来北京行的领导一职,才让李星辉乖乖爬梯锯树。
这棵枇杷树比安家兄弟年长,安育民喜欢端着饭碗蹲门口吃饭,一年四季,只有夏天的枇杷树能让安育民高兴,因为这个季节枇杷正当季,安育民吃完饭总会摘几棵枇杷放碗里,当成饭后水果。但自从李星辉锯掉树杈后,安育民再也没蹲门口吃过饭,一看到这棵树,就会想起这生中最丢脸的事,更让他生气的是,李星辉当时锯树的时候,树下还围满了穿着开裆裤,流着哈喇子的小孩,李星辉锯一下,树上就落几颗枇杷,任凭安育民在树上怎么喊,这些小孩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把地上的枇杷捡得干干净净。当整个树杈掉下来后,其中一个小孩甚至抬起树杈就跑,安育民眼睁睁看着一树枇杷离他而去。跟树杈同时落在地上的还有安育民本人,他一落下来甚至没检查自己受伤与否,拔腿就跑到陆李两家门前,当着一头雾水的陆旭阳和李星辉宣示这些家具主权。
陆李二人因为占到了天大的便宜,不好再得寸进尺,而且为了夯实安育民的承诺,还主动帮他把沙发桌椅搬回去。安育民回到家里,才发现屋子遭受的惨状,由于值钱的物件一个不少,他并未怨天尤人,让陆李二人把沙发桌椅搬到门口后,便卷起裤腿打扫屋子,见二人还没走,气道:“怎么?还想留下来吃饭不成?”陆旭阳说:“不需要帮忙吗?”安育民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那点小九九,是不是打量着帮我清洁了屋子,将来去北京就可以定居下来啊,想得美。”
陆离二人讨了个大红脸,讪讪而走。安育民花了大半天时间把屋子收拾到跟原来一样,就连沙发的位置也跟之前分毫不差,就在他以为台风从未过境,一切如昨时,突然在门口看到那棵跟从前不一样的枇杷树。本来压枝的黄枇杷一颗不剩,而且由于少了那个最大的树杈,枇杷树也变得跟一个被磕掉门牙的老太婆差不多。安育民想起那些被小孩捡走的枇杷,心里一疼,扶着墙慢慢坐回沙发上。
从那以后,安育民总觉得屋子被人监视了。他的房子地势比其他楼房高,楼层也比其他楼房多,门前的枇杷树在春夏秋三季都能起到遮挡作用,虽然也会相应阻挡安育民的视线,但他还可以跑到楼顶居高临下。自从枇杷树成了一只像被锯掉触角的蜗牛,安育民动不动就觉得有人在盯他的房子,他也透过这个没有触角的蜗牛壳去看别人的屋子,可却什么也看不到,坐在客厅也不敢再开着门,而是门窗紧闭,并时刻拉着窗帘。而且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旁若无人地在家里给自己打牙祭。他怕自己在厨房一颠勺,就有人闯进来分一杯羹。于是,从未失眠的安育民睡不着了,每天睁着眼睛留意屋外动静,早上醒来黑眼圈比皮蛋还大。他不敢再出门,倒不是怕别人旧事重提,问他为什么会挂到树上,而是觉得自己像光着身子暴露在成百上千双眼睛之下。
但他不出门,自有人上门。上门的是陆李二人,自从夏天救了安育民一命,他们再也没找过他,而是耐心等待炎热的夏季过去,一到天气转凉,秋风乍起,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安家,让安育民兑现他的承诺。为免有失,李星辉甚至还带上了那份协议,他爱协议胜过爱人民币,此刻当着安育民掏出来的时候,还像刚签字那会儿一样簇新。安育民挂在树上的时候,觉得如果有谁可以救他下来,他甚至能够以房相赠,但他现在好端端坐在家里,就觉得这只是邻里之间的举手之劳,假如还要报答,也忒影响睦邻友好关系了。
陆李二人非常了解安育民,估到他会抵赖,否则当初也不会让他签字。他们和远在北京的安邦国是发小,安育民从小就是老赖,明明写错了生字,还敢跟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当老师用《新华字典》当作证据,摆在安育民面前时,他也还有话说:“怎么?字典又出新版了?”长大后,与人打交道也经常念错字,当别人用手机把正确的字抛到他面前时,他照样还有话说:“读书时老师可不是这么教的。”当然,有一说一,这里面的确有安育民老赖心态作祟,但更多的还是文字跟手机一样,更新换代太快,很多以前错误的读法,由于读错的人多了,字典干脆将错就错,把错的当成对的。安育民自从高中毕业后,就没再翻过书,所以跟不上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安育民在麻将桌上也老耍赖,还没打几张,就敢把牌往外一推,说:“和了。”由于他的牌都跟其他牌混在了一起,所以别人只能吃哑巴亏,权且当他和了。但安育民的手气太顺了,几乎把把和,因此有人就多留了个心眼,瞅准他要推牌了,立即把其他牌搂到一边,然后去检查他的牌到底有没有和,这一检查,就发现了猫腻,安育民竟然诈和。不过他仍有话说:“不好意思,看错了,看错了,这局不算,再来。”但没有人愿意再跟他玩,若非看在安邦国的面子上,安育民的手指说不定早被剁秃了。
提起安邦国,也是那种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之人。他从小成绩拔尖,没有片刻懈怠,是在老师眼里“连午休都在思考的三好学生”。安邦国后来能考到北京,几乎无人意外,考不到北京,大家才会意外。他们对安邦国的了解,大都源于对方的学习成绩,可以说,安育民有多无赖,安邦国就有多君子。他们认为这对双胞胎就像电影里的“警与匪”。当然,这里面除了有安邦国本身的实力背书,更多的还是安育民的宣传效应。安育民每到危急关头,都会搬出远在北京的兄长安邦国,从而屡次化险为夷。安育民也乐于别人这么想,这样他不管在家乡做再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背后都会有北京的安邦国给他兜底。因此,他才敢欠家具店几千块眼睛都不眨一下。长此以往,许多被他占了便宜的人就迫切希望安邦国能回来一趟,帮他弟弟擦屁股。
“这回准错不了,我哥今年一定回。”每到年关,安育民都要回答这个问题。眼看到了大年三十,安邦国仍然没有回来,安育民也不急,因为一过年,按照规矩,就不能上门讨债了,所以他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搪塞过去,过了元宵十五再说也不迟。一眨眼就到了元宵节,讨债的禁忌过去了,安育民家的门槛也被踏破了,这回安育民赔个笑脸,请来人喝茶,接着打开手机上的携程,说:“不用你们催,这回我亲自去北京把我哥押回来,弟弟有难,当哥的也不能躲在北京逍遥不是?”本是缓兵之计,没想到却凑效了,来人果真不再上门讨债,但隔几天看到安育民还没走,又问上了:“你到底啥时候动身?”安育民看了看天,说:“不急,天气预报说这几天天气不好,等天好了再去。”就这么一推再推,出行的时间总是确定不下来,刚开始还能怪天气不好,后来就做起了自己身体的文章,不是说最近闹肚子身子不适,就是夜里着凉感冒了。因有安邦国在北京看着,所以他们不敢闹得太过分,有些人因为借钱不多,就自认倒霉,算了,但家具店的老板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经常在电话里威胁他要把沙发桌椅搬走。安育民不急不缓地回道:“行,你来吧,这沙发我也没看出哪好,你搬走了我正好买新的。”
安育民算是看出来了,这些人都是纸老虎,嘴上说得吓人,实际上连他一根毫毛都不敢动,原以为他能靠自己的哥哥混吃混喝一辈子,没想到那一纸协议为自己招来了天大的麻烦。此刻看着陆李二人皮笑肉不笑地盯着自己,安育民在心里啐了一句:“妈的,这两浑蛋真是天字第一号大无赖。”
二
安邦国整个夏天都在担心弟弟的安危,他不知道安育民被台风卷到树上有没有受伤,他离家多年,当台风刮不到家乡时,就会严重低估台风的威力,当台风翻山越岭吹到了家乡,又会严重高估台风的破坏程度。因为弟弟安育民吃了台风的亏,所以他心中就把台风等同于十二级地震,几乎一有时间,就给安育民打电话。
没想到这样一来,又让安育民发现了商机,不惜夸大自己的伤势,多从安邦国身上榨了几万医药费。开始安育民还有些不好意思,虽然他是不折不扣的无赖,但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用上这种手段,心里还是有些道德包袱的,就怕安邦国真的抛下北京的一切,回来检查他的伤势到底如何。后来见安邦国关心他的身体胜过关心自己的钱包,安育民就心安理得了,有时还把感冒发烧的医药单也找他报销。
有了安邦国这个自动提款机,安育民在那个秋天对庄稼也不怎么上心了,当有人去县城粜米时,安育民也看不上那千八百块,听凭粮食在家里发霉。他还会给自己戴高帽,碰到有人询问,就扯谎说自己在县城谋了一份好差事:“现在谁还种田啊,我上个两小时的班就比你们在田里刨一个月土还赚得多。”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欠的钱还一还了?”安育民碰到的刚好是他的债主之一。但他一点都不急,吃准了这个债主胆子小,不能拿他怎么样,连谎都不愿意扯圆就在对方面前扬长而去。碰到大债主,安育民就要多费点心思了:“刚上班没几天,等发了工资和奖金立马给你送来。”等了一个月,安育民还没还钱,这人就买着几分薄礼亲自上门拜访了,经过陆宅,陆旭阳瞥见了这人手上提的礼物,下意识地推了推李星辉的胳膊,说:“难不成安育民真在县里讨到了美差?”
“很有可能,毕竟县里也要买他哥的面子。”李星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陆旭阳当即改变策略,不仅不要安育民兑现承诺,还准备把家里那只老母鸡送给他“养养身子”。为了验证他们的猜想,陆李二人偷偷跟在这人身后,见这人进了安家客厅,彼此迅速分占大门两端,窃听里面能对他们时来运转的对话。
“何老板,你怎么来了?”安育民明显有些紧张。
“你藏得真深啊,我问遍了路人才打听到贵府的位置。”何老板说。
安育民到底失策了,没有好好利用门外那棵枇杷树,否则便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个不速之客,及时找地方藏起来,从而让债主打谷场上撒网,扑一场空。此时他在脑子里过筛子,急于想出招架之法,可因事出紧急,安育民几乎一筹莫展,索性不再说话,准备见招拆招。
何老板扫了客厅一眼,看到大白天里安育民还拉着窗帘,以为他真被台风下了死手,现在还怕见光,怕见风,怕打扰,不禁对自己不请自来有些过意不去,羞于再提欠钱一事。本来这番有问无答的对话完全可以镇住门外两人,但好死不死,安育民竟不打自招,抖搂出了欠何老板沙发和桌椅的钱。何老板见安育民没忘此事,便觉不虚此行,放下礼物准备出门去。慌得门外两人立马找地躲,互相撞了几次脑袋后,两人都捂着额头躲到那棵枇杷树后了。安育民送何老板出门,门外明明没人,还故作姿态嚷道:“领导,你何必这么客气来看我,理应由我去看领导啊。”见何老板摸着装满疑问的脑袋走了,安育民脸色为之一变,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道:“真他妈晦气。”
陆李二人从树后出来,李星辉跑回家揣上那份协议,陆旭阳则回去把刚抓到鸡笼里的母鸡放出来。两人在各自门口相视一笑,昂首阔步杀回安家。安育民正在拆何老板带来的礼物,见陆李二人上门,道:“我的领导真是太客气了,大老远提着礼物来看我。”话是这么说,但安育民却没让他们看清这是什么礼物,因为他知道这个礼物跟他口中的领导匹配不上,便把礼物放抽屉锁了。陆李二人看着他的背影尽量忍住笑意,在安育民锁好礼物转身的霎那,李星辉已把崭新的协议亮在了他面前。
安育民定睛一看,这才明白来者不善。他以前总把自己的话当成放屁,说完转身就忘,现在见自己的话白纸黑字写在了纸上,也就无从抵赖了,尤其上面还有他那个鬼画符的签名。安育民了解陆李二人,就跟他们了解他一样,知道不能再用老法子,一定要推陈出新,方能渡过难关。脑子转了几圈,终于被安育民想到办法:“真不凑巧,我哥刚还打电话回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北京玩,我正准备把你们哥俩也捎去北京呢,这不我儿子允文就打电话让我去厦门,我儿媳这几天快生了,缺人手。”
安允文的媳妇的确快生了,安育民没有胡诌。听到此事,陆旭阳情绪就有些激动了,安育民就等着他这个反应,把二人按到沙发上,继续说:“大家都是当爹的,多理解理解。”陆旭阳由情绪激动变成湿了眼眶,安育民安慰道:“不用着急,八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时再喝你孙子的满月酒也不迟。”
李星辉虽与陆旭阳是邻居,但陆旭阳的儿子被抓走那天却不在家,而是在县里打零工。县里的开发区需要工人,李星辉就带着一帮妇女承揽了这个活,干了整整两个月,干完回到家,关于陆旭阳儿子被抓一事,也被人家像嚼完的甘蔗渣,吐了,所以李星辉从始至终都不知此事,也听别人提过几嘴,但都以为陆旭阳的儿子不是又打人了,就是又被打了。陆家后生从小调皮捣蛋,打人和被打是常有的事,以为对方结了婚就能安分一点,没想到还到处惹是生非。看来流氓是胎带的,任谁都改造不了。
此时冷不丁听安育民说是被抓走了,李星辉这才后知后觉地多问了一句:“凭什么把人抓走啊?”陆旭阳的老脸挂不住,几次想走都被安育民按住了。安育民没想到这哥俩看似亲密无间,没想到却是面和心不和,决定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阵营,故意叹了口气道:“唉,事出突然,我们谁也没想到。”
李星辉迫切想听事情的原委,又不好表现得太过分,招陆旭阳反感,因此明明心里抓耳挠腮,脸上还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陆旭阳知道这事李星辉迟早会知道,与其让他去打听添油加醋的二手消息,倒不如主动把官方消息原封不动告诉他。至此,本是上门找安育民麻烦的陆旭阳却自找麻烦,一五一十透露了儿子被抓一事。
陆旭阳的儿子叫陆天仁,四年级时因跟同桌打架,被同桌用铅笔刀在脸上留下一条后来让他远近驰名的刀疤。仗着见过血,陆天仁一路霸道到了初高中,他的拳头没有多硬,但因脸上有条凶神恶煞的刀疤,所以让他的拳头所向披靡。他那条蜈蚣状刀疤让所有混混望风而逃,还意外得到一个女同学的青睐。高中毕业后,两人都没考上大学,各自瞒着家人在县城同居了。过了几年,陆旭阳才从别人嘴里知道这事,找遍了县城每间出租房,终于在城郊的一间民房堵到了那个逆子,正准备挥拳,瞥见那个女娃肚子凸起来了,扬起的巴掌便顺势软了下来。他将坏事当成了好事,要知道现在每个地方都盛产光棍,儿子虽然烂泥扶不上墙,不像安育民的儿子安允文这么有出息,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倒也没掉链子,不仅空手套到了一个女娃,还提前让他当了爷爷。于是,陆旭阳便张罗着让儿子结婚,由于儿子没有买票便上了车,所以陆旭阳就不想再补票了,彩礼意思意思就行了。
在谈判桌上,亲家母的脸色比那天的天气还阴。由于生米已煮成熟饭,女方家也没什么话说,丢下一句“别后悔”就走了。占尽便宜的陆旭阳还起身补了一句:“亲家母,到时别忘了来喝喜酒啊。”原以为儿子结了婚就能收心不少,没想到蜜月还没度完,又像白娘子喝雄黄酒,露了原形,不是到处去收保护费,就是替人看场子。陆旭阳每天看着在家里以泪洗面的儿媳妇,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变得这么野,连蜜月都拴不住裤腰带,后来才知道,原来儿子早就透支了蜜月,结婚就是多道手续的事。
如儿子没结婚,陆旭阳还可以跟他动拳头,但结了婚就只能用成人的方式解决,而成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但比领导还忙的儿子始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当儿媳妇在医院生产时,还是他这个做公公的陪在她身旁。好在老天开眼,孙子办满月酒的时候,儿子终于回来了,还主动帮忙做饭招待客人。没想到酒席刚开,鞭炮还没放完就迎来了两辆警车。从警车里下来三名警察,问清谁是陆天仁后,用手铐把人给铐走了。上门做客送手铐,这还是头一遭,陆旭阳傻眼了,客人也对桌上的食物丧失了兴趣,一顿交头接耳后便都离了席。儿媳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当时正躺在床上坐月子,两边太阳穴上贴着剪成正方形的狗皮膏药,听到这个消息后,本来充足的奶水突然干涸了,儿子把两个奶头嘬肿了还没吃饱,嘴巴一咧,哇哇哭上了。而儿媳也已昏了过去。
陆旭阳把收到的红包都拆了,用来托门子递条子打探消息。终于被他打听到事情的真相,原来帮人家看场子的陆天仁,出于义气,把前来卧底的两个便衣给打伤了。警察很快顺藤摸瓜找到了陆家,正好把潜逃在家的陆天仁逮个正着。法院的判决书也很快下来了,替人看赌场加上打伤警察,数罪并罚,判决八年有期徒刑,不得假释。
“他妈的,一定是那两个被打伤的便衣夸大伤势。”陆旭阳说到这里,情绪更加激动,“好借机勒索敲诈。”
李星辉问:“那么,你有赔偿给那两个便衣医药费吗?”
陆旭阳回:“怎么没有?但他们死活不收,扬言只有让天仁坐牢才能出这口恶气,还说我儿子这是在挑衅整个警察局。”
安育民说:“这我就得帮天仁说说话了,天仁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当众打警察,这都要怪那两个警察没穿警服。”
自打陆天仁被抓走后,因为亲家母有言在先,儿媳想回娘家而不得,为了照顾那娘俩,陆旭阳快六十的人了,还要去县里找活干。之所以跟李星辉走得最近,即因他能承接到县里大大小小的活,没想到与他称兄道弟这段时间以来,李星辉却再也没接到活,搞得陆旭阳以为他是因为天仁蹲局子成心不带他赚钱。现在看到李星辉确实不知道他儿子的事,终于放下心里对他的成见。
陆旭阳知道儿媳迟早会跑,陆家拴不住她,他现在什么也不盼,就盼着儿媳能晚走几年,起码等孙子大几岁再走,到时他就可以独自带着孙子等待他爸放出来。以前种地还能勉强糊口,现在多出两张嘴,家里的几亩地就不够吃了,但这把年纪又找不到合适的活干,之所以打算去北京,也是没法子了,想看看神通广大的安邦国能否帮他解决这道人生难题。
料到安育民这小子会找各种理由搪塞,上门之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安育民说什么,就一句话:“再不走抄了你的家。”没想到对方竟把待产的儿媳妇搬出来,本来占理的陆旭阳若还来硬的,有理也会变成没理。伤心事陆旭阳不想再提,每提一次,他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一败涂地,无数次在想假如时间可以像每年的台风重来一次,那么他一定不会打小就用拳头教育陆天仁,而是会像安育民教育安允文一样放任自流。可惜世上什么都有卖,唯独没卖后悔药,而且即便他真的改变了教育方式,说不定陆天仁照样会行差踏错。在人生这张赌桌上,抓到什么牌就得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还能反悔,那跟小孩子过家家有什么区别。因此,陆旭阳知道后悔改变不了儿子蹲局子的下场,他所能做的是尽量往前看,而去北京求助安邦国无疑是最优解,也是唯一的办法。
所以,哪怕他发过誓不再提家丑,但为了能打动安育民,不得不再次把儿子被抓的过程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然而,对安育民来说,再刺激的事说多了也没劲,而且此刻他急需让陆李二人恭喜他快当祖父了,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爷爷跟陆旭阳不一样,陆旭阳这个祖父是可耻的,他那个宝贝孙子会让他时刻想起被抓的儿子,而他这个祖父却是光荣的,有了孙子撑腰,以后还能更加无赖一点也说不定。因此,哪怕李星辉还想再听下去,安育民也得强行转移话题:“不过你们大可放心,我孙子的满月酒一定会回来办。”
李星辉是个嘴笨之人,见话题变了,即便心里着急冒火,也只好让安育民大谈不久之后的弄孙含饴之乐。安育民的喜事只对其本人受用,对李星辉却未必,不像坏事,对当事人无疑是个打击,但对他而言却不啻为一桩好事,他这辈子没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真要让他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到北京,估计也不会乐意,之所以跟陆旭阳合起伙来欺负安育民,也是想收拾收拾口碑不好的安育民。现在眼看北京去不成了,起码暂时去不成了,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样就不会因为中途毁约而得罪陆旭阳了。
“不过你要去了厦门,你家老人怎么办?”李星辉问。
要不说李星辉是个有心人,不说则已,说了肯定一针见血。安育民没想到这茬,他眼里从来只有自己,只有在自己遇到事的时候,才会短暂地想起家人。他不说话了,家里的老人绊住了他,不过他并未责怪生养他的老母,而是怪李星辉哪壶不开提哪壶,净裹乱。
…… ……
节选自《滇池》文学杂志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