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读《花城》: “燃烧的肝胆”与精神想象力 ——2018夏季诗歌读记(节选)
海男发表在《花城》第3期的长诗《幻生书》、冰逸发表在《花城》第2期的《废墟的十二种哲学——电影三部曲之长诗剧本》都让我再次想到了“一个诗人为什么要写作长诗”的问题。尤其是冰逸的具有探索性的“电影诗”(按作者的说法是一边拍摄一边产生的诗)已经不是“跨界”这样模糊而看似新鲜的词所能涵括的了,“没有电影拍摄脚本,只有一个故事结构。我们持续不断地拍摄,并通过现场激发而构成最终的长诗。这是我的写作形态;而电影也因此成为文学,成为绘画,和成为诗歌”(《访谈:永在和不复存在》)。何平显然对这个时代的诗人和诗歌充满了焦虑以及对“遍地都是诗人”狂欢化写作充满不满。这显现了一个批评家对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诗歌的期待。姑且不论冰逸的这首诗水准如何,何平的一段话是值得诗人和评论家们关注和自省的:“这是冰逸写作她的《废墟》的时代,这么多人顶着诗人的帽子,却没有人肯给她一顶,她也从没有自诩为诗人,她只是想写,于是写了很长的一首《废墟》。这是她自己的‘长恨歌’——是自己的‘长恨歌’,不是白居易的。或许,在一个遍地都是诗人的时代,必须重新选择做一个诗人,然后回到诗人的起点。”(《“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
海男在《幻生书》中给出了答案——“只有写下一首诗才能安魂”,“只有写下一首诗,她才可能编织好明天出门前戴的草帽”,“只有写下一首诗,才能安魂于黑暗”。
一首诗,仿佛在夜色中迎来了另一只蝉
你见过树林中翅膀透明的蝉吗?那时际,她随处漫游
只要搭上一辆车,倾听到来自小镇人的声音
就自认为已经搭上了去乌有之乡的车轮
乌有,是不存在的,是虚拟的,是人们在梦想中
涂鸦的地壤。她有一种追求乌有之乡的勇气
与“一个人为什么写诗”相对应的则是“一个人为什么读诗”。我更喜欢下面这句话“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沈苇访谈》,《诗歌月刊》2018年第5期)。作为一个阅读者和评论家,洪子诚仿照辛波斯卡更有名的那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 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说出“偏爱读诗的荒谬,胜过不读诗的荒谬”。沈苇通过具体的诗作回答了读诗和写诗的精神命题——“五点醒来,万物寂静 / 这无边无际的静 / 是世界已死的迹象 / 还是我死后能够享用的安详? // 醒来,踩到一双旧鞋 / 床榻如焐热的浮冰 / 漂向风暴的旷野: / 随破晓到来的各种蛮力 / 将再度上场博弈 / 更猛烈地撕扯你的心 // 但是,没什么 / 堂·吉诃德的瘦马 / 依然跋涉在冬日雪原 / 至少,我有一匹 / 要比Rocinante强壮些。”(《寂静》,《诗歌月刊》2018年第5期)
几年前,阅读海男的诗集《忧伤的黑麋鹿》的时候,我几乎被词语所构筑的黑暗和幻梦所笼罩,即使是偶尔透露过来的一点光线也未能缓解这无处不在的压抑与犹疑。而今,海男的长诗《幻生书》摆放在了我的面前,此刻窗外的天气越来越炎热。如今她递送过来的仍然是一个诗人的黑夜意识——她诗中的黑色场景和意象纷至沓来且密集紧促,让人难以喘息,她的性别话语、身体感知、独立姿态、梦幻气质(罂粟般的)、先锋色彩、文体实验、语言奇观以及精神内里(因果轮回、白日梦)一直在强化而不是消解。一只黑麋鹿在黑夜里。那么,你如何去发现她的不同?与此同时,从语言和诗歌本体的角度来看,海男的“元诗”写作倾向也很突出。元诗,也就是从诗到诗、以诗论诗的诗。这是一个成熟的自觉写作者的标志——“一首诗,仿佛在夜色中迎来了另一只蝉”。由诗到诗,由词到词,最终解决的是词语的挖掘和日常挖掘之间的交互过程。这同样是典型意义上的词语劳作(创造性和个人前提意义上)和精神激荡。海男是一个写作方向感极强的诗人,尤其是她的长诗和主题性的组诗不断叠加和强化着她独特的文本风貌和精神肖像。每个诗人和写作者都会在现实、命运以及文字累积中逐渐形成“精神肖像”,甚至有时候这一过程不乏戏剧性和悲剧性。比如,海男四岁时目击弟弟的死亡,五岁在金沙江畔看到一个白花花的年轻女人的尸体,青年时代父亲离世,这都对她的时间体验、生死观以及死亡想象有着重要影响。由此,我想到当年苏珊·桑塔格描述的本雅明在不同时期的肖像。这揭示出一个人不断加深的忧郁,那也是对精神生活一直捍卫的结果:“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般的那种凝视——似乎瞟向了照片的左下角”(《在土星的标志下》)。就作家而言,身份和角色感是不可能不存在的,甚至因为种种原因还会自觉或被动地强化这种身份和形象。在精神内里上我想到了盖伊·特立斯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显然,海男是一个仰望者,也是一个拒绝被遗忘的强力型的抒写者。空无与真实,现实和梦境,成为海男诗歌的两个同心圆。
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都在黑暗深处,这是一个黑暗中的独居者和漫游者以及自言自语症者,语言和梦是她的乌托邦。从这个方面来看,海男带给我们的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漫游者(今生今世、前世来生、此时此刻、远方、彼岸)的“夜歌”和“安魂曲”。这是一个女性未竟的白日梦和精神成长史,是一个奇绝的黑暗传,是亦真亦幻的碎片化的寓言——海男的长诗从来都不缺少戏剧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包括《幻生书》在内,海男的长诗都可以看作是精神意义上的女性成长小说(自我启蒙、自我获启),寻找、定位、自我厘定。她一直都在成长,但一直都没有长大。就如同长诗中反复出现的“云南”和城堡那样——她一直有着精神原乡的冲动,那个跋涉者、犹疑者和出离者却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到其间的安栖之所,多少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K。这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循环。这一循环过程仿佛诗人扔过来一个铁环,这个铁环又套着另一个铁环,冰冷铮铮,而你难以觅见黑暗中隐匿的手和脸庞。这是一个成长过程中极其情绪化的女性,焦躁,不安,分裂,敏感,迷茫。这是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未定不宁的时刻。成长过程中精神与肉体、虚幻与现实的砥砺、磨砺、抵牾、龃龉,都在海男的这首长诗《幻生诗》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这是带有“最后性质”的“回光返照”式的挽歌,因为其所叙述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维新”的时代难寻踪迹。这是纸上建筑,似乎可以战胜一切,又似乎片刻可成时代的齑粉。更像是一个人在和另一个时代以及过去的自我握手告别。无须多说了。在精神档案和现实履历中一个诗人在黑夜中完成的是一部黑暗传和“时间之书”。它已经在你的耳畔响起,似有似无,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倾听和作证。
 更多
更多

林白:在离开与抵达之间循环
对于两次收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创作奖的作家林白来说,她的“女性三部曲”——《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北去来辞》,正是用文字对女性生命体验所做的深刻探索。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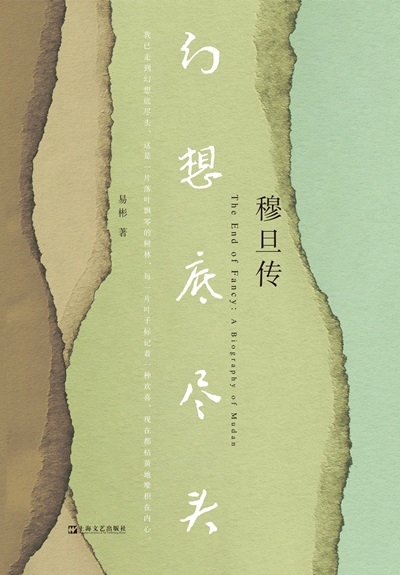
重读《赞美》:在命运和历史的慨叹中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