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品质与一种综合性
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背后都有潜在的揭示历史本质,把握时代精神的诉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以艺术的方式确立一个开端,重新讲述一个其来有自的故事,是一个建立文化自觉的问题。
史诗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和时代的需求,还是一个时代作家的智力需求,文学创作有时候也是一个对抗性竞争的过程,有一条漫长的作品系列,走进这个序列就应该打上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印记。
如果严格按照荷马、维吉尔、黑格尔、卢卡奇的史诗标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可称作“史诗”的体裁,但依然可以在某些叙事类文学作品中体味到史诗的感觉、史诗的品质,它已经从一个名词转变成一个形容词和定语,所以在日常行文中经常看到“当代工人的史诗”、“一个女人的史诗”此类表述。
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背后都有潜在的揭示历史本质,把握时代精神的诉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以艺术的方式确立一个开端,重新讲述一个其来有自的故事,是一个建立文化自觉的问题。黑格尔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者“圣经”。每一个强大的民族都有这种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民族的原始精神。
如果要给自己的时代命名,给予现时现世的诸种感受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性的表达,需要解决在什么样的价值基座上讲述故事,它决定了对历史起点和时间阶段的规划。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被一些观念和意识所挟持,并没有形成对这个时代相对客观公允的认识,以及对这些认识的形象化。
史诗品质一般所匹配的是宏阔的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件对虚构的直接参与。卢卡奇说,伟大的史诗是一种系于历史时刻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中国现当代作品中大量此类的作品存在,近百年历史的社会激荡成为作品中人物驰骋的疆域。亨利·詹姆斯推崇长篇小说是一种“精心构思的艺术”,作为对立面,他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萨克雷的《纽卡姆一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放在一起,称它们是“臃肿、松垮的大怪物”,充满偶然和任意的诡异怪诞的元素。在谈到托尔斯泰时,他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羁轭于其伟大的题材——全部的人类生活——如同一头大象被用于驮运,被轭于一间马车房,而不只是马车。”当代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称作精心构思的艺术,它们少了一些负重和不成比例的、溢出自己承担范畴的事物。
第三个问题是史诗性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如此称呼今天作品中的人物可能略微尴尬,粗略来说,就是那种强有力的人物,提升作品的色彩和高度的人。布鲁姆把《源氏物语》当做一部史诗作品来看,因为他从小说人物的身上看出了一种渴望的“光华”,那是一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向往,永远不得平息的欲念。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创作小说人物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与公众接触的行动,现在一些长篇巨制缺少的是具有公众性和讨论空间的人物。
史诗品质有时候被等同于宏大叙事,自现代主义文学洗礼一遍之后,内在有深度的个人成为更俘获人心的文学标准,于是宏大叙事成为一个特别容易讨嫌的写作方式。在尊重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的前提下,说到底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对比荷马史诗时代的竞争首席和城邦生活的主题,现在的时代精神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宏阔和丰瞻的内心。是怎么赋予史诗以新的活力,我们如何在哪里想象个人与共同体的联系,如何把关于震古烁今的时代判断修辞化的问题。在作出与整体性视野断裂判断之时,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历时化,书写与整体性视野断裂或者重新相遇的新史诗。
无论奥尔巴赫还是布鲁姆都曾把荷马史诗和圣经作为当代叙事学的源头,把二者在文体上的双峰对峙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起源,前者在一个整体性视野里记录英雄和神迹,后一个严肃描写凡人日常生活中内心钟摆的巨大摆动。新的史诗依然需要在这样的源头上做一些综合性的工作。史诗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和时代的需求,还是一个时代作家的智力需求,文学创作有时候也是一个对抗性竞争的过程,有一条漫长的作品系列,走进这个序列就应该打上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印记。
 更多
更多

林白:在离开与抵达之间循环
对于两次收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创作奖的作家林白来说,她的“女性三部曲”——《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北去来辞》,正是用文字对女性生命体验所做的深刻探索。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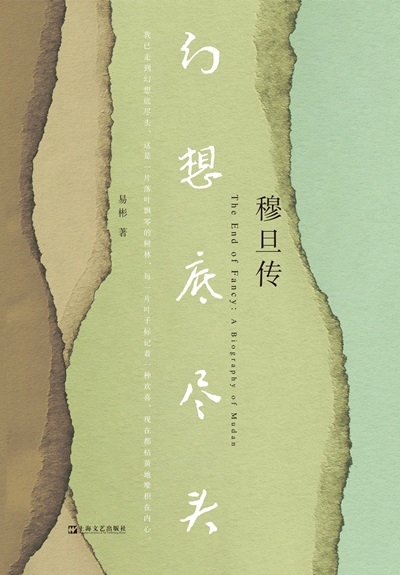
重读《赞美》:在命运和历史的慨叹中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