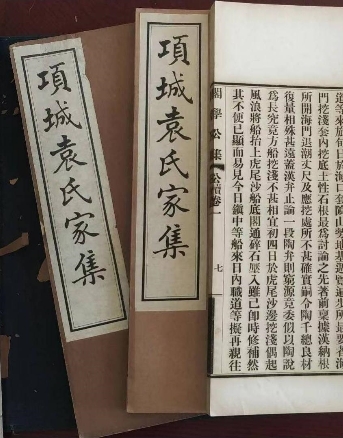北大荒人
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清朝的发源地,1668年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宗“龙兴之地”,下令废止招垦,实行长达200年的“封禁”政策,严禁汉族人民进入东北地区,致使这里成为荒无人烟的北大荒。
北大荒,它主要是指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建国初期的北大荒,是千里茫茫的荒原,冰天雪地,荒无人烟,是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每年冬季冰雪覆盖的日子长达半年之久,冷和荒凉是北大荒的主色调。
1947年以后,一批批的解放军官兵从解放战争的硝烟里走来,带着征战的风尘开进了北大荒,创建了第一批国营机械化农场。
1954年,王震将军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让麾下的10万转业官兵驻进了北大荒,戍守边疆,开荒造田,这批农垦大军也成为开发北大荒的坚实力量。
1968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百万知青涌进了北大荒,在诸多队伍里文化程度最高,从而成为农场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父亲作为山东支边青年,是1959年支边去的北大荒。据说山东总计去了12万支边青年,郯城县当时一起去北大荒支边的有一千多人,那时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去的。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在一起,以连(后改称队)为单位覆盖了整个三江平原。我们连队天南海北哪里人都有:贵州的,四川的,杭州的,上海的,北京的,山东的,河南的等等,南腔北调齐聚一堂,听懂的,听不懂的也都见怪不怪了,我们连队以山东人的居多。
当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进入正常轨道时,一个最大的问题也紧跟着浮出了水面,连队里的小伙子们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可连队的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北大荒,好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当时连队也给结婚的职工很优惠的待遇:有房住(马架),所有嫁来的媳妇都可以批职工吃国库粮。这在当时是很有诱惑力的。
很多都是老家给说成回去领来的:很多都是因为家里穷,听说到北大荒可以当工人吃国库粮就去了;有的家里是地主成分,不好找婆家,想着走远了就不受歧视了;有的是父母贪财得了人家的金表,拿了人家的银元才应的亲,做女儿的只好跟着走了;有的骗女方说在东北当官,把姑娘花言巧语骗去的……小伙子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娶媳妇,娶到家就算赢了。
也有自己找的, 有个细皮嫩肉的王老五,硬是擦粉抹脂去追一个五大三粗的黑大姐,最后还真娶回家了,结婚后两口子经常打架,打不过的就砸锅,然后王老五再走八九里路去买锅背回来,一路下来也是吵吵闹闹几十年……
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连队里还有不少光棍。有个三十多岁的寡妇领着三个半大的孩子,从山东老家投亲而来,有人给介绍了个老光棍,三个孩子都跟着老光棍姓,爸长爸短也叫的很亲热,一大家子过得其乐融融得,过了几年,孩子们都大了,老光棍却一命呜呼了。又过了几年,寡妇又找了一个光棍,和和睦睦的又过了些年,却终没有和寡妇白头偕老,临终时还在问:孩子他娘,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家了?
那时候,连里的干部也很关心老职工的个人问题。老李四十多了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有人给老李介绍了一个刚没了丈夫的农村妇女,带着四个都不大的孩子,小的才二三岁,连队派了一辆四轮车,把娘几个都拉了来,还专门分了两间瓦房给老李,还把娘几个的户口都转成了城镇户口,吃了国库粮,该上学的安排上学,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亲亲热热的,也没再生孩子。孩子们成家立业后也都很孝顺,老李直到八十多岁才安然而去了。
我上初中时有个罗老师,那时已有三十多岁了,中等个子,双眼皮大眼睛的长得很端庄,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看就很有修养和内涵,却很内敛。听长辈们说,罗老师是上海人,祖上是资本家,受过很好的教育,因受家庭的牵连被发配到黑龙江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后来又转到我们连队,在连队的小卖部里卖货。1976年“四人帮” 打倒以后,国家的政策放宽了,连领导就让他到学校给我们当了老师。罗老师有三个孩子,那时都不大,媳妇有精神病,不犯病的时候像根麻杆似的风一吹就倒了,犯起病来就撒泼骂大街,家里一般都是罗老师放学回家再做饭洗衣服……很多人都觉得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调回上海了……
和罗老师一起到学校给我们当老师还有一个杨老师,河南人,父亲是资本家,四十多岁了,很有文化,性情孤傲,之前在连队干农活。给我们当语文老师的三年里,要求学生每天写一篇小楷,一年365天雷打不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杨老师改变主意,而且必须用钢笔写,不能用圆珠笔写。我的字也在那三年里有了很大的进步,随着岁月的流逝,字里行间有一份阳刚之气,也流露着不同年龄段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份自信。也让我终生受益!
那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在那里没有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亲戚,没有族人,有的只是老乡。连队里的人以老乡为纽带凝结在一起,互敬互爱,相互帮衬,一家有事大家都帮忙。
小时候我就对老乡的概念有很深的认识,连队里有二十多户的人家是山东郯城人,大家都很团结。父辈们以年龄大小称呼,比自己大的见面称大哥,比自己小的叫姓后面的名字,自己的家属(媳妇) 也随着自己称呼,孩子们见了则大爷大娘叔叔阿姨的称呼,他们待孩子们也很亲切,其乐融融得像个大家庭。
父亲对老乡也有自己的理解。最常听父亲说的是:你李叔家(老家)在咱家(老家)南面的李官庄,有七八里路,隔着一条河;你常玉大爷家(老家)在咱家(老家)西边谢家官庄,有五六里路,翻过一座山就到了;你潘姨家(老家)离咱家(老家)远点,有十多里路,是李庄镇界牌的……走动的亲疏以老家相距的距离为准绳,一个村的就是亲兄弟了。
那时,我还没有回过老家,对父亲所说的距离并没有什么概念,也不愿去想象,也就是这耳朵听了那耳朵冒了,但说的多了也就刻在记忆里了。每当父亲说起老家大爷家的哥哥们的小名总是如数家珍,脸上的笑总是那么的祥和而又温暖,每当此时也是父亲心情最好的时候!我却总弄不明白父亲的郯城方言里的那些小名是哪些字。虽然父辈们都说的是家乡的方言,但我们的老师,那些来自大城市的知青老师却教会了我们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这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都受益匪浅!
老乡们说着一样的方言,按一样的家乡风俗习惯过日子。谁家盖房子,娶媳妇,嫁女儿,大家都忙前忙后去给帮忙;谁家有点什么事也都在饭桌上说道说道,操一回心;冬天没事的时候,围坐在热炕头上家长里短的拉拉呱说说话;有回老家的,挨家问问有什么事吗?有要稍的东西吗?……
前几日忽听说,那些看着我们长大,一声声叫着我们的乳名的父辈们,有不少已经不在,魂归故里了,心里顿觉少了许多,空了许多,也添了一些酸楚和惆怅,眼角湿润了许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林海莽莽,白雪皑皑,植被茂密,人烟稀少,却是老虎、熊瞎子、狼、孢子、野猪等等的乐园。自从建设兵团的帐篷和马架建起来以后,人们在山里伐木盖房子、割条子编筐、采花酿酒、摘野果、采蘑菇木耳、采药、打猎等等,只要你是勤劳的,山里就有你取之不尽的财富。
那时, 山里的狼或独行或三五成群,常常流窜到连队家属区觅食,圈里养得鸡、鸭、鹅、猪、羊便成了狼捕猎的目标。 熊瞎子常到苞米地里掰苞米,通常是掰一个夹在胳肢窝里,再掰一个再夹胳肢窝里,前一个就丢了,就这样,掰一个丢一个,最后抱着一个苞米摇了摇了的走了。老师们则常常借来数说一些同学:学一课忘一课,像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扔一个。
当时连队为了给职工改善生活,建了一个养猪场,狼便常常结伴趁着月黑风高来背猪。这里的背是指狼用尖尖的牙齿咬住猪的耳朵,一边拽着猪走,一边用尾巴抽打着猪。其实猪的耳朵并不厚,若它不跟着狼走,狼一用劲就把猪的耳朵咬透了,疼的猪只好拼命跟着狼跑。
1966年的那个冬天,年轻的母亲抱着一岁的我刚出门,就看见院子里有一条狗,却发现它的耳朵支楞着尾巴拖拉着,心说:不好,是狼!忙把我放在屋门口,摸起门口的棍子,一个健步就冲了上去,那狼一看不妙,便纵身翻过木桩扎的篱笆跑了。母亲每每说起这段往事,总是语气平静,神情淡定,没有恐惧,也没有惊慌……
那个时候,连队里有个潘大夫,有时连队里夜里有急诊时会夜里出诊。一年的秋天,潘大夫夜里出诊回家的路上,路过一片刚收完的苞米地,割倒的苞米节还一排排的堆放在地里,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条狼,正在不紧不慢的跟着自己,心里一惊,急中生智,就近抱起了一抱苞米节,走一段就蹲下来放一根苞米节,狼走过去谨慎的看看闻闻,发现没什么危险就又跟上了,潘大夫走一段再蹲下来放一根,狼就跟过去仔细的看看,然后再跟上……就这样,潘大夫一直到家,那条狼也没敢动手。当时北大荒有句谚语:狗怕弯腰狼怕蹲。说的是狗怕人弯腰捡石头打它,狼怕人蹲下来用枪打它的意思。
后来,随着北大荒的人烟越来越密集,很多山林都渐渐地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大豆玉米高粱,狼、熊瞎子、野猪也渐渐地不敢来骚扰了,渐渐地和森林一起走远了……
我出生和成长在那片黑土地上,耳闻目染父辈们开荒的艰苦岁月,看着北大荒人开垦出的千里沃土,成为北大仓,成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到驾鹤西去,还有很多和父亲一样的父辈们,也都相继相携而去了,然而北大荒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是北大荒的垦荒者,是北大荒的开拓者,北大荒人的后代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先辈们,那是我们对父辈们的敬意,是对那些开发北大荒的人深深的敬意!他们属于北大荒,他们永远是北大荒人!
北大荒人的品格,象西伯利亚的风一样的直爽,象绵延的群山一样的粗犷,象黑色的沃土一样的热情,……
美丽富饶的北大荒养育了我,那山峦叠幛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那开满杜鹃花的山坡,那开满鲜花的山林,那片黑土地……
虽然我已经离开那片土地20多年了,但那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却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潜入我的梦乡……而我的血管却永远奔流着北大荒人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