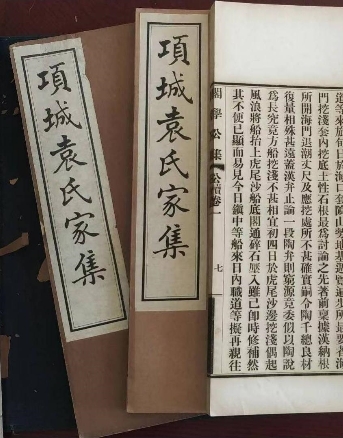偶遇王蒙先生
在北戴河一家酒店度假,吹着海风,踏着海浪,看海鸽子在苍茫的大海上翻飞,脑海里跳动着高尔基的“像黑色的闪电”搏击风浪的海燕;院落中的一株核桃树,像龙钟老汉,枝丫匍匐满地,形成一个核桃树厅,坐在厅中的圆桌前,葳蕤的叶子像巨大的手掌遮住阳光,之间或漏下斑斑点点的太阳花来,而青涩的核桃果像绿色的眼睛闪烁在我们的头顶,仿佛在偷听着朋友们地北天南的趣谈;几个孩子在厅内厅外欢快地穿来梭去,时而响来银铃般笑声。
那天中午,吃过简单可口的美食,我先离席,出餐厅消消食。当走到核桃树下,正准备钻进核桃树厅时,无意间一回头,看着四位年轻的男女陪着一位耄耋老人走了过来。老人戴着一副眼镜,花白的头发在太阳下闪着寒光,步履蹒跚,但并不要人搀扶。我定睛一看,这不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吗?我有点小激动,在心里惊呼:“妈呀,我看见真人了!”我收住正欲钻进核桃树厅的身子,但并没有迎着王蒙先生奔去,只是在原地站直了,默默地望着他的脚步。记忆里,早先年间读王蒙小说的画面不由自主地闯了进来。
1980年代,我那时还是鄂南崇阳大市乡下的一名中学生,莫名地喜欢上了文学,如饥似渴地读文学作品,发疯似的淘文学书籍。虽然大市藏在幕阜山中的褶皱里,但外面的资讯还是能传播进来,何况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信息确像是爆炸一般。而且,文学的穿透力无比强大,前天还在北京引起轰动的《班主任》,今天就在大市有了回响;昨天还在上海如春雷一般的《于无声处》,明天就炸到了大市。那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啊!我就是那时没日没夜睡在床上看小说,把眼睛看近视的。
偶然,听大市供销社卖货的人说,新到了几本热门作家的小说选,欲购从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连忙骑上自行车,从大市中学门前的陡坡冲下武长公路,再折向大市供销社。那是暑期,天毒热,刚爬过大市坳,先前只洇了一块的汗衫,已拧得出汗水来。到了供销社,我用汗衫擦了擦手,就走到柜台前。彼时的供销社里什么都卖,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有一旮旯卖图书,还大多是旧书,鲜有新书。而那天,我就看见几本崭新的、蓝色封面的书籍整齐地码在货架上。新时代毕竟来临了。
那好像是一套北京作家的文丛,我记得有《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邓友梅小说选》《刘绍棠小说选》等。其时,我已读过王蒙早年享有盛誉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知道但还没读过的《青春万岁》,总觉得王蒙作品有一股热烈的、纯真的气息迎面扑来,对王蒙的文字佩服得不得了;而刘绍棠则更像个传奇,听父亲讲他的《青枝绿叶》,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进了语文课本;只有邓友梅还不怎么熟悉,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数出荷包里的所有纸币和硬币,刚好够买三本,就把王蒙他们仨的书请回了家。
回到家,摇着蒲扇,先翻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清新的运河田园风情,虽然迥异于鄂南山区,但对于正在农村的我来说,更多的是亲切,对当年能进课本,啧啧称奇;邓友梅的小说,好像更多的是他当兵的经历,《我们的军长》等所表现出来的战争年代的生活颇能吸引少年的我;而王蒙被人们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风筝飘带》和《布礼》等篇什全在集中,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冲击。其实,当时有的段落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打破时空顺序和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新奇的意识流表现手法,跳跃的蒙太奇结构驱使你继续读下去,而且,越读越有味儿。可以说,那个年代,只要是见到“王蒙”二字,我就会去读。
后来,读到《青春万岁》时,我已是一个诗歌发烧友。小说里的一首诗,至今我都还能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人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幻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因为它契合了我憧憬未来和远方的青春。
再后来,读王蒙作品就渐渐少了,但对他的崇拜并没有消减,每一次他惊艳的作品问世,我都特别关注。有一年,省作协小斌主任去北京拜访王蒙先生,他知道我是他的拥趸,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当时,我有点懵,何惊喜呢?过几天小斌主任从京城回汉,我们在“汉高”小酒馆给他洗尘接风,我是怀揣着小斌主任所说的惊喜去的。酒喝得正酣时,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递给我。且说,我不是要给你惊喜吗?这就是。我接过一看,《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呀,真是惊喜哟,万分的惊喜。翻开扉页,王蒙先生的手泽仿佛还带着温度,顿时温暖萦怀。那一刻,我也顾不得不胜酒力,端起酒盏,就和小斌主任高兴地浮了一大白。
到了2022年,《长江日报》改版,《江花》周刊开辟了王蒙先生的“王蒙词话”专栏,越来越好看。每期报纸一来,我都抢着王蒙读。每每读时,总是被他睿智的思想、幽默的文笔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一个年近九旬的老者,还有那么旺盛的创作力、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
记忆还在像放电影一样地转动,王蒙先生已经走到我面前。我轻轻地问了声:“王先生好!”并不想叨扰他、找他签名、找他合影。然后,在他走过时,我又轻轻地念着他的诗句“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王蒙先生显然听到了我的念白,回过头来,含着笑,望着我,并扬了扬手。
我注视着他,目送着他,缓缓走出酒店院门。猛然想,王蒙先生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而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暮年,还如此健康,还能写出字字珠玑的长篇文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