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极端之美》:为文化点穴
中国举世独有的三项文化:书法、昆曲、普洱茶。散文家余秋雨特意把三章的次序做了一个颠倒——先奉上一杯好茶,再听一些曲子,最后以笔墨收官。
2017年8月,笔者阅 读了散文集《极端之美》,余秋雨著,2017年5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章。这部散文集之“三美”,凸显着文化人类学之美与文学人类学之美。
普洱茶之美
作者的《品鉴普洱茶》共八章。余秋雨先生把普洱茶列入,是一个提醒性的学术行为,借以申述一个重大趋势:从当前到未来,文化的重心正从“文本文化”转向“生态文化”。普洱茶,只是体现这种趋势的一个代表。
余秋雨说: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喝一口便知。
普洱茶的机秘是发酵!它的主角是微生物。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
普洱茶之美,美于文化人类学,美于文学人类学。
昆曲之美
作者的《昆曲纵论》共十六章。论昆曲之美,美于文化人类学,美于文学人类学。
昆曲之论中,最打动笔者的是余秋雨与白先勇两位文化大师的故事。昆曲在当代,会让人想到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会想到白先勇与余秋雨的文化之缘。
作者写到,22年前白先勇就邀请余秋雨到台湾发表一个有关昆曲的系统讲演,这也是大陆文人首次访台。在演讲中,余秋雨将昆曲定位为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范型”,这一观点让很多台湾学者吃惊不已,知音当然是白先勇先生。这个演讲后来还在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过,对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那个寒冷的冬夜,余秋雨和妻子马兰一直陪在白先勇身旁。随后,青春版《牡丹亭》名扬遐迩,余秋雨也一直担任阐释者,在香港发布会和北京大学,先后与白先勇先生作了两次对话性的讲述。
昆曲之美,美于文化人类学,美于文学人类学。
书法之美
作者的《书法史述》共三十四章。书法史述是对中国书法史的考察,也是中国文脉的梳理。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余秋雨对中国书法进行了图文并茂的爬梳,曾以文学的灵秀之笔评论说:“其书气韵端雅,秀朗流逸,有深山古寺之静”,这是联想之美。
余秋雨笔下的书法之美,如同一幅幽兰雅韵的画卷,仔细鉴赏是清泉穿岩,是流水出岙,是幽兰飘香,是竹摇藤飘.....。
笔者有感于作者对中国普洱茶,昆曲,书法梳理的系统性与深刻性。
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为书法、昆曲、普洱茶文化点穴——书法是纯粹的“文本文化”,昆曲是纯粹的“文本文化”兼“生态文化”,普洱茶是纯粹的“生态文化”。
《极端之美》是一箭双雕,它既是文化人类学之经典,也是文学人类学之范例。
——杨成栋定稿于厦门大学西村达观阁,作者笔名楠舟,现为中国和谐之声传媒丛书常务编委、杂志编委会副主委,报告文学代表作有《厚地高天》(获政府奖)《天山思想者》等,现为厦门大学人文讲堂主讲人。
 更多
更多

姚鄂梅:以笔为杖探向人性深处的暗礁与微光
“年轻时,写作是青春的自发倾吐,像《像天一样高》里对诗歌时代的追忆,那是没加任何雕琢的赤诚。随着年岁的增长,它逐渐蜕变为‘智慧型’的自觉表达。”
 更多
更多

“人民文艺”的香港之旅
1946至1949年间“人民文艺”在香港的历史际遇,尚未被充分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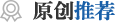 更多
更多

散文 | 山寨夜色
村里能出去打工挣钱的劳力,都出远门了。夜晚的山寨,再也寻不回我们小时候的热闹光景。堕谷村在山里算是个大寨子,三百多户人家,大部分还留着人。白天下地干活和下午收工的时候,村

散文 | 西大湖畔好村庄
西大湖有一千多个泉眼,是黑河岸边的天然湿地,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坐落于泉水之上的村庄明永上崖近年来依托自然条件和黑水国古城的悠久历史人文,改造原居民破旧民居院落,建成了三

散文 | 神农架散记
神农架观感

散文 | 想起那些吃杏的时节
留在作者小时候吃杏子的记忆,读来使人如身临其境一般,文章叙事清楚,脉络分明。也体现了作者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之情。

随笔杂谈 | 抬头的铺路石
在青石板铺就的古道上,躺着无数沉默的石头。它们被岁月磨去了棱角,被车轮碾平了脊背,在晨雾与暮色中编织成一条通往远方的银灰色绸带。这些铺路石从不抱怨,任凭牛车沉重的木轮从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