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戏未央
多年前,我在滕州汉画像石馆当讲解员。城东有座唐代的龙泉塔,馆舍依塔而建。每当夏日黄昏,天空一片霞红,院子里的合欢树开着粉扑扑的绒花,成群的燕子在塔顶飞舞盘旋。守门的张大爷在塔下开垦出一块薄田,锄掉杂草,种上花生,等秋天成熟,分给大家吃。他还从别处移来一株枣树,每年让我们尝到甜脆的枣子。有一回,几个美院的学生来参观,看到树上坠满玛瑙般的小枣,不禁眼馋。我一本正经地唬人,说这树可是汉朝时栽下的。竟有人真信了,对着它虔敬拍照。
彼时条件艰苦,几百块汉画像石,只能嵌在院中的长廊里。展厅仅有一间,摆一排米黄色木头展柜,用以陈列珍贵展品。有一块雕有百戏图的汉画像石被放在显要位置,它原是一座祠堂的后壁,厚重的长方青石上,刻着汉代最热闹的宴乐场景。
每回带着游客走到百戏图前,我会先告诉他们,这是镇馆之宝。此话一出,所有目光聚焦石上,正在交谈的也闭了口,皆安静地等我道来,想要的氛围便达成了。其实在我心里,每一块汉画像石都是镇馆之宝,我也曾把这封号给过周穆王拜见西王母图,给过日月同辉天象图。只不过百戏图,的确称得上是宝贝里的第一名。
工匠将石面打磨得平整光滑,犹如一张要作画的宣纸。弧面浅浮雕的技法,使线条浑圆立体,图案像是从石上自然生长出来,毫无雕凿之气。百戏是汉代乐舞杂技表演的统称,画面正中刻的是当时流行的建鼓舞。一根粗柱立在地上,柱上架一长鼓。两名男子,头戴冠帽,宽袖短袍,双手执槌,击鼓而舞。舞姿和鼓声应是生起了轻风,上方的羽葆飘荡起来。
左边有跳丸的艺人,向天空抛出七枚小丸,如同指尖悬着七颗流星。杂技大师正在案上表演折腰倒立,动作定格在难度最高的刹那。左下角坐两位胡人乐师,一抚琴,一弹瑟。石上并没有分界线,然而向右看时,已是仙界。两个羽人舞动长剑,另一羽人纵身飞起。一只神兽长着五个人头和两个鸟头。圆顶的仙树虬枝盘曲,拖着火焰般尾羽的凤鸟,站在树冠最高处。又有一个羽人站在凤鸟前,伸出双手,仿佛要向它乞求一粒仙丹。
这是与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镌刻下的神秘画卷。两千年前的滕州人,有着生则热爱、去且从容的开阔胸襟。正如这位不知名的祠堂主人,将人间欢愉与彼岸想象融于一石。他相信,此生的终点,不过是换个空间继续观舞听琴。长乐未尽,百戏未央。
可惜,这些无价的瑰宝,在业界虽早已著名,被大师赞美为伟大的艺术,在大众中却少有人识得。最刺心的,莫过于听到有人指着百戏图说,不就是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青石不语,任凭毁誉加身。我气了几回,也就罢了。
如此,十年过去,新馆落成,汉画像石有了更适宜的安身之处。我策划的“泱泱汉风·荟萃一石”——滕州汉画像石精品拓片展,也正式启程,走进了多家博物馆。我盼望更多人领略大汉气象,看见汉画的雄浑之美。巡展的海报用了百戏图,玄衣舞者敲击着朱砂染就的建鼓,那是属于大汉王朝的颜色。
最难忘的是上海初冬那日,在鲁迅纪念馆里布展至深夜。鲁迅先生痴迷汉画像石,搜集过许多拓本。他在给版画家李桦的信中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句话印在我们的展板上,也投射进每位汉画工作者的心里。当年先生宏富的收藏中,恰缺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此次能把展览带到他的纪念馆中,于我们来说,是做了一桩极有意义的事情。
当馆藏汉画像石数量已近三千件时,银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牌匾也悄然挂上了门楣。与此同时,“博物馆热”席卷大江南北,各地博物馆门前开始排起长队,看文物突然变成全民热衷的活动。意想不到的喧嚣,让从业者有些不适,然而也很快适应。展厅在一番提升改造后,百戏图依然位置显要,一束灯光照在石面上,泛出玉质的柔光。讲解员每天忙着迎接外地游客、研学机构、考察团、各路网红博主。而那些陪孩子或孙子来寻找作文素材的家长们,很难说他们中间没有当年曾经嫌石头无趣的人。
节日值班的午后,看到有美术老师带着学生来摹画车马出行图;穿曲裾深衣的姑娘们在百戏图前,或凝望石上的酒樽作举杯状,或展开团扇与两名男鼓手合影;参加社教活动的小男孩,胖胖的小手拿着拓包,蘸上墨汁,郑重地捶打着石板上的宣纸,墨色渐浓处,一条蜿蜒的龙身显形。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拓出中华文脉的基因,在那些古老的图案中,留存着永远新鲜的艺术密码。
闭馆之后,我从昏暗的展厅穿过。经过百戏图时,恍惚觉得手中似有一支指挥棒,若我静观,众神众人众物,也都屏息凝气;若我一动,鼓槌开始轻颤,羽人的翅膀抖落了细碎的星辰,琴弦自鸣,酒浆流动。纷纷扬扬,各行其是。
室外隐隐的声响惊醒了我,原来是门前广场上有人在练剑跳舞,唱戏吹笛。不远处的龙泉塔下,当年张大爷的花生地,变成了年轻人直播的露天舞台。而在我身边,那块被千万道目光摩挲过的大石,像一条渡船,载着两千年的热闹,缓缓驶向新的光阴。
 更多
更多

吕新:字数是有限的,生活才是无限的
“字数是有限的,生活才是无限的,现实、历史,都是无限的。千山万壑之间站着一个豆粒那么大的人,滚滚时间长河之中的一颗水珠,那就是文学与现实、历史的比例。”
 更多
更多

刘东:从“抗战文学”到“延安文艺”
梳理延安文坛的“结构过程”,以整体性视野重新审视延安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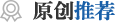 更多
更多

散文 | 我的故乡冰沟牧场
草原上,羊群如同天上的繁星坠落人间,缓缓移动着,悠然自得地啃食着青草。牧羊犬在羊群边缘灵巧地跑动,维持着秩序。在一处水草丰美、背风的小坡下,一群孩子正围坐在一位老阿爷身边

小说 | 南迦巴瓦的杜鹃
珠宝设计师与门巴族少女

诗歌 | 小镇日记(组诗系列之五)
“爱是全部的路途”/而我独守一夜

散文 | 在路上---雨幕下的念忆
车窗外雨势汹涌,混沌间雾气氤氲一片,天地仿佛笼罩着一张巨大且又湿漉漉的灰色网布。车轮在湿滑与战兢间踽踽前行,碾过积水的洼处,发出沉闷的呜咽。山势孤独又倔强地在蜿蜒盘旋中遥

散文 | 雨帘书
文章以 “雨” 为线索,串联起作者童年乡下、大学城市、工作后及中年时对雨的不同感受,体现心境随人生阶段的变化,借雨感悟生命与心灵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