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时代之症与突破之机 ——论当前青年作家的技术化倾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呈现的就是“多元与无序”[1]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具有明确一致性的思想潮流和创作方向。但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余年以来,以出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80后”“90后”青年作家的创作为代表,中国文学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技术化倾向。虽然青年作家[2]尚未占据文学主流位置,但他们代表着文学的未来,这一创作倾向也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文学整体态势的折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
任何文学都离不开技术,或者说,技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会重视技巧,追求艺术的提升和发展。但本文所言的技术化倾向不是如此,它的内涵是以技术为文学的中心和最重要的追求目标,深远的宗旨则是对技术的崇拜。
文学观念是文学倾向最直接的表征。作家们对文学观念的自我宣示虽然不一定与其创作实践完全吻合,但还是能够基本代表他们的心声。当然,要全面了解到青年作家们的思想观念非常困难,但以叶窥木,通过一个典型个案来予以展示也是可行的。《钟山》杂志从2014年到2018年连续五年举办全国青年作家笔会,让每个作家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文学思想、创作目的等,集结为《文学:我的主张》[3]出版。该书囊括了近70位青年作家,其中包括一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的优秀者。由于笔会对作家发言没有任何特别要求,而是让作家们充分自由地表达,因此,作家们的文章都具有较强的自我个性色彩,真实思想表达的可信度较高。作家们表达了很丰富的文学思想,其中也包括部分作家谈到文学的思想文化价值等,将“生存”“思想”等概念作为文学本质来认识。但大部分作家并非如此。尽管表达方式有显有隐,但很多作家都显示出将文学形式当作文学中心来看待的倾向,他们推崇各种文学形式的探索,将对艺术性的追求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其内在思想就是将文学理解为一种技术或方法。
青年作家们的创作与上述思想观念高度一致。以当前最重要的文体形式小说为例,青年作家们的创作特征都呈现出强烈的技术化特点:
首先,是较少关注宏大社会生活和事件,更多逡巡于虚拟和个人世界。扫描当前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直面现实社会生活的很少,虚拟世界成为他们最热衷于表现的生活。比如,当前科幻小说的最主要创作者就是青年作家,涉猎过科幻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更是人数众多。此外,历史——非探寻历史真实,而是以虚构、游戏和戏谑为特征的历史书写——也是青年作家们的主要创作领域。如青年批评家陈培浩曾这样概括当前的青年作家创作特征:“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去触摸历史,成了当下‘80 后’青年作家一种相当显豁的表达倾向,它表现在张悦然(《茧》)、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王威廉(《水女人》)、陈崇正(《碧河往事》)等作品中。”[4] 此外,还可以以网络文学作为典型加以分析——因为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作家基本上都是青年人,而且不少网络作家也曾经有过传统文学的创作经历,甚至身兼两重身份,所以,虽然网络文学在当前文学中的位置不明,但依然可以从自己的独特侧面传达出青年作家的某些创作特征。网络文学数量庞大,但毫无疑问,虚拟和想象是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特征。它的主要类型如穿越、盗墓、宫斗等都是科幻和历史,距离现实很遥远。
当然,这并非说青年作家们完全不关注现实,只是正如有批评家所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被个人体验过了的现实,是精神现实。于是,现实呈现出更为精巧、幽微,也更为狭窄的图景。”[5]青年作家们笔下的现实世界存在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基本上以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世界为中心。其二是狭小、琐屑,很少反映广阔的现实社会,更少触及同龄人之外更广泛的生活和社会群体。比如,“80后”的韩寒、郑小驴、甫跃辉等,他们从一开始就普遍性书写自己的成长生活。青春校园生活、乡村童年生活是这些创作最广泛的书写对象,也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主题。近年来,随着这些作家年龄渐长,成长记忆也书写殆尽,其中的部分作家逐渐远离文学,坚持创作者也基本上始终坚守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世界中,只是其范围从乡村拓展到城市,从中学校园拓展到了文化界。
其次,执著于对小说形式艺术的追求。青年作家创作都很注重小说的艺术品质,特别是对叙事能力的追求,致力于把故事讲得精彩、吸引人,追求突出的艺术想象力。他们的作品多叙事曲折、富有想象力,情感幽微而语言精致,具备“好看”的特征。这一点,评论界已经有较充分的关注,这里不再过多赘述。[6]
近年来最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群体之一“新东北作家群”,可视为典型。以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为代表的这一群体作家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很关注现实——尽管不是作家本人所生活的当下现实,而是20世纪90年代东北下岗工人的生活——并通过对个人生活和精神困境表达关怀,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在同龄作家中显得很突出。但即使是这些作家,也并不是将关注现实作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追求,他们的重心依然是在文学审美和艺术形式上。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个巧妙故事的优质题材,一个文学形式的优秀试验场。他们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依然是“虚构”和“技术”。如双雪涛就这样看待自己的作品:“《大师》全是虚构。真实的东西占多少?一点也没有。小说里的真实和虚构不是比例问题,是质地的问题。”“《长眠》是胡写的。完全撒开了写。原本想的故事和这个完全不同,但是具体是啥样的故事,早就忘了。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这样。”[7]因此,他们的作品少有对问题的针砭和执著追问,更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探讨,最多只有从人性出发的个人关怀,甚至不乏戏谑化的故事营构。作家们最突出的创作特色,也正如有学者的概括,是在幽默、荒诞与方言等艺术技巧方面的探索,而非思想上的突破:“‘80 后’作家笔下的‘铁西叙事’更具有后现代的风格,叙事形态更加灵活新颖,结构多变,时间跳跃,文化符号更加生活化。”[8]
上述技术化特征是对当前青年作家创作的概括,但它也具有时代文学特征的更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这些特征在其他年龄段作家创作中也有一定呈现。比如,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就呈现出明显的非现实倾向。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较之于同时期的现实题材创作,无论是主题的丰富性还是作品数量,历史题材创作都占据明显优势。如近几年出版的一些重要长篇小说,如刘震云《一日三秋》、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余华《文城》、胡学文《有生》、葛亮《燕食记》、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王跃文《家山》、邵丽《金枝》、叶舟《凉州十八拍》、叶兆言《仪凤之门》等等,都是在不同历史文化中逡巡。只是相对来说,与青年作家们相比,这些作家的创作背景更深远,对其技术化特征有所遮蔽,青年作家的创作历史比较短暂,技术化的创作倾向就更突出,也在当前文学中更显示出其代表性。
二
当前青年作家创作的技术化倾向,不是某个作家的个体行为,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潮流背景,是社会现实和历史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高度技术化时代的直接产物。最近二三十年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智能化科技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到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都受到改变,包括人们的思想情感世界。文学也深受科技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软件的文学创作,完全改变了以往由人类创作文学的历史,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文学的关系。科幻文学的快速发展,也体现出文学对现实科技发展的密切关注,蕴含着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和想象。科技也对文学观念和思想产生影响,渗透到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创作方法中。正如青年作家王威廉说:“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统治一切,更加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无条件许可。换句话说,技术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义话语,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9]当前青年作家的技术化倾向,就是时代潮流对文学影响的体现,隐含着技术主导时代产生的“技术崇拜”思想。
与技术因素密切相关的消费文化也起到一定影响作用。技术发展对消费文化有深刻影响,因为高科技带给人们更多的生活便利,技术的意义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进一步促进消费文化的发达,并决定消费文化的特征和方向。比如大众阅读,随着科技进入人们生活,人们更倾向于采用简单便利的电子和图像阅读方式,内容上也日益朝被动接受的低级化和通俗化方向发展。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文学作品要获得大众认可,必然要适应时代消费特点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学需要朝着故事化方向充分发展,努力运用高超的叙事技巧,把故事讲述得精彩、吸引人,才能获得市场上的成功。
时代文化的影响所针对的是所有群体,青年作家成为典型代表是时代效应的结果。技术快速发展和消费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是在1990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精神和信仰渐次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新科技工具、新媒介方式,也迅速进入人们的生活。对于这一时期的成年人来说,由于他们之前已经有一定的文化准备,所以具备一定的免疫力和对抗性。而“80后”和“90后”完全是在这一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其直接的文化产物。他们既缺乏稳定的思想资源作为精神依靠,也很难形成确定的思想方向,只能接受消费文化的无情侵蚀,他们最有效和最可能的反抗就是依靠技术,在技术化潮流中寻求自己的创新和价值。而且,在对新科技的掌握和对新媒体的运用方面,青年人无疑是最快也是最熟练的。所以,青年作家成为技术化时代文学潮流的代表具有一定必然性。他们是技术时代的产儿,也自然要承担技术化的思想。
其次,是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果。当前文学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让我们想到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包括创作题材上回避现实、选择历史,包括以技术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都与先锋文学潮流有着很多的相似。确实,从精神资源上说,“先锋文学”的影响是当前技术化文学潮流形成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从文学发展角度看,它可以说是对“先锋文学”遗产的继承,是文学主体性的生长愿望。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有充分的必然性,它代表了文学追求自律、自我形式发展的强烈愿望。虽然作为潮流的“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时间,但就像王蒙在1990年代初对“先锋文学”退潮做过非常准确的判断——“先锋文学”之所以不再被人重视,不是它被人们拒绝,而是它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文学观念的常识了。[10]在当前青年作家的谈话和创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影响痕迹。前述《文学:我的主张》一书中,大部分青年作家在谈到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崇拜对象时,大都列举卡夫卡、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双雪涛、班宇等也赞誉“卡夫卡伟大”,以之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班宇更明确表示:“我对先锋文学很迷恋,多年以来一直是现代派的忠实读者。”[11] 从这个角度说,青年作家的技术化创作倾向具有文学自我完善和修正的特征,蕴含着新文学内在的艺术成长和完善的欲望和诉求。
当前文学技术化倾向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相关文学思潮的身影。这一点在上海文学中体现得最为典型。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当年“先锋文学”最早兴起的区域之一。在“先锋文学”退潮之后,上海对其“遗产”的接受时间最早,效果也最突出。代表之一是《萌芽》杂志从1997年开始举办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活动具有全国影响,特别是在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可以称作是近二十年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其早期获奖者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固然已经成为“80后”作家中最早具有全国影响的群体,后来的更多青年作家,也有相当部分参加过比赛和获奖,受其影响而从事创作的“80后”到“00后”作家更是难以数计。“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文学的技术性质,将艺术性作为第一品质。此后不久,“创意写作”也在上海的大学教育中迅速兴起,并影响到全国——复旦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的学校,王安忆是最早的“创意写作”导师,培养出了甫跃辉等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意写作”的基本内涵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如出一辙,都是将文学理解为一种技术,一种可以教育的科学文学。以这一观念为主导,就是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训练,作家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化培养。
最后,与青年作家们的现实处境和自我追求有密切关系。与成长环境一样,“80后”和“90后”作家的文学处境也比较尴尬。其一,前辈作家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借助于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建立起来的力量已经无法复制,这或许会成为后辈作家的巨大精神阴影。后辈作家要取得创作成功,必须另辟蹊径;其二,这些青年作家在相对平静和规范化的环境下成长,人生道路普遍缺乏更多的坎坷和复杂,生活阅历也比较匮乏,他们无法按照前人的创作模式写作,只能另找突破;其三,他们生活的时代,文学已经严重边缘化和商业化,消费文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他们既感受到压力,也难逃其诱惑。“80后”青年批评家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12],在同龄作家中得到广泛共识,正是这种情绪的典型表现。
所以,青年作家们的技术化文学倾向中也体现着他们自我突破的追求愿望。一方面,在对技术化的追求中蕴含着他们突破环境限制的愿望,他们以之为突破前人窠臼、凸显个性价值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他们对文学的坚持。他们以深化文学技术高度,寻求改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来促进文学得到更好的社会生存空间。
此外,如作家石一枫所表达的:“再加上中国文学有过一个特殊的阶段,关心这个也不合适,思考那个也不稳妥,最后发现只剩下琢磨技术才是最‘本分’也最贴切的……这种背景可能也加剧了对技术过分重视,以至于眼里只剩下技术的情况。”[13]现实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也是技术化写作潮流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
当前文学的技术化倾向是时代多方面因素推动的结果,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总体而言,青年作家们的技术化倾向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对他们个人创作,对时代文学方向都造成某些负面影响。
其一,也是最根本的,是对时代认识的误区。技术化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也无法抵御,从趋势说,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会越来越快,它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会日益强大。但是,如何处理与技术的关系,是完全的认同乃至屈从,还是呈现出自己的独立乃至反抗态势,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正如很多人文学者提出对科学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我们既应该认识到科技的意义,也一定要看到单一性科学发展的危害。如果没有必要的节制,特别是人文精神的引导,科技发展最终很可能让人类文明走向歧途,甚至会导致人类走向末路。当前社会中的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以及心理危机都显露出这样的趋势,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作家们做现代科技的简单否定者,以停滞和保守的思想面对社会发展,我们只是认为不应该做科技的简单崇拜者,而是要保持人文的清醒和冷静,对时代进行主动思考而不是成为被时代奴役的对象。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文文化,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是文学等人文学科存在的价值,也是其意义之所在。
从这个角度说,当前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技术化倾向折射出作家精神勇气上的某些匮乏。这并非是单纯针对青年作家们的责难。事实上,在科技巨大统治力的影响下,整个人类文化都呈现出科技膜拜的趋势,人文精神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影响力也日益缩小。就世界文学来看,技术化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内在化、个人化和技术化的特征也弥漫其中。比较21世纪世界文学与19、20世纪世界文学就可以发现,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样具有深刻思想性和深远关怀意识的作家越来越少,更多作家朝着精致却显狭窄、细腻却欠高远的方向发展。如何坚持文学个性,保持对科技崇拜文化的清醒距离,是世界文学共同面对的难题,却也是文学不可回避的使命。
其次,对文学本质认知的误区。毫无疑问,技术是文学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却绝不是最核心的要素。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深刻的人文关怀思想是文学的根本性主导,也是其意义和生命力之所在。如果将文学理解为单纯的技术、形式,是对文学价值的严重局限,也将使文学丧失其在社会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品质。正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唯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诗人和作家所能恩赐于人类的,就是在于提升人的心灵,来鼓舞和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人类昔日曾经拥有的荣耀,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绝不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从而使人类获得永生。”[14],文学需要表达、探索爱和同情等情感,需要展现出对抗苦难和罪恶的勇气,以及揭示人性的复杂,讴歌美和善。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现实的介入和关怀,承担时代的思想、意义和信心,是文学不可回避的责任,也是当前具有技术化倾向作家们所特别需要注意和警醒之处。著名作家阿来在讨论“创意写作”时,曾批评过其中的一些问题,实质上也是对技术化文学思想的针砭:“我们的文科教学存在过度阐释,并没有提供一种真正面对新世界新问题、寻找新方法的艺术的可能与勇气。”[15]
对文学接受的认识也存在着误区。如前所述,青年作家们之所以将艺术性作为文学的首要追求目标,与他们重视文学接受和读者问题有密切关系。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理解文学接受的本质。对读者来说,精致的技术(艺术)只是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而绝非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故事等技术性因素也许能吸引读者于一时,但很难做到持久。相比于技术因素,精神内涵对文学接受意义更深远。“任何艺术作品中最主要、最有价值而且最有说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这种态度的一切地方。”[16]这是当年托尔斯泰非常睿智的论断。文学赢得读者最根本的因素是作者心灵的投入与对所书写对象的倾情关注。只有作者真正投入情感,书写他们的真实生存处境和关切点,传达出他们的内心渴求和深层心声,才能让他们产生深入而持续的兴趣,保持对文学的热爱。特别是在这个物质文化泛滥的时代,人们更渴求精神上的尊重和理解,更追求在文学中得到认同和共鸣。当然,最理想的方式是既具有高超的技术性,又具备文学的心灵关怀和真实生活表达,将文学技术融入现实生活和人文关怀当中。
技术化倾向已经对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和限制。正如有批评家所注意到的:“他们可能尚且无力就宏观的结构性问题来进行叙事,转而投入到过去的哀伤与当下的无望之中,希望和目标是缺失的”[17],当前青年作家创作没有呈现出一直向前、向上的势头,而是平行发展,甚至是下滑的趋势(典型如一些“80后”作家曾经气势逼人,让人对他们满怀希望,但其文学光辉却是日益黯淡,一些作家甚至逐渐淡出文学创作)。特别是这一作家群体始终没有创作出具有独特思想和文学个性的代表性作品,建立起他们在文学中的稳定位置。无论是对作家个体还是对整个创作群体来说,这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技术化倾向隐含着一些思想上的认识误区,但并非没有意义。换言之,青年作家们对技术的追求并非缺陷,而是需要改变以技术为文学中心的思想观念,理性地对待文学中的技术因素。如此,在这一潮流基础上,也可能绽放出非常有意义的文学前景,对青年作家们来说,也可能创造出突破自我的重要契机。
其一,蕴含着与中国文学传统深入关联的重要契机。文学的技术因素与思想观念之间不是绝对隔膜,深入的技术探索很可能会触及精神层面的因素。特别是青年作家们的技术追求,本身就包含着期待大众接受的因素。这样,他们在寻求故事讲述多元化和技巧化的时候,必然会联系到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会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学审美因素和小说技巧之间的关联——因为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本就是大众审美习惯的重要塑造者,要切近大众审美,借鉴中国传统小说技术(艺术)是必然的路径。
所以,青年作家们的技术化追求,有意无意间就触及了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也就是文学如何借鉴民族文学传统,如何呈现民族文学个性的问题。如果能够真正深入地借鉴传统文学技术,又不放弃现有的现代文学技术特点,而是进行有机地交织融汇,将很好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现代回归,并进而可能从技术进入思想、从自发进入自觉的层面。如果能够将技术探索深入到中国本土审美传统,并融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完全可能诞生出具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真正创造性的艺术杰作,并通过读者大众的认可,赢得社会文化中的较大影响力。事实上,在当前部分青年作家的艺术探索中,已经可以看到某些明确的古典小说影响印记,以及对传统思想文化意蕴的某些探寻。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创作趋向。
其二,从青年作家角度说,这当中也蕴含着他们拓展自我的一个重要契机。如前所述,这一代作家具有较强的影响焦虑,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生活积累上的先天缺陷。他们目前尝试以技术化来作为自己的创作突破口,确实不是没有其合理性,只是方向存在误区,难以获得应有效果。其实,青年作家们从思想角度来进行自我突破也同样具有合理性。因为生活经验匮乏并不妨碍深刻而独特的思想。最著名的例子是卡夫卡。卡夫卡的生活经验也比较狭窄,但他通过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剖析了我们时代的人类困境,表现出独特而具有深刻创造力的思想价值,从而抵达了同时代文学的最高峰。青年作家如果能够调整好方向,将对文学技术(艺术)的热情与对思想的探究结合起来,以思想深度来深化自己的文学创作,其生活经验匮乏的缺陷将迎刃而解,也可望进入文学的更高境界。
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作家们还可能以之为契机,通过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对西方的发展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呈现出独特的思想意蕴。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少缺陷,特别是在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层面上,它具有明显的非人性特点。但在哲学精神层面,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当前人类社会遭遇战争危机、生态危机、精神伦理危机等诸多困境,这些困境与西方文化的单向度发展主义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中国传统哲学的人与自然和谐、中庸节制等思想具有对发展主义的针砭和批判意义,可以启迪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其变得更为健康和合理。如果青年作家们能够在文学创作中借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现实、科学发展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文学思考,将会极大地提升中国文学的品质,给世界文学以惊喜。那样,既可推动中国文学抵达高峰时刻,也可望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注 释:
[1] 丁帆:《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文章虽然针对的是乡土小说创作,但也可以作为对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整体概括。
[2] 本文的“青年作家”主要指出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作家,也包括部分出生于1970年代后期的作家。
[3] 贾梦玮主编:《文学:我的主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 陈培浩:《从青春自伤到历史自救——谈李晁小说,兼及“80后”作家青年想象的蜕变》,《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5] 岳雯:《80后作家,文艺的一代》,《光明日报》2014年11月3日,第13版。
[6] 目前对“80后”作家作品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艺术角度,对作家们的艺术探索有较全面细致的阐述。参见金理:《小议“80后”文学之入史可能性》,《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7] 双雪涛:《关于创作谈的创作谈》,《西湖》2014年第8期。
[8] 刘巍、王婷绣月:《沈阳籍“80后”作家的“铁西叙事”——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9] 王威廉:《后记: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野未来》,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页。
[10] 王蒙、潘凯雄:《先锋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先锋》,见《今日先锋》编委会编:《今日先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11] 班宇与理想国宝珀文学奖的对谈。见理想国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vOFOZOJLV0Ln13HwVNFUqg。
[12] 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3] 石一枫:《不敢说是主张》,见贾梦玮主编:《文学:我的主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14] [美]威廉·福克纳:《世界因诗而永生》,见程三贤编译:《给诺贝尔一个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精选(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15] 周茉:《创意写作:培养消化新生活的艺术家——2018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暨创意写作高峰论坛举行》,中国作家网2018年11月15日。
[16] [俄]弗·格·切尔特科夫:《笔记》,见[俄]康·尼·罗姆诺夫等:《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周敏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17] 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更多
更多

王家湘:我的睡前书都是侦探小说
“那个时代的读书往往就像扇子一样,看着喜欢就扩充出去了,一环扣一环,像牵引式的阅读。”
 更多
更多

“这叫我去问谁呢?”——费孝通的问号
“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
 更多
更多

诗歌 | 清河边(组诗)
我坐下来,目光投向对岸 那一簇簇野花仿佛为我盛开 又仿佛与我无关

散文 | 柜台后的木兰花
纵使前路崎岖漫长,只要步履不停,便终有抵达晨光的可能。那柜台后木兰的静默姿态,已化作我心底一句无声的箴言——弯折不是屈服,只为积蓄下一次更坚韧的挺立,生命最磅礴的力量,

散文 | 秤与心
文章以父亲的老秤为线索,通过丧礼宰牛、借钱不还、压岁钱等事例,展现乡村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者在新旧观念碰撞中,思考如何在血脉传承与理性规则间校准 “心秤”,探寻传

散文 | 八里牌
八里牌让我见识了最大的木头。桃花冲林场的大木一杪冲天,所多的是杉木,金钱松、罗汉松及椴木也成片。大木被伐倒,裁成一段一段,堆在公路边上,整日里弥荡着一股清香的杉木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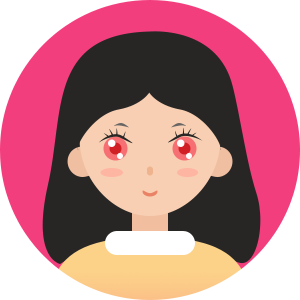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小说 | 标准音
距离中考志愿填报截止只剩下48小时,陈岚为儿子林澈精心规划的“最优路径”——报考本市顶尖高中理科实验班,与儿子内心燃烧的音乐梦想发生剧烈碰撞。这场冲突不仅撕裂了亲子关系,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