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4年第3期|朱秀海:死无葬身之地(中篇小说 节选)

朱秀海,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乔家大院》《兵临碛口》《远去的白马》等;中短篇小说集《在密密的森林中》《出征夜》《第十一维度空间》《永不妥协》等;散文集《行色匆匆》《山在山的深处》《一个人的车站》等;电视剧作品有《百姓》(两部)《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家大院》《天地民心》《诚忠堂》《血盟千年》《海天雄鹰》等。另著有旧体诗集《升虚邑诗存》《升虚邑诗存续编》《升虚邑诗存又续编》等。
导 读
激流群哮,海声浩荡,一道闪电在夜空中亮起来,将乌云撕成两半。一个社区医生被带到幽深的宅院,死亡的阴影降临,各路人等聚集于此只为审判宅院主人的命运,而社区医生也将在此完整地目睹一个人跌宕起伏的一生。
死无葬身之地
朱秀海
暮色浓重,但是在大地黑暗的底色之上,西天清朗的海空低处仍有一线暗红的残霞横亘在数条深灰色乌云之上。而在海空的另一边,不大一块浅褐的云丛中不时会亮一下白色的闪电。他头天到得晚,幸好房子是早就租好的,妻儿又暂时没随他一起来,一个人总归好办,按照那个貌似很急迫的合同约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了班。原先知道他要服务的是城市的一个边缘社区,没想到边缘得那么远,几乎就是远郊,也可以说就是乡下,因为在濒临大海的城市白色主调的建筑群和他签了十年工作合同的社区之间隔着面积广大的荒野,头一眼看上去竟给了他一种无边无际的深刻印象。荒野上植被茂密,林木葱郁,让人感到压抑,透不过气来,好在这荒蛮沉默的一片绿色海洋中到处开着花,赤橙黄绿青蓝紫,绚丽夺目,不是一般的有气势,与城市那边隐约可见的海有一拼。这类地方对于旅游者或者避世隐居者来说相当不错,空气清新,馥气四溢,离海不近也不远(最近的海湾据说只有十分钟车程,刚来第一天就要上班他当然没时间去看上一眼,而能够随时看海恰是他下决定抛弃北方某内陆省城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工作到这座岛上做一名社区医生的原因之一)。只是社区就在这荒蛮广大的一片之中,居民住得分散——一色高档别墅小区,或是一栋别墅自成一区——社区医生却只有他一位,虽然去机场接他的社区主任告诉他,如果不够他们还会考虑为他再聘请一位助理,但话外之音他也听出来了,至少目前这个看起来和城市主体建筑群在海岸边的延伸线差不多等长的社区将只有他一名医生为辖区居民服务。服务的范围无所不包,岁数不大领导风格却显出强悍作风的社区主任却不想在这方面和他讨论,并在初次对话中就暗示说,他们答应跟他签那么高薪酬的合同时上面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谈话结束时,社区主任无意间还说了另一句话:
“本社区的居民同意聘请您来的条件之一,就是相信您能够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一个白天情况尚好,很忙,但不知为何医生仍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忙。黄昏时分下了几滴雨(这地方总是多雨的),之后又晴了。下班时间到,他给最后一个冒雨送上门来的年轻外伤患者缝了针,裹伤固定,又帮过了下班钟点才到的另一名老妇开了治便秘的药,是啊,全方位的服务,他想。因为仅有的一个护士兼司药也在休产假,他连她的工作也兼了。然后他又等了一会儿,才关门回到临时公寓里,胡乱泡了一包面——还是累,主要是头一天,有些紧张,不想下去到一条有村级吃食店的小街上找吃的,那里其实有些看上去还不错的乡村小店,连咖啡店都有——恰在他要把第一勺面送进口腔时手机铃声响了,接他紧急出诊的专车也到了楼下,甚至司机也直接跑上来,帮他提起出诊包,这次是要他出急诊。
一路上那辆一眼就看得出价值数百万的豪华商务车一直在比车顶还高的暗色植被中穿行,使他有一种出了门就一脚蓦然从白天跨过黄昏直接进入黑夜的沉重和不真实的印象。大风从海上强劲地吹来,路两边的暗色植被随风动荡起伏,车子如同航船在海浪中颠簸前行,让他不适,想呕吐又止住。好在患者所在小区到了,由一条半公里长的私有的直道与环岛公路相接,一座完全陌生的暗黑森林中的村庄出现在眼前,与那种如同连车带人沉入一片深水的窒息感极其吻合。村口已经站着不少人,奇怪的是他分明看到了路灯,却一盏都不亮,这些人在黑暗中像一些影子一样飘忽不定,若隐若现,同时又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分明是在议论着什么,看到车到了,便都住口,把面目转向他。医生下车,从他们中间走过,留意到自己还是错了,不是一座村庄,而是一座被汽车灯光短暂映亮的占地宽阔的独立住宅;这些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村庄的入口,而是这座大而无当的豪宅大门外的空地。豪宅的两扇大铜门半掩着,有一盏门灯却不亮,完全不可能从昏暗的夜气中照亮空地上那些模糊难辨的面孔,却让医生冷不丁地感觉到人群中暗藏或者正在酝酿着的某种越来越惊恐和歇斯底里的气氛。当然它们不过是些梦幻般的即来即逝的瞬间印象,医生这时想到的只可能是病人,可是从那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影中他已经听到他们喊出的话语:
“是医生!医生来了!”
“快领进去,他就要死了!”
“别磨蹭了,你来晚了!”
“……”
医生跟随一名他其实并不知道身份的粗壮男人进了宅门,流水般的瞬间印象在继续:一时间他觉得这座宅门更气派了,简直是一座单独雄伟的建筑,高大、威严、现代,门前还有两尊汉白玉的狮子,一人多高,在夜气中张牙舞爪。随后他被粗壮男人引着经过一座天井式的庭院,几盏不大明亮的庭院灯让他难以看清其间的景物,他很快被接着迎上来的几个模糊的人影带进了豪宅的主体部分,一座占地豪阔的四层宫殿式主楼,并很快被单独领进了楼门,进门时他再次发觉头顶上仍然只亮着一盏灯,光线越发昏暗,灯光只照亮了门内一小块大理石雕花地面,其他空间都藏在户外流动的夜气般的阴暗中。他意识到一路从庭院真正随他走向主楼的人影越来越少,进门时除了那个壮汉,他仅仅注意到门灯光亮照不到的昏暗中,紧靠楼梯的地方,隐约闪过一个妙龄女子的影子,转瞬即逝,他没看清她的脸,能感觉到的只是她的衣香鬓影。接着他被壮汉匆匆带上了二楼,进入病人的房间——凭空间之大和装饰风格之豪奢他想到了这是主人的卧室——那个引他上楼的壮汉并没有进来,只是停在门外,抬手朝卧室深处一指,抛下一句话,转眼就不见了:
“他就在那里!你快去看看吧!”
医生发现只剩他一个人立在病人房间后很快就从初始的震惊中镇静下来。医生人过中年,小肚腩都有了,见过的世面不少,像许多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样,现在也模糊地认为人生来到世上就是受惊吓的,然后你就有了资历,遇上什么事情也不会蒙圈了。他放下出诊包,故意慢条斯理地取出手套,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戴好,顺便粗枝大叶地留意了一下这间显然像豪宅的每一部分一样故意装修出某种夸张怪诞风格的宽大卧室,注意到在半圆形罗马柱、丘比特爱神小雕像、几幅敦煌壁画风格的天花板和壁布之外,一个靠窗的墙角上居然还立着一盏差不多杵到天花板上的落地灯,汉代墓葬出土的长信宫灯的形制,只是举灯的不是胡人而是一位脸上涂了两团胭脂面目诡异腰肢袅娜衣带飘飘的宫女。像整幢建筑内外一样,这间卧室的灯光也不亮,注意到这件事他才发觉整个房间居然只有这一盏宫女举灯亮着。医生试着在墙上寻找别的开关,想打开更多的灯,让房间更亮些,以便能看清楚病人。但是没用,他找不到开关,只能放弃,一边走近病床,一边将目光投向病人。后者仰卧在一张同样大得夸张的床上,身子被一床薄被子裹得很严,只露出了一个半老男子的面孔。他还是再次被惊到了,即使躺在这么大一张床上,病人的身躯仍显得高大伟岸,两只大脚也从被子里露出,几乎要伸出到床外去。那盏孤零零的宫女举灯的微弱光线并不能直接照到病人脸上。于是这张脸除了轮廓线条细部也显得模糊。医生久经战阵,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见惯了这样的脸,它们接近死亡,正在死亡,但仍没越过生死之阈。医生做了一个深呼吸,先弯腰伸手试了试病人的鼻息,然后按照职业程序动手检测这副一息尚存的生命躯壳目前的状态。最终让他魂飞魄散的一幕还是发生了:病人离他最近的一只大手刚才还毫无生命迹象,这时突然抽搐了一下,两根手指抓住他的手腕,医生觉得自己听到了一声来自地狱深处的近乎无声的叹息:
“帮帮我……”
只用短短五分钟医生就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手提出诊包离开了那间鬼气森森的卧室。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壮汉并没有在门外等他。他在昏暗中摸索着找到楼梯走下去,走向一扇半开的门,仍旧没有人,还是那盏昏黄的门前灯亮着。他出门,才看到壮汉和刚才在庭院里见过的几个黑影左左右右地向他跑来。“医生,他现在怎么样了?”有人问。医生什么也没说,匆匆走过庭院,这时跟上来的黑影由五六个增加到了七八个。没有人再问什么,大概他们都听到了第一个迎上去的人问他的话,并且也都觉察到了医生的缄默,有几个人就在医生走向的那座很气派的高大宅门后面停下了。医生感觉到他们里面有一个细瘦的影子很像方才他进入主楼后在灯光昏暗处模糊发现的年轻女子,后者只是远远地跟着那七八个黑影走了几步,并没有跟上来。
现在医生走出了那座高大的宅门,站到了门前的台阶上,发现聚集到宅门前空地上的人影更多了,比他来到时增加了一倍还多。大风劲吹,空中有了一种暴雨将至的湿热气息,乌云全部遮没了天穹,四周围的树丛发出巨大的呼啸声。虽然如此,他站在这里仍觉得眼前比刚到时亮了一点儿,第一次注意到这座独立的、被林木和高大植被簇拥包围的豪宅大门外的空地面积有多么大,空地那一边还有可以停车的车场。除了已经麇集到这块空地上的人影,那些闪亮的车灯的光芒帮助他注意到正有更多的人和车陆续赶来,同时方才那一种惊恐、悲伤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也正随着更多人车的到来悄悄地被强化,它们如同一群沉默的野兽,暂时蛰伏在黑暗丛林的深处,还没有以一声突然的长嗥打破狂风、乌云、林木的啸叫,时间本身加给它们的谨慎与克制绷紧得如同一张膜一样薄的平静。但他的出门已经扰动了这张膜,原来还是三三两两一丛丛一簇簇站立的人形黑影忽然像昏暗的河流中滞留的团团漂浮物一样向他漂动过来,又像暴雨后激流中的漂浮物聚拢到河心岩石前一样在他身前聚拢,最终汇成黑压压的一片。他以为自己终于能看清这些人的脸了,但是诡谲的事情又发生了,豪宅大门前的唯一一盏灯突然熄灭,黑暗瞬间吞没了一切,包括那些他想看清的人的脸。他想到了躲开,但错过了机会,这些在黑暗中他仍然能模糊看到的人影从四面八方围住他,将他逼下了台阶,站到了空地上,他在这段他们向他聚拢包围的时间里听到了他们小声的嘈杂的音乐般多声部的话语,真正听清的却是这些话语中不连贯的单个的字和词,它们不是在表达这些字和词本身的确切含义,而是在通过它们表现自己参与到今晚这场令所有人猝不及防的聚集后的感受和要承担的情绪与压力,其中最不缺少的就是震惊、担忧、恐惧、悲伤,最不可理解的还有愤懑与怀疑,不愿意接受已经听到的信息。如果说他们就是夜气笼罩下的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这些情绪就是湍急的激流中的漂浮物。同时要越过阻拦住它们的河心的岩石,涌向它们暂时的目标,也就是医生,然后所有的漂浮物,不,情绪,又在同一瞬间化成了急切与焦虑的叫喊,冲着医生响起——
“你见到他了?他怎么样了?”
“不会是真的吧?”
“你快说呀!我们要知道真相!”
“……”
黑暗中这些模糊的人影还在越聚越多,不过仍算不上豪宅大门外空地上已经聚集的众多人影的全部,其他后到的人们离得太远,都溢到空地外的私家道路上去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医生的出现,但这最先聚拢上来的一群也成了黑压压的一片,推拥着他在湍急的激流中移动。医生开始有了一种随时被他们卡住脖子陷入窒息的恐惧感。在这些黑影中他听到了男人们低沉、有力、喑哑、连呼吸带喘的强大声息,但更多的却是女人们多种声腔和情绪混杂在一起的急促的追问。当然是这样了,危机一旦发生,最沉不住气的总是她们,男人们无论为了尊严,还是天性如此,总会较为镇静,哪怕是故作的,也会比女人表现得稳重和矜持,虽然他们内心不见得真比女人更沉得住气。但是嘈杂的女声过了一会儿还是低下去,仿佛喊了很长时间后连她们也忽然明白了,医生一直保持的沉默只会在一片混乱中被某个听起来最具权威感的男声打破。
一个显然过了中年的男人的身影完整地出现在他面前,医生顿时觉得这是他今晚看到的第二个高大伟岸的男人,因为他的影子几乎遮没了他面前的全部夜空。
“你是医生?”他用一种很沧桑却仍旧有力的嗓音问道。
“是的。”医生终于开了腔。
全方位的服务——他又想到了这句话——是不是也包括向这些人服务。可他们真的全是本社区的居民吗?
“我们有问题要请教。”
“不用客气,你们想知道什么?”他不情愿——十分不情愿——地反问道。
“刚刚听说了他的事情……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不马上送市里去,干吗在家里拖着?”
医生想说什么,还没有出口,高大伟岸男人身边的又一群男女叫喊起来,并把前者挤到一边去:
“你只是个社区医生,你行吗?”
“快叫120吧!”
“难道要拖到他死吗?”
“……”
这些叫喊声像方才一样嘈杂,几乎淹没了豪宅周围林木的狂啸。医生重新恢复沉默。一时间他认为这也是他的权利。
“不要喊了,难道医生不比你专业?连医生都选择了不叫120,那就是说……”
嘈杂的男女声低下去,风声和林木的啸叫声重新在医生的耳边高亢宏大起来。
“那好吧,你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过了一会儿,那个高大伟岸、极具权威感的男人的身影回到先前的位置上,再次开口道。
“不好。”虽然有继续沉默的权利,但这一次医生还是忍不住给了他和他们一个最简洁和肯定的回答。
“怎么不好?”又有人冲他喊,其中夹杂了更多女人的哭腔。
医生坚持自己的权利,继续用沉默回应这嘈杂的一群。
黑压压的一片恢复了安静。还是高大伟岸的男人,站稳自己的位置,想了一想才道:
“怎么不好?”
“我是医生。有职业操守的。未得到家属允许前,我不能泄露患者目前的状况以及不能叫120的原因。”医生用有点愤怒的声音道。
“我们就是家属。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一个女人忽然像条灵巧的鱼从鱼群中游出一样,从高大伟岸的男人身影后钻过来,站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丈夫,”她回头模糊地指示了一下伟岸男人,回头向着医生,声音咄咄逼人,“我哥哥目前处在独身状态。我们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到了,可是不让我们进去看他。我们有权从你这里得到真实消息。”
医生朝她看一眼,夜气浓厚,近在咫尺他仍然看不清楚这个小个子半老女人的脸。虽然她的话说得气势逼人,让人无法置疑,但他仍然不能仅凭女人自己的这番话就相信她。他选择不理她,继续沉默。
“我太太确实是他唯一的妹妹。以他现在的婚姻状态,他的亲属除了我太太外就没有别人了。”高大伟岸的半老男人改用一种更耐心、也更斩钉截铁的声调道,试图说服医生,“你应当相信她的。”
医生只是看了看他——仍然看不清男人的脸——他继续沉默下去。
“那好,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也不用藏着掖着,这也不是藏着掖着的事儿。”咄咄逼人的小个子女人完全不耐烦了,又站到丈夫面前来,尖声冲医生发泄自己的愤懑并主张权利,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我哥哥自杀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人这会儿一定不在了,只有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医生才会拒绝叫120把他送进城里急救是不是?……还有,他是服毒自杀,这个也必须确定,告诉我们,他是吗?还有下一个问题,这里面有没有刑事犯罪,有没有可能是他杀!”
又一道人影的激流向这片黑压压的人群奔涌而来,它们比刚才的任何一支激流都更有气势,几乎可以说以摧枯拉朽之力荡开了潴聚在它面前的人群之影,直接在医生面前停下。由于它的到来,就连刚才一直气势逼人地对医生说话的小个子女人和他身后的伟岸男人也很被动地让出了部分空间。
“你是医生?”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立即嘹亮地响起来。
“我是。”这次医生决定主动回答,他说。
“刚才有人在这里说她是他的唯一亲属,谁敢这么说话?要说唯一的亲属,我才是——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别人谁都不是,首先他自己就从不承认!”那女子四下环顾所有的人影,比刚才的小个子女人更加严厉、更气势逼人地说道。
“哎我说美丽,话可不能这么说。不管以前发生过啥事,到了今天这种时候,我总还是他的表妹,是你的亲表姑吧?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来这里争什么,我们只是听到消息,就最先赶了过来!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谁?”是小个子女人在说话,这会儿她又不是唯一的妹妹而成了表妹了,并且退到了高大伟岸丈夫的身后,气焰低下去不少。但接着悲伤来临,夜气里出现了哭泣的声音、擤鼻涕的声音,连同越来越不平的喘息。“你一个小孩子知道啥?要是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你知道啥叫艰难?当年要不是我和你表姑父在最关键的时候借给他一笔钱,他头一家公司就开不成!所以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他的公司里有我们的份儿!”
“再说你妈妈也早跟他离婚了,你连姓都不随他的,公开声明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不能算是他的闺女了吧?”年轻女子身后的人群中,一个男子突然恶毒地插话道。
年轻女子蓦然回头去寻找,当然她看不清说话人的脸,她连那人在什么位置也发现不了,但她的锋芒还是仿佛被那人挫伤了,瞬间整个人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不过很快就缓过神儿来,怒不可遏,开始反唇相讥并哭泣:“我妈是和他离了婚,可这毕竟不能改变我是他女儿的事实!我那个声明是我妈违背我的意志发的,我根本不承认!说到底你们不全是为了他的财产继承来的吗?好吧,你们今天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听着,只有我才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该是我的就是我的,谁也甭想拿走我的东西!”最后,不知是不是觉得力尽词穷,她爆发式地大声号啕起来。
一个年轻男人的影子突然从后面挤开其他人影,冲过来将女子抱在怀里,大声道:
“亲爱的,别哭!我来了!我在这里,看谁敢欺负你!”
女子像是被毒虫蜇了一样,骤然不哭了,全身激烈发力,要甩开他,又回头啐那人一口,叫道:
“你给我滚!我爸出事了,你倒冒出来了,快回去找那个让你喜欢的婊子去!别缠着我!”
接下来更令人惊骇的事情发生了:那对刚才还和年轻女子唇枪舌剑势不两立的半老男女——自称的表姑和她伟岸的丈夫——猛然冲过去,用力将年轻女子从男子怀抱中扯到自己这边来,那伟岸丈夫又顺势一掌,将年轻男子向后推了个趔趄,随着人群呼啦一声后退,年轻男子被推倒在地下。
“滚!你个小瘪三!你没听她讲吗?这里没你的事儿,有多远滚多远!”
这时有人叫道:
“医生呢?医生不见了!”
医生这会儿已经离开了,他利用了这群人疯狂撕扯的空当,悄悄溜进了空地前方的车场。那里停了更多的车,还有一串串的车开进来寻找已经不多的空车位。已经停下的车上坐着司机,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参与到人群的纷乱里去,一个个事不关己地坐在车里玩手机,几个热火朝天打怪的小伙子口中不时发出“嚯”“嚯”的叫喊,以表达着他们的兴奋或者成功,手机屏幕上变幻的七色光反照着他们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医生已经想离开了,他不想继续留在混乱中,但他必须找到那辆接他来的豪华商务车,让司机把他送回去,他自己是不知道路的,但他并没有很快找到。
这会儿他已被另一些人认出来了。这是些一直站在车场边缘、像是并不关心宅门前空地上人群中的争吵、其实却在密切观察事态发展的人。他们中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但都是男人。医生觉得与方才他走出豪宅大门后遭遇到的人们相比,这些人才是与今晚的事件关系重大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代表。
“医生你好,”一个将近中年的男子友好地向他走来,截住了他的路,人很清秀,戴着一副新近流行的白边眼镜,“你是需要帮助吗?……啊,今晚对你来说也是不好过的不眠之夜……”
医生像是被他的话惊醒了一样站住了,下意识地冲他点一下头,就像陌生人相见时要打个招呼一样。全方位的服务。他又想到那个词组了。好像就连这个人也明白他今晚不可能想离开就离开这里一样。不过他心里反感这句话,像方才面对宅门外那黑压压的人群时一样,医生此时也不想回答眼镜男的任何问题,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既不信任,又觉得不对任何人讲话是他的权利。男人方才的话只是出于搭讪的需要,并不是真的关心他,有点想掩饰什么,有点言不由衷,说不定有别的目的。于是他就沉默地站着,望着后者同样被手中一块手机屏幕反照着的聪明面孔。
“真想不到出了这种事。”眼镜男继续对他说着自己想说出的话,仿佛他和医生早就认识,并且是稔熟的朋友,又仿佛他们并不熟,但他仍然强行说出了那些话,仿佛只是在说给自己听,那样医生就不能挑理儿了:“他真那么做了,事情就有一点点麻烦。首先他的集团公司要被清算,还是一家上市公司呢。这个年月谁也不知道它的真实财务状况。我们那笔欠款要是拿不回来,公司当然还能撑下去,但别的资金状况不好的公司就完了。这种事情司法还会介入,还有银行。再有假账,牵扯的面更大。违法的事情也不敢说就没有,一些关联公司会不会爆雷,真不敢想啊……啊,对不起,我不该跟你说这个,这也跟您说不着对吧?哎,正好遇上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谁也不再为他做任何事情了?真的什么事也不能为他做了吗?要是这样,我们眼下还待在这里做什么呢?”
医生叹一口气,想想也是啊,这么多人待在这里……心一软就回答了他一句言不由衷的话:“等。”
眼镜男仿佛忽然被惊醒了,像是他一切都明白了,甚至从医生说出的这个字里悟出了更多含意,被手机屏幕照亮的聪明的眼睛瞬间睁得又大又圆,狂热地看着他,“那就是说,自杀真的发生了,可事情却刚刚开始……要等家属,不,是要等更有权威的人赶过来善后!……”
医生什么也没有再说就离开了他,继续往车场深处走。他不该对眼镜男说出那个字。今晚他只是个局外人,一个有责任为本社区居民做全方位服务的医生,除了豪宅的主人是死是活之外他不该蹚进任何一潭浑水。可是他还是找不到那辆送他来的高级商务车。
有些车远远停在车场外通前方环岛公路的私家车道两边。又是不大一会儿工夫过去,来的车更多,车场停不下,停到了那里,车道上则是后到的聚拢起来的大大小小的人群的影子。医生像一线细流从一条昏暗和激流翻涌的河面的一侧曲曲折折地穿过去一样,从车场走向私家车道,拿定主意一定要从面前一丛丛一簇簇的人群的暗影中间穿过,其实是想去那些停在私家车道边的车中找到他要找的商务车。找到了商务车也就能找到司机吧?谁知道呢。和宅门前的空地和刚刚离开的车场不同,私家车道两边连一盏微弱的路灯或地灯也没有,夜色到了这里更加浓稠,化不开的墨汁一样,这样他稍微放了心,因为没有人再能随便一回头认出他,当然他也认不出任何一个人,只能恍恍惚惚地感觉到他们一群群聚集在一起的影子。他突然一惊,因为他还是隐约听出来了,自己刚刚在车场上对眼镜男说出的那个字好像已经飞快地传到这里来了,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现在等在这里的意义只剩下了等。他一个人默默在谁也看不见他的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想到即便是这样他也用不着太担心什么吧,他并没想过要主动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他走了一段路,还是找不到那辆豪华商务车。
“……如果真是要我们等,那就是说,人已经不在了,”一个声音沉浊的男人在医生身后说,叹一口气,“人嘛,哪怕一生轰轰烈烈,干多少大事,总有这一天……回想起来,小时候他家里多穷啊,父亲早死,他和弟弟两个人只能一个上学,他放弃了。他兄弟据说这会儿都是国外大学的教授了。没有哥哥哪有弟弟的今天啊。”
“听说他们弟兄俩现在关系并不好。”另一个女人接上了话头。
“人到国外,心变坏了。”又一个女人说,“忘本。有一年春天,他家里只剩一块地瓜,他娘早晨将地瓜蒸熟,一刀切成两半,一半给他哥哥,另一半留给小儿子和她自己。因为哥哥要到工地上扛大活儿,养活全家。可是哥哥并没吃掉那半块地瓜,出门就把地瓜包在衣襟里,怕它冷了,躲在村头,等弟弟吃完自己那四分之一份出门去上学,这时他才一跳现身,将不舍得吃的地瓜塞给老二,说:‘你吃,你要上学呢,上学费脑子。’”
“别人说谁谁谁是孝子,都是面子上的功夫,他不是。他一说他娘二十八岁守寡就哭。开头他也不挣钱,但每天就是让头一个老婆饿着,也不会让他娘饿着。后来他成了那么大的老板,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可他娘住院,他不让任何人侍候,自己在医院守着,大小事亲力亲为。老太太脚趾生疮,别的办法排脓都嫌疼,他趴上去用嘴一口口把脓吮出来,后来他娘的脚好了,他的嘴肿得像个大倭瓜。”前面的女人说。
“他每年都做慈善。老家镇上的小学是他盖的,柏油路是他修的,桥修了两座。另外还以集团公司的名义捐建过两所希望小学。”
“他的集团公司员工最多时六千人,等于是养活了六千个家庭。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也是最大的慈善。希望小学啥的和这个比不了,差老鼻子远了。”
“各位,打住。他到底死了没有呀,你们就开始了,听上去像追悼会。万一他还没死呢?……”
医生不想听下去,他今晚来服务的社区居民就是个圣人也和他不相干,再说他也不信这个世上真有圣人。他不得已碰了碰身前的一个黑影,从旁边挤过去,继续朝前走,在夜气中努力辨认停在私家车道边的车,发现这边停的车更多,都排成了长长的不整齐的两排,一直延伸到半公里外的尽头。车道上拥挤的黑影不见稀疏反而更加密集了。他被另一个为数不少的人群再次挡住。别处的人们或者静默,或者悄声讨论着什么,但气氛总归是压抑的,像刚才已经开始悼念的一群甚至充满了悲伤和惋惜之情,但从这不小的一群黑影中,却不时爆发出阵阵哄笑。
“……有一回,我们公司要申请一笔贷款,我就不说哪家银行,是一家市一级的支行,总之他们的女经理就是不批,说我们资质不行,贷出去就是一笔坏账。她说得不错,这笔贷款后来真成了坏账,可我们当时急需这笔贷款周转,贷不出来我们‘嘎嘣’一声就死掉了。我万般无奈,不知怎么就想到了他,其实我们并不熟,我抱着有枣无枣打三竿的想法去找他,要他帮我想办法。我说:‘哥,怎么对付这娘儿们?你不帮兄弟我就完了。要不干脆你借给我一笔钱算了,反正你有的是钱。’你们都见过他一旦动起歪脑筋时那个样儿,他一脸邪魅地笑看着我,大四方脑袋歪着,两只三角眼里放光,问:‘那娘儿们真的油盐不进?’‘真的油盐不进!’‘真是这样,我这里就还有一个主意。你把她上了!’我当时真被他吓坏了,脸恐怕都不像脸了,我说:‘你开啥玩笑?我这会儿把她当菩萨趴下磕响头她都不睬我!’你们以为他说了啥?他说:‘你傻呀,当菩萨拜当然不行,但把她上了说不准就行!’那种事儿我还是想都不敢想,‘不不不不,’我说,‘哥,我走投无路了来求你,你这是给我出的啥主意呀,你这是要害死我还要在我脸上撒尿。换个别的主意!’没想到他不高兴了,满眼都是看不上我的意思,说:‘滚吧你!’……”
一阵哄笑后,医生听到一个男人嘻嘻笑着,催促道:
“接着说接着说!后来呢?……你把那女人上了?”
“这个就算了……反正是有人上了,后来贷款下来了,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20%的水头!”
“太狠了,给你出那么个馊主意,就敢拿这么多,你还有赚头?”
“他怕啥?这笔贷款他又没打算还!”
“你们这群坏人,金融界的风气都让你们搞坏了!”
医生听到了又一阵哄笑。
“罢了罢了,就当是个笑话,甭当真!甭当真!”一个听起来显得老成一点的男声响起,话到这里他自己却又笑出了声:“这些年他挣多少钱我不眼红,我眼红他老婆换得也太快了!十年换了五个……办法其实很老套,就是让人事到各大学招前台小姐,要最漂亮的,校花,然后再让她们一个个做自己的下一任……”
“能让你这个采花大盗心生嫉妒,他听说了不知乐成啥样呢。换老婆算个毛,这些年他明里暗里……哈哈,听说他还有个《采花宝典》呢,都是实战后总结出的经验,打一仗进一步!……”
人群中再次响起一阵哄笑。这时却有人挪动位置,意外地给医生让出一条缝,于是他便又像一线细流一样在被浓重的黑暗夜气笼罩的河道中流过去,马上又一次被挡住了脚步。这新的一群人影发出的特殊气息和窃窃私语让他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伙女人。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女生物学家呢!”一个中气不大足的女人用一种吃醋十足的腔调说,“后来这个女人跟他闹得也最凶。长得太难看了,非要他跟我离婚娶她……我说离就离,早晚得离,后来他们真结了,三个月又离,所以好多人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我就知道。那女人还为他生了孩子呢,”一个年轻点儿的女人马上接过话头,声音里充满了不屑兼仇恨,“新婚之夜他还对我夸口,平生胜仗无数,就一仗败了,大败……那天他喝醉了,自鸣得意,说那女人丑是丑,可他到底上了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知识分子!……我呸!”
“可后来听人说……啊,那时你也跟他离了,”第三个声音更年轻的女人哑声哑气地说,“那娘儿们跟他离了后,告诉她的闺蜜,她嫁给这个猪头其实就是想借种生孩子,说眼下法律还不允许她克隆自己,要是能她就不嫁了,后来才发现她便宜占大了,不但从猪头那里借到了种,还讹了他一大笔钱,养她自己和那孩子……她人丑成那样,本来打算一辈子和生物学结婚,没想到还交了这么一段烂桃花运,人财两得!……”
医生不想再听下去了。这群女人中有一个方才回头瞅了他一眼。当然在漆黑的夜气里她看不清他,可他还是担心被其中某一个女人看出了他是一个男人。他完全不想听这一小群显然拥有共同身份的女人谈话,并且也不想让这群对传出死讯的男人同仇敌忾的女人觉察到他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一辆车半个车身停进车道边的树丛,车里有一个女人在低低哭泣,半开的车门外一个男人在低声地劝解:
“你别哭了……你和他处了那么久,他是个什么东西你还不清楚……”
“那个女明星,婊子,前天我还在一个电视剧里看见过她……他和她是不是真事儿?”车里哭泣的女子突然开口问。
“是不是真事儿?”男人似乎想了想才回答,“这么说吧,有一个算一个,只要让他看在眼里……他的坏一是网眼儿密,只要让他盯上,再传出点儿事情来保不准就是真的;二是他敢跟她们砍价,有些是事前,更多是事后,要一百八十,事后只给四十,她们能拿他怎么样!……”
“那她们也不委屈,总是拿到了钱……好像她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似的……网上说她们的价码都是半公开的!”车里的女子又哭起来,“可他怎么对我呀,一直骗一直骗,到了今天他人都死了,什么钱我也没看见……”
“有些事吧,你们恐怕都不知道。有一回喝醉了,他搂着我的脖颈子说:‘兄弟,你是我的办公室主任,我拿你当兄弟,有件事你就没发现吗?和女明星搞绯闻是花钱最少效果最好的公司广告。老子在北京的大电视台做一个广告要花一个多亿,播了也就播了,棉花扔在水里,连个“扑通”声也听不见。可和她们搞绯闻不一样,她们多的都有大几千万的“粉”,只是我能成功地花点儿小钱儿把她弄上床,她的那些“粉”就会自己全体出动在网上把我和我的公司扒个底朝天!’‘她们身后都有一帮“铁粉”,开始时坚决不信我会上了他们的女神,拼命去辟谣哇。哈哈,很好,反正都是给我和我的公司扬名。’‘更有一帮“黑粉”和“狗仔”,天天等着黑她们,无风三尺浪,逮着这么个“大瓜”那还不得天天把我送上热搜哇。’‘哈哈,就花那一点小钱儿,让几千万人日复一日铺天盖地地给我打广告,我梦里都笑醒过!’后来他还专门雇了个律师,觉得火候到了再发个声明啥的,虚张声势说要控告那些‘狗仔’和‘黑粉’。这是他的一计,叫作‘火上烧油’……我跟了他这些年,做这些事他真是乐此不疲呀,都上了瘾了……我再跟你透个他的怪癖吧,其实也不能说是怪癖,好多大老板都有这种怪癖……每天一上班先上网百度一下自己,一旦发现他的名字和各种绯闻掉出了热搜前十就不高兴,就把他雇的那狗屁律师叫来,劈头盖脸地骂他工作不力,热度怎么就掉下去了呢……那律师就装神弄鬼地帮他做分析,说前面这一干女明星消费得差不多了,应当转移战场,有一个新的什么‘流量小花’最近大火……人家不干?没关系,找个什么开业的机会把她骗去,两人单独照个合影,发到网上弄个假绯闻,然后再发声明辟谣,告某某‘狗仔’,好,热搜‘噌’的一下又上去了!”
“我就是那个时候让他骗到手的,”车里的女子不管不顾道,“我刚上班给他做女秘书,姑奶奶根本看不上他,就因为他说要跟这个被盯上的‘流量小花’见面,好些事情得让我去办……你知道他有多不要脸又多会花言巧语,居然对我说干这种事得是他信得过的人才行,我刚毕业,没经验,稀里糊涂地就中了招儿……”
医生继续朝前走。这样的故事他已经听得太多,跟他一个社区医生有何相干?但他还是站住了。他在黑暗中注意到了一辆豪华商务车,很像送他来的那一辆,但又不是,在车的另一侧,树丛边上,一小群男人正在进行一场范围有限且不想让人听到的讨论。
“……他倒是事大事小,一死就了。我认为我们今晚就要联手成立债权人联盟,统一授权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准备对他的集团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同意!”
“我也同意!”
“本公司长期和恒通永达会计师事务所合作,他们信誉度高,在国内外都有成功的破产清算记录,我提议委托他们!”
“反对。这个恒通永达会计师事务所最擅长的就是做假账,用他们我绝对不答应!我提议从国外请一家专业的破产清算公司,比如比利时的FBD!”
“既然我们几位都到了,债权人联盟就算成立了,有不同意的吗?”一个大佬级的男人最后打破沉默,开口加入谈话。
医生没有从别人口中听到反对的表示。
“那好。一致通过。至于用哪一家清算公司以后再让下面的人去协商。现在要紧的是一旦他去世的消息被确认——估计就是今天晚上——那个社区医生能说出一个‘等’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债权人联盟要立即派出联合律师团,向法院提出冻结他公司和私人资产的申请,并且请求立即生效。”
“他现在还有什么资产呀,”一个喉咙里不太干净的老男人不时咳嗽着说,“公司早就成了空架子,徒有个虚名儿罢了,听说还在香港和国外借过高利贷,窟窿有多大只有自己知道。”
“我这里有一张他名义上的资产清单。让我的助理念一下,没想到的大家说出来补上。一定要在他的死讯被公布的下一秒钟向法院提出申请。”大佬级的男人说。
一个徐娘半老的女子打开手机,屏幕上显出一行行楷体字。夜气妨碍了医生的距离感,女子手机亮起来时才发觉自己就站在她身后,于是就被动地看到了这份似乎是匆匆记下的清单:
一家房地产公司(两处烂尾楼盘,估值40亿)
一家大致还在正常经营的制药厂(估值9个亿)
一家虚张声势的文化公司(长期亏损,目前浮亏80亿,说要拍电影和电视剧,除了传出了和多名女明星的绯闻,什么剧也没做)
一处一直没投入开发的港口,占地5000亩地(上市公司年报上估值50亿)
一幢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写字楼(20亿)
一架飞机(已抵押,现值3000万不到)
上市公司(长期ST,本人占股12.8%,全部做了质押)
银行负债400亿,到期未付利息140亿
待收款11.46亿
现存员工3000人,每月发薪2500万
女子念完了,手机屏幕暗下去。
众人沉默起来。
“他好像法国还有个酒庄。”
“他在香港还有幢楼——有年头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卖掉还债了?”
“他在马尔代夫是不是还有一座小岛?”一个话音打战的老男人不大肯定地说,“前几年我听他说过一次,兴许是吹牛,但也不一定。说是他新搭上了一个三线小明星,答应带那女孩子去马尔代夫玩,脑子一热花10个亿买下一座岛,还说紧跟着就要在岛上建个大会所,不请国内的了,请国外顶级的女明星,朱莉娅·罗伯茨、苏菲·玛索那种上档次的,请我们都去玩。”
“还有这幢房子。对了,还有一辆当初花2000万美元定购的限量版OJH轿车,全世界只出了七辆。”
“你们都忘了前几年他花八个亿拍下过一幅世界名画,说是莫奈的。”一个年轻一点的男声响起。
“那些值不了什么钱。”大佬级的男人粗暴地打断了众人的话,“真进入破产拍卖程序,八个亿买的画可能连一千万都收不回。那车眼下两百万没人要。房子更不值钱,倒是这块地皮,值个几千万。”
夜更暗了,医生只能摸索着往前走,才能不被伸到道上的树枝刮到脸上。今晚上他多么无辜地听到了这么多秘密,觉得自己的心都承受不住了。这所有他听到的谈话都是有重量的,即使与他无干。
医生下定决心再也不会被任何一群人影挡住了,这次他一口气走到了私家车道的尽头,再往前走几十里就是环岛公路了。这里停下的车还是很多,但人影终于稀落。他看到了最后一个男人,不,仍然只是一个人影,远离最后一个人群的影子,若隐若现地和几辆车一起隐藏在车道边的黑暗里。当然也可以说不是隐藏,是那些车和树丛的黑暗将他隐藏了进去。医生心中一动,与其说是到了这里还有人这件事本身惊动了他(原来以为走到这里再不会有人了),不如说是这个男人孤单地站在这里眺望着豪宅又不走过去,身边也没有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的身影,一下子震动了他的心。
形单影只的男人也看到了他。两人面对面站着,在黑暗中感觉距离很远,其实很近。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但沉默是不能长久的,谈话还是由男人冷不丁地开始了。
“你是谁?”
“……”
“不会是那个医生吧?你是吗?”
医生听出来了,虽然男人貌似在用一半玩笑一半瞎蒙的语气问他话,但他又似乎不相信医生会给他一个值得他信任的回答。
“是的。我是。”医生突然用肯定的语气说,一边对男人如此对自己问话心生气愤(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一边朝树丛边挪了挪身子,以免停在车道中间影响人车通行,虽然他知道这时不再会有什么人和车赶过来了,今晚上能赶来的人和车都到了。但是我不该受到这个男人的轻视,他想,我虽然只是一名社区医生,不像这个社区的许多大老板一样声名显赫,但难道这样就让他们有权利可以随便用轻慢的语气问话吗?全方位的服务不包括这一条吧?面前的男人猛吸了一口烟,面部有暗红火光亮了一下。医生又被吓了一跳,他因为烟火的这一亮从身后的树丛间模糊地瞥见了一条小径。而一旦发现了它,他也就马上想到这座豪宅除了身边这条私家车道外,还在树丛中隐藏了一条通向它某个隐秘旁门的曲折小径。
更让他不敢相信且以为自己看走了眼的是,他还在发现小径的同时恍惚意识到另一个男人刚刚通过小径离开。医生的大脑像只老式灯泡爆裂了一样,亮了一下又熄灭,随后他就想到了这个男人是谁。
“你看到他了,是吗?”黑暗中很近地立在他面前的男人将嘴角的烟蒂吐到地下踩灭,一边说道。仿佛刚刚被一道闪电划开的黑暗重又拉上了它厚重的帷幕,医生仍能感觉到男人又对自己微微昂起了头颅,用一种他看不到却能清晰感觉到的奇怪的嘲讽的微笑快活地看着自己。医生的脑瓜乱成了一团迷雾,和身边的夜气差不多,忽然又觉得自己刚刚看到那个男人的同时,还看到了方才进入豪宅主楼后从楼门灯光一侧的昏暗中感觉到的那个影子般的女子,她方才也和男人在一起,并和男人一样随着他的出现一闪就消失在树丛间的小径深处。
“这种把戏只有他玩得出来……不,我该说也只有他到了这种时刻还有胆量玩出这种把戏……但你只是个社区医生,你是无辜的,他不该把你牵扯进来。”
男人在黑暗中的话语再次弄痛了医生的心,却也将他一片紊乱的意识重新唤醒。他觉得这一忽儿脑瓜清楚多了,回头正视对方,道:
“刚才他一直都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是吗?”
男人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这个对他的态度一直高高在上的男人,他心里恨死他了,可奇怪的是夜气虽然没有变得疏淡,他的距离感却恢复了,逼真地感觉到对方是今晚他在这次鬼影憧憧的出诊中遇上的第三个高大伟岸的男人。
“可他终究明白自己玩砸了……你暂时帮他隐瞒了真相,还代替他本人在大门外的人群中间走了一趟……你这会儿摸一下口袋,说不定就能发现他偷偷放进去的小玩意儿,不过也可能没有,但无论如何你听到的话他方才站在这里全都听到了……他想搞一个他自己的死亡测试,却被人喝了倒彩。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他知道自己的路真走到头了。他抖了一辈子机灵,今晚上这个机灵抖得既不好笑,也不出彩。”
医生没有去摸口袋里是不是有个硬硬的小东西存在。此刻无论对于他还是那个人都不重要了,他想。现在他知道自己进入了游戏,登上了舞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完全有权利被主演们告知更多的剧情,无论它是悲剧还是喜剧。
……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第3期)
 更多
更多

王家湘:我的睡前书都是侦探小说
“那个时代的读书往往就像扇子一样,看着喜欢就扩充出去了,一环扣一环,像牵引式的阅读。”
 更多
更多

“这叫我去问谁呢?”——费孝通的问号
“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
 更多
更多

诗歌 | 清河边(组诗)
我坐下来,目光投向对岸 那一簇簇野花仿佛为我盛开 又仿佛与我无关

散文 | 柜台后的木兰花
纵使前路崎岖漫长,只要步履不停,便终有抵达晨光的可能。那柜台后木兰的静默姿态,已化作我心底一句无声的箴言——弯折不是屈服,只为积蓄下一次更坚韧的挺立,生命最磅礴的力量,

散文 | 秤与心
文章以父亲的老秤为线索,通过丧礼宰牛、借钱不还、压岁钱等事例,展现乡村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者在新旧观念碰撞中,思考如何在血脉传承与理性规则间校准 “心秤”,探寻传

散文 | 八里牌
八里牌让我见识了最大的木头。桃花冲林场的大木一杪冲天,所多的是杉木,金钱松、罗汉松及椴木也成片。大木被伐倒,裁成一段一段,堆在公路边上,整日里弥荡着一股清香的杉木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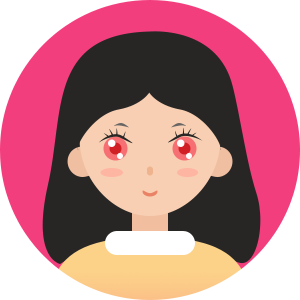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小说 | 标准音
距离中考志愿填报截止只剩下48小时,陈岚为儿子林澈精心规划的“最优路径”——报考本市顶尖高中理科实验班,与儿子内心燃烧的音乐梦想发生剧烈碰撞。这场冲突不仅撕裂了亲子关系,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