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公”与“私” ——以鲁迅书信与文集、全集编纂为例
中国现代作家交游广泛,留下数量巨大的书信。这些书信,作为一种特殊文本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虽然很难洞悉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笔者仍不揣谫陋,试从 “公”与 “私”的角度切入,也就是把中国现代作家书信存在的社会圈、关系网,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这两个写作与阅读的空间予以考察。如果分别用一句话来表示,前者是以政府职能部门、教育机构、传播媒介等为依托而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后者是日常生活中能交流思想、分享心情的亲友构成的个人关系网。
在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交换、传播过程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又怎样相互影响?从这一视点出发,下文以鲁迅书信与文集、全集编纂为例,对中国现代作家书信文本的存在形态及其变异试作考察和论述。
一 “书”“信”有别
“书”“信”二字,古今含义有别。在古人那里,“书”是“书”,“信”是“信”,泾渭分明。如《世说新语·雅量》云:“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1]后来,词义衍变,“书”“信”混用,通称书信这一种文体。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二《信》篇云:“今人寄书,通谓之信,其实信非书也。古谓寄书之使曰信。陶隐居云:‘明旦信还仍过取。’又虞永兴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乐府云:‘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坠井,一去无消息。’皆可证也。”[2]就是说,“信”最初是指“寄书之使”即所谓信使,后来才出现“书”“信”混用。
“书”和“信”作为古代文体,也有所不同。书是一种起源较早、臻于成熟的文体,在古代典籍中不可或缺。它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公文,如上书、奏书等;一类是亲友往复的文字,即简、札、牍等。后来的所谓“信”,更倾向于后一类的文字。周作人对此说得比较透彻。他在《周作人书信》序中不但说透了“书”“信”的区别,还说透了二者的衍变及其优劣。宋代所编文集在处理书信问题时,开始将“书”“信”分离与区别:“书”是“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即强调公共(社会)性质的书简,可以收入正集;与之相对,“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3],是强调私密(私人)性质的信件。这种分离与区别,在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里依然存在。下面以鲁迅书信为例作一简要梳理。
第一,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书”强调公共(社会)性质,与之相对,“信”强调私密(私人)性质。在鲁迅书信中,这种“公”“私”区分十分明显。鲁迅草拟或参与撰写的公函,参与的联名宣言、通电,自然都属于公共性质的书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是写给个人的书信,这些书信有一部分发表于报刊,后来收入杂文集,如:1925年发表的《通讯》《北京通信》,收录在《华盖集》;1926年发表的《上海通信》《厦门通信》,收录在 《华盖集续编》。第二,作为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书”和“信”的接收对象有着根本区别:前者一般是政府职能部门、教育机构、传播媒介及其代表者,后者是日常生活中有交往的个人。相应地,“书”主要面向社会网络传播,而“信”主要在个人交际圈内传播。鲁迅为北京女师大学生起草请求撤换校长杨荫榆呈教育部的公函,呈送对象是“教育部总长”章士钊,而鲁迅参与的联名宣言都在当时的报刊发表。私人信件的接收对象是有名有姓的个人,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有疏有密,有的后来反目成仇,如周作人、高长虹、林语堂等。第三,从篇幅长短来看,“书”相对较长,而“信”则大多是短篇,有的只有寥寥数字,如1927年12月6日鲁迅介绍荆有麟拜见蔡元培的信,连同署名和日期在内总共21字。第四,从信息内容来看,“书”陈述的是非日常的、特殊的内容,“信”叙述的是日常的内容。鲁迅书信中的“书”,都涉及公共事务,一般针对突发事件而发表主张、表明态度;“信”则主要为文学活动和日常生活传递信息、交流意见。如,鲁迅起草的前述呈“教育部总长”函,是因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无辜开除学生,激起公愤;鲁迅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多数是为了交涉作品出版事宜,而写给家人如致母亲的50封信,有关孩子的内容最多。第五,从语言表达来看,“书”典雅正式,“信”通俗随意。鲁迅草拟的公函,用典雅的文言写成,而私人信件则用白话,甚至夹杂绍兴方言,有人甚至发现,鲁迅书信中有若干“骂人”的土话[4]。第六,“书”大都一事一议,故而可据重要内容拟定标题。鲁迅起草的前述呈“教育部总长”函,手稿无标题,发表于《驱杨特刊》时,标题为《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收入《鲁迅全集》时连同另一封公函,合署名《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即使没有提示中心内容的具体标题,也可冠以“通信”“××通信”或“答×××”之类的题目。“信”的内容比较驳杂、丰富,时常不分主次,无法就内容拟题,即使编入文集全集,也仅以编号为题,以示区分。此编号,或为书信编次。如1925年3月21日致许广平信在《两地书》里标题为“二”;或为写作日期,如1927年1月2日致许广平信,标题为“270102 致许广平”[5]。第七,从风格来说,诚如周作人所言,“书”“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信”“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鲁迅的“书”,措辞严谨、情感内敛,“信”则措辞随意、情感收放自如。《两地书》中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嬉笑怒骂皆由性,有“天然之趣”。
以上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分离与区别,在书信被编入文集、全集时最为明显。那么,现代作家书信如何入集?在书信入集过程中,“书”“信”之别,与书信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在此笔者拟略陈一得之见。
二 书信与文集编纂
文集有总集和别集之分。书信作为应用文体,可收入总集或别集。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编入文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两个及以上作家的书信,作为书信总集出版,如孔令境编《现代作家书简》(1936);二是单个作家的书信,作为书信别集或与其他文类合集出版,前者如编入《沈从文别集》(1991)的《湘行书简》、后者如《于赓虞诗文辑存(下)》(2004)同时收入于赓虞《论诗》、集外文和《书札小辑》。
在私人空间写作和阅读的现代作家书信,极其不稳定。它们作为手稿被作家本人或收信人及其周边亲友保存。这些以自然状态保存的书信,会出现散佚或腐坏。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书信毁于战火或人为销毁。结集出版的郁达夫书信、朱湘书信,不足百封,实际数目远不止如此,现存的只是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一部分。目前能见到的鲁迅书信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几千封信,或散佚难觅,或被人为销毁。1932年年底鲁迅自述:“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直到近三年,我才大毁了两次。”[6]其他一些现代作家也曾大规模毁信。赵清阁烧毁了老舍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沈从文保存在他大哥处的积累四十年的书信,被付之一炬;康濯写给孙犁的几捆信,同样交给了一把火。这些现代作家书信,尚未进入公众视野、得到社会认可,就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我们现在见到的现代作家书信,从某种意义说,都是劫余硕果,得来不易。现代作家书信脆弱,极易散佚,结集出版给书信文本提供了一个面向社会的载体,并使之得以保存、流传后世。换言之,现代作家书信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是因为文集为其提供了安身保全之所。这一过程,也可以这样表述:现代作家书信最初作为一个只在极少数人之间传播的私人文本,通过文集编纂,变成公开面向大众的公共文本,即进入公共空间,具备社会性和历史性。
在现代作家书信编为文集的过程中,公开性的“书”和私人性的“信”被区分开来。不同于现代作家的“信”往往以单行本方式结集出版,“书”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似乎是它的宿命——只有与“信”或其他文类合编才能入集传世。以下,试以鲁迅书信与文集编纂为例,分别考察“书”和“信”编入文集的具体情形。
目前尚未发现鲁迅或其他现代作家的“书”单独结集出版。这类公共性比较明显的文本,其入集的一般过程为:手稿→发表于报刊→入集。鲁迅的此类书信,大多是他答复报刊编辑部或个人的公开信。例如:《答文艺新闻社问》最初发表在《文艺新闻》第二十九期(1931年9月28日),《答北斗杂志社问》最初发表在《北斗》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1月20日),后来都收入1932年10月出版的《二心集》,成为鲁迅杂文的一部分。即是说,在与“信”或其他文类合编出版之前,“书”已经离开私人写作空间,进入报刊营造的公共空间并产生影响。对“书”来说,入集不过是转换到文集营造的公共空间,进一步扩大影响和保存传世。从发表于报刊到编入文集,此类书信始终处于公共空间,因而无须增删修改。也就是说,由“私”转“公”,其文本内容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文本身份和文体身份。
无论作为手稿的书信是否具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公共性质,只要它不公开,就都是私人空间里的私密文本,一旦发表出版,就变成面向大众的公共文本。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同一书信发表于报刊与编入文集,所面对的公共空间及对相关公共空间的影响有所不同。发表于报刊,是以单封书信的个体身份面向大众传递信息,在它背后有近期发生的相关人事作支撑。比如,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的写作背景是,1934年8月19日出版的袁牧之主编《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开始连载袁梅(袁牧之)所作《阿Q正传》剧本,《戏》周刊编者遂在该刊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希望他“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7]。《寄〈戏〉周刊编者信》则是回应《戏》周刊第十四期关于鲁迅的若干问题,并就所载阿Q像谈观感。这两封信的写作背景,特别是涉及的人和事,不但没有私密性,反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有公之于众的需要,这是它们被公开发表、由“私”转“公”的基本条件。由于事后不久发表于《戏》周刊,发表时自然没有必要做任何说明。在此过程中,书信成为勾连鲁迅、《戏》周刊编者与读者的桥梁,而鲁迅、《戏》周刊编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这两封信所处的关系网。当这两封信后来被收入《且介亭杂文》,无异于从《戏》周刊营造的公共空间剥离出来,原有的写作背景及其语境几乎荡然无存。虽然无论在《戏》周刊发表还是编入《且介亭杂文》出版,都展现了这两封信的公共性质,或者说,都实现了由“私”到“公”的转变,但是二者的文本身份和文体身份并不相同,需要甄别。文本身份(textual identity)是符号文本最重要的社会关联,它与文本发出者、解释者的身份有关,但不等同于它们的身份,它主要由发出者的意图赋予。现代作家的“信”发表于报刊,其发出者是作者,收入文集,则发出者变成文集编纂者,由于作者和编纂者的文本意图不同,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便是“信”失去作为报刊文章单独发言的功能,而是作为文集作品集体发言。文体身份(stylistic identity)最初由作者在私人空间设定,一旦书信发表出版,其文体身份就需要在公共空间中重新确认。前述鲁迅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书信手稿,原本仅存在于私人空间,与私人性的“信”无异,当它在《戏》周刊发表,面向大众提供信息,手稿由私信转变为公开信;后来编入《且介亭杂文》,则意味着同时具备了公开信和杂文两种文体身份,不但向大众提供信息,还提供文学文本。此外,还需要注意到,表面上,“书”是写给某人或某群体,通篇话语构成“写信人—收信人”的封闭结构。但由于它发表在公共空间,作者的言说其实在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在私密空间进行——虽然有将言说空间私密化的外壳。“书”的这个特点,也使它收入文集、全集均无阻碍,并且无须删改。
在现代作家公共性质的“书”由“私”到“公”的转变过程中,书信权属鉴别至关重要。权属有待鉴别的书信,一旦编入作家文集,可能在公共空间产生虚假映像,导致以此为据的文学史被歪曲、偏离事实真相。比如,鲁迅没有参与拟稿而仅应邀署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长期被不加区别编入鲁迅文集,以致成为鲁迅曾与后期创造社联手的证明。涉及书信权属问题的主要有两种“书”:一种是作家口述、他人代写或代签名的书信;另一种是两人及以上之联合宣言、声明、通电等。第一种均被直接编入文集,如“鲁迅口授,O.V笔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于《文学丛报》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署名鲁迅,后来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此后出版的鲁迅文集、全集都依照此说。其实,对于此类书信是否入集,须视具体情况来决定。据冯雪峰回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他按照鲁迅“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8]。当时和冯雪峰“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的胡风回忆说,冯雪峰把自己草拟的信念给病重的鲁迅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事后鲁迅认为冯雪峰模仿自己“一点也不像”[9]。这封信,是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从《现实文学》杂志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既然如此,这封信的作者就很难说是鲁迅。即便鲁迅本人,对于他人记录的文稿,也是“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10]。第二种书信入集问题,更复杂[11],争议也更大。笔者认为,此类书信的主创者是实际起草人,而与列名者、挂名者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能考订明确实际起草人,则著作权归其所有;若是尚不能明确,则由于无法将此类书信的著作权交给参与署名的所有人以平等的方式共占共有,目前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将其分别编入各人文集。鲁迅致张琴孙信,以《维持小学的意见》为题,曾发表于1912年1月19日《越铎日报》。其原信虽是周作人手迹,署名却是周树人、周建人,且由鲁迅亲笔修改定稿,应收入鲁迅书信集。
上述以“分割”著作权方法处理现代作家“书”的权属,也适用于两人及以上的现代作家私人书信的入集。此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将通信者一方的书信结集出版,如《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2010)与《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2014)分别出版;另一种是将原有的双方通信集拆解为单方面书信后入集,如鲁迅许广平通信集《两地书》,被分割其著作权,分别单独收入《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1)和《许广平文集》(1998)。“分割”著作权,难免破坏往来书信共同营造的话语空间,消解通信的完整性,因此,通常做法是以往来书信集的形式出版。
“信”(私人书信)在编入文集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文本形态:一是原信(手稿或依据手稿的抄本、影印本);二是编辑整理本;三是基于原信的注释。在现代作家的“信”由“私”转“公”即编入文集的过程中,这三种文本形态在公共阅读空间的功能和影响有所不同。原信对书信原生态的呈现和保存,是其他文本形态无法替代的。由于书信往来双方所共喻者不必细述,信中时常有双方默会于心而后世读者如坠五里云雾中的“暗语”,因此有必要做适当的注释。如,萧军撰写的鲁迅致萧军萧红信简注释,不但与鲁迅书信在公共阅读空间构成多声部奏鸣,以致鲁迅书信连带的人际关系网越发复杂、微妙,还增强了鲁迅书信的可读性。全集中的书信注释,亦如此。不同的是,全集中的书信注释,因其撰写更多受制于一定时期政治、文化、学术而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风云的“晴雨表”。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就“正是这个时代文化政治风云的体现”[12]。第二种文本形态即编辑整理本的情况非常复杂,下文重点探讨。
私人书信在入集之前,一般没有在报刊发表过,尚保持原信的零散随意状态,对其做一些编辑整理是有必要的。然而,对照现代作家书信原信与书信集,往往会发现,在原信入集过程中,作者本人、亲属和整理者自觉规避某些言语,先后进行增删、修改或重写,由此出现异文,有的甚至成为“衍生型文本”。鲁迅许广平往来原信与《两地书》初版本[13],便是如此。鲁迅在编辑《两地书》时,采用筛选掉一部分通信、增删文字等方法,对原信作了“去言情化”“去隐私化”“去政治化”和“去刻毒化”处理。其“处理”动机和原因,也就是制约和影响两人通信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的因素,大致有人际关系、图书出版市场、大众读者需求、政治意识形态等[14]。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三种本质性的变化:一是书信存在的人际关系网发生了由“私”到“公”的变化;二是文本形态变异,由普通书信转变为书信体散文;三是作者发生变化,由原信的作者分别为鲁迅、许广平,转变为“鲁迅”或“鲁迅、景宋”。
需要指出,上文所述制约和影响因素,具有相对性。无论人际关系、图书出版市场还是大众读者需求、政治意识形态,都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彼时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此时未必要顾及。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例。在鲁迅编辑《两地书》的1932年,原信中涉及中共、苏俄、国民党内部党派的言论属于政治敏感内容,因而被鲁迅作了“去政治化”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风气下,这些内容不再“敏感”,不但不需要删改,反而有必要保留甚至突出。如陈漱渝所说:“《两地书 》原信(主要指许广平致鲁迅函)虽然个别文字有些芜杂,有些文字直接涉及时人或时政,在当时公开发表易招忌讳,但时过境迁,原信则显得更为真实,细节更为丰富,特别是对情爱心理的展示更加坦诚细腻,因此,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 。”[15]由于各种制约和影响因素具有相对性,顺应时过境迁后相关观念变化,《两地书》不断再版、新版,形成依据鲁许原信和依据鲁迅编辑整理的《两地书》这两大版本系列。较为独特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1996),该书营造了一个特别的《两地书》手稿空间,既有“有直写的、横写的”“嫌文字之表达不足画上图”“毛笔写或钢笔写的”原信[16],也有鲁迅手抄的《两地书》,由此书信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呈现出水火相容的奇异景观。
三 书信与全集编纂
如果说,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编为文集出版是由“私”转“公”,那么编入全集则既可能是由“私”转“公”,也可能意味着由“公”返“私”。这是因为,书信被编入现代作家全集有三种情况:未曾入集出版的书信入全集、已收入文集的书信入全集和曾收入文集、全集的书信在新版全集漏收。第一种情况,一般是新发现的佚信,编入全集对它而言意味着突破多年潜隐的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第二种情况,由于收入文集时已经进入公共空间,因此被编入全集的主要意义,在于确认作者权属、成为作家作品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公共空间回到私人空间;第三种情况,意味着新版全集漏收的书信,从公共空间回到私人空间。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常见缘由,是书信著作权不属于作家本人或权属不明。其中,大多为两个及以上的作者集体署名。
集体署名的书信如何编入现代作家全集,至今尚无共识,全集编纂者各行其是,显得比较混乱。大致而言有两种做法:其一,凡是有明确署名的书信都予以收录,无论集体署名还是单独署名,也无论亲笔签名还是他人代签。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录鲁迅书信的原则便是如此,该卷收入鲁迅和茅盾联合署名的三封致伊罗生信,均为茅盾起草,有一封鲁迅只签了名,有一封没有鲁迅的任何文字。其二,集体署名的书信,有的收录,有的不收。“鲁迅 景宋”联合署名的《两地书》自问世以来,相继被完整编入1938年、1958年、1973年、1981年、2005年等版本的《鲁迅全集》。而2011年版、2012 年版、2013 年版《鲁迅全集》,要么将《两地书》整体删除,要么只收录其中的鲁迅致许广平信。对于鲁迅参与的联名宣言,却全部收入。由此来看,集体署名的书信如何入全集,“既涉及文献的权属,也关乎全集的编选体例”[17],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凡是有明确署名的书信都予以收录的做法不可取。这种做法无视书信作者的复杂性,容易出现错收、误收。对于集体署名的书信,首要的是区分作者对该书信的贡献大小,这是判断书信作者权属的主要依据。《两地书》的作者权属问题,是鲁迅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分歧较大的一个话题。1997—1998年《鲁迅研究月刊》《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新民晚报》《法制文萃》等报刊对《两地书》是“合作作品”还是鲁迅“编辑作品”,有过热烈讨论,讨论结果倾向于认为是合作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承诺“在以后出版物中,为《两地书》支付整体版税”。[18]然而,《两地书》版权问题至今仍有争议,在现代作家集体署名书信的权属判断中也有代表性,故而下文再作讨论。
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政策法规司编写的《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二五”普法读本》,“合作作品”必须同时具备“共同创作的合意”和“共同创作的行为”两个条件,“仅提供辅助性劳动,如抄写、记录、校对等,不属共同创作”。而“编辑作品由各作者分别创作,经编辑人汇集到一起,与合作作品有区别,关键在于这种作品没有作者共同创作的合意与行为”[19]。具体到《两地书》,1933年的初版本虽署名“鲁迅、景宋”,但从其编辑整理来看,许广平主要从事素材提供、书稿誊抄、后期校阅等辅助性工作,负责体例编排和原信删改的是鲁迅。《两地书》里连许广平书信,也有鲁迅“加添了一些新的材料,增写了一些新的文字,用以充实和丰富原信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容”,“删去了一些感情色彩异常鲜明、措词尖锐的批评”[20],可见鲁迅对《两地书》的贡献最大,甚至可以说,《两地书》主要反映鲁迅的思想观念。有人说《两地书》“实际上是鲁迅的‘重新创作’”[21],此言虽嫌夸张,但突出鲁迅对《两地书》的主创地位,是合理的。《两地书》及以此为依据的各种版本,实为鲁迅编辑整理、鲁迅许广平合著的“编辑作品”,只署编纂整理者姓名、不署作者之名,也是可以的。《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2009)、《胡适许怡荪通信集》(2017)、《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沙汀卷》(2009)等,即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几个《两地书》版本,仅署名“鲁迅”,许广平并未提出异议,说明她认可这种署名方式。就此而言,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入《两地书》是对的,2009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11年版《鲁迅大全集》、2013年版《鲁迅全集》等“肢解”《两地书》,不收入原有的许广平书信,则欠妥。
以上讨论《鲁迅全集》收入《两地书》的状况,未及手稿。一般来说,现代作家书信手稿即为原信,但也有例外。《两地书》手稿有三种:一是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手迹即原信;二是许广平抄写本;三是鲁迅抄写本。许广平抄写本是《两地书》的底本,但这个抄本已不知下落。原信和鲁迅抄写本由许广平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捐献给国家机构,见者极少。文物出版社在 1978 年至 1980年先后分函出版《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八册),收入鲁迅致许广平的书信手稿78封,而鲁迅抄写的《两地书》被收入该全集的文稿卷。2002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其书信部分,与文物出版社版相同。鉴于鲁迅抄写的《两地书》手稿与原信差异较大,已成为两种不同文本,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收入文稿卷,与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区别开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称为“《两地书》原信”或“《两地书》真迹”,则不准确。因为,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写作时间在1925年3月至1932年11月之间,此时还没有“两地书”之名。
对于鲁迅参与的联名宣言,也应当视鲁迅对联名宣言的贡献大小而决定是否编入全集。例如,刊载于《京报》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22],鲁迅的签名虽排在第三,但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份宣言的铅印件旁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也就是说,周树人(鲁迅)才是“拟稿”人,因此这份宣言被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附录”。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参与拟稿而仅应邀署名甚至他人代签的书信,则不必编入全集,如鲁迅与创造社成员联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现代作家全集编纂及增补修订,常见失收已经公开发表、已经考实的书信,失收档案馆、纪念馆未发表的书信,失收带有书信功能的便条和请柬,甚或删掉书信中部分内容和部分附件[23]。这表明,在现代作家全集编纂过程中,现代作家书信的“公”与“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原本已经公开、由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的书信,因新版全集失收而流散集外,一定程度上由公共空间重返私人空间,成为全集增补修订时的辑佚对象,一旦作为佚信被发现,又增补进入全集,再次实现由“私”到“公”的转换。这种“公”“私”之间相互转换,在多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间存在,甚至成为修订、重新编纂《鲁迅全集》的缘由和动力之一。1938年版《鲁迅全集》失收上千封书信,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系列予以收录;1958年版《鲁迅全集》,实际收集书信1165封,但书信卷仅收入334封,于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予以增补,却未收部分已发现及后来新发现的鲁迅书信,以至2005年版《鲁迅全集》新增佚信20封。而《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1933年1月26日和3月16日致台静农信等,都在2005年版中失收,相对而言,这些书信重新回到了私人空间。有的书信在编入全集时被删掉部分内容和部分附件,借此树立或维护作家的“正面形象”,然而若干历史细节和真相因此被遮蔽乃至扭曲[24]。
现代作家书信在编入全集过程中出现的“公”与“私”之间相互转换,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编纂标准。一个作家的全集要有多全才算“全”?是否一篇不漏才能称全集?全集的意义在于“全”,还是另有评判标准?这样的问题,多年来困扰着全集编纂者。有学者认为:“作家可能随意的一篇日记、书信、回忆录,这些材料的存在确实有其本身的意义,但如果不能在文学史建构中发挥作用,那么在我看来,多一篇还是少一篇意义并不大。”[25]故而认为,全集编纂不以“全面”为标准,尤其是对于著作权不明确和涉及隐私的书信,要么干脆不收,要么删改后收入。然而,多数全集编者和读者认为,全集贵“全”,应该收录已发现的所有作品。以至在书信编入全集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种反著作权、反隐私权的理想,即为了尽可能全面收录并保留书信原貌,应该不顾通信另一方著作权,将双方通信一并收入,并且可以公开通信双方隐私,供人们批评研究。在这里,令人惊讶地出现了一种全集编纂标准高于著作权、隐私权的倾向。为了“使读者看到鲁迅原信的全貌”,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收录《两地书》之余,又收入鲁迅致许广平原信68封。在这一趋势中,出现了对现代作家和书信的重新想象:现代作家(主要是去世的经典作家),被定义为“透明人”[26],即使其思想意识最深层、最隐秘之处,也可以彻底公开;而书信,被想象成可以帮助现代作家“走下神坛”“回到复杂而完整”的人[27]。更为激进的做法,如《台静农全集》(2015)第十二册,题为《台静农往来书信》,收入他人致台静农书信60封,竟然多过台静农本人书信53封。在这些全集的编纂者眼中,尽可能全面收录书信并保留原貌是第一位的,因此一并收入通信另一方的书信,“从而将全集只收集主一人所作、兼收其合作作品的一般理解‘再问题化’,为我们打开了重新想象、定义‘全集’的空间”[28]。
四 书信所含诗词的入集
中国文学传统一直隐隐相传着“引诗”习惯,文人书信亦如此。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引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引录他人之诗;另一种是引录本人之诗。限于篇幅和题旨,这里只说第二种。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现代作家书信,都有不少包含诗词,约略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随信附录诗词,另一种是书信正文夹杂诗词。这两种情况自古就有,是古代文人交际在现代社会的遗绪。近年发现的胡适早年致胡近仁信,引诗颇多。其中,多数诗词作为书信附录,今见胡适致胡近仁诗词稿十二件,都是随信附录。诗词夹杂在书信正文的情形也常见,如1941年老舍、王冶秋致吴组缃的信中夹杂的人名诗[29]。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提及,有的书信本身以诗词形式写成,也就是说,以诗词代信。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晖居士”(胡适)与周作人的《方外唱和诗钞》。藏晖居士的来信,只有八行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但这首诗“借梦境来劝驾”,规劝周作人尽快南下。以诗词代信,常见于现代作家题写的字幅、签名本、明信片等。这一类题写赠人的诗词,具备书信的基本要素,同样是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应视为一种特殊的书信。比较而言,现代作家书信所含诗词的整理入集,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鉴于其作为文本在“公”“私”之间转换的复杂性,以下两种情况需要仔细斟酌:
第一,见之于现代作家书信的诗词,能否以及如何作为单独的诗词作品入集。
书信所含诗词,有的在作者生前已经编入作品集,后来所发现的诗词,在编入文集和全集时,即参照这些作品集将它们辑录。表面看,此事颇简单,其实尚需酌情辨析,分别处理。
仍以鲁迅为例。鲁迅的诗作,绝大部分本人未曾交付发表。1935年杨霁云收集鲁迅诗作十三题十四首,经鲁迅修饰后,编入《集外集》。其余的鲁迅诗作,均为《鲁迅全集》编者多方辑佚所得,编入《集外集拾遗》和《集外集拾遗补编》。这些鲁迅诗作,以旧体诗居多,大都属于“以诗词代信”类型。于是,问题随之而来。一是要不要单独成篇入集;二是从信中摘录出来、单独成篇后,既脱离书信语境而成为独立文本,也容易造成作品之于《鲁迅全集》而言的重复辑录,那么,该如何入集?
首先,编纂《鲁迅全集》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全集收录的作品以作者生前编订的各个集子为依据和底本,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确定一个标准:凡是鲁迅本人编订或得到鲁迅审阅修饰后才编入集子的书信所含诗词,就不要另外摘录单独成篇。因为在鲁迅生前已完成了从“私”到“公”的转换,它们不再是集外之作。
其次,随信诗作能否摘录出来、“以诗词代信”的篇目能否单独成篇入集呢?应该可以,因为二者都是鲁迅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这些书信里的诗词,如果不能以诗词形式单独成篇,无论从阅读还是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都会被淹没。事实上,就现代作家书信附录的诗词和“以诗词代信”的篇目而言,书信不过是一个壳、一个载体,作者附录的诗词和“以诗词代信”的篇目,本来就为的是单独抄示、披露给收信方,故而可将其作为诗词稿入集。如《哀范君三章》最初发表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诗后有致周作人短笺,此诗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
最后,须酌情摘录夹在书信正文中的诗词。夹在书信中正文中的诗词,哪些可以单独成篇摘出,哪些不可以?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凡是具有完整、独立审美意象、审美表达和审美价值的诗词,可以摘录出来单独成篇。如,鲁迅题赠许寿裳的《自题小像》《答客诮》及其他数首旧体诗。如果只是为特定情节的发展、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以诗词形式、诗词语言所作的描写、叙述、咏叹,或者诗词本身无法脱离书信中介绍性、解释性的文字,则不宜摘录出来单独成篇。如,1941年3月18日、6月7日老舍致吴组缃信中“求对”的人名诗[30],若是单独摘出入集,就会失去上下文的说明和解释,其对联式的几行人名诗,无头无尾,让人难解。
第二,书信所含诗词在发表或入集过程中的修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又一种情况。
此类修改包含两种需要区分的情况:一是文字、诗句的改动,一是诗体的改动。诗体的改动,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旧体诗改写或活剥为新诗,如徐志摩把李清照的词改写成白话新诗,鲁迅活剥张衡《四愁诗》为“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二是旧体诗体式改变,如从绝句改作律诗。文字、诗句的改动,是诗词文本的局部调整、变更,而诗体的改动,属于一种新的创作,是诗词文本根本性的变异。这样,我们对于书信所含诗词的入集,就可以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凡是部分文字、诗句的改动,应视为该诗作的异文本,一般不宜摘录出来入集;凡是诗体的改动,应视为单独成篇的诗作,可以摘录出来入集。譬如:为编辑《集外集》,鲁迅从日记里抄写《题三义塔》等6首诗,以书信形式转交杨霁云,且对其中个别字词做了改动,形成不同于“日记版”的“书信版”。对此,在校勘时对异文出校即可,不必另外摘出来入集。原《集外集拾遗》中多首诗作,收入《鲁迅全集》时标题做了改动,有一些改动甚至很明显,比如把《无题三首》这一题目下的三首诗列出来,分别加标题,因而将其单独成篇入集是合适的。
书信所含诗词在入集过程中引致的文本状态变化,迄今尚未有人提出。考虑到这种文本状态变化,存在于几乎所有现代作家书信的入集过程,确实有必要予以简要讨论。在入集以前,书信及所含诗词被传递给收信方,由收信方本人或亲属保存,不能也不会发生改变,它们在私人空间保持相对稳定,处于文本稳定状态。一旦被收集起来编辑整理,就进入文本汇集状态。最后,通过结集发表出版,形成文本凝定。换言之,书信及所含诗词的入集,其实是一个文本凝定过程,它“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31]。只有结束文本稳定状态、进入文本汇集状态,书信及所含诗词才可能实现由“私”转“公”。文本稳定是书信及所含诗词作为交际方式的性质使然,文本汇集则是作家社会影响、编辑出版者的刊印能力、读者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使然,不应混为一谈。书信及所含诗词的文本汇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书信集或诗词集的形式出版,此时“文本的选录重在体现编者的思想及诉求”;另一种是编入全集,这是以“全录式文献集成”为本位的编纂行为。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私人空间原已稳定的书信及所含诗词文本,进入文本汇集的新阶段,发表出版后,在公共空间实现文本凝定。从此,它们以文献而非文本的面貌,不仅在观念史层面上,也在阅读史层面上,参与现代作家形象和文学经典的建构。
余论
中国现代作家书信被编入文集、全集,实为“以私人之名,行共享之实”,展现了私密文本转向公共文本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影响或重要意义,在于重塑现代作家形象。我们需要了解作家的全貌,但文学史展现的只是依据作家主要作品构建的作家形象。比如鲁迅,他被文学史塑造成面目严峻、横眉冷对的斗士。私人书信由于直面现象直接表达观点而随心随性,因此书信里的鲁迅,感性、风趣、可爱。一旦私人书信编入文集、全集,发生变异,成为公共文本,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后,被整合到文学史真相和细节的叙述之中,使作家形象更为丰富和复杂,有的甚至影响作家形象塑造。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具有重写文学史的意义。有鉴于此,大量发掘、整理出版现代作家书信,在学术界受到文学研究者普遍赞同和期待。然而,在社会层面,作家书信尤其原信的披露和出版,往往要面对侵权处罚和道德谴责。2013年夏北京某拍卖公司未经杨绛同意,拍卖并公布“钱锺书书信手稿”,“杨绛很受伤”,有媒体质问:“拍卖书信还是拍卖伦理?”[32]杨绛控告收信人和拍卖公司侵犯著作权和隐私权,最后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20万元并赔礼道歉。通过这起案件的判决可知,即使书信原件所有权人也不能侵犯写信人的著作权、隐私权、发表权、接触权、追续权。但所有权人享有合理处理书信原件的权利,如出售、赠与。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分离,导致此权利二分法。如何区分界定著作权人、所有权人的权利和义务,争议颇多,有待深入探讨。现代作家书信由“私”转“公”,所涉及的侵权问题的复杂性,远非普通文学作品可比。即使不存在侵权问题,也要符合社会道德标准。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委会曾为要不要收入《两地书》原信犹豫不决。有人赞同,有人明确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两地书》原信属于隐私,原作者不愿披露全貌,才在公开出版前做了修订。如果公开出版,是否有违作者生前意愿?”[33]2013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录张爱玲103封信件。这些信件涉及张爱玲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对此,有许多“张迷”公开表示不满,认为“张爱玲是个爱面子的人,应该尊重她的隐私,而不是过度消费”,更斥责编者夏志清的这种行为“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34]。显然,现代作家书信由“私”转“公”,还要接受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检验。由于有法律和伦理道德两方面的把关,现代作家书信结集出版、进入公共空间后,往往能产生典型示范作用,成为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道德力量。亦因此,《两地书》《爱眉小札》《海外寄霓君》等现代作家情书能够影响几代人的爱情观。而近年来电视、互联网上各种书信诵读类专题节目,也才能够跨越历史时空,传递特定的思想道德文化内涵,受到观众喜爱。
书信蕴含的道德力量,可以从其特征得以诠释。非虚构性是现代作家书信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其非虚构性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注重读者与语言行为的功能,使书信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或政治的艺术而非审美的艺术。再者,因书信特性,现代作家书信编入全集、文集,比其他文字更需要附加注释,这些注释不单是对书信文字的解释,也暗含了编者的见解和思想观念,由此在公共阅读空间对读者产生规训,即注释向读者提供规训的文本,其中大多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因此,现代作家的身份符号与书信文本,一旦由“私”转“公”,往往成为文明之体、教化之力,作为推动现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治理、政治生活以及日常活动中,构成一种毛细管式的道德文化力量。
为何现代作家书信与全集、文集编纂,会勾连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笔者认为,这主要缘于现代书信保留了诸多中国古代书信的特性。在古代中国,书信是文或文章的一种体类。古代的书、尺牍、简、函等,不仅是信息传递与人际沟通的途径,也是一种社会教化的手段。虽然“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粗疏地代替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西方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及与此相应的文学观、文学思潮,把中国文学套入了“西装马甲”中,但是现代书信却异乎寻常地从格式到常用语,都保留古代书信风格特色,有的(如公函)甚至除内容之外,与古代书信无异。现代作家书信于是具有新文学文体所罕见的一些价值和功能,如时序迁化、人伦规范、政治标准、情感沟通、群体认同、是非辨别等。既有感性的私情,也有理性的大义;既涉及上层,也关联下层;既有人事,也有超人事。因此,现代作家书信一旦入集,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或者从公共空间隐退到私人空间,难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生活的点点滴滴,总能勾连出相关人际关系。
注释:
[1]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第34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2]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参见《〈周作人书信〉序信》,《苦雨斋文丛·周作人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第25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陶沙:《鲁迅书信中若干“骂人”的土话》,《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2期。
[5]《270102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鲁迅:《序言》,鲁迅、景宋《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第1页,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
[7]《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256页。
[8]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28—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35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9]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第106—10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5 页。
[11]有的学者指出,仅鲁迅参与的联名宣言,就至少有四种情形:同一宣言文本的不同版本中署名顺序有异;宣言起草人并非最末一位签名者;集体署名的宣言乃由二人起草者;实际起草而未署名者。(陈子善:《现代作家的联名宣言》,《文汇报》2019 年 7 月 15 日。)
[12]王锡荣:《从〈鲁迅全集〉的注释看中国80年代文艺(上)》,《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第4期。
[13]“初版本”指鲁迅、景宋著《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版,以下“《两地书》”均指此版本。
[14]详见韩雪松:《〈两地书〉原信与初版本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6月,第51—154页。[15][33]陈漱渝:《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鲁迅全集〉——我参与修订“书信卷”的情况与感言(上》,《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第2期。
[16]倪墨炎:《论〈两地书〉的成书与出版》,《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
[17]易彬:《现代作家全集的文献收录问题献疑两例》,《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
[18]周海婴、周令飞:《鲁迅是谁?》,第148页,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19]新闻出版署政策法规司编:《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二五”普法读本》,第159页、第1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张小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与〈两地书〉》,《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11期。
[21]李歌:《简说三种鲁迅“全集”的缺憾与失误》,《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第10 版。
[22]《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京报》1925年5月27日。
[23]葛涛:《编辑全集应该重视作家纪念馆的藏品——以鲁迅博物馆所藏现代作家书信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
[24]相关实例可参见龚明德《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中华书局2013年版)。
[25]刘勇、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
[26]将中国现代经典作家定义为“透明人”,由作家本人及亲属、研究者和大众读者共同完成。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坦言:“在中国现代,鲁迅已成为公认的最为透明、最无隐私的作家。”(陈漱渝:《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鲁迅全集〉——我参与修订“书信卷”的情况与感言(上》)。周海婴在公布《两地书》原信时曾经说明,许广平不止一次对他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保管人员说过“我的信件,可以在我死后发表。”周海婴甚至感觉到公布《两地书》原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我感到,今天再不实现母亲的遗愿发表这些书信的原稿,将是对研究者和读者大众的一种欠债了。”(周海婴:《书后说明》,《两地书全编》,第65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7]袁盛勇以《两地书》为例,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
[28]王贺:《“非单一作者文献”与全集编纂——从〈两地书〉与〈鲁迅全集〉之关系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2期。
[29][30]参见方锡德:《老舍、吴组缃与“抗战人名诗”——老舍致吴组缃七封信考释,兼谈人名诗的唱和》,《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
[31]叶日华:《明代: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32]何映宇:《解析名人书信拍卖:满足大众窥探私生活欲望》,《新民周刊》2013年5月30日。
[34]李晓璐、陈庆辉:《张爱玲信件出版引热议作家隐私该不该公开出版?》,《广州日报》2013年4月24日。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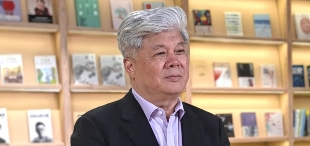
聂震宁:带着三本书去北京
我的第一个书房,应该说是初中时期的图书馆。我也曾在长篇小说《书生行》里重点描述过,学校图书馆对我而言,可说是恩深似海。
 更多
更多

张守仁:独有慧心分品格 不随俗眼看文章
“张守仁老师去世后,我家座机再没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