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形象打通事物的 外在生命与内在生命 《伯爵猫》的掘发与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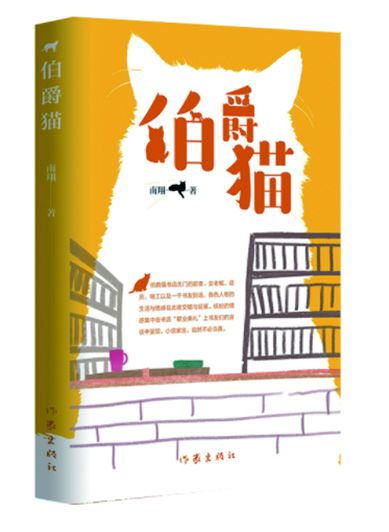
南翔是一位执迷于日常观察,像画家一样注重视觉形象的小说家。小说家获取写作灵感的路径很多,有时埋首书斋博览群书汲取营养,有时需要主动采风收集灵感,有时源自生活的被动刺激。切近观察南翔的创作生活,会发现他是一位富有现实生活热情的作家,经常主动外出采风,接受新事物新生活的视觉刺激和审美体验。笔者得益于平日对他的切近观察,对他小说的创作机制略知一二。小说体裁的特殊性,在于可以随意遮蔽作家的现实身份,自由自在地表述。作家成了皮影戏表演者,躲在幕布之后操控,让影子说话,并且赋予影子以生命。如果仔细揣摩的话,还是可以寻得作家身份的蛛丝马迹。若与作家本人有切近了解,更有助于理解小说文本中的奥义。
在《伯爵猫》这本短篇小说精选集里,伯爵猫、乌鸦、果蝠、玄凤、珊瑚裸尾鼠、车前草等动植物,无疑都具有象征属性,成为小说视觉叙事话语的核心。
除了象征,小说中的场景描写也旨在传达视觉形象,南翔正是场景描写的高手,小说讲究画面感与舞台效果。之前的短篇小说《绿皮车》精心勾勒车厢场景,反映世道人心,如今的短篇小说《伯爵猫》细描精绘了城市角落小书店的动人画面,折射都市众生。《伯爵猫》有他小说的一贯特点,也有一些新的掘进,比如对都市爱情的探索。
爱情,可以说是一种至死方休的对生的赞许,是小说叙事永恒的追求。伯爵猫书店的书友们、女老板、店员、维修工等人物,也都或明或暗地遭遇了一些情事。女老板娟姐的神秘情人,生活在他城却从未出场,谜团一样回荡在书友们的言谈中,还有她与律师之间难以言传、无疾而终的情愫;一对职场男女在伯爵猫书店结缘,很快发展成情侣,过上了二人生活,不再来书店,似乎书店已经完成了使命;店员阿芳与在娱乐城上班的阿元,他们的爱情也面临着困境,阿芳担心阿元受到夜场风气的熏染而变坏;修理书店招牌灯箱的中年电工,言辞之间透露出是一位在城市里吃喝嫖赌洒脱不羁的主。这些爱情集中在书店“歇业典礼”上书友们的言谈中加以呈现。小说中书友们讲述的情事,是在虚构文本中的另一重虚构,书店情事便产生了一种影影绰绰真真假假的艺术效果,拓宽了想象的空间。
鲜明的现代知识分子文人趣味
1.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式的传神语言。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象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从《伯爵猫》更能看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对南翔小说的影响。比如小说开篇:“今年的冬天有点冷……阿芳从春潮鞋店出来……不到七点,天就黑尽了……” 稍微对文字敏感一些,就不难感受出其中古典白话小说的味道。当然,这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文学趣味。南翔从不掩饰自己对白先勇、汪曾祺等小说家的偏爱,而这些作家的古典白话小说式的语言,势必深深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
言为心声,语言是文学的形式和载体,是一位作家整体文化素养的表现,也是审美趣味的反映。在短篇小说《珊瑚裸尾鼠》中,“肖家父子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只要是父亲的语录,不管中听不中听,儿子一律照单全收。但凡建言来自母亲,即使包了糖衣、裹了缎带、镶了金边,那小子也不会痛痛快快、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典型的南翔式语言,简练、自然、畅快,带着醇厚的学者书卷气。
南翔小说的语言特质在短篇小说《乌鸦》中也十分明显。虽然作家本人在序中说,《乌鸦》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篇幅最短,却写了一段长长的历史,但笔者认为,历史仅仅是该小说诸多向度中的一个,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这篇最短的小说却是作家“三个打通”(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文学理念熔铸得最好的小说,也是作家“三大信息量”(丰盈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美学理念得以集中体现的小说。篇幅虽短,包蕴丰富,精粹而现其高深,偶得而见其魂魄。
“少年关进来的头几天,情绪不佳,却也只会哭泣。少年哭泣是无声的,坐在木板床上,双脚收拢,两臂环抱,头有一半是埋在臂弯里的。”小说开篇即是一幅中国古典写意画,古典气韵贯穿始终。看守觉得他是倒霉蛋,“就像他每天上下班必经一段蒿草垂头的小径,有时是采一串蛇莓,有时是摘一两颗金樱子,捋去毛刺,丢进嘴里嚼出浆汁来,再噗嗤一口唾得远远的。只是再后来,他得知少年所犯之事,不仅不大,且根本只是怀疑,当无法破解便拿他是问,原因是他有一对同样倒霉的父母。这样串在一起就合乎自然,如同他采摘的蛇莓,要么一串都很甜爽,要么一串都很酸涩……”以路边随手采摘的一串蛇莓隐喻“株连九族”,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就近譬喻,浑融一体。
2.抵达人性深处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书写。
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中的小说主人公多是现代都市知识分子。《玄凤》中的壮年夫妻祥龙和少春,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是典型的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小说中的“大张”,虽有家庭与子女,却“满世界旅游、摄影,养猫养狗养鸟”,过着“人生玩家”式的逍遥生活。每个人物都并非作家本人意识的简单投射或作家本人的传声筒,而是拥有独立的声音与生命,有着各自独特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这便是南翔短篇小说叙事现代性的表征。当然,限于短篇小说文体的特点,人物的心理演变与腾挪的空间有限,但已经表现出某些复调特质。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具有主体性的人物,奏响了都市生活的大合唱。就《玄凤》来看,丁克夫妻和大张都并非作家本人的生活状态,甚至不是作家的生活理想。作家放任主人公做出自己的生活选择,而不刻意干涉。
无论是《玄凤》中养鹦鹉的丁克夫妻,还是《珊瑚裸尾鼠》中在阳台上养过诸多动物的肖家父子,小说对其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家庭日常生活呈现,并伴有微妙且深入的生活感受。比如曹老师看到自家阳台上的兔子和刺猬,“痒!一股细如丝线游走如蛇的瘙痒,从大腿蜿蜒上升,很快穿过了腰肌、肚腹,向四周扩散。有那么片刻,曹老师像被电击一般僵直笔立,她想体会那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是大脑幻觉还是身临其境?”作家敏锐地抓住了中年女性“痒”这一鲜明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感受,将对家庭日常生活的表现推向人性深处。
3.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和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与当今世界生态意识是相通的。南翔的诸多小说,则充分体现了这种生态伦理和生态意识。
在短篇小说《珊瑚裸尾鼠》中,从把家居阳台变成动物园,到不远万里前往布兰布尔礁拜祭珊瑚裸尾鼠,小说人物处处展现现代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趣味和生态关怀。以中国传统的祭祀方式拜祭澳大利亚官方宣布灭绝的哺乳动物珊瑚裸尾鼠,这种貌似不伦不类的举动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站在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来看,自然不是用来征服的,而是用来和谐相处的。
南翔的这篇小说堪称生态小说的佳作,在描写日常的同时,重申了文学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功能。关注物种的灭绝,是一种跨物种的终极关怀,也是关注人类自身,毕竟,人类释放出的恶魔终将回归到人群中去。欧美文学和影视作品素有隐喻 “世界末日”的传统,这背后其实蕴含着对人类未来的种种忧虑和人类去往何方的探索。近十年来南翔就发表过一系列生态题材小说或与生态相关的作品,例如《最后一条蝠鲼》《哭泣的白鹳》《老桂家的鱼》等,当然也包括这篇《珊瑚裸尾鼠》。
生态小说看似寻常,实则难以驾驭,非行家里手不能运筹帷幄,一不小心写作意图便压倒了艺术表达,沦落为广告呼吁式的宣传文本。《珊瑚裸尾鼠》深深扎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土壤,以谜底渐渐揭开的方式抽丝剥茧,带出澳洲之行和珊瑚裸尾鼠,可谓自然巧妙。
在笔者的印象里,南翔的小说,要么塑造人物钩沉历史,要么虚构地点寄托往事,很少以自己寄身的城市深圳为小说背景。新书《伯爵猫》却收录了多篇地道的深圳背景小说,人物也呈现出鲜明的深圳特质。这似乎昭示着,作家开始在写实和虚构之间,在过去与当下、本城与彼岸、理想与世俗之间,寻找到了新的平衡点。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可谓他近五六年短篇创作的集大成者。作家运用古雅的语言,打通事物的外在生命和内在生命,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生态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这标志着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