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经验与巴金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城市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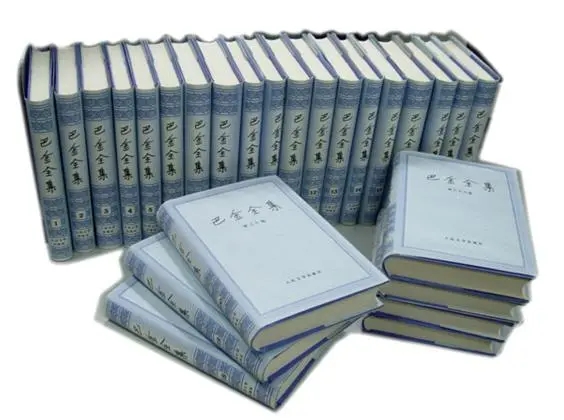
《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摘要: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是一部描写家庭的小说,可高公馆本身却是城市的生活景观。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城市的现代性与家的守旧落后二元对立,可事实上,作为包容家的容器,巴金所写的城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它有着极强的地方经验和独有的生存方式,而通过对于成都生活模式的考察,不仅能够让我们以此窥探城市居民生活理念的变化,同样亦能够发掘出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巴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关键词:风景 底层 鸣凤之死 《娱闲录》 成都模式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描写的是成都高公馆的故事,这座公馆虽坐落于成都,可小说里的“成都”感并不重,巴金所写的高家更像是全中国所有家庭的缩影。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研究《激流三部曲》也多是从高家本身出发,可却忽视了“家”之外的承载空间,即城市的意义。作为家之外的更大的社会集合体,小说中高公馆里所发生的事情,诸如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兄弟姐妹的求学,公园里的聚会,这些内容都与成都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打麻将”、“茶棚喝茶”这些极具成都特色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多出现在小说中。司昆仑所著的《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更是以巴金的小说去比对成都的发展演进史,可见小说中潜藏着亟待挖掘的“城市记忆”。某种意义上说,成都不同于北京、上海的城市特色,它自有的风情和生活逻辑孕育了独有的“风景”与“意识”,丰富了现代城市书写的文学谱系。
一、被发现的“风景”与底层世界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风景”有许多现代作家都有相当细致的描写,茅盾在写《子夜》时毫不吝啬地将笔墨聚焦于声光电影的上海,捕捉异质空间的都市文化。在《子夜》的开篇,茅盾就进行了一场上海的“风景特写”,苏州河的污水,黄浦江的码头,外滩公园的音乐,外白渡桥,以及电车、洋栈等等,这些景物如“庞大的堆积物”铺展到读者面前,几笔便勾勒出上海的新奇感和现代性。可在巴金的家族小说中,我们却见不到这些特写式的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风景”,景物描写基本都围绕着故事里的人展开,甚至几乎没有直接的城市风景描写。在电影艺术中有一个说法,当我们将流动的电影作平面图片来观看,则需要“景深”来帮助表现画面空间的“体积”和“层次”。诸如茅盾关于上海及吴公馆一家的描写方式,它更类似于电影中场景与场景,画面与画面的转接和调换。可巴金的写法则不同,它的画面是多层次的,展现方式多取的是“长镜头”或“大景深”的镜头,通过场面调度表现不同“景深”之间边缘与地位的差别。在《家》中,开篇的写法像是被拉长的镜头,先是在雪路上走着的行人,而后镜头不变,觉慧和觉民从人群中走来,以二人的游走展开叙事。无独有偶,后来当巴金写到成都的少城公园,他几乎也没有把太多的笔墨花费在景物描写上,而是直接对焦在公园集会的青年人身上,将公园的背景彻底虚化,只借觉慧的心理变化,给我们诉说公园的意义,说它是一个“新的天地”。
事实上,巴金写风景不过都是在写人,或准确地说他写的是被人“发现”的风景。在小说中,故事的开篇和结尾都是流动着的人,人作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和行动主体,看到了“风景”。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曾谈到“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1]对这些“社会观察者”而言,他们“发现”的风景与他们的心境联系在一起,是心灵的“镜像”。《家》中不断强调觉慧是人道主义者,所以他看到的行人是苦行的路人,是艰难生活的轿夫,巴金借这些“游荡的人”描写了成都市内一个个鲜活的市民,他们是在“公馆”中与觉慧、觉民共同居住的“家人”,亦是道路上和他们同行的“路人”,或者是那些学校里的同学,公园里碰到的“游玩”、“集会”的人。“公馆”、“道路”、“学校”、“公园”这些日常生活景观本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在巴金笔下,这些“风景”只因人才变得鲜活和有意识,在巴金的“风景”构图中,城市空间是认识人的“装置”,而人也是认识“城市”的“装置”,这是画面“重叠”的效果。而不仅是《激流三部曲》,其实巴金写了许多“游荡的人”,诸如觉慧、黎先生、汪文宣都曾在成都、重庆间游走,这类漫游者可能和本雅明所提出的“都市漫游者”的概念有些许出入,他们不再是“有闲”,“有产”的都市绅士,通过“漫游”的形式发现都市的绚烂与奇异。对于巴金笔下的这些漫游者,他们所发现的街头场景不过是生活场景的复现。某种意义上,这些街头游荡的人也在进行着一种“城市表达”。他们所发现的“风景”,组合成了巴金家族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借助于这些或苦闷或意气的游荡者,巴金所勾勒出的“城市面影”既不是迷醉的风光与变换的色彩,重点突出人面对巨大的都市文明时的惶恐与堕落,以及现代都市对人的异化和精神的折磨,也没有一味地将城市转变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实质上却是“乡村化的居住地”。[2]他所写的“城”,是“家”之外的生存空间,在那里不仅有倾向于乡村化的小市民,也有着不同职业、不同审美,不同代际的各色人等,他聚焦的那些都市边缘的“漫游者”,也并非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浮光掠影,而是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者。而那些“游荡的人”从“记忆中出现的生命活动与特殊的生命的沉思”,[3]也不只是从都市这一层空间中生发,这些人对都市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围绕着城市中的“家”生长起来,以“家”为基点,在家与家外间开展生命活动,进而产生“城市经验”。其实,这样的写作逻辑和以“城市”为标杆的文化想象或者是被发现的风景,其本质要与“家”对标而视。例如被觉慧视为“新的天地”的少城公园之“新”不在于其“西化”的装潢,少城公园里仍旧是茶棚林立,人流攒动,它的“新”在于同学茶棚集会中所形成的与“家”不同的“新”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家”是城市里独属于“中国”的 、“本土化”的伦理经验,而走出“家”在城市游荡的人所发现的城市风景,是在中国式的本土经验中所滋长的集体的文化想象。不同于那些被浮华的城市所挑起的性欲的压抑与情绪的难解,巴金所写的“城市”是一座极具烟火气、中国性的生活之城。城市叙事嵌套着家族叙述的视野和逻辑,其本身就包含了更为复杂的,既同质又对立,既接受又憧憬,也抵触也反思,还不得不依赖的多样情绪。
鲁迅曾提到过“侨寓文学”的说法,在他看来“侨寓”多指作者自己,即那些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因为无法回到曾经的“故乡”,不得已在作品中隐现着“乡愁”。鲁迅用“侨寓文学”来解释“乡土文学”,用一种“间隔”的眼光来审视已经远去的“故乡”和以“乡愁”为标志的情绪。事实上,“侨寓文学”的产生伴随着地缘间的地理迁移,是由田园乡村向现代城市“移民”后所产生的特有的文学种类。作为城市的“侨民”,“寄寓”在城市中,对遥远的故乡进行怀念、反思,产生审美,追寻精神上的“原乡”,以慰藉“身”未能至,“乡”未能回的遗憾。虽然巴金与鲁迅一样都远离家乡飘散于外,可来自成都的巴金他所裹挟的“乡愁”却并非指向“乡土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家族意义”上的“成都”。巴金小说中的人是正在适应城市化,或者完全城市化的人,他们并没有对曾远离的“乡土”产生太多的眷恋,在那些游荡的人的眼里,眷恋、期望、矛盾、冲突的来源不是“故乡”与寄居的“城市”,即原始田园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对抗,而是来自于现代文明内部的,“家”与“城”的对峙。某种程度上,为了制造这层冲突,“家”被巴金赋予了很多现代文明中的诸如拜金主义、滥情主义等“反面”色彩,以及残留了旧有的“威权主义”,而“城市”则被巴金以更为鲜活的、明朗的、积极的“现代视野”来形容,形成了特有的“家里”、“家外”的内外之冲。
可是,任何事物都非绝对的二元对立,纵使是巴金倾泻了许多个体情感,控诉着家族不合理制度的《激流三部曲》,其中的“家”与“城”都非完全的对立,“城”中的晦涩与阴暗也被巴金留在了小说中,城市中生活的艰辛,底层人民的不幸,林林种种,都借助于觉慧和觉民这些“游荡的人”的“观察”给揭露了出来。巴金写的“城”不是新感觉派的“片段”的、“浓缩”的城市体验,集中表现城市的“一景”、“一类人”,他笔下的“城”是铺展开的,多维度、多层次的,而非“折叠”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巴金并没有过多地向我们展示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体验,在这些多阶层、多类型的描写中,“游荡的人”是叙述的主体,在所有描写中最具权威性,既是故事的体验者,亦是外围的叙述者,对城市进行多维透视。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借助觉慧、觉民这些游荡的人,巴金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底层世界”。司昆仑考证说,在巴金生活的青年时代,“监管成都的人试图限制成都城区内部及与周边农村间的人口流动”[4],尤其是在杨森接管后,管控更为严格,[5]对于这些底层生活的人,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办法走出成都,成都鲜活的城市体验自然影响了他们的思维,为他们带来了一套“成都模式”的生活理念。
二、底层女性的城市突围与世俗的现代性
在《家》中鸣凤是着墨较多的一位底层少女,作为故事中从未走出成都的女性角色,她并没有如同那些接受新知的男性一样,积极地参与到以北京、上海等地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震荡中,始终未能走出四川的她,并没有成为这些接受新知的男性的启蒙对象,反而与这些以北京、上海为想象模式的青年男性们形成了交锋。在“鸣凤之死”的章节中,巴金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描写鸣凤的心理活动。在鸣凤的心里,她从人的自然生理年龄将其划定为“少女”,而非从“社会结构”中定性为“仆人”,而后她想获得被爱的权力,可她觉察到觉慧的爱无法拯救她,“反而给她添了一些痛苦的回忆”。[6]于是,鸣凤完成了对觉慧英雄主义的祛魅,为爱弃己身殉的心有所波动。那到底鸣凤爱什么?文中写她“爱生活,爱一切,可是生活的门面面地关住了她,只给她留下那一条堕落的路”。但鸣凤决不允许将她的身子投到那条堕落的路上,故而她“痛惜地、爱怜地摩抚着它”。[7]她在认识自己的身体,并找了一面晶莹清澈的湖水,将其选为寄身的地方。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是从智识精英女性的视角来剖析鸣凤与觉慧的恋爱。相较于觉慧人格中表现的“现代性”,鸣凤终究是“奴性在心”的小丫头,非琴那样的现代女性,而鸣凤与觉慧的恋爱则“恰恰体现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金的多重潜意识,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性的性别权力关系。”[8]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在鸣凤与觉慧的恋爱关系中,觉慧占据主导地位,鸣凤最后也甘愿为情献身,以死来成全这段爱情神话。换言之,鸣凤和觉慧都被包裹在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向外辐射的西方现代性叙事的逻辑内,面对鸣凤,接受了北京、上海等地新思想的觉慧是启蒙者,而鸣凤是留在成都的落后的待启蒙的女性。可这样的论断却似乎忽视了鸣凤本人的心声,陷入了以“觉慧”为中心的判断中,遮蔽了爱情另外一方的付出与挣扎。纵观巴金所写的“鸣凤之死”的段落,经历了复杂心理活动的鸣凤,她所要“殉”的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道德伦理”,也不是觉慧的“情”,而是为了作为“人”的鸣凤而殉。她并非为了封建道德伦理保住贞操,在决定跳湖时也清楚认识到觉慧的爱和她爱着的一切,她拒绝堕落,只是拒绝顺从权力,拒绝在权力压迫中自我规训。她抚摸自己的身体,则是在感受“肉身”。“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于身体之上”,[9]对于身体的发现是抗拒同一性的表现。她在临死前感受了自身的生命结构,摆脱了“陈旧的灵魂”,发现了“身体”这一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0]并找到了自然世界的一面湖水,建构了“肉身主体”与“自然世界”的桥梁,选择以“死亡”反抗其该有的“命数”,肯定其应有的生存价值和尊严。当她喊出“觉慧”的名字时,她的“弃己”和“受难”不是为了“变形的爱情”,也不是为了“抵达生命的制高点”,“由此可获得平凡的幸福所无法提供的情感上的极大欢愉”,[11]而是为了证明自我存在的合法性。某种意义上,虽然鸣凤将要形成的“自然天性”依然搅在她与觉慧身份之别的社会问题中,不过与传统意义上五四时期“恋爱至上”的口号不同,觉慧只是充当了“救难者”,而非鸣凤情痴的“投射者”,她不是在觉慧的身上“发现自己的生命和最高意识”,[12]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滋生。觉慧的“救”在于帮她实现梦景——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少女一样笑谈、享乐。
其实鸣凤的想法有迹可循,巴金在开篇便写了她的梦。而在她临死之际,这样的梦更为清晰了,鸣凤滋长了“人”的意识,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憧憬。与黄妈、张嫂这些从乡下进城的老一辈人欲望不同,近代成都的商业性与高公馆内的生活刺激了鸣凤产生新的欲望,使她不仅可以直视自己的生理变化,亦能够体察直面内心的渴望,完成对预定归宿的反抗。其实鸣凤阶层递升之梦与阿Q的土谷祠之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超越了土谷饲之梦。巴金所写的鸣凤不再安于原有的生活秩序,有了与生活切身相关的欲望,但又打破了阿Q式的权力的倾轧与制造,具有了人性平等的意识,她渴望到处是那样的乐园,有着无尽的欢笑。鸣凤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尺的五四新文化视域之外的另一种形象,即那些来自底层民众实现生活理想的本能求生欲。由于成都特殊的管理制度,鸣凤这样的小丫头不能逃出去,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抗争”和“叛逃”,可她滋长出的人的意识却并非由“觉慧”启蒙,我们自然也无法将其纳入到以“觉慧”为中心的爱情关系中,当然也无法将鸣凤的觉醒与北京、上海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牵扯上太多的联系。其实何止是鸣凤,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很多底层女性虽然行为上在“逃婚”、在“离家”,但终其实质,这些叛逃不过都是为了“生存”。直至40年代,还有北平生活的李杨氏抛离丈夫,逃离出家,与她的邻居刘福来去外地开启新生活。当然,这并不仅仅只因为与“西洋文化与制度的比较之后”,与一个不相识的异性结婚,消极共度一生,已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了”,[13]对于生活在北平底层的李杨氏来说,她对启蒙、革命等宏大的名词一无所知,她与邻居逃离更多地是为了获得好生活,相较于她原来的丈夫,邻居刘福来更能够为她带来幸福。而这样的判断不过是依据日常经验中的趋利避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和对困顿生活本能的抗拒。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意识和身份表述被推出历史地表,被包办婚姻、伦理道德困扰的女性的生存隐忧映射了整个社会全体人的生存困境,女性解放成为人性解放的题中之意,女性这一群体也似乎被裹挟在了西方现代性的叙事中。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在未能到达北京、上海等“都市”,未曾了解“西洋文化或制度”,或者在智识界的争论之外,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还有着无数个被新文化公共舆论所遮蔽的女性。类似于鸣凤与李杨氏这样的女性,她们虽然没有与中心的文化震荡产生较多关联,可却属于各自生活区域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早在1909年,成都便建成了连拱廊商业场,少城公园也在1910年落成,在高家中就连高老太爷也都习惯于逛百货商场,消费意识在近代成都逐渐蔓延。城市对商业的欢迎自然也改变了市民的生活结构。在民间商品消费文化的作用下,鸣凤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形成了以“物”为代表的想象,“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她更注重的是“华丽的外观”和“展示性景观”。[14]由于鸣凤所在的高家是成都北门首富,9岁便来此的鸣凤,在吃穿用度上自然有了参照标本,滋生出以享乐、消费为诉求的人生理想不足为奇。至于李杨氏的逃走,有学者称她这样的行为既不能像古代社会那样“作为违背伦常的行为而施以严刑”,也无法纳入“女性自由的进步话语”,“于是只能尴尬地停留在司法实践与公共舆论的幽暗处”。[15]实际上,这种“边缘”和“幽暗”的判断取决于我们惯常依赖的以西化进步叙事为依据的价值标准,但若是我们打破这种惯常的观念,而从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或边缘、或幽暗的现象之于中心点的文化震荡而言,则是很好的补充。事实上,关于“现代性”的表述是多样的,它不仅只有西方学理的传入与接受此一种路径,在未曾有过接受行为的社群中依然自发形成了以“求生意志”为代表的平民精神[16]和中国式的“世俗的现代性”,鸣凤的以“死”相抗,李杨氏的“逃”均如是。它们在行动上或思想上与启蒙现代性无意识地完成了接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的研究视野形成了张力。可以说,面对着广阔的世俗社会,鸣凤、李杨氏乃至觉慧都不能想当然地言其“新”、“旧”,尤其是在情感关系中,“启蒙”、“革命”等宏大的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某种意义上,生活在城市的鸣凤已经具有了世俗意义上的现代市民意识,摆脱了传统乡村生活的理念和方式,日常生活赋予了她较强的生存欲望和求生能力。甚至在鸣凤与觉慧的爱情交锋中,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始终绞缠在一起,纵使是浸润了新文化的觉慧也接受鸣凤通过“寻父”来完成阶层递升。
三、成都模式与双面“成都”
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形态,世俗现代性的形成与近现代成都市的生活风气有直接联系,换言之,成都市中特有的日常物质文化生活不仅锻造着它的风貌,也具体影响着它在文学中的呈现和表述。于成都而言,1903年便有警察巡逻,与此同时,还建造了公共的商场让过去沿街叫卖的蔬菜商贩集中营业。[17]这些管控措施都影响了高家人的生活,觉慧、觉民走在长长的公馆街上,巴金用了“干净”一词来形容这条街,可见市政交通和城市面貌的整洁。而当成都被枪炮所袭,城市管理失控,蔬菜供应不足,高家人吃起饭都寡淡无味。在文化方面,近现代成都对于新文化的接受并不只是被动,经过了一系列新政改革之后,成都的文化空间极度混杂,既有相互周旋的军阀染指,又有类似五老七贤等地方保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各类群体。但政治领域的混乱亦引发了思想层面的松动,成都也自发形成了新文化、新思想的诉求。类似吴虞这样的人物,在成都既能够公开批判儒家思想,却也未曾影响他的舒适生活。[18]相较于上海的“欧风美雨”,成都有其典型性特征,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成都得以保留其传统”,“西方对成都的影响微乎其微”。[19]成都内在的日常文化具有很强的吸附性,一面自发生长着世俗的现代性,某种程度上也改良和润色了西方文化,并将西方的一些现代城市标志加以中国化的改造。当戏院、电影院传到中国时,北京、上海等地竞相开设这些西式、洋化的戏院和影院,可在成都,这些城市景观却依旧未能撼动成都固有文化模式,很多戏院往往和茶室结合,在茶棚里上演各色剧目,有旧戏,有新剧。[20]在少城公园中,到处是茶棚,成都人习惯在茶棚谈天说地,这里产生了中国式的公共舆论场域。不同位置的茶棚吸引的受众也不尽相同。觉慧也是在这样的茶棚,结识了与家庭环境迥异的新的天地,滋生了全新的认识,与他曾读到的书渐渐地融合在一起,真正从实践上、生活中感知了新文化。
在近现代的成都,以茶馆为据点的公共空间的发展甚是热闹,也是在茶棚艺术中,经常有各种说书人,说书的内容大抵是英雄、侠客,尤其是英雄叙事在成都广受欢迎,一些演讲会也时常开展。郭沫若说过他曾于1912年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听过名为《英雄与性冲动》的演说。[21]在成都的一份近代报纸《娱闲录》中也出现了不少武侠小说,这些小说将“性”的表达上升了一步,演化为“情动”,情动中不仅有个人感情,也将这份激情冲动与宏大的历史叙事勾连,统称为“侠情”。与古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不同,《娱闲录》中的“侠情”小说还多描写民间身负绝技,心怀天下的平民女英雄。例如《彩姑娘》、《义妓》等。在晚清之际,很多士大夫阶层乐于勾画“西方美人”相,在他们看来,“东西方美人之争不是比拼容貌,不是竞赛诗文,而是‘妇女救国的责任’”,为了让女性承担这样的表意功能,做一位“理想的女豪杰”,“批风抹月、沾花弄草、不商不兵、以弱为美”的具有传统东方古典美的美人们多被视作为“亡国灭种的万恶之源”。在这样的强国保种的现代诉求下,东方女杰焕发出雌雄同体的色彩,甚至在描写和论述中有意强调女性的“雄强尚武”。符杰祥说虽然在晚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多强调“东西方女杰并驾驰”,可在阐释过程中,“被赋予救国意义的‘西方美人’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22]可是在《娱闲录》中一些被赋予救国救民责任的女性侠客的身上,我们既能够看到她们“眉宇间有伟男子之度”、“性尤豪爽”的“雄性特征”,也能够找到她们“翩矫若夫飞鸿游龙”[23]以及“雪肤花貌”[24]的传统女性化的一面。这些女性英雄除暴安良,营救危难,“言情必能推强侮,而能洁身以报知己”,也可“言自由结婚”。[25]这些“侠”接受了“自由结婚”之类的五四时期的文化议题,在中国传统审美基础上自然生成了对女性力量感和“感时忧国”的追求。可以说,《娱闲录》中所写的“侠”,不仅已经有了五四时期的一些精神内核,且跳脱出了梁启超艳羡的“西方美人”的思维模式,同样是“尚武”、“救亡”、“婚姻自由”,刘觉奴、定水等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可能。
其实,自古以来,成都乃至川渝都是个充满着侠气和江湖气的地方,滋生了不少脱离秩序的任侠和豪侠,并孕育了独有的袍哥文化。司昆仑说“层级明显”、“尊崇中国传统侠义”的袍哥文化与“巴金这样的人拥护的民主观念形成对立”,[26]但事实却有待商榷。诸如巴金写觉慧,在觉慧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之前,巴金就给他冠以“侠义”。觉慧对“侠”的理解,不仅让他意识到了“力”,萌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诉求,也牵动了他情感的萌芽,纵使在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后,当他面对着爱情和工作的两难之境时,他最先找出的说辞也是颇具豪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某种程度上说,巴金借“侠”这样一个失序的英雄群体去考察恋爱、婚姻,以“性冲动”,以“情动”,甚至冠以更大的激情,这正是巴金所处的成都文化场域精心讨论、实践过的,觉慧的“现代”观念也并非空中楼阁般由西方文化强制性输入,而是在尚武、尚力,顾念天下苍生的“侠”文化的基础上一点点生长起来。甚至在写崇拜着苏菲亚的“琴”、“淑英”等新女性时,纵使巴金在巴黎时曾为女杰写过传记,可他也没有将她们完全打造为“西方的女豪杰”,巴金说她们“美丽”、“活泼”、“纯洁”、“可爱”,善作诗文,喜爱游湖,完全没有忽略她们女性化、古典化的一面。
实际上,在小说中,巴金始终无法回避自成体系的成都文娱生活。在成都的公共文化领域中,《娱闲录》作为《四川公报》的增刊,创刊于1914年,此刊从传统的小说、戏曲、艳词中汲取营养,加以新思,传播于世。办报之初,便以“惩恶劝善、匡谬正俗”为主旨,为达到宣传效果,“特假游戏为面目”,使人“乐于感受”,“而不自觉耳”。[27]这本杂志的主编是吴虞、李劼人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还未拉开新文化运动序幕时,他们几人便在四川开始鼓吹和倡导新文化了。李劼人以“老嬾”之名在《娱闲录》上发表了白话小说《儿时影》,吴虞也在此刊上发表过许多论述新文化,有反孔思想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游戏小说、纪实小说、西史小说等刊载。这个杂志以其“文化性”与“娱乐性”、“世俗性”的多面性,吸引了巴蜀地区各个年龄层的受众。某种程度上,《娱闲录》代表了近现代成都文娱生活的面影,它不同于上海的文化标识,尚处于较为混沌、多元的局面,有着未能抗拒的世俗性,也闪动着新的生命活力和需求。而此种文娱生活氛围注定了成都模式与摩登都市的不同,那些光鲜亮丽的城市坐标,高耸入云的大楼、西餐厅、咖啡馆、明星等现代性景观在小说中通通失语。巴金所写的消费与物化和对个体的凝视,都依托于成都社会特有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生活情状。可以说,“地方体验”塑造了小说中符合中国经验、成都视野的现代市民,而非西方学理层面的“市民”,律师、教师、实业公司职员等新兴职业在巴金的笔下大多是悬浮在生活之外的新鲜的“名词”,唯有他所熟悉的青年学生活动有大范围的展示。司昆仑曾说吴虞和巴金的祖父圈子里的人对《娱闲录》的热情不亚于巴金一代对《新青年》的期盼。[28]从《娱闲录》到《新青年》,巴金笔下的成都有它无法抗拒的外部输入的“现代性”,但也从未拒绝成都文化中自发生成的现代社会的到来。换而言之,巴金写了“双面成都”,即从复杂多元的世俗生活的“成都”中渐渐意识到了一个理想中的“成都”,而这样的“成都”是觉慧“侠”思想中奇异的国度,亦是后来的“上海”。某种意义上,是“成都”生产了“上海”,而非“上海”覆盖了“成都”。这也不难解释缘何巴金写不出觉慧到达上海后“群”的生活,大抵是因为“上海”也有着双面性,觉慧终究还是要面对日常起居以及市民层面的“上海”。
注释:
[1]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3页。
[2] [美]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摘要)》,邓卓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3]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1页。
[4][26][28] [美]司昆仑:《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何芳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31页,第151页,第199页,第53页。
[5][17][18][21] [美]司昆仑:《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王莹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第152页,第229页,第227页。
[6][7] 巴金:《家》,《巴金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
[8] 刘园、张宏:《现代性别权力关系的隐形书写——对巴金<家>中主仆爱情关系的分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9]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0]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2页。
[11] [美]李海燕:《心灵革命:1900-1950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12]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3页。
[13] 陈衡哲:《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
[14]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5] 康凌:《女人为什么逃婚?——马钊<逃婚妇女,都市罪犯,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读后》,《圆桌2015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16] 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9][20]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第120页。
[22] 符杰祥:《『中国苏菲亚』是怎样炼成的——秋瑾与『西方美人』的文化政治》,《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
[23] 觉奴:《彩姑娘》,《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5年第19期。
[24][25] 定水:《义妓》,《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4年第6期。
[27] 闲不得:《答某报之作戏评一者》,《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4年第4期。
- 周立民: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2022-02-07]
- 周立民:巴金与傅雷的“君子之交”[2022-01-27]
- 从巴金到冯雪峰,“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新年续讲[2022-01-05]
- 巴金小说《家》的日译本[2021-12-07]
- 巴金发绣像[2021-11-25]
-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2021-11-18]
- 一部未完成之书,见证鲁迅与巴金的友情[2021-11-12]
- 陈喜儒:《随想录》的诞生[2021-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