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出版界的一次“亲密接触”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叶新 柴晓慧 2020年08月11日07:09

王云五于1943年访英,在英国国会受到上下两院议长欢迎后致答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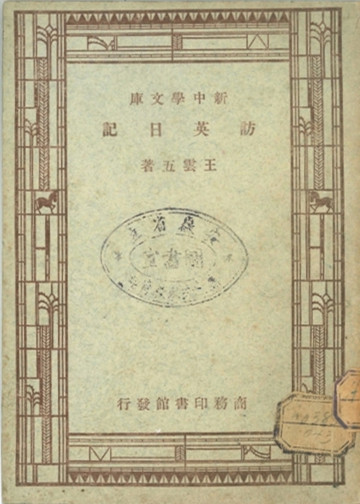
王云五著《访英日记》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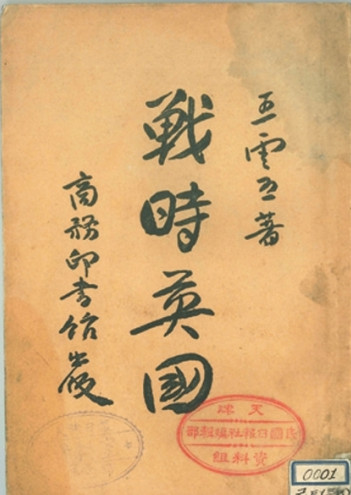
王云五著《访英日记》书影
据笔者所知,我国与英国出版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接触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做环球之游,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和出版。在英国,他拜访了英国著名的朗文、钱伯斯、纳尔逊等教育出版社,意图做其在中国的图书代理业务。第二次是1930年,新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做环球之游,拜访了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社董事长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艾伦-昂温出版社董事长斯坦利·昂温等,并与前者合作出版麦克米伦图书的中国版。第三次是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王云五以国民参政员资格,作为中国访英团的五位成员之一在英国逗留约八星期。在访英期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在履行国家公务之外也兼顾单位公务,实地拜访和参观了诸多出版社、书店和图书馆,还有报社、广播台等。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访问已经不再是走访个别的出版社或者出版人,而是上升到了中英两国出版界官方交流的层面。笔者根据王云五所著的《访英日记》等史料,对他与英国出版界的此次交往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
1943年11月18日,中国访英团一行五人由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带队,乘飞机从陪都重庆出发,12月3日到达英国首都伦敦,1944年1月28日启程回国,在英国本土逗留不足两个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王云五也与英国出版界频频接触,始终不忘自己中国出版人的身份。
1943年12月24日到27日,王云五与胡政之、温源宁三人前往访问剑桥大学。12月24日下午五点钟,王云五参观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因为整个出版社已经休假停工,只能由主事者单独导引,往各部门参观。据介绍,该出版社的主持机关是剑桥大学出版委员会,委员由大学校友推举,各委员再推选其中一人为主事者,主持日常行政,而重要出版方针和预算则由委员会决定。
1944年1月1日下午,王云五和中国政府驻英国代表叶公超一起去英国著名出版人维克多·戈兰茨(VictorGollancz)的乡下居所共度周末。戈兰茨是英国左派出版人,于1937年10月首先出版了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他对我国一向颇有好感,时任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ChinaCampaignCommittee)副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即极力主张援助中国。两人第一天谈到深夜才散,第二天还畅谈了战后和平问题。1月7日午间,王云五又赴戈兰茨组织的宴会,在座多系出版界中人,大家相互交换了意见。
二
由于此次中国访英团的规格较高,再加上王云五兼具国民参政员、商务总经理的双重身份,他自然受到了英国出版界的热烈欢迎。1944年1月18日下午,英国出版业公会(ThePublishersAssociation,即英国出版商协会)特地为王云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出席的有现任会长、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金斯福德(Regi⁃naldJohnLethbridgeKingsford)、前任会长斯坦利·昂温(StanleyUn⁃win),以及该协会理事二十余人。斯坦利·昂温是艾伦-昂温出版社(Allen&Unwin)总经理,1926年著有《出版概论》(TheTruthAboutPublishing,也译为《出版实况》)一书,该书被誉为“出版圣经”,分别由我国的书海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两个译本。
在此次欢迎会上,王云五首先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我国战时出版业艰苦奋斗的情形,以及战时出版的趋势,然后和英方人员交流意见。作为《伯尔尼公约》的创始成员国,英方则希望中国在二战结束后加入该公约,参与国际版权同盟,并希望中英签订双边版权保护协议。
对此,王云五认为,世界各国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目的是相互保护对方包括翻译权在内的版权。在欧洲各国间,一种文字的书籍翻译成他国文字之后,免不了妨碍原文书籍的销路,因此有保护版权的必要。而中文和欧洲各国文字相差太远,不是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字差异可比。在中国,一种外国文字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不仅不会阻碍原文书籍的销路,而且有利于它们在中国的流通。中国人学习欧洲文字,尤其以英文为多,但是与中文相差甚远,因此学好的不多。如果有中文译本印行,则有助于中国人对原文书籍的了解。在可能时,中国人必然会被译本的畅销引起对原文书籍的关注,因而增加原本在中国的销路。中国极少数对原文书籍比较精通的人士,则会直接去读原本,而不读译本。因此,王云五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的时机尚未成熟。
而作为中国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反过来认为,如果英国人想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书籍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他不仅不会对此生气,而且会大加鼓励。王云五举例说:在他逗留伦敦期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西门华德(WalterSimon)曾来信要求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实为《市民千字课》——笔者注)翻译成英文,并附原文对照;这超过了翻译许可的范围,但他仍然大力予以支持,并为之写序。
至于我国翻印欧洲书籍,引起欧洲各出版社不满的问题,王云五认为,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欧洲文字书籍在我国售卖价格过高,超出了一般读者的购买力的缘故。如果欧洲能在出版原文书籍的同时,再在中国出版一种廉价的版本发售,就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因为战事尚未结束,中外交通梗阻,欧洲原文书籍事实上无法运到我国销售,为供应中国人文化食粮起见,战时的翻印问题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动。等到战事结束后,欧洲各出版社如能考虑到中国读者购买力低微的问题,给能在中国大量发售的出版物专门印行中国版,廉价发售,则翻印问题就能解决了。经过王云五的解释和陈述,英方人士大多表示谅解。有出版人建议如果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不妨附加一个条件,在若干年内不受翻译权之约束。
笔者认为,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是否加入《伯尔尼公约》、保护其成员国公民的版权,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拖得越久,对中国出版业的国内发展越有利,但不利于未来我国出版业在海外的发展。实际上,中国从1908年被要求加入《伯尔尼公约》,到1992年加入该公约,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单就民国时期而言,翻译出版的外文书籍约占图书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国出版界长期享受无偿翻译西方图书的“红利”。因此,当时的王云五代表的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的利益,也代表了中国出版界的共同利益。
在这次高规格的见面会上,中英双方都表明了态度,亮出了底牌,这可以说是中英出版界之间一次良好的沟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欢迎会上,有位理事要求王云五介绍一两种关于我国现代社会状况的书籍,供其翻译成英文出版。王云五也提出想要了解英国出版业情况。过了几天,应王云五的要求,英国出版业公会会长金斯福德还特地来信告知1938年到1943年的英国书业概况。王云五认为,英国人重视统计,实在是英国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则缺乏任何统计,即便有,也是延迟多时,与英国无法比拟。
据统计,在战前的1938年,英国总计出版图书16219种,1939年减为14904种,1940年减为11053种,1941年减为7581种,1942年减为7241种,1943年减为6705种。经过计算,1943年的出书种数仅为1938年的41%。其逐年减少的原因,实际上是英国纸张消费的限制。英国大宗的新闻纸战前均来自海外,战时力从节约,由政府限制,按战前各出版社消费量的20%供给,因此出版种数不得不随之递减。英国出版业能维持到战前41%的生产水平,还是有赖于印数的紧缩和书籍排版行数的加密。
关于书籍排版行数加密这一点,非常凑巧的是,王云五在不知英国同行的做法之前也是如此操作。“七七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内迁。他就实施了一种战时的节约版式,即尽量减少空白,增加行数、字数,于是一面大小相同的书,以前只能排五百字的,改版式后可排一千字上下,增加了一倍的字数。战前出版的书籍,天头地脚的空白较多,战时重版,如未经重排的,则将天头地脚尽可能减缩,如此可减少20%的用纸。而就每本书的出版而言,则尽量减少每次的印数,增加重版的次数,不增加多余的库存,这样可减省三分之一的用纸。而此次与英国同行交流后,王云五发现双方的做法如出一辙。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英国战时出版的书籍也有比战前数量增加的种类,由此可见英国人在战时读书兴趣之所在。与战前相比数量增加的种类包括海军陆军类、航空类、农业畜牧与兽医类、银行与财政类等书籍。而与战前相比略有降低的种类是政治经济与当前问题类、地理与地图集类、社会学类等书籍。与战前相比减幅最多的类别包括人名录与指南类(仅为战前的9%)、东方学类(仅为12%)、教育用书类(仅为23%),以及游记探险考古学类和小说类(均为30%)。不过,与我国相比,英国作为老牌的出版强国,其战时出书量仍然较大,我国与之无法相比。
三
1944年1月19日下午,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创始人艾伦·莱恩(AllenLane)前来拜访王云五。他将当时企鹅出版的书籍各选一种赠送给王云五,后者则将不需要的几种书籍退还。企鹅出版的平装书系列主要为廉价发售,虽然所收入的作品多为通俗书籍,但也有一些是专门著作。艾伦·莱恩表示也愿意选择一些中国出版的当时名著,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还与一些英国学者见面,其中不乏商务印书馆所译书籍的作者。1943年12月11日,在我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的安排下,王云五与英国名作家H.G.韦尔斯(H.G.Wells)、科学家奥尔多斯·赫胥黎教授(AldousHuxley)、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和作家普里斯特利(JohnB.Priestley)等餐叙,交换意见。
1927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梁思成、向达等翻译的《世界史纲》(TheOutlineofHistory),就是H.G.韦尔斯的名著。当时韦尔斯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他学识渊博,见识公允,与其他人相比,尤其让王云五感觉闻名不如一见,对他更加敬佩。晚上10点韦尔斯与王云五告别回家,临别时盛情邀请王云五如有空,即到他家长谈,并说自己十分想写一本中国史著作,但是资料缺乏,如果王云五能够久留英国,则极其愿意与他合作。王云五虽然觉得其盛意可感,但恐时间不允许,也就没有与韦尔斯再见面。过了一两年,王云五即离开了商务印书馆,而韦尔斯也去世了,包括艾伦·莱恩和韦尔斯所提出的出版合作也就无从谈起。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与前两次相比,中英出版界的第三次接触规格更高、更具现实意义。毕竟王云五代表中国出版界在英国出版界最高的行业组织成员面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他还与斯坦利·昂温、金斯福德、艾伦·莱恩、维克多·戈兰茨这样的英国出版界重量级人物进行了接触,并与英国出版界就中英版权双边保护、出版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探讨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可能。这一次的中英出版界“亲密接触”可谓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