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德克的悲歌 ……无法被描述的黑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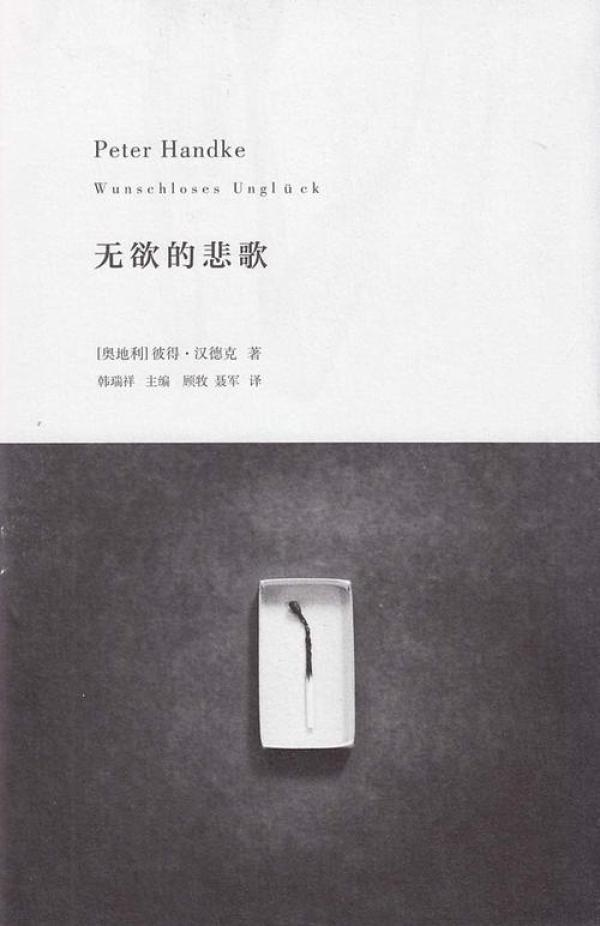
《无欲的悲歌》
去年10月诺贝尔奖颁给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之后,他在媒体上热了一阵。当时我们都不会想到在几个月之后,因为“悲歌”与那些无法被描述的黑夜,读汉德克有了真正的痛。这几天在关注疫情微信上各种日记式文本、图像的同时,读汉德克的《无欲的悲歌》(原书名 Wunschloses Unglück,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我想到的是湖北那个五六岁的小孩,爷爷死了之后一个人靠吃饼干活了下来,想到那几个昼夜对惊恐中的孩子来说会漫长成什么样子,想到没有任何人在黑夜中一援其手,令我更痛心地体会了汉德克在书中说的那句话:“黑夜是无法得到描述的。”(355页)
本书由两部小说组成,包括《无欲的悲歌》(1972年)和《大黄蜂》(1966年)。汉德克创作《无欲的悲歌》的契机是他母亲在1971年自杀,这部小说就是以一位五十一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叙述者“我”感到有必要撰写母亲一生的故事。小说叙述沿着两条路径延伸,一是讲述母亲的故事,二是对这种讲述的思考和论述,讲故事与如何讲故事交织在一起。故事讲述的是他母亲生与死的真实编年史: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守秩序和忍受命运的道德教育,阅读文学使她有能力认识自己,但她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对自我生存的压迫和毁灭,自杀成为她的必然归宿。《大黄蜂》是汉德克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促使他放弃法律专业的学习而转向文学创作。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斯拉夫克尔克小岛上(现属克罗地亚)的故事,一个盲眼的小孩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弟弟,同时在黑暗中感受煎熬。但是作者并没有好好地讲述这个故事,而是以断片式、马赛克式的方式讲述对童年处境和事物的真实感受,因“失明”而打开了记忆之门以及全身的知觉,在记忆、知觉与想象的交替、跳跃、重复中表达了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焦虑、不安和痛苦等复杂感受。
阅读史上有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阅读者与写作者在某种特殊时刻的相遇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交流和更为激烈的心灵碰撞。我想谈的是,《无欲的悲歌》中的这两篇小说在今天的阅读感受肯定不同于一个多月之前。汉德克自己对“阅读”的理解就很有启发性,他强调自己作为“孤独的读者”,阅读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伟大生活;他觉得“读者才是世界之心”。而作为写作者,汉德克一直很警惕传统戏剧、小说可能“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让观众“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灌输”。因此他的早期作品多采取反结构、反情节、反人物塑造的形式,《大黄蜂》就是例子。在后来的《无欲的悲歌》中他有意转型,对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不再一味排斥,在叙述风格上也变为平易和略感流畅,但是他通过夹叙的议论、对写作本身的苦思与诘问邀请读者参与到他的感受与思考之中。很显然,他对读者的阅读有很高的期待,他希望读者能获得个人化的、特别的阅读经验。有理由相信他期待的是读者能够沉浸在自己的生存处境中去阅读,去感受和质疑生存与社会的所有悲剧。在这样的阅读者与写作者对话的语境中,由于我们所处的阅读时刻、所感受的现实氛围,无疑使《无欲的悲歌》不再仅仅是关于母亲一生的“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大黄蜂》也不再仅仅是一堆断片似的记忆和想象——在我们当下的阅读感受中,汉德克的关键词、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情感和反抗欲望,变得无比强烈和锋利。
在汉德克的词典中,“活着”是一个很扎心的概念。我们现在更能体会的是,“无欲的悲歌”之悲还不在于母亲最后的自杀结局,而在于为了“活着”而发出的绝望心声。在母亲的一生中,家庭、社会和战争磨难无情地剥夺了她的生之乐趣,使她从一个健康的、有文学阅读兴趣的女子变为失去个性、欲望、尊严和对未来梦想的“落寞的行尸走肉”。最悲剧的是,到了最后她才发现自己虽然活着,但是“我根本就不是人了”。人这样活着与动物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同样扎心的是,“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毫无机会,一切都注定了……最后,注定的一切随着死亡而圆满。就连当地女孩儿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也是这样: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9—10页)她在写给丈夫的遗书中说,“你不会理解的”,“但是我已经不能想像继续活下去了。”(61页)因对于“活着”的认识而变得绝望与决绝(“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别无选择”——61页),在最后时刻以自杀挽救最后的尊严。在疫情肆虐的黑夜中,“活着”也成为一个关键词,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同样扎心地想到“活着”的真实状态,那究竟是欲望的还是无欲的悲歌?
汉德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同时,一直把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性作为或隐或现的观察角度,个人的“活着”状态折射的是社会的存在状态。政治是“无欲的悲歌”中无处不在的幽灵。“活着”是那么无趣和痛苦,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从未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未有过自己的尊严、从未真正活过,汉德克的“悲歌”中不但有人道精神的悲悯,更有对社会和制度的政治批判。他认为母亲的故事不会与政治无关,但是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承认、会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政治家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跟他们说话时,他们不是回答,而是表达立场。‘反正大多数事情都没法拿来讨论。’只有那些能够用来讨论的才是政治要关心的事,其他的事就得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和自己的主达成协议。如果有哪个政治家真的关心起谁,那倒会把人吓住了。那无非套近乎而已。”(48页)他极为平实地讲清楚了政治家的政治与普通人的命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想对母亲说的是,不能把政治家的“关心”当真。对他母亲来说,一生中与政治靠得最近的是在纳粹政治意识的播弄下感受到的兴奋与骄傲。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出现了新的社会景观:“群众集会以火把游行和纪念会的形式举行,大楼添上了新的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后,一个个面貌一新,和善可亲,森林和山峰也焕然一新,历史事件被当作大自然的表演展示给乡下人看。” 母亲感到兴奋,“第一次有了集体经历。就连枯燥的工作日也有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深夜’。一切迄今无法理解和陌生的东西终于都显现出一种伟大的关联:一切都相互归结为一种关系,就连那令人诧异的机械式劳动都有了意义,成为节日。每个人此刻所做出的动作都组合成一种运动的节奏,因为他在心里看到无数其他人同时在做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因此获得了一种让人既能产生安全感,同时又能感到自由的形式。”“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所有这一切使她感到一种笼统的、不确定的骄傲,感到自己学会了表达。(13—14页)汉德克很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和什么样的兴奋与骄傲。在《大黄蜂》中,他描述了一位负责在乡下执法的警察:“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这儿就交给了他,他也有意从外表来炫耀这种权力。不论走到哪里.他都穿着那双笨重而结实的皮鞋。倘若身后有不好的预感时,他肩上总披着那件厚厚的棉大衣。他把一只手放在领扣上,举起另一只手示意,就像穿着制服行国礼那样。”(92页)这可是活灵活现、一点也不夸张啊。
在他早期剧作《卡斯帕》中,主人公天生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畸形儿,在教师的帮助下终于学会说出一个句子,但是语言也使他被异化为没有个性的机器人。汉德克把政治与语言的关系揭示得很清楚,卡斯帕最后挣扎着说自己被搞糊涂、被控制了,更令人痛心的是他说“我从未看到过自己:我没有进行过值得一提的抵抗。”在母亲的故事中,汉德克的质疑是:“不管往哪儿瞅,一片盛世。‘政治’——有吗?——这个词不是一个概念”,它与任何实在的东西无缘,只是被当成一种提示词,一种形象化的与人无关的比喻。(15页)这是“活着”的另一种悲歌,也是黑夜中最难得到描述的一种社会存在。似乎出于不甘心被政治与语言联手击败,汉德克曾经表示要写《卡斯帕》续集,让那个年轻人反抗到底:虽然知道了“任何一种反抗都没有意义”,但他还是以自杀表达了对那个世界的反抗意志。
在“活着”的无趣、麻木和政治的异化、压迫之下,汉德克对死亡恐怖的叙述同样是那么扎心,更令人不忍。“我去年夏天在她那儿时,有一次看到她躺在床上,那样悲惨的一副模样,让我竟不敢再靠前一步。就像是躺在动物园里一堆落寞的行尸走肉。看到她不知害羞地袒露自己是一种折磨;她身上的一切都扭曲、破碎、开裂、发炎,五脏六腑扭结在一起。”(51页)“她醒来时身体就已经伤痕累累。她任由一切掉落在地上,希望自己能跟着每样东西一起掉落。”(52—53页)很残酷的是,作为她的儿子,“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之前,我常常忘记她,顶多有时想起她这辈子做过的蠢事会有刺痛的感觉。现在,她实实在在地向我挤靠了过来,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她的状况我一清二楚,甚至有时也完全会感同身受。”(52页)“葬礼那天早晨,我独自在房间里守着尸体待了很久。突然间,个人的感情和流行的守灵习俗达成了一致。那僵死的躯体在我看来显得异常地孤单和渴望爱。”在葬礼完成后,他突然产生要写母亲的欲望。(64—65页)难道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亲情变得真实和有血有肉?产生这种意识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与恐惧?与死亡相关的是葬礼,但是在疫情的肆虐中连葬礼也成为难以获得的奢侈,更想到那个小男孩是如何用被单覆盖着爷爷的遗体,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庭被这样无法得到描述的黑夜所遮盖。
还有,在汉德克的写作词典中,“旅行”、“疲倦”(“厌倦”)、“异乡感”、“陌生时刻”等也都是关键词。汉德克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历过一场的生存危机,“生存下去”成为严重的问题。这时期他的《缓慢的归乡》四部曲(1979—1981)表明那个虚伪、丑恶、僵化、陌生的世界与他格格不入,他对现实世界感到厌倦。在现实中行走、观察和感到厌倦,这是汉德克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大黄蜂》中,以“背旅行包的人”为标题的小节出现了四次。在这里“旅行”涵义是逃离与观察,有多少人是第一次真正读懂了在“旅行”之中的这两个词的残酷涵义呢?厌倦既是孤独个体的感受,也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反抗——因厌倦而逃离,或者因厌倦而反抗。在《试论疲倦》(1989年)中,汉德克描述了种种疲倦状态的痛苦与恐惧感受,疲倦甚至因与罪恶联系在一起而产生羞耻感。因此他要从疲倦而逃离,在逃离中观察,在观察中反抗。
由于成长经历的影响(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父亲是德国人;十九岁才第一次见到生父,1971年母亲自杀身亡),汉德克摆脱不了“异乡人”的感觉,对于德国、奥地利或斯洛文尼都没有明确的归属感。作为“异乡人”的感觉是,必须一直从自身体验中认识不同的地方,一直试图寻找属于“家”的感觉。结果是,“我觉得文学、写作才是我的故乡”。这也是一种厌倦与反抗。除了异乡感,还有“陌生时刻”。在什么时刻,我们会对人类感到陌生?当你在小区路口遇到一个熟悉的小哥因某种职责而产生权力感进而突然换了一副面孔,那是一种陌生时刻,你同时伴随着困惑:这人今天怎么了?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异乡人”和“陌生时刻”,使他不得不从熟习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环境中自我放逐出去,不断获得关于词语、姿态、图像、景观的另类体验,最后通过在文学中的“叙述”而回归到更真实的世界。
谈彼得·汉德克,文学与国际政治的纠缠也是无法回避的。反对他获得诺奖的人说他在政治上有问题,为其辩护者则说要坚持文学的独立性。问题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把文学与政治分割开来,他是一位很政治的作家。九十年代以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动荡、南斯拉夫战争等国际形势在他文学创作中不断反映出来,他直面战争与人性的灾难,对西方媒体政治提出的尖锐批评。在受到媒体攻击后他一意孤行。在这方面,他的政治就是控诉战争,反思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他坚信自己的观察与亲身接触所得到的真相。他常常会对报道中的事实表示怀疑,希望知道的是“这事被证实了吗?”他质疑的是,“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难道不会有朝一日写成另外的样子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有记者问汉德克是否承认发生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他说“我更喜欢厕纸,而不是您那空洞无知的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我们会感到陌生还是熟悉?
最后回到那句话:“黑夜是无法得到描述的。”为什么?汉德克说是因为“无以名状”与“难以描述”,“现在这个故事却真的和无以名状,和难以描述的恐惧瞬间息息相关。它描写的是那样的瞬间,意识在其中因为恐惧而猛地一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恐惧状态,它们如此地短暂,语言对它们来说总是措手不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梦境过程,如此地恐怖,你会在意识中像蛆虫一样经历它们。”(30页)没有在黑夜中感到绝望和哭泣过的人,能如何体会这种恐惧与无法描述的感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