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邓晓炯的澳门本土叙事
澳门回归后,澳门本土性和文化主体性不断彰显,文艺创作持续新变;另一方面,创作者也更加主动地介入社会议题。邓晓炯对澳门本土叙事的实践既契合潮流、又坚持创新,在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有着自己对澳门历史命运的思考;在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期许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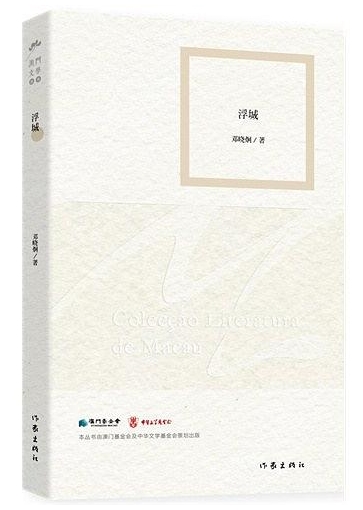
《浮城》,邓晓炯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澳门作家邓晓炯的小说集《浮城》包括四篇中篇小说:《刺客》(2005)、《迷魂》(2008)、《浮城》(2013)、《转运》(2003)。四部作品虽并非依时间线写作,却在事实上为读者建构出了“浮城”这一完整的意象,通过立足于多个时间点描述“浮城”的命运与不同“浮城”人的身世遭遇,使历史超越了具体的“浮城”人群和“浮城”本体,成为小说真正的叙述主旨。换言之,以“浮城”作为能指的所指已经超越了澳门这一单纯的地理场所,指向了更为复杂深沉的历史与文化交互层面:“既包含着殖民时期的惊惶与骚乱,也包含着后殖民时期的犹疑和焦虑,既有寻找刚健主体性的魅惑,也有可怕的后现代性迷失……”(李掖平:《对澳门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质疑 —— 评邓晓炯小说集<浮城>》,《百家评论》,2015年第5期,第119-122页。)探古访今、由事及人,邓晓炯一笔笔勾勒“浮城”的轮廓,并以“浮城”为载体展现、追索澳门历史,寄托他对身份归属的探讨、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借用殷国明的话:“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澳门, 不是我们眼前的这个五光十色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澳门, 而是一个文化澳门、 精神澳门, 一个充满幻想、情感和创造力的澳门。”(殷国明:《追寻小说中的文化澳门——第五届澳门文学奖小说评选作品评判札记》,《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第25-29页。)

邓晓炯
对历史的探索
澳门本土历史的书写日益受到重视,对澳门历史的探索与追寻是邓晓炯笔下的永恒主题,既契合潮流、又有所创新。
《刺客》与《迷魂》皆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来。《刺客》取材于澳门总督亚马留被沈志亮、郭金堂等人刺杀的历史事件,但小说并非平铺直叙地说明前因后果,也并未浓墨重彩地刻画刺杀场景,而是多次切换叙述角度,从澳门总督、刺客以及经办此案的两广总督的视角,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去思考并刻画刺杀事件前后的澳门,从而展现给读者近乎全知全能的阅读体验;而同一件事的不同人、不同立场又构成一种奇异的互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意在文后给几位小说人物兼历史人物设计了“后记”,并节选了《清史稿》等文献中对此次刺杀的描述,甚至做了简易的纪事年表,这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在于补充而非简单以之为背景。
《迷魂》取材于1622年6月24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企图攻占澳门的战争,作者创意地嵌套了一个“穿越”的剧情,让年轻编辑麦奇因卷入一宗谜案而灵魂穿回400年前经历震撼人心的葡荷澳门战役;与此同时的400年后,迷案在侦查、麦奇被抢救,双线并进缠绕,最终麦奇苏醒。虽然套了个科幻穿越的外壳,但《迷魂》的叙事是严肃且克制的。麦奇试图理清400年前战争的真相,而他与400年前历史紧紧相连的这份特殊情结,也为读者提供了还原历史的新视角。
邓晓炯对澳门历史的探索在《浮城》中较为特殊。故事发生在三千年后的一场拍卖会上,一本记载了澳门历史的日记正在被拍卖,日记主人是澳门移民的后代,因意外窥见了新澳门的“漂浮岛”计划而被财团追杀。但奇怪的是此时的澳门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过去式,在地图上不留一丝痕迹。旧澳门结局如何?漂浮岛计划是否成功?新澳门为何消失在历史地图之上?主人公最终到底命运如何?是生是死?文本布满了稠密的象征,作者由此表达自己对澳门现状的思考。
对身份的追寻
米兰•昆德拉说:“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景凯旋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而澳门文学正是这样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实验室”。澳门文学之根在中国,但同时澳门又有着4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史,复杂的历史让澳门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游离;事实上,邓晓炯的作品无不流露出“我是谁”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他在极力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当澳门作家试图以文学去重塑已逝的历史时,实则反映了澳门人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渴望。”(朱寿桐主编:《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46页。)其原本的身份认同是长期的、几乎难以排解的,而这种主体性缺失的心态也因此不免在其文字中流露出来。
《刺客》文中有处细节,当刺客沈志亮身陷囹圄,他同往日从未认真瞧过的秋虫对视,本想一巴掌拍下去,却在其眼中看出一派视死如归的大义,“对这只小虫子来讲,一个秋天也许已经太长,而它的生命也实在太短,短到被拍死也不会觉得是杀了生、造了孽”,便放下手来;又想到古往今来人们来来往往,只有秋虫争鸣的夜晚不变,心中有所感慨。而当两广总督徐光缙下了斩首令从沈志亮牢房走出时,“一只不知何处而来的秋虫飞了过来,撞中徐光缙的肩头,两广总督扬手,‘啪!’虫子被拍成了一滩浆汁。总督大人掏出丝巾,擦了擦染污的官服,一头钻进等候多时的官轿……外面,秋虫们此起彼落的嘤鸣声却越发响亮了起来。”被拍死的秋虫象征着即将赴死的刺客,而依旧嘤鸣着的秋虫则是仍在葡萄牙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代代澳门民众。一只秋虫被拍死了,并不代表其他秋虫会停止嘤鸣,相反,“嘤鸣声愈发响亮了”,喻指澳门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迷魂》开篇,作者这样描述灵魂脱壳状态:“据说,人要等到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才会意识到灵魂的存在。此刻,麦奇觉得自己就像一颗悬浮于半空的微尘——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甚至连动弹一下手脚也无法做到。麦奇想努力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却发现自己被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紧紧包裹。如此诡异的感觉,让麦奇手足无措,一个问号占据了他渐渐变得虚幻缥缈的意识:我现在到底在哪里?”事实上,麦奇灵魂出窍来到了400年前的澳门。但这个问题不止如此,他是在追问自己、询问读者——“我到底在哪里?”结合篇名“迷魂”,麦奇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他在寻找答案。
《转运》围绕着一枚“转运”筹码展开,它可以使人逢赌必赢、转败为胜,但筹码的主人却因此深感痛苦并最终选择自杀。“我又一次陷入了绝望,无论我怎么费尽心机,那只该死的筹码就是输不去!也就是说,我永远也不可能重返原本的生活,既然如此,我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世上没有多少人能抵挡住它的诱惑。”筹码的作用被作者有意放大,而在主人公收到了那枚转运筹码后,他的行为却只是“偶尔拿那枚转运筹码出来看看,甚或把玩一下”。他常常思索:“究竟,是什么在操控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那些转运灵符?抑或,是我们自己?”这种看似神秘主义的表述,实际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主义困惑:是否有神灵存在?人类能否自我选择命运?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了,但即使反思如何深刻警醒、如何深入也终究无法逃脱命运,只能“看看”“把玩”,或者像筹码的占有者一样,在死亡中逃离命运的藩篱,这无疑流露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对未来的期许
除了探寻历史与自我,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澳门发展的质疑与反思,体现出他对澳门未来的期许,这一点在弥散着科幻意味的小说《浮城》中尤为突出。《浮城》中的澳门形象有着相当发达的科技元素,给人以惊喜感,但我们仍不难从中窥见深刻的传统文学痕迹,如双翼约三四十米的“鲲鹏”被全息投影出来与同是投影的海上巨龙相决斗等等,其整体观感还是将传统想象纳入了现代体验之中。另外,《浮城》中新旧澳门的设计也很有深意:在澳门赌业发展和本地居民生活的种种矛盾已不可调节的情况下,赌业大亨们经政府许可选择一片海域并填海重造一座海上赌城,将澳门所有博彩企业和设施都搬离,在每年缴纳巨额赌税的前提下永久独享“澳门”之名;旧澳门则变成了无名城,游客不再来访,工商业凋敝,住户们纷纷移民,剩下的只靠新澳门的分红为生,而随着原住民的慢慢老去,澳门这个城市也慢慢被人遗忘。联系当今博彩业盛行的澳门,不得不说作者这是在用文字记录并提醒澳门。在小说结尾,拍卖官连续发问:“怎么样,现在有人打算出价了吗?”得到的却都是沉默。没有人关心那本日记或者三千年前的“澳门”,安东等人对故土消失的忧虑,也像拍卖官手中的那把锤子一样因无人应答而被悬在半空,而这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的。
澳门回归后,澳门本土性和文化主体性不断彰显,文艺创作持续新变;另一方面,创作者也更加主动地介入社会议题。邓晓炯对澳门本土叙事的实践既契合潮流、又坚持创新,在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有着自己对澳门历史命运的思考;在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期许与展望,如《浮城》关于过度城市化的思考,《转运》对于博彩业的描写等。事实上,邓晓炯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澳门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三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