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百年外国文学研究评述
来源:世界文学(微信公众号) | 陈众议 2019年10月08日15:50
本文主体来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之序言,亦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双年会开幕词。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综观百余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学科同中国文学学科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
一
首先,“百日维新”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等“托洋改制”论是继承“洋务派”的“体”“用”思想,并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林纾也因此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论更是振聋发聩,令时人耳目一新。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
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若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坚定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此外,“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的“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第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第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尚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利用外国文学宣传科学、民主和民族独立思想。如此,英、法、德、意、西文学和俄苏文学、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以特刊形式得以评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还联手茅盾创办了《译文》杂志。除国外现实主义文学外,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也一股脑儿进入我国,后者在上海等地掀起了现代派诗潮。从鲁郭茅、巴老曹到以冯至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和以卞之琳、穆时英为旗手的新诗派;中国新文学大抵浸润在蜂拥而至的外国文学和本国现实两大土壤之中。而且,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大抵是一手翻译、一手创作的“双枪将”。故此,围绕外国文学翻译,作家鲁迅和瞿秋白曾同梁实秋和陈源等人进行辩论。鲁迅1935年在《“题未定”草之二》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翻译观,他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顺统一”说。这些都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判断。这已经明确涉及文学翻译“归化”和“异化”的平衡问题。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译学、出版和评价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新文学,乃至白话文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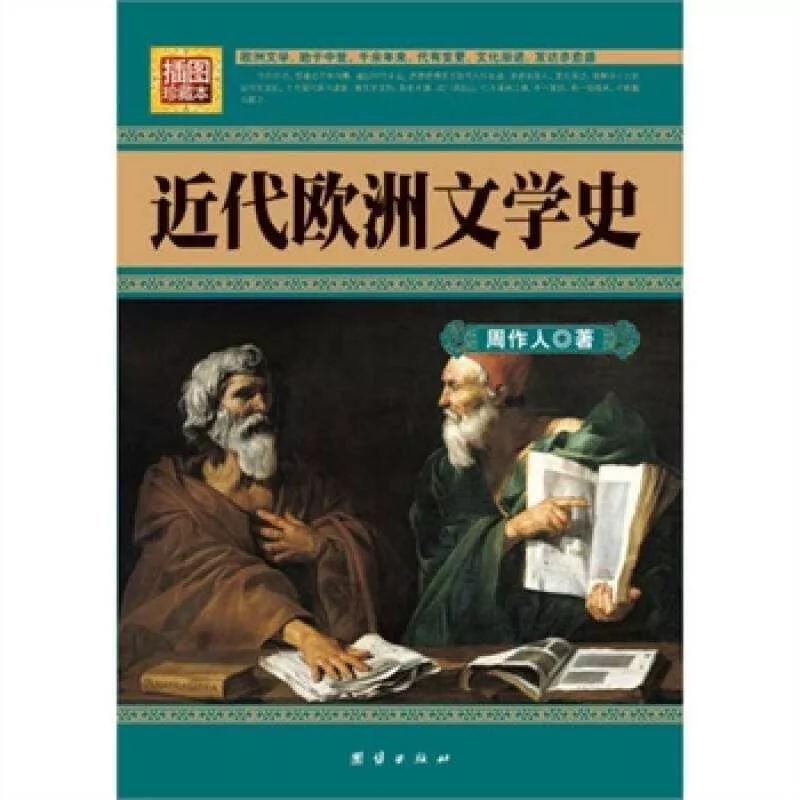
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
出于革命斗争和思想启蒙的需要,外国文学的译介一直十分注重思想性。鲁迅自《摩罗诗力说》起便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战斗精神激励外国文学工作者。茅盾关于外国文学的不少见解也主要基于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茅盾的《西洋文学》、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吴宓的《希腊文学史》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专题著述。虽然这些作品还称不上多么深入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出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俄苏文学和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先是受到了“学衡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林语堂等人的讥嘲。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封杀与追剿。就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一度嘲讽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由是,鲁迅曾赞誉苏联文学的译介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郑振铎更是认为“灌输外国的文学入国中,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从“娜拉的出走”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批热血青年在外国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或抗日救亡。
二
“五四”运动以降,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新文学旗手,一大批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参与文学创作,反之亦然。其中有胡适、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张闻天、夏丏尊、陈望道、李劼人、王鲁彦、李霁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沈从文、穆旦、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周扬、傅雷、卞之琳、李健吾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值得称道的是,李健吾对文友巴金早期作品《爱情三部曲》进行了严肃批评,洋洋万言中除了肯定巴金作品的社会意义,认为其风格的阙如令人遗憾。巴金积极回应,这场持续达半年之久的笔墨官司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却并未摧毁二人的兄弟情谊。同样,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鞭辟入里,有时甚至字字珠玑。他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坐标,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不仅以机巧取胜,而且在情欲的驱动下使人物显得绚丽夺目;但《倾城之恋》惟有华彩,失却了骨干;至于再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如《连环套》则内容贫瘠,只剩下作者本人了。如上批评即使今日读来,仍余温绕梁、令人感佩,盖因伟大的文学不仅要有风格、有机巧,更要有思想内涵、精神境界,反之亦然。换言之,作家须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既充满激情、富有想象,又细节毕露、异彩纷呈。而这些无不要求作家对生活、对时代社会有深入体验和犀利洞识,同时又才情兼备,善于文心雕龙。二者缺一不可。

巴金早期作品《爱情三部曲》
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翻译家、作家、评论家往往三位一体,从而使文坛呈现出积极的批评氛围。古风未祛,许多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可谓诸子百家式的诤友。
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跃上了新台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最初十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四五年是准备时期。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了解外国文学的学者不一定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在参加一般知识分子初期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被规定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补习。联系外国文学工作的实际,他们同时需要借鉴苏联同行的经验。为此,不少人还自学了俄语,以便直接阅读有关原著,甚至翻译苏联学者的外国文学史著作。经过这段时期的准备,在1955年和1956年之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相继出台,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一大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但是,工作刚取得了一些经验,成果还来不及得到检阅,1957年就开始了全民整风运动。翌年,学术批判运动迅速展开,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残余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受到了批判。然而,与此同时,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提出要引进一套外国文学名著。嗣后,“三套丛书”工作启动,它们是“外国文学古典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丛书的名称略有调整,但围绕“三套丛书”所展开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全面推开。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并接手“三套丛书”工程。这为新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部分作品
总体说来,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固然十分关注外国文学,但从研究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虽不乏亮点,却并不系统。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出发(也许只有俄苏文学研究是个例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对别、车、杜和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苏作家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无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除迅速从苏联引进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别、车、杜及一系列由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著述,同时对俄苏及少量的西方文学开展了介绍和研究。颂扬苏联主流文学自不必说,当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1959年的十年总结与反思,除了肯定与借鉴苏联、东欧文学,以及一些亚非拉革命文学的有关斗争精神,其他文学和研究方法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首先是对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然而,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筚路蓝褛,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不少经验,引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被极“左”思潮完全吞噬。明证之一是对姚文元的批评。姚在《从〈红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1958)中以偏概全地全盘否定西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界的有关同志就曾旗帜鲜明地对其进行了反批评。
分歧固然早已存在,但从1960年起中苏矛盾开始公开化。此后,苏联文学被定义为修正主义。极“左”思潮开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蔓延,其核心思想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正是在1960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给西方文学普遍地戴上了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三套丛书”步入停滞状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外国文学研究因中苏关系恶化和极“左”思潮干扰开始陷入低谷,及至“文革”结束。在长达十几年的历史进程中,外国文学被扫进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垃圾堆,极少数幸免于难的也成了简单的政治工具。正常的研究完全处于瘫痪和终止状态。自此至1977 年,外国文学研究全面进入休克期;但奇谲的是,即使是在十年浩劫期间,外国文学也以口传、手抄和“黄皮书”(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以西方文学作品为主,这些书的封面多为黄色或灰色,故称“黄皮书”或“灰皮书”。“文革”期间,这些书悄悄流传) 等形式成为一股沁人心扉的暖流。
四
197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再一次全面启动。“三套丛书”重新出发,古今各国文学研究遍地开花,可谓盛况空前。外国文学史、国别文学史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从传统现实主义到先锋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外国文学研究思潮喷涌,流派纷杂。设若没有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快速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是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国学者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观点)不可谓不经典。同时,设若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多元包容态势。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却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步伐又远远大于其他领域的步伐。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深刻。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四十年,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坛,而且在拨乱反正、破除禁锢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并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此外,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 思想奠定了基石。1978年初,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论争。虽然开始的论争仅限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有关人道主义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是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多达七百余篇。这无疑是对“文革”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一次清算。两年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虽然用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诸如此类的讨论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权等认识问题上拉近了距离,并一定程度上对丰富这些价值和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镜。尤其是四十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国文学母体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作家抵达高原创造了条件。
然而,综观七十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第一,前三十年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其中有十几年还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后四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但否定中也有肯定”;第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大有裨益。
必须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是非观、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种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我称之为“三无主义”)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为了颠覆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嗣后又被列为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这是一项向着学术重构的研究书系,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计划”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双向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左拉和芥川龙之介,第三系列由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乔叟、《圣经》文学、《一千零一夜》等学术史研究及其相应的研究文集组成。
学术史或学科史的梳理与研究不仅是温故知新的需要,同时也是端正学术思想的基本方式,而且它最终是为了面向未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明天的学术发展铺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倡导的这项学术工程既必要又及时,它必将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和“三个体系”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且指出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或可称之为“三来主义”)。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自然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之,“改革开放”后虽然“乾坤倒转”,西学东涌,却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提供了精神养分。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空前繁荣,译本之多、成果之众,不可胜数,甚至产生了令人目眩的规模化、市场化效应,推动中国文学从政治到美学的多重转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明显取法西方范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良传统与学术立场。其中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外国文学翻译界、研究界直接介入中国文坛的脚步逐渐停息,甚至出现了背弃中国文学母体的渐行渐远和为翻译而翻译、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这显然背离了“五四”精神,并使外国文学研究偏离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向度。其次,我称之为“唯文本论”的东西大行其道。这种“拔起萝卜不带泥”的批评方式每每置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于不顾,从而顺应了“文本之外,一切皆无”的后现代形而上学。再次,文学批评不再取法辩证并看多面。至于大到思想境界,小至作家风格,则不再受到应有的关注。而从作品到“文本”,看似小小的称谓之易,实则洋溢着学界的某种心流。我的问题是:圆够大,心安在?
近年来,随着“四个自信”和同心圆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二为方针”和“二为方向”正日益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研究界的重要体认。一批立足于“三大资源”和“三来主义”,致力于经典重估和构建“三大体系”的精品力作开始崭露头角。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