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捎话人”刘亮程
来源:现代快报 | 2019年01月09日0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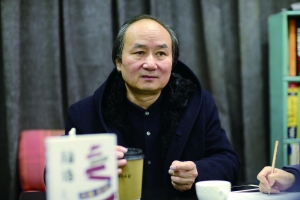
刘亮程说,《捎话》是一部关于语言之困的书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
冬至那天,南京下了雨。在书店角落里一落座,刘亮程紧了紧衣服,和在座的记者们招呼:“南京这冬天最冷得冷成啥样啊?”
他说,新疆的冬天也冷,但日照充足,人的体感温度会更高,晒着冬天的暖阳非常惬意。新书《捎话》的出版,将他千里迢迢“捎”到了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天。
20年前,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让刘亮程蜚声文坛,随后有《在新疆》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一次,甫一出版即横扫各大文学榜、好书榜的长篇小说《捎话》让暌违多时的他重回公众视线。
1
小说名为“捎话”,一个现在很少用到的词,通讯发达了,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捎话”。但这本书,虚构了一个一千年前发生在西域的故事。
以捎话为职业的翻译家库接到了新的任务,捎一头毛驴到敌对的阵营。为此他要穿过很长的一段路,途经许多战场和村庄。跨越边境的漫游让这个翻译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最后他完成了使命,折返回去,毛驴却在死后附在了他的身上,让他喊出了驴声。
那时候传达一句话,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与空间,穿越风沙、骄阳还有战争。一句话的到达,遥遥无期。在这个过程中,风声、驴叫、人语、炊烟、鸡鸣狗吠甚至还有鬼魂都在向远方传递着话语。所以《捎话》整本书都是写声音,写语言,写“捎话”这个词——从地上往天上传的语言,从此地往彼地传的语言,从一种语言往另一种语言的传递。
刘亮程生活的新疆就是这样一个语言丰富的地区。在古代,有数十种语言到达过塔里木盆地,四大文明也在那相会。即使在现在,刘亮程工作的文联,办公室对面坐的就是一个哈萨克女孩,说着哈萨克语,在文联的楼道里面,会经常听到数种语言的说话声。
“尽管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你只懂汉语,但是你知道他们说的是跟你共同生活的这块地方,共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所以新疆跟内地的不同就在于,每一件事可能都会有五六种语言去说,不像南京这儿,早晨下雨了,所有的雨都在被汉语说。新疆那个早晨假如下雪了,那么至少有五六种语言在说下雪这件事,有五六种语言在说太阳的升起和黄昏的落日,所有语言都在说这些事。但所有语言中天亮和天黑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你不穿透语言之间的隔障,你是不理解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捎话》这本书,它在言说语言的沟通的同时,也在呈现语言的隔障。”刘亮程说。
“几十种语言在通行,一种语言就是另一种语言的黑暗;人不能做到好好捎话,战争是捎话最极端的形式。”书中,位于东边的毗沙国与西边的黑勒国势不两立,从一句“毗沙西昆寺的高墙挡住了黑勒的太阳”的谣传开始,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开启了几十年的战争。
2
刘亮程是汉族人,长相却“很新疆”,早年他留两撇小胡子,那就更像。他在文联工作,经常有同事跟他说哈萨克语,跟他说蒙古语,他们都把他认成本民族的人了。
刘亮程说,新疆那个环境,很容易让人长得不一样,他父亲不像新疆人,但父亲把他生在新疆以后,他就长成了这样。
“新疆那地方地域辽阔、阳光直射,经常在太阳底下走就会眯着眼,眯着眼久了,眼球就朝后走,目光变得空茫深邃,还有饮食,吃肉食多,然后颧骨这一块肯定就宽了,气候干燥,皮肤和面部肌肉的收缩,使得人的脸上少有表情。”
1961年的冬天,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酒泉逃荒到乌鲁木齐。那时的乌鲁木齐正在修建中,没有多少城市的样子。在河边拉了一冬天石头,父亲对这个遍地芨芨草的城市有点失望,他们在老家饿坏了,想找的是一个有粮有地的地方。第二年开春,天寒地冻,父亲拖家带口往前走,最终在沙湾县一个叫做黄沙梁的村庄停了下来。
“那会儿逃荒都往新疆,新疆都设难民收容站了,到村里,村里面会主动给你落户口,然后给你分点口粮,让你先把日子过下去。”
父亲在路边的泥地里,挖一个“地窝子”,差不多两米深,一半地下,一半地面,人手一伸就够到房顶,刘亮程降生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十几岁。“每天夜里,都能听到旁边人的走路声,有时候,一只狗从屋顶跑过,噼里啪啦的声音惊天动地。”
刘亮程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就以黄沙梁为写作对象,他在书中构筑了一个人畜共居的村庄。《捎话》承袭了前作一脉相承的世界观,是在“万物有灵”之上建立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驴是书中仅次于人的重要角色。
早在写《库车行》的时候,刘亮程发现,当时库车人口40万,有4万头毛驴。每当巴扎日,有上万头驴车聚集在大河滩上,景象非常壮观。这种陪伴了人几千年的家畜,使刘亮程产生了类似于家园乡情的深厚感情,他试图像理解人一样理解动物。
3
在作家里面,刘亮程产量不算高,通常三五年写一部,写得很慢。《捎话》从2014年开始写,写了四年,中间写写停停,写不下去就放一放,但他每天会打开电脑,看看里面的人物长得怎么样了,他觉得写作就像长树,“可能缺一年都不行,缺一年肯定缺很多东西,你可能自己感受不到,但它确实是这样”。
这几年,刘亮程在乌鲁木齐300公里外的菜籽沟村建了一个木垒书院,全家人也搬到村里居住。
那是他建的一个养老的地方,中国文人都有这种情怀,老了以后归隐山林。他从小在村里面度过,老了以后还希望耳边不时传来鸡鸣狗吠,抬头能看到星星。“只是养老还太早,不是还没老嘛,所以顺带在那个环境中建了一个书院,晴耕雨读。”
刘亮程说,这两年看了很多历史书籍,对人类心灵的改变更感兴趣,想了解一个人群的悲欢、生老、宗教之思。
传说在新疆的天池旁边,有一片西王母的蟠桃园,里面有三千年开花结果的树,有两千年开花结果的树,也有五百年、两百年开花结果的树。刘亮程觉得,历史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就是历史的一种结果。一千年前的那一次开花,正好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之果。我们就生活在历史的果实之中。当一千年前的一段历史被我感知,用我的方式书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现实小说。历史被我们理解和消化的那部分变成了现实。所以,历史并没有过去。我们穿透千年的尘埃,看到的似乎是历史,但它更是今天。”刘亮程说。
对话
好小说是孤悬于
历史之外的单独存在
读品:这部小说的题材与古代西域有关,你能谈一下小说题材的最初来源吗?
刘亮程:《捎话》的故事背景和西域地理历史有隐约的一点关系,但它是虚构的小说,不是历史。小说可以借助历史,但好的小说一定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一个单独的存在。
读品:作为一位作家,似乎你本身就能看到声音之形,并赋予声音色彩。
刘亮程:我有悠长的听觉。早年在新疆乡村,村与村之间是荒野戈壁,虽然相距很远,但仍然能听见另一个村庄的声音,尤其刮风时,我能听见风声带来的更遥远的声音,风声拉长了我对声音的想象。那时候,空气透明,地平线清晰,大地上还没有过多的嘈杂噪音,我在一个小村庄里,听见由风声、驴叫、鸡鸣狗吠和人语连接起的广阔世界。声音成了我和遥远世界的唯一联系。夜里听一场大风刮过村庄,仿佛整个世界在呼呼啸啸地经过自己。我彻夜倾听,那个我早年听见的声音世界,成了我的文学背景。
读品:人羊的故事让我想到古代的一些酷刑,历史上真有其事吗?
刘亮程:我在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录中,读到过突厥人制造干活奴隶的故事,他们把刚剥下来的羊皮,做成头套,缝在俘虏的头上,羊皮一干,便收缩,紧紧箍在俘虏头上,里面的头发长不出来,便朝脑子里长,时间久了脑子就变得只会听主人的话。人羊也许受这个故事启发,小男孩脱光钻进活剥的羊皮里,羊皮最后长成人的皮,人羊就做成了。这是我最不想写的一段,但写好又不想删了。
读品:你早年写诗,后以散文赢得声名,现在写小说。但无论散文还是小说,语言都是非常诗性的。诗歌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亮程:其实我写诗歌的时候,还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诗人。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诗人。最好的诗歌语言应该是抵达事物本质的一种语言。它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诗意地飘忽于事物之上的夸张的浪漫的语言。最好的诗歌语言,都有极强的穿透力。用这样一种语言,我觉得无论去写散文也好,写小说也好,它能够体现这种语言本身的力量,让语言直达事物。
刘亮程
祖籍甘肃酒泉,1962年出生于新疆沙湾县,被认为是继沈从文、汪曾祺之后,当代作品最经典、最畅销的乡土文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及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等。多篇作品入选教材。现为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曦/文 顾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