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耀明:写小说的人都有张酒桌,先自醉,而后醉人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18年12月15日09:52
台湾地区小说家甘耀明的长篇小说新作《邦查女孩》简体版近日出版。甘耀明的长篇小说都沾染着历史氛围,历史是旧痕,无所不在,但他自言不太喜欢历史大于小说:“我喜欢写人在那样的历史中的摆荡,带着我主观的见解,带着我的主观笔痕,这是创造文学艺术,而不是服从历史。写小说的人都有张酒桌,先自醉,而后醉人,无关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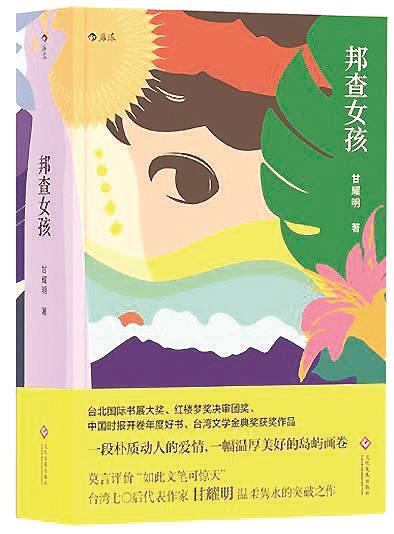
在古老的“摩里沙卡”,生长着四千多万棵树,18岁的阿美族少女古阿霞,逃出隐身多年的楼梯间来到这里,遇到患有不语症,却可以和森林对话的伐木少年帕吉鲁。故事出自台湾地区小说家甘耀明的长篇小说新作《邦查女孩》,两人的相遇不仅仅是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更呈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地区迷人的自然文化。该书简体版近日出版。
创作动机酝酿生发自2003年,甘耀明走访花莲县摩里沙卡(现为林田山林场),受到了触动,决定以那里为场景,写一本关于伐木、登山与自然的小说。文中的少女与少年则与他的真实生活经验有关。
《邦查女孩》中的古阿霞与帕吉鲁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一个是受到性伤害的女孩,在楼梯间躲了五年才愿意到社会闯荡。我最初的起心动念,是写一个女孩在山林间的受挫与成长,经过多次翻转,才塑造了古阿霞。”谈及书中人物的性格塑造时,甘耀明说。而对于另一位主角帕吉鲁,他的语气略显停顿:“男孩患有不语症,受霸凌,是由祖父刻意培养出来的怪胎,目的是保护森林。”帕吉鲁从一个真实故事中走出来——甘耀明曾经在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教书,入学的学生都要经历口试。某天,来了一个高年级的女孩,资料上写着患有“选择性缄默症”,她只能在家跟父亲沟通。面试持续了19分钟,女孩全程没有说话,最后一分钟时,作为面试官之一的甘耀明使用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招数。他温柔地对女孩说:“你要来我们学校就读,是不是要展现一下诚意呢?你可以讲几句话吗?”女孩用30秒时间紧紧盯着他,剩下的30秒,她开始“说话”,不是用嘴,而是用眼睛。她的眼睛瞬间红了,一直哭一直哭……回想这段经历,甘耀明似乎陷入某种情绪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理解了一件事:对于不语症,我们以为可以用平常的处理现实人生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女孩,但我们的理解是需要学习的,没有这个过程,便自以为聪明地横跨了某种界限。”
帕吉鲁的不语症,让他很难理解熙熙攘攘的社会,但是甘耀明并没有让人物止步于此,他给了这孩子一片广阔的任意驰骋的山林。当帕吉鲁回到山林,他便如山林之子,灵活自如。甘耀明对于山似乎情有独钟:“植物眷顾了山川,形成浓密繁复的多样性生态,动物也受庇荫。上千年来,山林之子们唯有在自然中才感到自在,他们研究出不同的植物药性与食用性,拯救灵魂与身体,却也只挖掘了森林十分之一的潜力。十分之九的森林秘密,像是梦境,山林是活的。”
从早期的小说《神秘火车》开始,甘耀明就在时刻反思:“在每篇的写作过程中,我总是思考,这篇小说有没有可能发展出相关系列;或者在语言、风格或意象上,延展出自己的特色……”其后,他接连出版了《水鬼学校与失去妈妈的水獭》《杀鬼》《丧礼上的故事》《邦查女孩》《冬将军来的夏天》等作品,或许可以从外界的评论中获得这样的一种认知,他的作品的确形成了某种风格与特色,后面连缀的词眼可以是“童话色彩”、“魔幻写实”与“乡野传奇”。
“我生于苗栗狮潭乡,那里的山脉青壮,草木在阳光下闪着明亮的色调,河流贯穿纵谷,里面游着鱼虾,以及古怪的传说。”乡野是孕育传奇的地方,甘耀明小时候从祖父母、父母口中听了不少关于鬼神的传说。长大后,他日渐意识到这是长辈们在不同场合表达生命教育的意涵,也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乡野传奇本身的荒诞奇幻与上世纪80年代传入台湾地区的魔幻写实相融合,成为甘耀明书写的一把钥匙。他由此被称为六年级(指1970年代出生)“新乡土文学”的代表。魔幻写实强调在现实上拓展时间和空间,“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写实不是舶来品,它在我们周遭。我们往日选择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疯狂不理性的元素。事实上,那些看似疯狂的宗教节庆、民族传说、荒诞言词、巫术蛊惑等,都不该因科学或理性,将其严峻地推到角落,这些素材经过加工后能成为艺术”。甘耀明进一步解释说,台湾地区的魔幻写实,经张大春、宋泽莱、林燿德等人之手后,到了1990年代,这一类型更接地气,其原因正是乡土文化的觉醒与再挖掘。不同于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取材现实,反映悲苦,甘耀明认为其内涵大有不同,两个时期只是“乡土”两字沾边,书写方式与关注对象均有落差,可说是不同的书写,“新乡土文学”是更自由的书写,精神不离此地。
可能因乡野记忆大多来源于童年,又或者与甘耀明长期从事儿童创意写作教学有关,他的小说常常以儿童叙述呈现,这种设置使得他的乡野传奇更具迷幻色彩之际,又多了童话的浪漫之美,但这种美不是单纯的儿童乐园,甘耀明认为大部分的童话仍然呼应现实,打破人与动植物的理性隔阂。
他也许正是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他觉得故事永远存在,只是改变灵魂面貌,通过一篇新闻、一场电影、一则八卦、一个广告,都是展现巫术的时刻。他乐意与儿童分享“巫术时刻”,很多文学作品,比如苏童、莫言的故事,他会经过转化说给儿童听。他也希望自己写的故事能召唤成人读者“观照自己内心的小孩”。甘耀明以为网络时代,人们像幽魂游游荡荡,也不过是找人听故事,或讲故事给人听,寂寞则是人们需要故事的根源。
故事深植在内心,有待某天被讲述,被倾听,而“说故事”这件事情又不那么容易,需要技巧和策略。甘耀明认为“说故事”这件事是中性的,故事是人的重要资产,美好记忆凝结后,可以传承,这样对人生就不会太悲观。所以他选择了一种不那么悲观带点幽默的方式说故事,在轻盈中描写伤害、死亡、战争等沉重主题,他以一幕幕戏谑的情节尽力去淡化哀伤。“磨墨有个要领是重按轻移,写小说的悲沉,其实也应该这样。人生多半不是英雄诠释,凡人多是小角,小丑也要上场呀!他总是在笑,分明眼角都画着泪水,读者不该亵渎他的笑中带泪。”
相比以故作诙谐的语言去面对厚重的历史,甘耀明更愿意采取的是稍稍疏远的态度写普通人生活的历史面貌。他认为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的历史,一种是写下的历史。对于写历史的小说家,肯定是想当个最自由的历史学家,叼根野草,写他的野史。“那是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酒桌,而非陈寿写《三国志》时颤巍巍的史烛。写小说难免都建立在某个历史场域,只是这历史布景要深衬,还是淡景。看各自选择。”他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沾染着历史氛围,历史是旧痕,无所不在。但他自言不太喜欢历史大于小说:“我喜欢写人在那样的历史中的摆荡,带着我主观的见解,带着我的主观笔痕,这是创造文学艺术,而不是服从历史。写小说的人都有张酒桌,先自醉,而后醉人,无关酒了。”
在甘耀明的小说实验室,他尽情调配修饰一切出现在小说中的事物与细节,不太在意转变发生种种痕迹。他更看重作家书写小说时的策略,策略影响小说。“《杀鬼》是精力无限、带着躁动脾性、小孩的书写方式,语言与人物动作,如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仪式,我知道已过中年就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只有年轻气盛才会这样写。这种昏罗帐的斑斓色度,我庆幸年轻时写过。《丧礼上的故事》较倾向口传文学的记录,而《邦查女孩》更像中年写作,我指的是笔法,比《杀鬼》收敛许多,它不会带着啃劲,是软硬适中的面包。”从作家的角度出发,策略的解释也可以延伸到他对于短篇与长篇小说创作的比较上,他认为前者处理灵光乍现的想法,处理完,又到等待,所以要频换姿态。而长篇则是长跑的开始,要是素材与想法整理好,就可以上路。“短篇因为有较多要遵守的创作限制,要挣脱裹脚布较难,长篇小说不用,穿着布鞋就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