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的“文学三十年”
来源:晶报 | 伍岭 2018年08月08日2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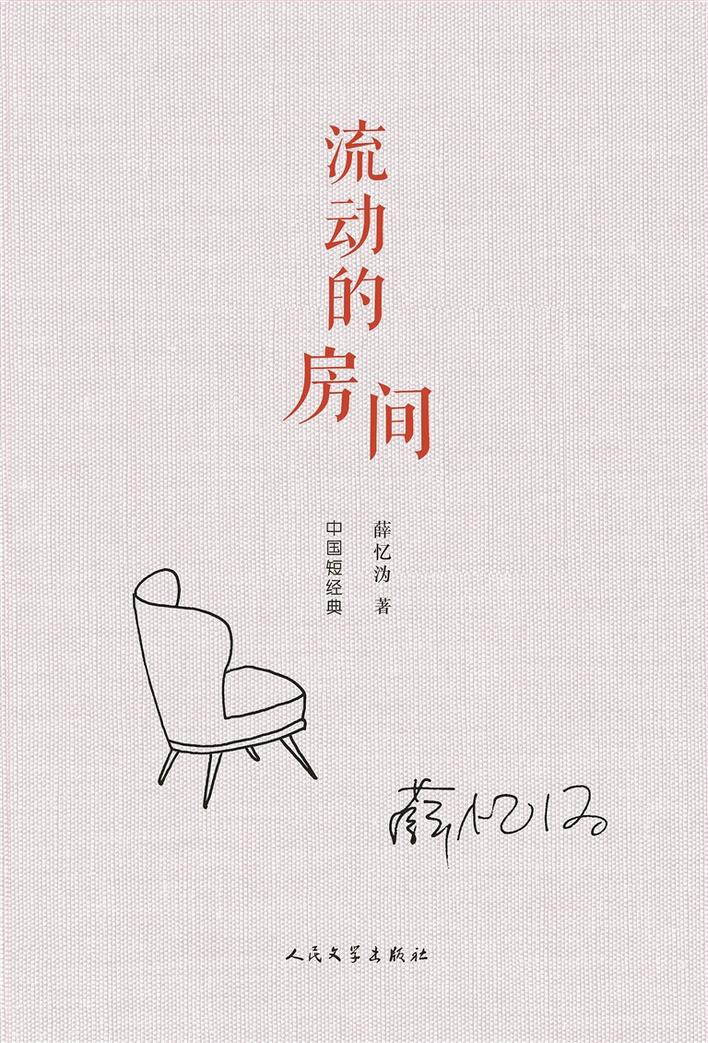
薛忆沩 不同时期 部分作品 《流动的房间》2018年版

《异域的迷宫》 201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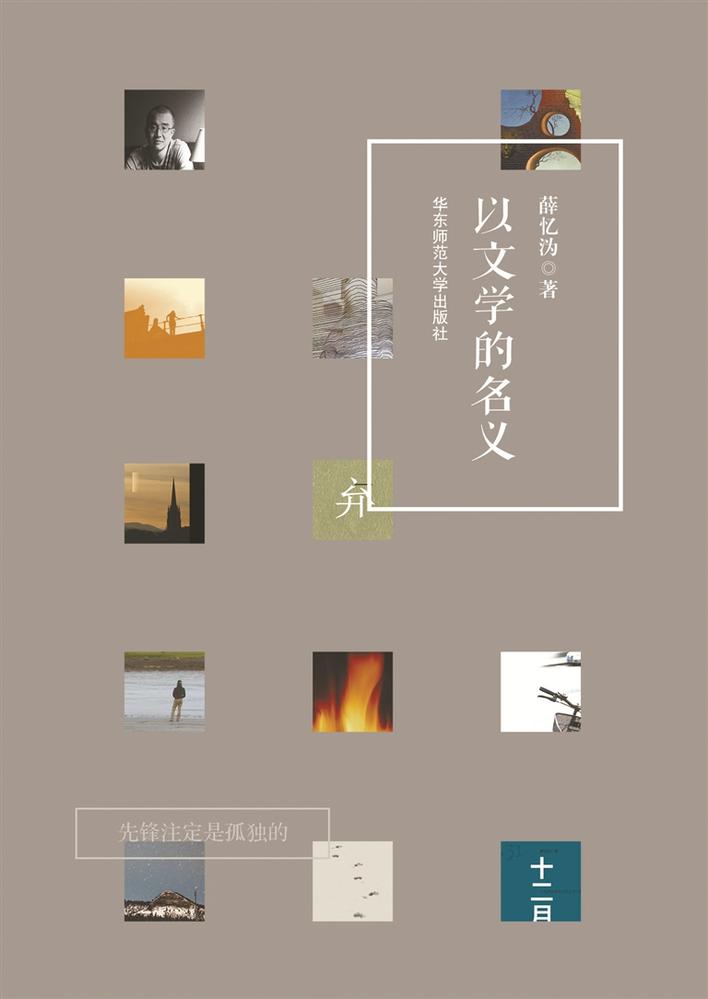
《以文学的名义》 2018年版

《深圳人》法文2017年版

《出租车司机》201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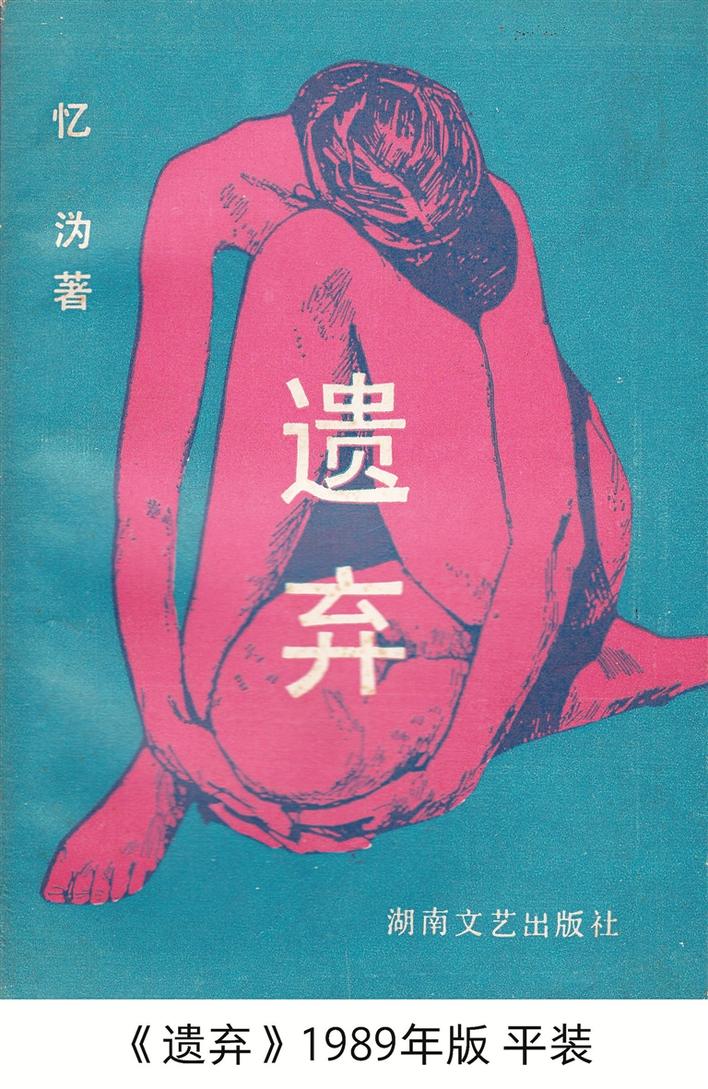
《遗弃》1989年版
2012年夏天,薛忆沩的五部作品同时由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出版,因此中国的出版界有了关于“薛忆沩年”的说法。这一年也同样是薛忆沩文学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出版,其中有两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的作品更是高达五部。这样的状态是所有人在2012年前都不可能想到的,也包括薛忆沩自己。
这样的状态仍在继续。今年,薛忆沩又有三部作品出版,分别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异域的迷宫》和访谈集《以文学的名义》,以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
薛忆沩能够持续保持这种状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从《作家》杂志于1988年第8期头条发表他的中篇处女作《睡星》算起,正好是他进入当代中国文坛整整三十年。“三十而立”的薛忆沩不仅是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知名作家,随着《深圳人》等作品的翻译出版,这位近年来从深圳走出的作家已引起了可观的国际关注。
我想得最多的是艰辛而非成就
晶报:你如何看待自己用三十年时间取得的文学成就?
薛忆沩:在翻开1988年第8期《作家》杂志的那个瞬间,我当然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在文学的道路上走这么久和走这么远。很多人都说我走的是一条最特殊的文学道路。回顾过去,我想得最多的是艰辛而不是成就。就以《睡星》为例,那是我在1986年初就已经完成的作品,可它却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经过那么多的退稿,才最终与读者见面。类似的经历后来也不断在我这三十年的文学道路上重复。可以说,艰辛是文学教给我的第一个关键词。我感谢这三十年的艰辛,因为它不仅深化了我对文学的情,还强化了我对生活的爱。当然,我也感谢所有那些让我一次一次看到希望的人。
晶报:《流动的房间》是你由花城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小说集。后来,这部小说集成为你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关注的“重写”的主要目标。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版与2006年的原版已经只有名义上的联系。这个新版作为你“重写”的重要成果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作品。现在这个最新的版本应该不会再有太多的更新了吧?
薛忆沩:是的,这个最新的版本只是改正了残留在2013年那个版本里的一些编辑和印刷上的小错。准确地说,它只是2013年那个版本的重版。对我个人来说,这次出版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它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很小的时候,看着家里书架上那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我就梦想将来也要在那里出书。没有想到,一直等到了这个年纪(差不多是鲁迅谢世的年纪),才终于等到这样的一次机会。这次出版大概也是对我这三十年来的专注和执着的一种褒奖吧。
晶报:2012年,以《异域的迷宫》为题的随笔在《收获》连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这也是你“非虚构类写作”才能的第一次全面的呈现。从那以后,我相信读者的心里开始并存着两个“薛忆沩”,一个是虚构的行家,一个是非虚构的高手。你自己如何平衡这两种角色呢?
薛忆沩:我的非虚构经历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从2006年开始同时为《随笔》杂志和《南方周末》写作读书专栏就应该是我非虚构写作的第一次高潮。然后是2010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写出的《一个年代的副本》。那部篇幅等同于中篇小说的作品让我对自己驾驭非虚构的能力有了基本的信心。将近3万字的随笔《异域的迷宫》就是在这种信心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它的确很受读者的喜爱。当时就有不少读者希望我能够写出更多的续篇,将来结集出版。
六年之后,随笔集《异域的迷宫》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对喜欢我非虚构写作的读者的一个交代。我自己并不觉得有必要在这两种写作之间做刻意的区分,因为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写作技巧都可以在两种写作里通用,而另一方面,虚构的“现实”和非虚构的“现实”相比,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谁更合理,谁更真实。但是,自从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出版(也就是2016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发表过虚构作品了。我对自己的这种无虚构的现状有点恐惧(笑)。
我将访谈当成是创作的延伸
晶报:《以文学的名义》是你的第二部访谈集了,第一部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出版于2015年。仅仅过了三年,你的访谈又足以结成一集出版,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好像与创作关系不大的访谈活动。还有,频繁的访谈难免会导致经常的重复,你又如何面对这个难题?
薛忆沩:我的访谈体验开始于1999年9月,也就是我的“文学三十年”进入第12个年头的时候。《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就是那以后到2015年以前的大部分访谈的结集,而《以文学的名义》是最近这三年主要访谈的结集。是的,这种结集的速度多少反映了我的文学状态,比如出版的频率和作品受关注的程度。我一直将访谈当成是一种与创作密切相关的文学活动。或者说,我将它当成是创作的一种延伸,就像创作本身是写作者生命的延伸一样。所以,我总是称访谈为“作品”。我注意到自己最近这三年来用英文写出的访谈也已经积累不少了。也许将来我还会有机会出一部英文的访谈作品集呢(笑)。
晶报:提到这个话题,我想到你的作品的翻译情况。最近这两年来《深圳人》《空巢》等作品都相继“走出去”,并获得可喜的国际关注,关于这些,国内的媒体已有不少的报道。在《异域的迷宫》一书里,你也有两篇感人的作品专门谈及你的两位法语译者:关于林雅翎女士的随笔《最后的午餐》催人泪下,而关于《深圳人》法语译者的《乔装成“村姑”的天使》让读者诚服文学的神奇。能否说这些成功在你的文学道路上是没有悬念的结果?
薛忆沩:我不这么看。我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得不到翻译的重视,现在重视的程度也与作品的数量不成比例,这本身就很像是一个悬念。当然,我没有抱怨。汪德迈先生曾经与我谈及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法国之后“从来”就得不到法国作家同行的赏识。这种状况让这位著名的汉学家深感痛心。他认为受到同行的赏识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我的作品翻译出版之后所获得的许多好评就来自同行。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破。尤其是《深圳人》。不久前,我收到法语版出版商转来的一封很长的法语邮件,是她的一位作者写来的。这位作者不仅充满激情地写出了自己对《深圳人》里面一篇篇作品的感受,还充满激情地表达对小说作者的敬意。还有,年初悉尼作家节的主管来信说当地一家著名画廊的负责人是我的粉丝,她希望在我去那里参加作家节的时候专门与她做一场关于《深圳人》的对谈。一部翻译自汉语的短篇小说集能够成为受到如此关注,让我意外又开心。
写作者最大挑战是“下部作品”
晶报:从2002年初的移居“异域”到2012年中开始的“文学爆炸”,正好经过了10年的时间。记得乔伊斯也是在离开故国整整10年的时候迎来了自己文学生命的转机。你如何看待写作者经历上的这种相似?
薛忆沩:我喜欢读作家的传记。与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经历上的相似总是会激起我的感叹。这里说的经历主要是“苦”的经历。写作是与贫穷、寂寞并且与失败关系密切的事业。伟大作家遭受的磨难对后来的写作者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当然,你注意到的这一相似好像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这应该只是巧合。
晶报: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专注和执着的“文学三十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但是,我感觉你自己对这个话题并不是特别兴奋。为什么?
薛忆沩:“文学三十年”面对的是过去。而对写作者最大的诱惑和挑战总是“下一部作品”,也就是他的未来。我现在对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既充满了期待又充满了焦虑。我希望它是一个新的开端,我希望它能够为我的另一个“文学三十年”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