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的缘起与展望 ——程光炜教授访谈
来源:《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 程光炜 张亮 2018年07月25日07:33

作者介绍:
程光炜,1956年生,江西省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年谱研究。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等核心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著作有为《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二十讲》《文化的转轨》等,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等大型丛书数种。曾多次赴欧美、日本等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讲学、访问。

一 工作坊的缘起和现状
张 亮:程老师好!据我了解,能否请您简单回顾一下2005年起开设“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博士生工作坊的最初想法?
程光炜:我在台湾开会,看到那里不少大学的研究所,采取欧美大学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培养研究生,对我颇有启发,这样萌发了在人大开博士生工作坊的想法。起初两年,抱有试试看的心理,没有明确的路线图。随着李建立、杨庆祥、黄平、张伟栋、李云、李建周等有才华和活跃的博士生的出现,我心里的学术规划逐渐清晰起来,就是把1980年代文学“问题化”,以作家作品带问题的研究方式,呈现那个年代文学思潮、流派、论争和形式探索的地理结构。其间,我和北大中文系的李杨老师合作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辟“重返八十年代”的专栏,分批发表人大、北大学生的研究论文,受到学界关注。后来,我们的工作坊论文编成“八十年代研究书系”和《文学史课堂》(与杨庆祥老师合编)等丛书,在北大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些成果,使“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初露端倪。
张 亮:工作坊成立以来,刚开始做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后来转向七十年代文学,接着做了一段九十年代文学,现在又回到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能否请您谈一下这样调整的原因?
程光炜:法国年鉴派有一个“时段史学”的说法。他们所说的时段史学,是在反对宏观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微观史学的设想。但是微观史学内部也潜藏着宏观史学的视野和框架,两者其实并不矛盾。“重返八十年代”就是一个微观史学的设计方案。它设想把八十年代切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段落,在这个框架里让当时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沉淀下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研究。按照我后来的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
这也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规律。从事一段研究以后,人们会发现文学史里面有一个前因后果的秩序,例如,1980年代是怎么发生的?那它前面起源性的东西就不能被屏蔽掉。比如,1980年代很多小说的主人公特别喜欢“对话”,喜欢在作品中发表议论,《北方的河》《北极光》《波动》《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爱,是不能忘记的》《布礼》都是这样。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习惯,可能来自20世纪60、70年代强调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革命传统教育的风气。也就是说,1970年代的思想资源,到1980年代,还在文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有时候可能还是支配性的。所以,我们决定暂时放下八十年代,做一段七十年代文学试试(这些成果,被编成《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做1990年代文学也是这个原因,1980年代文学有时感到做不下去了,很多问题纠结在一起,无法展开,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查资料时发现,有一些问题在1980年代只是一个苗头,它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才构成一个问题,有充分展开的可能性,比如出版社与书商这种出版的双轨制,作家个体户、签约作家等等。王朔在1980年代就号称是“作家个体户”,当时响应者寥寥,到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时这个问题才浮现出来。因为书商出版物的冲击,1980年代中期,一些纯文学刊物受到冲击,订刊物的读者急剧下降。到1990年代初,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鼓励文学杂志自负盈亏,一度使很多杂志濒临倒闭。八十年代就这样以九十年代的面目存在着,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看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通过做1990年代文学研究,重新摸摸1980年代文学中被我们遗漏的某些现象。进一步说,如果倒过来做做1990年代文学,例如文学与革命、文学与市场,才知道1980年代只是历史很小的一个段落,1990年代才是漫长的;反过来说,1990年代只有在反衬1980年代的时候,才会发生意义。1980年代如果也从1990年代反观自身,其中的意义才能具有爆发力,可以深度地被呈现。这是一个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历史视野。将三个十年相互参照,可能比单纯做其中一段更有意思。
鉴于后来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1990年代无法沉淀下来,我们只做了一段1990年代文学研究,就重新回到1980年代这个老根据地上去了。
张 亮:相比于十几年前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近两年的研究是否面对着研究心态、方法和语境的不同?您以前总结过“历史分析加后现代”的方法,但现在似乎不那么看重理论了,甚至要求一些文章做理论减法,让史料自身去说话。您能否谈谈其中的变化?
程光炜:你很敏锐,看出了我们前后两个阶段研究重心和方式的变化。2005年到2014年,工作坊确实很强调理论对问题的穿透,是用理论带问题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能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尤其是框架感。但是长此下去,研究本身的不足也暴露了出来,比如,史料文献较少,写出来的论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另外,我2010年从澳门大学做客座教授回来,渐渐也发现,这种训练方法弄到最后,可能会疏远所谓的“学问”。我是从现代文学转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由于受导师陆耀东先生的影响,知道问题所在。这种偏颇,也许会对学生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影响,我过去的一些老学生,有的在自觉地做着调整,也有一些调整得比较困难。如果说责任,这首先在我。
除上述原因,转向“理论减法,史料加法”这一方面,还与文学史研究的阶段性特点有些关系。一般而言,文学史研究,最早都是提口号、说问题、亮招牌。热闹过后,就得坐冷板凳,到图书馆、知网上下功夫。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是一个笨功夫,太聪明了不行,过于取巧更不行,因为学术研究看重的是耐心、耐力,包括对比较寂寞生活的忍耐等等。陆耀东先生那代学人,都是这样的。在武大跟他读博的三年,我对先生多少有一点点研究,注意到如果一个关键材料没找到,他宁愿放下很多年不动。这样做虽然吃亏,但一旦做出来就不一样,是底气很足的。因为有材料说话,你怎么驳都驳不倒。我跟学生转向这一方面,实际是按照文学史研究的规律在做当代文学,邵部的《萧也牧之死探考》、谢尚发的张洁身世考察和“沈从文热研究”等以史料见长的文章发表后,颇受学界同行的称赞,就是这个原因。当然,由于1980年代文学还沉淀得不够,有时候是我们功夫下得不够,有时候则是作为当事人的作家不愿意配合,或者能够找到的史料有限。我们这两年其实并不容易,所谓“八十年代文学的史料文献研究”一直是举步维艰,进展得很缓慢。
张 亮: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既有批评家的角色功能转变的问题,又有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不能用史料呈现出来的事实面貌去掩盖个人的艺术判断。像您写王安忆、莫言的文章,批评的眼光与历史的纵深是相辅相成的。您如何看待文学史和批评的角力?工作坊一直立意文学史研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程光炜: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我从来不认为文学批评不重要,只是不太赞成做当代文学的人都去弄批评,凑热闹,天天出席各种研讨会,以结识作家为荣,不愿意沉下心来做文学史研究。然而,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决定了很长一个时期里批评家都会扮演重要角色。以我个人的经验,有过文学史研究的训练,再偶尔写点文学批评文章,会比较有底气,不会乱说话。原因是,批评者首先具备了“史家眼光”,他会在文学史的纵横参照里谨慎地做出选择,不将作家新创作的作品看成是“石破天惊”的现象,不会大惊小怪,在这种谨慎持重的心态中写出的批评文章,自然会好看一点,有一点韵味,比较厚实。例如,洪子诚、黄发有和张均等老师在做文学史研究之余,写的一些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就比较耐读,不空泛。黄平老师称之为“史家批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认为,做文学史,一定得有充盈、丰富、敏感的艺术感受力,否则,文学史研究就太枯燥无趣了,跟数学物理公式一样。现在有一些当代文学文章,很像社会学文章,读起来很是头痛,可能作者的感觉十分良好。我对此一直不能理解。最后,我想说,充分隐含着文学史家本人个性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与一般的文学史教材和著作,可能会有所不同。
二 “八十年代史料文献收集整理”的重点和难点
张 亮:这两年重新研究“八十年代”,您将史料文献收集整理的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程光炜:涉及的方面可能很多。我觉得比较紧迫的,是当代作家身世、家世,事件的前因后果,思潮流派发生始末,历史转折点等等方面,可能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逐步地、全面地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对一个作家而言,你不了解他的传记材料,想对他的创作进行深入研究会很困难,比如,莫言与外国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究竟怎样,贾平凹关于中国传统文学、古典文学、琴棋书画等等的修养问题,张承志与“文革”、内蒙、考古、宗教等的关系渊源,这些基本的东西至今没人清理和研究,史料文献的收集也尚未开始。自然,从大的方面来讲,应该启动编选关于1980年代的大型史料文献丛书的工作。在此之前,我和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合编了一套《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近二十本,细分为《伤痕文学研究》《反思文学研究》《寻根文学研究》《先锋小说研究》《新写实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和《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等,是以思潮、流派为中心编选的丛书。出版社原计划2017年推出,现在估计还要推迟一段时间。另有《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450万字,4大本),也在出版社放了四五年,因为增订、校对等原因,还没出来。此外,跟我们工作坊密切相关的是课堂论文对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意义重要但进展缓慢,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张 亮: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了好的选题,却没有材料可做,有的涉及内部材料没有公开,有的由于作家或其亲属的意愿,有的难辨史料真伪价值。这种困难也反映出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您如何看待收集整理作家史料之难的问题?
程光炜:确实是这样。有些虽有一点材料,但作者在怎么利用、处理和吸收上存在问题;另一些是没有材料,或者缺少关键性的稀见材料,所以即使仓促写成文章,价值也不大。这种事情是千头万绪的,一点一点地做吧,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当然,先行者面临的困难,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
张 亮:有几位师兄的文章是围绕当代报刊和杂志(比如《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来做的,如何把握大量、庞杂、琐碎的材料,使之脉络清晰,集中到论题之下,也非一日之功。想请教您,处理这种类型的历史材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程光炜:夏天对1979年到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重读,就是在大量庞杂、琐碎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整理出来的一篇文章。尽管课堂上大家对这篇文章提了不少意见,我觉得它仍然是一篇值得肯定的研究文章。夏天从上学期起,就一本一本地读《丛刊》,文章从初稿到完稿,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这种认真治学的态度应该鼓励。从他的工作可以看到,即使读杂志这种史料整理工作,没有多年磨炼摸索,没有实战经验,要想一下子把它写好,没那么容易。这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不上手不知道,一旦上手,才知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我1990年代初跟陆老师攻读博士的时候,开始也不会从材料里整理问题,不知道如何将繁琐的材料条理化、问题化,变成一篇有意思的研究论文。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慢慢才学会怎么化繁为简、去伪存真,把杂质淘汰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看来,史料家不光是文学史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的眼光、素养、经验,都决定着材料的取舍,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学生应该多写、多做,时间长了,眼光就会刁钻、独特,与人不同。《丛刊》现任主编李敬泽先生是著名批评家,但他有个说法也很有意思,他说做材料也得有才气。
张 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及相关史料的关系,也会影响对史料的选取、结构、阐释。对于您这代学人而言,个体经验是构成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也深深影响到研究方法和历史认知。但对于年轻一辈而言,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都是在回溯中建构起来的,材料更容易作为知识的对象。那么“八十年代”与“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不断地转化新时代的新经验,使之成为历史认知的一种模式和动力?
程光炜:从2005年带着博士生“重返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一个研究者跟历史的亲近,找到所谓的“历史感”,非一日之功能够达到,得反复参与课堂讨论,与老师同学交流,在实践中摸索。我们工作坊这种形式,提交文章、大家提问、作者回应等等环节,其实就是在找一种适合于作者的“历史感”。只有读那个年代的材料,写出文章,再容大家评论甚至挑剔,才会慢慢感觉到历史的存在。研究者与历史的关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亲历者”“当事人”的研究,另一种是通过读材料、触摸历史并研究这些历史现象,后天逐渐获得,二者没有优劣之别,主要要看个人禀赋、才华和下的功夫。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大量读理论书尤其是史学理论书,比如英国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安托万的《历史学十二讲》、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我自己认真读过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一、二卷(三卷四卷还没来得及读),读他的《历史哲学》,真的受益匪浅。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眼光,也做不好文学史,顶多是个学术工匠。当然纯粹做史料,也可以造就一个好学者。另外,对历史始终葆有好奇心,也是不断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和动力。
张 亮:“八十年代”毕竟还是离我们很近,好处在于容易获得一手材料,发现新问题和新证据,但是也容易使人局限于时代的理解,因为我们本身可能还在“八十年代”的余绪中,很难说这样的“历史化”是不是足够“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所以“重返”在我的理解中不是一劳永逸的,“八十年代”依然是需要“不断重临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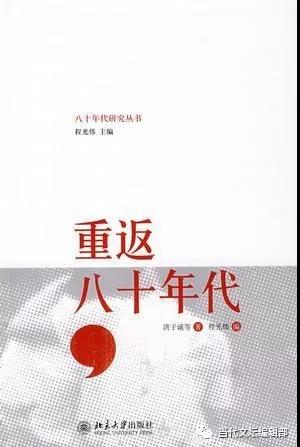
《重返八十年代》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又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有时候容易陷入材料的琐碎和过分细化,缺乏一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视野和历史意识。可否请您谈谈在处理文学史问题时该如何应对“远近之辩”和“小大之辩”的困境?
程光炜: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读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这两本书,他们对研究者与历史的关系,今天与过去,以及两种历史叙述者(一种是当事人和亲历者,另一种是与当时历史无关的叙述者) 在重演当年历史时应取的角度和如何保持距离感等问题,都有很多精彩的讨论。这些观点,对我研究1980年代文学史有重要启发。
三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异同
张 亮:陈思和、王德威两位老师主编的《史料与阐释》,既收了新发现的辜鸿铭信件、老舍的未刊创作这些“现代”文学史料,也有胡风的佚文、贾植芳的信件等“当代”文学史料,并有“论述”“年谱”专栏,有意对现当代文学做一个打通和梳理。想请教您,当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在目前的史料文献整理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哪些不同之处呢?
程光炜:陈思和、王德威两位老师主编的《史料与阐释》每期都给我寄,这本杂志在搜集整理现当代文学史料,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史料文献方面,有很突出和扎实的成绩。陈老师学生张业松教授是专做胡风年谱和研究的,所以,他提供的材料相当可靠有用。陈老师与贾植芳先生有师生之谊,与其说他在整理贾先生的资料,不如说他自己也是资料的亲历者和当事人。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因为历史距离的关系,相当部分已经沉淀下来,因此史料文献本身的价值也在提高。而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料文献,一方面还没沉淀下来,另一方面有的作家目前不太愿意把它们拿出来,例如日记、通信、创作札记等,即使有些自传自述材料,大多也语焉不详或有所隐晦,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对这一时期文学史料收集整理的工作。
张 亮: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制归功于王瑶、唐弢等先生的努力,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当代行为和当代问题。您曾以“鲁郭茅巴老曹”等现代经典作家的当代命运为维度来研究建国以来的文化转型,也一直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这是否和现代文学史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
程光炜:我在《文艺争鸣》上主持一个“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栏目,主持语里有一段话,可以代表我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应该吸取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些看法,在此抄录一二:“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兴起,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学科方向,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它的‘古典文学化’。也就是,不单把现代文学看做是一种活动的历史,同时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历史现象,按照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式,对之进行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和积累,进行大量和丰富的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现代文学变成一种有历史来路、前后传承和看得清楚(吴福辉教授语)的文学史现象。在我们看来,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进行初步的问题、边界和方法的探讨之后,应该向着‘现代文学化’的目标前行。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具有自身历史的独特性,但是不可能脱离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血脉联系而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链条上,当代文学也许只是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尽止的中国文学历史道路的一个小小的驿站。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学理上逐步完成相对完整的叙述,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和看得清楚的学问,这一长期、繁琐和细致的研究工作,需要当代文学史同仁的共同努力。”
张 亮:随着现代文学学科逐渐被经典化,一方面带来现代文学史学建构的成熟,另一方面,研究似乎越来越退守书斋,变成一种职业化的知识生产,丧失了与当代对话的能力。当代文学研究在借鉴其方法的过程中,会不会也逐渐面临这个问题?可否请您谈谈,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平衡“历史化”和“当代性”?
程光炜: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在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同时,如何保持它的敏锐的“当代性”?你是在说,它不仅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同时又能和当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息息相关。之前,我曾写过一篇讨论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的问题,涉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批评了一些沉闷的现象,说到一个学科方向在经过一个较长的活跃期之后,会有一个如何避免审美疲劳、陷入停滞期的忧虑。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与1980年代相比,确实沉闷了不少,鲜有活跃的思想争论、充满活力和拓展性的学术研究,很多一线学者或进入古代文学,或转向近代文学和思想史,有的还准备作“六七十年代”研究,主力阵容空缺后,它过去曾经拥有的相当成熟的“历史化”,确实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本身的衰落。这个现象,值得现在做当代文学的人充分警惕。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还不必担忧,因为很多学者都是以把“当下”带入当代文学史的方式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这些学者身上的“当代感”还非常鲜明和突出。然而,等大规模的、相对成熟完备和系统的史料学工作完成之后,会不会出现你担忧的这种情况,现在还无法评估,可能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四 问题和展望
张 亮:我感觉最近的课堂文章更偏重史料收集整理,早期那种立足于文本细读而勾连出社会语境的“重返”方式似乎削弱了,研究的视野在文本外部不断扩张,这样一来文学文本的内部空间会不会被挤压?不同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以“文学”进入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和有效性在哪里?
程光炜:你听了一个学期的课,也参与了讨论,已经能够感觉到“材料”与“问题”之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确实是这样。实际从去年初到现在整整一年时间,我们课堂上的文章偏重史料搜集整理,情不自禁地忽视了如何点出问题、用问题去牵引材料,这已经相当突出。我几次在课堂评论中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没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也许作者自己被材料淹没,还不知怎么从材料中脱身出来,总之,反映了博士生们在收集整理材料的同时,如何利用材料的研究能力和实际水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训练和摸索才能够逐步克服,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我的老师批评我材料引得多。你得让作者在实践中自己悟过来,自己觉醒。我有时候心里其实很着急,但也知道光急没用。
另外,你说的社会史视野会不会压抑文本空间的问题,也有可能存在,这得看作者怎么掌握尺度。有的时候材料不够,作品薄弱,就得用社会史充填进去,扩充作者作品内部的不足,释放其中的能量。假如作者材料较多,作品很强,再加大社会史难免就给人画蛇添足的印象。所以,有一个作者如何掌握尺度的问题。我近年写文章,喜欢在文体上变来变去,有时偏重材料,有时偏重文本分析,就是想避免你说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次次得手
张 亮:现在自媒体和电子化越来越发达,作家的言论、日记、对话等材料越来越分散、随意和易得,个人信息和当代事件也有了更多真假难辨、隐秘难寻的空间,这势必会给文学的外部研究带来很多问题。您认为,若干年后的“当代”文学研究,史料文献收集整理会出现什么变化?那时的“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又会经历怎样的新的“重返”呢?
程光炜: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现象。我现在主张先切出一个历史段落,比如以1990年代末为界,先做纸质上的作家相关材料,流落在互联网上的则暂时放下,等弄明白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后再说。以后的史料文献搜集整理是否会受到互联网的制约、限制和影响?肯定会有,但这已经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时我已经退休了。
张 亮:去年课堂上讲读的几篇关于杨绛、宗璞、汪曾祺的文章,我们的讨论,更多落在如何组织材料和集中论述、如何确立一种重评的史观等问题上面。就您看来,目前工作坊的研究与写作仍存在哪些问题?
程光炜:一个是这些作家留给我们的材料不够,还有一些材料游移在可以采信和不可以采信之间,这样你去开展他们的研究就会步履艰难。当然,也有利用有限的材料时,敏感度和开发问题的能力比较薄弱的问题。课下我跟不少学生讨论过,说“如果我来做,怎么怎么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我来说,不存在可以不可以做的问题,主要是应该怎么做、如何下手的问题,我觉得以后博士生可以在后一方面加强自己的能力,也即开发问题的能力。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你可以注意到,有些研究能力强的学者,即使在材料匮乏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有效的研究,是因为他们本人开发问题的能力较强。
张 亮:可否谈谈当下您比较关注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您对于工作坊之后的研究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程光炜:我只局限在作家层面来谈吧。我的估计是,对一些创作成就突出、作品获得文学界公认的作家,比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人,下一阶段,可以把重心放在他们的传记研究上面,如年谱、家世、地方志、文学地理等等。对一些存在争议、文学史评价还有待讨论研究的作家,比如张承志、韩少功、路遥、王朔等,我认为还要加大他们的文学史讨论,主要讨论文学批评、社会思潮对他们的“压抑”,其作品探索与当时社会的复杂纠缠等问题。我对张承志、路遥的评价比较高,可能与很多同行不一样,理由可能就是基于注意到了文学批评、社会思潮对他们“压抑”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文坛时尚的问题,这种文学时尚,就对路遥这种不受时尚影响、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有气象的作家非常不利。还有,就是希望重新开展对“30后”作家,比如王蒙、张贤亮、张洁、高晓声、张弦、李国文、丛维熙等的研究,从做年谱、传记开始,再深入到其他方面。这一代作家与前后几代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后,工作坊也可以分一部分精力去做当代文学“公案”的发掘、追寻和探究,比如“废都批判”“《马桥词典》抄袭问题”“二王之争”“王朔现象”“戴厚英现象”“张承志现象”等。这些问题我们以前做过,有的成果还不错,但仍然有空间和别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注意一下稍微边缘一点的作家。
关于这个文学史工作坊,最后还想提到2014年到2016年间,我与李陀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合作的“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坊的一部分。这个工作坊,主讲者是七八位在校和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其中不少学术亮点,在《放宽小说的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有所体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翻这本书。“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这个名称是杨庆祥老师提出的,组织工作也由他负责,对主讲者和其他发言者观点的整理,则由他的一些硕士生完成,应该感谢他们辛勤的付出。
结语

张亮:谢谢老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