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街》:一条街,一座城
摘要:被批评家李敬泽称为“乡野间的先锋”的王方晨,一个济南城的客居者,用系列短篇小说从容不迫地书写济南市井文化品格,创造文学济南新形象,用一条虚构的济南老街构建一座大城济南。“老实街”系列短篇小说引发的不仅仅是人们对正在流逝的市井人情、传统文化的哀悼,还有对儒家道德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与作用的严肃思考,更有对复杂人性及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度探问。
关键词:“老实街”系列短篇小说;市井人生;道德品行;济南文化
作为山东新生代作家代表,王方晨执着于中国乡土文化的剖析与追问,他用三十多年时间、六七百万文字,以他的家乡金乡县为原型,构建了一个乡土文学小镇“塔镇”。随着《公敌》《老大》《芬芳录》等长篇小说的出版,“塔镇”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一个地理概念、齐鲁文化的重要文学地标。近几年,客居济南的王方晨又以《大马士革剃刀》《鹅》《世界的幽微》《阿基米德的一天》《歪脖子病不好治》《弃的烟火》《八百米下水声大作》《花事了》《天在兹》《大宴》等系列短篇小说,为山东省会城市济南搭建了一条“老实街”。王方晨笔下的“老实街”是一条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中被拆迁掉的济南老街,它具备济南独有的地理文化风貌。“老实街”系列小说主要叙述了拆迁前后“老实街”以及附近街巷所发生的事情,每篇小说都以“老实街”居民复数的“我们”作为叙述人,以一、二个人物为中心。整个系列小说人物关系前后照应,故事情节有头有尾,写作风格完整统一。作为市井济南缩影的“老实街”,又成为了拥有两千七百多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古城、自开埠一百多年的现代都市——济南的文学地标。
一、老实街里的市井人生:平凡中见奇崛
王方晨将文学世界的“老实街”安放在现实济南的市中心“狮子口街”和“旧军门巷”之间,“老实街”上有公馆、大杂院,还有面馆、药铺、竹器店、纸扎店、卤煮店、杂货铺等商业店铺,街口还设计了一眼“涤心泉”。“老实街”的居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既有锁匠卢大头、鞋匠宋侉子、竹器匠唐老五、剪纸世家老祁、开馍馍房的苗凤三、开杂货铺的鹅等从事传统行业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小学校长芈老大、国营照相馆摄影师白无敌、排爆警察邰浩、电台主持人朱小葵、省发改委主任张树等在现代社会体制中求发展的人。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自觉与现代文明进程接轨的自开埠现代商业城市,拥有独特自然风貌、丰富历史遗存、深厚文化积淀,汇集了各类人才,“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作为济南市声望极高的老街巷“老实街”, 它的这些看似是一群凡夫俗子的居民们,却都各自深藏着不平凡,有着传奇般的前世今生。
《大马士革剃刀》里开百货铺的左老先生左门鼻,家里居然藏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大马士革剃刀,他用这把极其珍贵的名刀给自己剃头。左家在民国时期是济南莫大律师家的马夫,莫律师随国民党去了南方,临走前把房产全部赠给了左家。然而,左门鼻没有将莫家大院据为己有,坚持住在大院的厢房,维护着莫家大院原来的样子。左门鼻秉承着祖传的古风遗训,自己在狭小的偏房开着百货铺子度日,童叟无欺,甚至作赔本买卖,静静地等候着莫家人的回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房产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大律师。《阿基米德的一天》里绰号“阿基米德”的穆泽宽、穆泽厚兄弟,他们深居简出,像遗世独立的古代名士隐居在“老实街”的胡同深处。兄弟俩离群索居,终身未娶,相依为命,互相护持。兄弟二人身世复杂,他们是解放初逃跑的大律师穆先生遗弃的孩子,母亲也是被穆先生包养的情人。穆大成年后在大学当校工,患有自闭症的穆二则痴迷于化学实验,终身宅居家中提炼化学晶体。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从不参与“老实街”的是是非非,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没有沾染俗世半点尘埃。最后,兄弟俩死在一处,在他们床下里却意外地冒出一股清泉,那股神奇的清泉正是兄弟俩纯洁心灵的具象化载体。《阿基米德的一天》里还有一位与穆二一样喜欢摆弄瓶瓶罐罐的奇人裘七郎。北边高都司巷的裘家,早年间是历城县里的名门望族,“这裘七郎不光交游不广,连自家亲友也无往来,冷心冷面,每日携了三五小童泛舟大明湖。小童也有长大的时候,大则遣散,因之身边小童不断。”[1]这篇小说里还有一个畸人艾小脚,他自幼习医,医术高明,但是身为五尺男儿,却喜欢扮女装,尤其喜欢裹脚。《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的主人公小耳朵也是一位奇人。小耳朵是街道劳保厂仓库管理员,泉城义务地下水位播报员,听觉敏锐,自言能听到地下八百米下的水声,老街坊则猜测他跟老道学了法术,会“大搬运”,能探知地下埋藏的宝藏。小耳朵虽然生活艰辛,下岗自谋生路的时候也从未想要利用自己的天赋异禀来改善生活,而是恪守本分,一直用超常听力为大家义务播报水位,寻找丢失的物品。异禀的能力并没有让小耳朵的生活与众不同,他呵呵地同普通人一般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小耳朵被邻居桂小林灌醉,被他拉着去听宝、探宝才发生变化。“老实街”上的人在这一刻流露出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小耳朵彻底失去了对“老实街”的美好幻想,借儿子的手剪掉了自己的耳朵。失去耳朵的小耳朵由异人恢复为常人。《八百米下水声大作》里的另一位奇人是老祁。老祁头出身剪纸世家,幼习剪纸,练就了一手高超剪纸本领,掌握独门绝技“剪毛功”,剪人剪物,都栩栩如生、有毛茸茸之感,在“文革”时期还剪过天安门城楼上的伟人像,被省“革委会” 作为国庆十七周年献礼之作,大张旗鼓地送去了北京。大儿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死于非命后,伤心欲绝的老祁丢掉了剪子。90年代老祁头重拾故技,且收小耳朵患自闭症的儿子为徒。
“老实街”历经沧桑的中老年人中隐匿着奇人,不管你是否发现,他们都自身光华闪烁;“老实街”的年轻人中也出没着异人,他们在关键时刻发出炫目的光辉,平凡中见奇崛。《鹅》《世界的幽微》《花事了》《天在兹》中竹器匠唐老五的女儿鹅,是一个未婚先孕的美丽女子,一个一直在追寻爱情却没被爱情眷顾的女人,但是,她却不悲戚愤怒、不自怨自艾,顶住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精神压力,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平静地生活在“老实街”。鹅认识到无论是“老实街”土生土长的张小三、马大龙,还是“老实街”之外的老常、大老赵、高杰,尽管他们也都不是完全无情无义之人,但是,他们贪恋的是一时欢愉,不是她追求的心灵契合、敢于担当之人,所以,她游走在他们之间却未嫁给其中的任何人。鹅是一个大胆叛逆、敢于袒露生命真实需求的女子。“老实街”没有因为鹅未婚先孕而排挤、拒斥她,他们愿意相信古代神话,默认鹅的儿子是踏石而生,这种的认知可以看成是“老实街”人对鹅个人名誉的善意保护、对“老实街”道德名声的维护,鹅却公开地带着她的私生子去喊每个情人“爸爸”,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举动,“让老实街的道德表象轰然倒塌”,也“实现了一个女人最大的生命抗争”。[2]遗憾的是鹅对命运的一次次抗争没有换来她所追寻的幸福爱情,反而击垮了她最后的人生信念,她向成功商人高杰屈服,让整条“老实街”走向了覆灭。《歪脖子病不好治》《弃的烟火》里的朱小葵作为从“老实街”走出去的年轻人,践行着“老实街”的信条,为了帮助受到欺凌的弱者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在“老实街”即将走向覆灭时拼尽全力进行抵抗,不惜丢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排爆警察邰浩,尧大司农后稷的后代、二十四孝之一弃的子孙,在女友朱小葵失踪、“老实街”被黑社会恶势力所支持的光背党围城的时候,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丰润与秀拔,整个人容色黯淡、瘦骨嶙峋,而且灵魂出窍,见人就泪光闪烁,像游魂一样呆傻无能,忍气吞声。直到排爆中受重伤后遇到因为反抗恶势力强拆而受迫害的吴司机,他才振作起来。身体上的炸伤让他走出了心灵的创伤。邰浩不顾家人阻挠和“老实街”亲朋好友的反对,单枪匹马、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之路。作为排爆警察,他在侦破黑社会开发商和省委高官制造的爆炸案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一个颊上微微有疤的年轻警察长久仰望苍穹”的场景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时候,后稷、弃的子孙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了。
老实街将这些各具特色、自带光华的新老市民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事着不同行当,在不同领域谋生,在“老实街”的道德规范滋养与影响之下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相互扶持帮助,形成了一个温馨惬意的社区群体,但是,在商业化、现代化的拆迁大潮之下,“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3]
二、“老实街”里的道德品行:老实宽厚与虚荣胆怯并存
作为当代齐鲁文化重镇、山东省府所在地,济南无疑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老实又是它们的基础。“以‘老实’命名一条老街道可以理解为一种德性,再扩而大之可以理解为一套良知系统。”[4]显然,王方晨将代表济南城市风貌与精神的老街巷直接命名为“老实街”,是有着宏大的文化意愿的,他不仅要构建一条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老街老巷,还要探讨在现代进程中中国本土文化——儒家道德文化的命运与作用。
尽管地处繁华闹市,“老实街”是一条古风犹存、古训犹在的老街。在“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大马士革剃刀》中,王方晨就明确写道:“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为立家之本。老实街的巨大声望,当源于此。”“学老实,比老实,以老实为荣,是我们从呱呱坠地就开始的人生训练,而且穷尽一生也不会终止。”[5]对老实的尊重与信仰,使“老实街”居民形成了一个想象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彼此互相寻求安慰,驯服异质,获得了安全感。在《八百米下水声大作》里,作家又再次感叹到:“我们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却能把老实街过成熙熙和乐的世外桃源。多少年了,老实街从未弃老实之风,邻里和睦,厮抬厮敬。伤和气的事,不能说没有,也是少见。”在小说中王方晨不断地书写“老实街”人的善良仁义、温柔敦厚、淡定从容、处惊不变。
《大马士革剃刀》里左门鼻仁义厚道,诚实友善,是老实街的道德典范,正是在左门鼻这些德高望重长者的垂范之下,老实之风深入到“老实街”的骨肉肌理之中,“老实街”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古韵,“老实街”人也养成了强大的道德自信。左门鼻的言行不仅熏陶浸润了土生土长的“老实街”人,也感染规范了“老实街”的外来者,连地痞流氓也很少敢来老实街滋事惹乱。作为老街的新来者,理发师陈玉伋很快被“老实街”人的崇高道德情操所感动,激发了他善良淳厚、腼腆老实的品行,他高超的理发技艺和周到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左门鼻的信任和赞赏,左门鼻要将名贵的大马士革剃刀赠予他。左门鼻两次真诚赠刀,陈玉伋两番执拗送还,赠送之间成就二人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友谊,见证了二人的崇高道德品行,也成就了一段“老实街”的当代佳话与美谈。《花事了》里出身于历城县名门望族、民国时期曾享受过繁华富贵的老花头,安于现在平淡的市井生活,面对家族与个人大起大落的命运,不抱怨不后悔。老花头古道热肠,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成就了老实街一对对有情有义的佳偶眷侣。《歪脖子病不好治》里的雅士名流芈芝圃老先生,历尽人生沧桑,智慧豁达,淡泊名利,气定神闲,宛如“老实街”的一根定海神针,不断给后进者人生指导和帮助。《阿基米德的一天》《鹅》里的“老实街”居民,不去纠缠穆氏兄弟的复杂身世以及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不去干涉鹅未婚先孕和开放式的性为,他们有意遗忘或者遮蔽这些尴尬的事实,让这些“异人”在“老实街”安稳地生活下去。《弃的烟火》里,面对恶势力光背党的围困示威,“老实街”居民没有惊慌失措,仍然按部就班地按照原来的节奏生活,他们以静制动,无视入侵者的存在,让恶势力的示威落空。
仁义厚道、淡定从容、处境不变,这是“老实街”的品行,也是“老实街”的能耐。靠着它,百余年来“老实街”平稳地度过了“兵燹天灾,兴亡分合,世变风移”,任凭世界兵乱匪祸、政变风潮,以老实为荣的“老实街”居民以不变应万变,把“老实街”过成了世外桃源。难道世界上真有桃花源般的世外桃源?难道王方晨是在悲悼被现代化大潮侵袭而渐行渐远的市井道德和人间情味?为那些已经被拆迁或者正在被拆掉的老街老巷唱挽歌?代替“老实街”上已经“风流云散”的孩子们感伤怀旧?王方晨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王方晨手持大马士革剃刀,将锋利的刀刃指向了隐藏在“熙熙和乐的世外桃源”背后的“幽微的世界”,揭示人性复杂多面的本质。
大马士革剃刀成就了左门鼻与陈玉伋两位老实人的友谊,也见证了友谊大厦的崩塌时光。被大马士革剃刀剃掉了全身毛发的老猫蒙羞沉水而亡,“老实街”居民将窥视的目光与猜忌话语投向了外来者陈玉伋,在“老实街”巨大道德气场的压迫之下,陈玉伋蒙羞病逝。道德具有示范性、指导性,道德也有规范性、压抑性。“良知系统一旦固化,其对个人行为的宰制就是全方面的和铲平主义的。”[6]面对虐猫事件,“老实街”居民发出了“谁让老猫蒙羞,也是让我们老实街居民蒙羞?能把一只猫剃得如此之光的,究竟是怎样一只魔鬼的手”的慨叹与追问。如果说让无害的老猫蒙羞自沉的人具有魔鬼之手,那么,让无辜的老实人蒙羞而亡的人则具有魔鬼之心。具有极高道德的“老实街”居民都间接性地参与到了虐杀老实人陈玉伋的行动之中,而小说结尾暗示人们,直接虐杀老猫进而导致陈玉伋死亡的“魔鬼的手”竟然来自“老实街”道德典范左门鼻。道德是后天熏陶、培养的结果,修心才能养性,但是,再高尚的道德也不能彻底消除人心的暗流。左门鼻、老花头这些“老实街”的道德典范,他们的心底也潜藏着阴暗的角落、幽微的世界。虚荣心、嫉妒心打破了左门鼻的仁义厚道之心,面对外来者陈玉伋日益高涨的道德声望和人气,左门鼻失去了他的从容与淡定、诚实与厚道。在“老实街”上,老花头是以古道热肠、慈祥和蔼、积德行善、淡泊名利的长者形象而存在的,出手撮合成全了许多佳偶良缘,但是,他却一直没看透鹅该找一个怎样的归宿。其实,不是老花头看不清鹅的需求,而是他不敢正视自己内心涌动的欲望。超脱了世俗功名利利禄羁绊的老花头,能控制住自己的灵魂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肉身。在故事的结尾,老花头对于鹅身体的贪恋欲望暴露无遗。由此可见,用强大理性建立起来的道德终究抵抗不过人的七情六欲,月老花神般的老花头终究也还是个有着血肉之躯的普通人。“老实街”居民,出于自私愿望,混淆视听,阻止穆氏兄弟年迈的父亲前来找寻失散多年的儿子,让穆氏兄弟孤独终老,至死也没品尝到来自父爱的亲情暖意。“老实街”对穆氏兄弟复杂身世的有意遗忘,对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的不干涉,一方面显示了“老实街”的善良厚道,包容豁达,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老实街”的敷衍塞责、自私冷漠。穆氏兄弟这对奇人被隔绝在“老实街”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之外,自生自灭,以至于死去多日才被人发现。正如在“老实街”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张树所言,“你们封杀了阿基米德。”《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的“老实街”居民们,听说小耳朵具有“听宝”的本领后,贪婪之心爆发,使计谋引诱小耳朵给自家“听宝”发财;小耳朵的父亲因为记恨小耳朵免费给外人“听宝”却忘了自家老子、因为嫉妒孙子跟剪纸大王老祁头情同祖孙,居然不顾孙子的身心健康,将患有自闭症的孙子藏了起来。“老实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以“老实”为人生信条去掩盖彼此间“不老实”的事,对此,彼此之间虽心知肚明,却又互相极力掩饰。
“老实街”居民遵循着百余年来祖辈制定的道德规范,他们信奉“老实人的武器,强大莫过于老实” [7]。老实曾让“老实街”人拥有了大智若愚的风范、处惊不变的气度,他们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兵燹天灾,兴亡分合”的百年。面对着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强大道德自信的“老实街”人依然相信:“要变你就变,反正你把老实街搬不走。老实街在这儿,东有旧军门巷,西有狮子口街。涤心泉流了千百年,说不流就不流了?”[8]事实上,一味的老实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激烈挑战,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时代。在90年代盲目无规划的大规模城市拆迁与扩建之中,存在了百年之久的“老实街”消失了,流淌了千百年的“涤心泉”也断流了,“老实街”的儿女们四散飘零了。作为百年老街、名街的“老实街”之所以走向衰落与消失,除了城市主政者决策不当以外,也与“老实街”人的道德品行、文化性格有关。老实背面是软弱胆怯、胆小怕事、不思进取。善良厚道的“老实街”居民“一遇类似来者不善的事,我们老实街的居民都想不起该怎样阻止” [9]。当街痞进入陈玉伋的理发店时,“老实街”人都知道此时凶多吉少,却没有人敢出头阻挡;当黑社会光背党气焰嚣张地横行在老实街,甚至肆无忌惮地跳入被“老实街”人视为生命泉的涤心泉洗澡的时,“老实街”男女老少居然都隐忍了,全街一片沉默死寂,无一人敢挺身而出、反击反抗,只有在经历死亡洗礼走出心灵创伤的邰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面对“老实街”居民整齐划一的“退一步海阔天空”规劝声,邰浩宣称自己不再是“老实街”人,他从这个安全的共同体中退出了。“被玷污的涤心泉,映照出了我们心底的懦弱,我们就像一个倒栽葱,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0]“老实街”居民面对强权统治、暴力奴役,只会忍让退避妥协;他们屈服于强权暴力,精神麻木、身心疲劳。当“老实街”居民们准备联名抵制拆迁的时候,“老实街几个有年纪的老祖宗,已主动与政府签下了拆迁协议”,面对这种阳奉阴违的卑劣行径,“老实街名望最大的左老祖宗发话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既为老实街的居民,还是老实些。跟政府对抗没有什么好处?宽厚所街不宽厚了,老实街不能不老实。千古同理,老实人不吃亏。”[11]在这种思维和心理支撑下,“老实街”和它的居民在现代化大潮之中不可能摆脱流散飘零的命运。“老实街”的终结者是现代化拆迁大潮,也是“老实街”居民固守的老实原则。王方晨将这条老街命名为“老实街”,既是对温暖惬意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悼念,更是对它的反思与质疑。
三、老实街与济南形象
“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12]城市形象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物理结构之中,还存在于虚构的文本之中,所以,当代人谈起济南的时候,首先就会想起刘鹗、老舍等近现代作家对济南的描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城市“本事”不会不言自显,每一种城市形象、城市文化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每一类人群都会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不同类群的人对城市的解读与想象是不同的,他们提供给人们的城市读本也各具特色。当“把一个人同某一个城市联系在一起”时,“城市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他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 [13]当一个作家在描绘某一个城市的时候,必然会把个人的生命体验、价值立场、文化理念、人生理想等代入其中,此时的城市形象就是一个文化、文学的结构体。
作为历史文化悠久的现代都市,济南的城市面向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现代化步伐比较平缓的城市,济南的城市文化性格有其独特而稳定的一面。来自鲁西南乡村、善于书写乡土文化的王方晨,在一次访谈中曾表达过自己创作“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心理感受:“‘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创作,将让我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了自己亲切的村子。”[14]王方晨没有写繁华喧嚣的商业新街、时尚炫目的商界精英,而是选择了一条具有古风古韵的老街作为济南城的代表,让老街里土生土长的居民们带领人们走近济南、认识济南、品读济南。“我们老实街是老济南的心脏,青砖黛瓦,那些屋脊,山墙,影壁,斗拱,挂落,哪一样都让人看不够,哪一样都有讲究。”[15]“老实街”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济南是“都市里的村子”。“都市里的村子” 是济南这座城市的一个侧面,也是济南和老济南人的底面与底色。王方晨写出了老济南人的老实善良、宽厚谦逊、安分守己,写出了这座城市对传统齐鲁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尽管“老实街”系列小说重点写的是90年代一条老街上的济南风貌和济南人生活,但是,王方晨没有让笔触止步于“老实街”、停滞于90年代,而是不断地前后张望、左右逡巡,通过对历史悠久具有地标性的山水、建筑、街道等物理意义空间和身世复杂人物的社会性呈现,写出济南独特的地理文化风貌以及城市发展史,把老济南的风韵风情、文化性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不过,王方晨并没有沉醉在由“都市里的村子”滋生的“亲切感”所带来的舒适与安逸之中,而是一方面探入“亲切感”的背后,揭示其背面所包含的虚荣守旧、软弱胆怯等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正视现代商业文明与与欲望文化,写出新生城市文化对传统文化性格的挑战以及传统文化性格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不适与危机。“老实街”上的两眼清泉——“涤心泉与“浮桴泉”的存在与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济南这座以泉水而闻名天下的现代城市的兴衰起伏。“涤心泉”的清澈泉水滋养了“老实街”世世代代的居民,最终却没能将“老实街”居民的内心涤荡如初,反而成为了“老实街”居民失去自我的起源地,这意味着传统文化纵使有悠久的历史,也抵挡不住商业大潮的冲击,甚至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浪潮之中退化为不堪承受的道德负担。阿基米德兄弟家中出现的“浮桴泉”让兄弟俩不用再到“涤心泉”取水,新泉的出现切断了他们与“老实街”居民之间存留的唯一联系通道,使本来孤独寂寞的兄弟俩彻底与世隔绝,也给阿基米德兄弟的命运增添了一份凄凉。具有传统文化名士风范的阿基米德兄弟的去世与新泉水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文化守卫的失败以及新城市文化精神的出现,传统文化的消逝带给人的是绵绵的凄楚与哀婉,而新的城市文化精神所拥有的活力与进取精神也是不容回避的。
被批评家李敬泽称为“乡野间的先锋”王方晨,一个济南城的客居者,用系列短篇小说从容不迫地书写济南市井文化品格,创造文学济南新形象,用一条虚构的老街构建一座济南大城。“老实街”系列小说开拓了王方晨文学创作新领域,也创立了他城市写作新风格。不论写乡村,还是写城市,王方晨的“哲学底色和深度”不变。正如胡平所言,他所要探索的始终是“人性、文化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16]。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短篇小说引发的不仅仅是人们对正在流逝的市井人情、传统文化的哀悼,还有对儒家道德文化在现代过程中的命运与作用的严肃思考,更有对复杂人性、幽微世界的犀利追问。
参考文献
[1]王方晨:《阿基米德的一天》,《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
[2]房伟:《令人谔异的“幽微”世界——论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短篇小说》,《文艺报》4月21日。
[3] [5] [11]王方晨:《大马士革剃刀》,《天涯》2014年第4期。
[4] [6]马兵:《市井道德与人间情味——王方晨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文艺报》2014年8月15日。
[7] [8] [9] [10] [15]王方晨:《弃的烟火》,《山花》2017年第9期。
[12](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3]张英进:《中国现代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4]舒晋瑜:《王方晨: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亲切的村子》,《中国作家》2016年第5期。
[16] 胡平:《先锋性、哲学底色和深度》,《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2日。
 更多
更多

格非、杨好:生活充满烦恼,但人可以快乐
两位作家认为“没有经验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一个好的作家,有很好的修养,有很强的思考力,才能捕捉住神来之笔。
 更多
更多

李今:为建成资料、档案中心的文学馆亲历散记
40年后,不能不忆起从零起步,初创时期的艰难。
 更多
更多

诗歌 | 崖头如碑(组诗)
崖头上的老人与崖头下的村庄 是两个世界,中间一条石板路间隔

散文 | 薄荷的里下河奇旅
在里下河这片钟灵毓秀之地,我,薄荷,悠悠然开启独属于自己的奇妙旅程。

散文 | 梅雨有信
原来这江南的梅雨信,不过是大地蘸着无尽水痕,写给凡间的一封封情书。它无声低语:且让日子慢些,看草木吸饱水汽,山色渐渐朗润,待云开雨霁,自有明媚铺陈开来——生命之丰润,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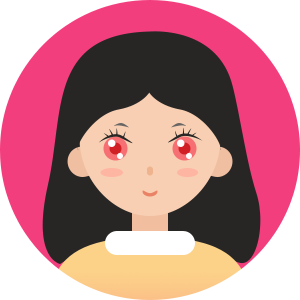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散文 | 情因黄河起
恍如隔世,在横亘着新与旧的堤坝上,俯视星空下古老而又年轻的黄河,仰望黄河上璀璨的星空,与时间老人默默对视,与万物共怀的依是归来的羞涩少年。

散文 | 忆母亲——井水浸透的端午
母亲将溽热的端午喧嚣、活色生香的故乡光景,连同她深沉无言的爱,如同箬叶包裹的糯米,一并封存于时光的静水深流;那井水的寒凉浸透了粽子的糯软,也浸透了记忆深处母亲温热的指尖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