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克兰的炽热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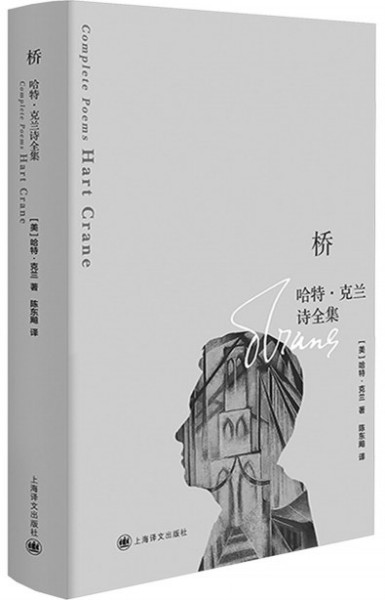
有一次与诗人翟永明做文化播客,老朋友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写诗? 我答曰:写不好啊! 我没好意思告诉相识二十余载的翟姐,当年我也写诗,不仅写了,还多次发表,收入诗集,好在没用现在的名字。二十年间,偶尔我也动念,想重拾写诗的笔,可是当我亲眼目睹同龄人站在年轻人中间,朗诵那些自以为是不知所云的句子,我的那一点儿勇气就消失了。就我所见,大多数自诩为诗人的家伙,无非在干同一件事情:将微不足道的自我感动加以稀释,转换成跳跃的、有节奏的文字蒙太奇。在这种看似巧妙的卖弄中,既没有真挚的情感,更没有深厚的心智。我甚至怀疑他们中间有些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诗,就像猫根本不清楚它拨弄的球体到底是乒乓球还是毛线团。以赛亚·伯林说,人们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假定受到过多的审视。一旦有人要求他们探究这些假定背后的预设或者真相,他们就浑身不自在。另一方面,伯林也承认,探究这样的真相也可能“瘫痪”行动。在诗歌的问题上,我大概属于后者。
这时候读《桥:哈特·克兰诗全集》,感觉自然很特别。在哈特·克兰(Hart Crane)的诗歌里,我能感受到某种矛盾的东西,其冲突之大关乎性命。然而正如诗人所思所写,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在面对“什么是诗”的问题——是否具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我认为是判断诗人有无巨大潜质的试金石。通常来说,这种意识会对诗人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予以统摄、形成平衡,尽管对克兰而言其效果显然有时间上的限度。
那么,哈特·克兰究竟是如何看待诗歌的呢? 这要从两方面来判断。一是看他的诗歌创作,二是他的诗歌评论,并将二者联系起来理解。《桥》这本诗集收录了克兰的一篇题为《论现代诗歌》的小文,我觉得相当重要。文中诗人宣称“诗歌是一种建筑艺术”,这怎么解释? 是指它们应该有类似的结构吗? 还是指共通的韵律感? 又或者他想到了德国人谢林所谓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试图改造这般流俗的表述,从而让诗歌与建筑互为喻体? 仔细读下去我发现诗人的想法远不止于此。在他看来,建筑要承担桥梁的隐喻,以便诗歌与科学互通往来。
需要强调的是,克兰所说的“科学”不能跟科技划等号。准确地说,此处的科学,指的是柏拉图意义上的人类理性。因此,诗人在他的诗歌创作里想达成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人的情感与理性之间架起桥梁。为何这部诗集中最为重要的组诗以《桥》命名,道理就在这里。
可是怎么说呢? 克兰的诗论远不如诗歌本身那么吸引人。他的表述过于诗化,缺乏连贯的逻辑。好在他精彩的诗句更会说话——在组诗《桥》的最后一篇《亚特兰蒂斯》里,克兰将柏拉图描写的亚特兰蒂斯视为艺术的至高理想,在那里人类的情感与理性高度统一,一切与爱有关的知识都处于和谐与条理之中。我认为,这才是哈特·克兰对诗歌的理解:一切与爱有关的知识。
将《亚特兰蒂斯》与《论现代诗歌》相互参详,关于诗人的重要事实就逐一清晰了。在诗中哈特援引柏拉图,在文论里他大幅引用的则是湖畔诗人柯勒律治。而柯氏有一句名言,想必哈特·克兰非常熟悉。柯勒律治说,一个人生下来,要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要么是柏拉图主义者。毫无疑问,哈特·克兰是一个钟情于理念的柏拉图主义者。难怪年长20岁且风格迥异的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暗地里喜欢揣摩他的诗,因为那里面有“柏拉图”。
明白了以上几点,克兰的诗歌就没那么晦涩了。同时,我也就明白了他在现代英美诗歌传统中的位置。有人说哈特·克兰的诗歌深受T.S.艾略特的影响,这话不准确。克兰与艾略特的诗的确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但是我想认真读完这本诗集的读者都会感觉到,克兰对艾略特的反抗! 这一点,从他们截然不同的核心隐喻里就能辨识出来。如果说艾略特的核心隐喻是荒原、是废墟,那么克兰的核心隐喻则是桥、是塔,是白色的建筑群,更是有别于荒野自然的“人造物”。这样的隐喻或象征,足以将克兰与艾略特区分开来,并与惠特曼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虽然惠特曼的诗观远比克兰更加恢弘更加复杂,但是他对工厂、城市、建筑等“人造物”的吟诵,肯定深深地影响了克兰这样的后来者。
这是一种浪漫的美国精神,可惜对于哈特·克兰而言过于沉重了。在《哈特拉斯角》一诗中,诗人一再呼唤惠特曼的归来(也是文明的归来),用“信仰的音节”振奋“今后岁月的记录者们”,然而他终究辜负了自己的祈愿,短促的一生燃烧得那么暴烈——1932年,33岁的诗人从横渡墨西哥湾的轮渡上投海自尽。“因此是我走进了崩坏的世界/去追索幻想中爱的陪伴,它的声音/风中的一瞬(我不知被抛向何处)/但并不长久保留每一个绝望的选择。”(《崩坏之塔》)也许,当世界袒露了它那残酷的真相,行动(包括诗歌创作)就必然“瘫痪”。崩坏之塔,离荒原不远了。所以,我将克兰视为连结惠特曼与艾略特的脆弱一环。
然而幸运的是,哈特·克兰仍然滋润着无数爱诗的人。如今,《桥:哈特·克兰诗全集》有了完整译介,读者终于可以像读同样早逝的王勃、雪莱以及兰波那样,去亲近一颗炽热而幽微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