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好奇心让我不愿意轻易对事物下结论
来源:《花城》 | 2017年03月24日08:11

◣何平 | 三三 ▼
何平 (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2013年,你的《离魂记》出版时,你说:“我可能是全上海最懒的小说作者。”我觉得你现在仍然是。你自己觉得呢?
三三 (青年作家):我觉得自己正在向“长三角洲最懒的作者”发展,上海已经不足以局限我了……
何平 :“三三”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而且我喜欢“三三”这两个字的读音。为什么是“三三”这两个字呢?别有深意,或者就是随意?
三三 : 因为真名叫“姗姗”,笔名随意取了谐音,但用这个笔名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三三”其实是“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我很推崇的价值守则,其中有一种包容性的寓意。另外,说到“三三”的读音,有一种很散漫的气质,而且平舌音偏向江南方言,宋词里有“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大致就是那种感觉。
何平 : 我最早读到你的小说是《离魂记》。2014年,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读”要找两篇年轻作家“故事新编”作为年轻大学生进入鲁迅《故事新编》的铺垫,我选了一篇笛安的《广陵》,另一篇就是你的《离魂记》。大概同样生于1990年代,学生很喜欢你的小说,读得也仔细,仔细到他们去查故事可能发生的时代有没有草莓?仔细到他们想问你为什么王宙洗的是草莓不是其他。我也好奇为什么是“草莓”?
三三 : 法语里的名词是分阴阳性,如果植物也可以这样分,那我觉得草莓应该属于阴性,是一种女性特质很强的植物,甚至会带有一些情色的意味,类似的植物还有樱桃、桃子等,但樱桃有些太现代化;桃子则又太过笨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人拿着一筐桃子在河边洗,似乎就没什么美感,不如草莓轻盈。而王宙洗草莓这个行为,其实是暗含着一种对女性的屈服在里面的。
何平 :《离魂记》封面有句话说:“无限接近王小波,传奇也可以很现代。”可能就是指的《离魂记》这一类的小说吧?我在上课的时候和学生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两个作家值得关注,一个是王朔,一个是王小波。王小波小说面子是好玩,里子则是智慧和对世界的不看好。王小波的文学气质很难学,你基本把它接过来了,但你这一类小说并不多。
三三 :写《离魂记》这类小说时,我已经读过王小波的很多小说,王小波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可能是《青铜时代》,讲长安城里充满戏剧性的风起云涌,或者是《黄金时代》,其中融合了作者对苦难的切身体验,但我最喜欢的是《白银时代》,那本书里有对未来魔幻的想象,在一个银子的世界里,所有人物都在分崩离析。我所喜欢王小波之处,并不是他小说背后有什么寓意,而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浪漫。
那时候我选择去写传奇改编,并不是刻意想模仿王小波。不过,撇开文字不谈,我和王小波在生活中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都很刚毅,越是身处逆境,越是偏要逆流而上;再比如我也在沉默中思索过无数问题,写小说时大可以侃侃而谈,但本质上是沉默而疏离的人。
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想接近的作家,那应该是马尔克斯。在写完《离魂记》之后的几年里,我无意中得知,原来马尔克斯也是王小波的偶像,那种感觉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老师。我非常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想象力,以及那种表演感。称之为“表演感”,并不是说它虚假,而是读马尔克斯的小说时,我感觉作者是冷眼旁观的,作者早已明白了一切本质性的道理与结局,能感受到那种哀伤是如此极端而又节制。
封面上印了“无限接近王小波”,我其实是很羞愧的,差点买一升修正液去书店把这行字涂掉(捂脸)!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散发着浓浓的傍名牌的感觉呀,同时这样的概括也局限了我自己,我的三棱镜能折射出多种光芒,而王小波风格只恰好是那时最耀眼的一道。何况,也不能真的和王小波相提并论,我和王小波之间大概隔了至少3个冯唐。
何平 :可能你并不想,也确实没有王小波那么深刻。比如你说《白雪公主的四个结局》:感觉有点太抖机灵,而不像是小说。其实,小说也不一定就是沉重扎实一路,抖抖机灵也很好。我恰恰看重你小说的机灵劲儿。
三三 :我们生活的密度会因为输入的信息而改变,在我看来,抖机灵的故事会减少这种密度,使生活轻盈上扬,而注入深邃情感的小说会增加密度,使日常生活沉淀下来,前者令人快乐,而与后者相匹配的则是内敛的思考。
我个人更倾向于把小说当做一件严肃的事,让它区别于故事、创意的,是小说中的情感。人们也会为花枝招展的小故事感到惊喜,但类似《白雪公主的四个结局》的小故事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眼前景色虽好,可是看过也就忘了,无法留下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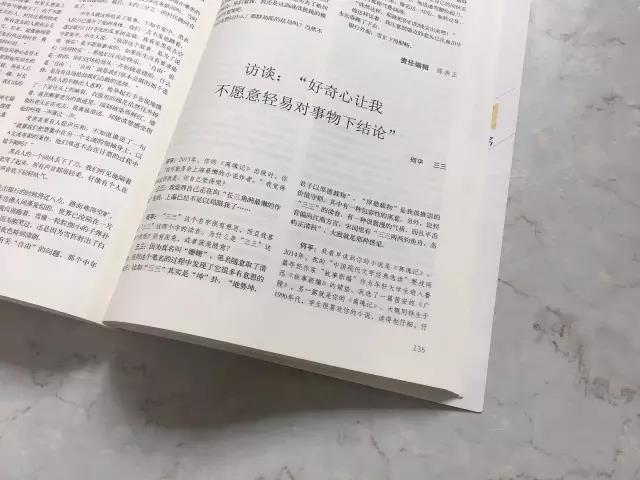
何平 :还有就是想象力。我觉得你《离魂记》《白雪公主的四个结局》《奔月》这一类的写作不失为一种好的训练想象力的方式。我一开始看重你的也是这一类“故事新编”。
三三 :我一直把想象力用作某种开拓的工具,不仅为了去讲述一个新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从宏观角度来说,更是为了打破固定的模式,朝未知的方向探索,这样每篇小说才会有新的生命力,而不仅仅是对过去自我的复制。我想象力的来源大概是好奇心,好奇心让我不愿意轻易对事物下结论,相反,保持开放的心态,相信各种突如其来的可能性与改变。
除了“故事新编”,我还会写一些带有想象的荒诞故事,但那些故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一度让我很迷惑。比如说,我写过一个进入中年危机的男人对衰老充满恐惧,他时常梦见自己掉牙齿,每次做这样的梦都让他非常惊恐,但在经历许多次类似的惊恐之后,他选择把自己所有的牙齿都敲落;再比如有一个工作很忙碌的人,陪老板坐直升机去拜访客户,在飞机上,他逐渐变成了一只长颈鹿,随着躯体的增大,他感到很闷,在他再三恳求之下,同行的老板终于同意打开机舱让他透透气,但就在他把头伸出去,无比满足的时候,他的脖子被直升机的螺旋桨削断了……
我觉得好的小说是有序的,想象力应当向整体屈服,而不能占领整个舞台。
何平 :你的另一类小说沉身中国式家庭的内部。和“抖机灵”的那一类小说不同,你这一类小说异乎寻常的冷且静,是一种“剥开”和“揭破”的写法,你几乎不抒情。就像我微信和你聊的,你对各种各样的“家庭”方式很恐惧,被你剥开和揭破的家庭也是种种不堪。这里有超乎你年龄的“寒冷”,这种寒冷既是故事本身,也是你不动声色的叙事推进。
三三 : 人生中的大部分关系都是可抛弃的,但血缘关系是强制性的,无论是否愿意,有些名字生来就出现在户口簿里,以至于家庭成为一种很特殊的存在。在家庭这个狭小的框架里,每个人仍然会有自己的秘密,当个人的空间遭到家庭成员有意或无意的侵犯时,那些隐忍的情绪便暗中酝酿。
我和父母相处的方式比较清淡,不常与父母分享情感,写的小说也不会给父母看。大概也是因为我悲观,总以为深入了解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种种误解,而且我也不希望父母因为了解我而对我产生怜悯、内疚、敬畏等各种多余的情感,那会让人尴尬,因此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关系。
爱丽丝·门罗在《亲爱的生活》末尾有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家人之间的感情,那些留下伤害却也被迫和我们拴在一起很多年的家人:“我们总会说他们无法被原谅,或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
何平 : 甚至,你的写作,阴冷荒寒,几乎是一种世界观。你的“不看好”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某种意义上,你的小说是世界的各种“不看好”大观。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三 : 我逐渐才明白,盲目的热情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要去改善世界,首先必须认清真实的世界——冷漠、残酷、靠着极其功利的守则在运转,是在把握客观情况的前提下,仍然选择相信那些好的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爱在绝境中绽放的那种珍贵时刻。
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个极度不爱聊天的人,总是忘记回别人消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把那些需要回复的聊天框暂时置顶,等到有心情了再去回复,要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的冷漠,实在很难。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也时常认真考虑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张定浩老师在写《既见君子·陶渊明篇》时说,“爱,是在目睹到尘世的美之后,把自己交付出去后得到的回音。如同潮水一般,爱是在两个人之间循环激荡的过程。”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讲到爱,“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川端康成的《山音》里也提到过爱,“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希望对方先看到。”
我时常因此迷惑,尽管我早就有心理准备,无论我积攒多少知识与经验,能做的也就是离“爱”更接近,那其实是一个我永远无法真正解开的谜语。许多深夜,我穿着拖鞋,乘电梯下楼,坐在小区里凉亭前的椅子上,我的情绪沉降到C大调,四下里悄无声息,世界忽然变得裂纹重重,就像哥窑出产的瓷器。我感到孤独,可是我已经不再拥有对他人表达孤独的意愿,对很多事也不再怀有激烈的情感。
也是前阵子,我忽然想明白,自己这几年最了不起的事是,无论怎么被他人辜负,至今没有失去对人性的信任。就像我从前隐约感受到的,实际上我满怀深情,只是这些深情无家可归,这些爱没有对象,它更像是一种希望,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所以,其实我这种“不看好”只是一个立足点,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世界,归根结底,我是对世界怀有深情的。

何平 :《白塔》和上面的这两类小说又不尽相同。它不依靠“故事新编”的母本,也不全来自现实经验,而是想入非非的世界。但你好像对这样写作尝试并不满意,你自己觉得你想做的和已经做到的差距在哪儿?
三三 : 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个讽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群劫匪去抢银行,但他们并不想要钱,而是要塑造一种新的秩序,抢劫更珍贵的东西,比如他们想要银行里的人们在总统大选时自由投票,但他们尝试过之后,发现这些务虚的东西不可操作,还是拿钱来得实在。
讽刺类的小说,向来是难写的,因为作者极有可能会受困于概念,而导致情节薄弱,这篇小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概念化冲淡了小说本身的逻辑,细节也显得目的性非常强,而在我的预期中,这篇小说本应该更加荒诞有趣。
人物描摹也有不如意之处,本来之所以用第一人称来写,是为了使“我”在描述过去被人欺负的经历时更疯狂,更加歇斯底里,尽管一切已经过去,“我”的人格还是受到压抑,就算日后境况变好了,我在同学们面前还是抬不起头来。“我”很敏感,所以时常能感觉到同学们对我的鄙视,“我”很骄傲,所以我要在他们说出对我的鄙视之前先拆穿他们的心思。在实际写这篇小说时,我觉得歇斯底里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不过,虽然对这篇小说本身不是太满意,但并不会排斥去写新的东西,无论结果如何,尝试本身就给人一种正在变完整的感受。如果有有意思的灵感,还是会抓住来做文章。
何平 : 是不是小说是可以从你的日常生活分离出去的世界?或者是你偶然走出生活的那个“异界”。我们谈各自生活很少。但我感到你对生活不乏热爱和耐心,比如你可以在圣诞节前想着拍一百棵圣诞树。
三三 :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些分裂,在日常生活中,我尽可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优势而企图凌驾于人,也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特别的事,一切都是默默完成的,我只希望自己能和人山人海融为一体,不要有任何标新立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存在,不止小说,那些浪漫、那些自己去虚构的意义都属于“异界”。除了想拍一百棵圣诞树之外,还做过许多有意思的事:
比如,我会在深夜的优步拼车里装鬼,吓拼车的陌生人。
比如,有一次心血来潮,我按照斐波那契数列的规律和一个朋友聊天,分别隔1、1、2、3、5、8……天和他聊天,这个数列递增得非常快,按照规律,我第13与第14次对说话之间要隔一年,虽然最后也就没有联系了。
再比如,我是那个吃完麦当劳会用番茄酱在盘子里写“再见”的人。
写小说是汇集各种“有意思”的重要方式之一。
【选自《花城》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