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文学是鞭子,我就是被抽打的那只陀螺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微信公众号 | 王诤 2017年02月04日09:00
2016 年7 月底,女作家张悦然推出了个人创作生涯中最新一部长篇小说《茧》。新书发布会放在了京城地标性建筑——798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被冠之以“80 后的精神成长”,颇有点破茧成蝶的意味——距离作家上一部长篇小说《誓鸟》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年,《茧》的面世显然有些姗姗来迟;更关键的,就像现场嘉宾梁文道指出的那样:这是第一个80 后作家那么认真严肃地回应历史问题,这种追问在当下显得非常重要。

「上下」“ 游逸”系列外套「上下」“ 风轻”系列连衣裙「上下」“ 大方”系列围巾 摄影:解飞
张悦然:1982 年11 月7 日出生于山东济南,中国当代女作家,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A 组一等奖获得者。14 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其作《陶之陨》、《黑猫不睡》等作品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巨大反响。2002 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 最受欢迎女作家”。长篇小说《誓鸟》被评选为"2006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最佳长篇小说。2016 年发表最新长篇小说《茧》。
经验需要时间去等待
“十年,我觉得真的是阔别已久的感觉。”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张悦然颇为感慨,“ 上一本书《誓鸟》出版在2006 年,我写完以后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放慢脚步。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了。我觉得关于青春的一些特别本能的、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比较完尽地展现了。过度的表达其实是对青春的一种透支。当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已经变得很沧桑了。我想我应该按照自己内心的节奏来写作。所以我就慢了下来,没想到过了那么久。”

《茧》2016 年8 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茧》这部小说采用了双声部叙事结构,通过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为读者呈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缠绕恩怨。
小说叙事原点是一桩发生在“文革”时期骇人听闻的罪案:“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在山呼海啸的批判会上,一家医院的热血职工将一根两寸长的钉子,从副院长后脑摁了进去,令后者变成了植物人。
浩劫过后,尸身一般的受害者依旧在呼吸,而凶手是谁的问难则令人窒息。张悦然通过不断抽丝剥茧,还原历史场景,观照当下两人日常生活,映衬出历史的迷雾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覆盖在下一代人身上的困局……
凶手是谁?这是每个读者都忍不住要追索的事体:是怯懦温和、后上吊身亡的内科大夫汪良成?还是医术高超、后功成名就的院士李冀生?张悦然显然没有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意愿,“我也没有答案,作家只是提出问题、沿着问题去寻找的人。对于真相,我尽可能展现更多的面,哪怕能找到此前没被照到的一个小角落。我无意于构建宏大的历史背景,只是关心我的人物的命运,关心他们和父辈的关系。承载给每个个体的历史,并不比集体、国家的历史要微小。”
梁文道曾认为,写这段历史的作家主力都是像余华这一辈的亲历者,因而他很高兴“一个80 后作家能站出来那么认真严肃地追问父辈。80 后如何收拾残局?这代人怎么跟父辈的历史和解、宽容、原谅、接受?”
从小生活在医院并在作品中时时紧握着人性解剖刀的余华则态度超然,“或许在今天的人看来那是一个离奇的谋杀案,但是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那是比较普遍的谋杀案。但《茧》把生活的状态写得如此之好,而不是依靠曲折的情节和谋杀案来吸引我。”
在之后一系列的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愿意对这本小说发表看法:冯唐提到了张悦然在这部作品中描述“复杂缠绕”的能力,“从一个家庭,到一座城市,到一个国家,是背后诸多力量集成在推动某件事情发生。”许知远则在声称自己之前确实没有读过所谓“80 后”的作品后说,80 后不该是高度“去历史化”的一代人吗?在他看来悦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一个作家的本质是对世界本身有洞察和理解,这种理解既源于自身的独特经验又源于对广阔世界的探索之后的一个深层的经验。”
也许只有和张悦然同样出道于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韩寒对此抱持一种平视的达观与放松,他说自己被《茧》“文字冷冽的风格”所吸引,“但这种冷淡和性冷淡不一样,会有温馨和希望。”说这番话时是在2016 年上海书展上,韩寒坐在张悦然的身边。在为老友站台时,韩寒甚至还遭遇到一名倒韩者的袭击,后者在现场将一瓶矿泉水直接砸向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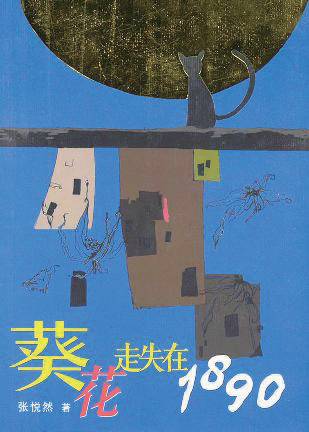
《葵花走失在1890》2003 年6 月作家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个80 后作家开始反思历史,为什么令如此多的人侧目?年末岁尾,和张悦然坐在人民大学校内的一家咖啡厅里,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她。她不愿意简单地接受一种外界对她和同龄作家的比较。彼时,郭敬明刚刚导演完一部偶像云集的《爵迹》,韩寒也在公布新电影《乘风破浪》的庞大阵容,主题仍是华丽青春,而张悦然在暗夜间独自探寻父辈的历史。因为在她看来这没有对错,只是自己“仍然选择了文学。”
选择了文学,之于张悦然而言像是一种宿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创意者,近二十年来一直担任大赛总干事的李其纲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写下了他对“新概念”中诸多人与事的回忆。在提及张悦然时,李其纲说自己记住了这个女孩,是因为她在讲到文学之于她的意义时用到了一个比喻:文学是鞭子,她就是被文学抽打的那只陀螺。
从“新概念”和《萌芽》起步后,2004 年前后张悦然也曾被成功包装为“玉女”与“金童”郭敬明并列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当年出版的图文集《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甚至收入了两组彼时她的个人写真集,题名为《嚣艳》和《沉和》,间插在《小染》等三篇小说中……但这一身份很快被张悦然自己扬弃,在商业化的诱惑与写作之间,她竭力维持着文学的超然与平静,她的日常行止是低调的,但对文字的考究和洁癖却始终如一。
在2006 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誓鸟》后记中,她甚至坦承道:“我是呓人,卖梦为生。”

《誓鸟》2006 年11 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如果说曾几何时“生活经验匮乏的怀疑与局促”还是张悦然写作的短板,那么眼下的《茧》显然可以为她扳回一城。张悦然告诉我,这十年来自己多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我教书、我编杂志,这跟之前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我对历史、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了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多更宽广的理解和看法。这些是我在2006 年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的,不管是通过阅读、还是朋友的讲解都无法得到,这就是经验,你在写作中就是需要它,你就是需要等待它。”
对话才女张悦然
如此不吐不快,为什么不一气呵成成就这本小说?我注意到你前后用来十年来完成它,是历史的表述,还是讲述的模式让你觉得困难?
张悦然:《茧》 可不是一气,不知道多少口气。难在我们这代人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在我,我不想把它做成一种控诉或是复仇,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这个东西里有非常多的层次:我们跟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父辈、祖辈的关系有非常多的层次,有爱、有恨、有决绝地想跟他斩断关系,也有希望把它弄清楚抓在手里。所以它很复杂,有点像油画,你要一遍一遍地涂,涂很多层才能出来那个效果,所以这个不能急,这不像写意的东西,几笔就完了,它需要一个很慢的过程。
这个小说为什么采用两人对话这种交错形式?你当时如何考量。
张悦然:一次,我的叙述方式前后换了很多,最后才确定的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承载着不同的东西,爱和恨,很多很多东西,这是一种支撑和回应。这个写法其实蛮困难的,后来定这个写法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但可以试着做一下。大概是两三年前,我把之前的东西都推翻了,以前不是这个视角,也不是这个人称,我全改了。
所以小说集中的完成时间还是在近两年?
张悦然:对,你说的没错。之前的故事已经成型,也写了很多字,忽然要换人称就得重新写,重新写就得把之前有用的东西拿过来,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愿意承认要重写,就会安慰自己。这个过程是蛮痛苦的,两三年前突然发现要换人称的时候真的有种崩溃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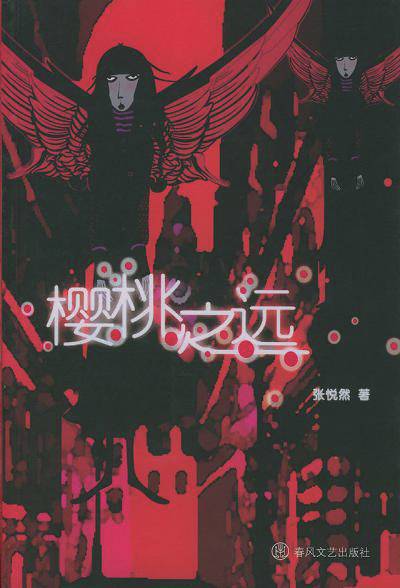
《樱桃之远》2004 年1 月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 年时,你是“新概念”作文竞赛的第一名,2008 年时你已然是这个比赛的评委之一了,就像是你现在在人民大学授课的身份,张老师,谈谈95 后学生们对文学的感觉吧?
张悦然:他们的阅读很丰富。这些孩子问我的问题,我都蛮吃惊的。比如有人问我当年菲茨杰拉德没有海明威名声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菲茨杰拉德的地位在提升,海明威在下降,他们问我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的,我也挺想知道。
张悦然:我跟他讲这个是跟时代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菲茨杰拉德的故事里有“美国梦”的概念,这个概念经过“9·11”等一系列事件会再度被人提起,再度被人审视。
海明威有着强烈的风格,影响了很多人,但那个内核和主题可能离现在的人没有那么近。但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个时候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有点呼应,跟当下美国也有呼应。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厉害,我在那个岁数肯定问不出来。还有学生问我如何看待胡兰成和木心?因为他的高中老师曾禁止他读这些甜腻、缺少特别正的思想的文字。我告诉他,你喜欢就去读,因为这个年纪就是会对字句、对词,对很多细节感兴趣的年纪,你当然会喜欢这样的东西,毕竟他的行文那么漂亮,又那么美,有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东西”。我觉得一定不要放过这个阶段,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
好吧,你那个阶段读什么?
张悦然: 读村上春树,那个时候他挺流行的,读杜拉斯,也读卫慧、棉棉。
谈到阶段性成长,我注意到你也曾被定位成“玉女作家”,这明显是有暧昧色彩的,但你似乎不愿意被商业绑架。
张悦然: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大概只有二十一、二岁。后来我就很警惕。特别的,2006 年出版《誓鸟》以后,我意识到特别有名、特别流行的话:你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就会被消费掉,很容易过时。
女人最害怕“过时”,所以你对这很敏感?
张悦然:不,是你的文学会过时,你的东西会随着这个潮流一起被冲走。像我们经常说我那个时候还读谁谁谁,这些人其实都已经被冲走了,因为他就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我觉得你必须要沉下心来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不停地在外面晃,不停地去增加曝光,不停地上各种节目、通告,然后把自己变成多元身份的人,一会儿是主持人,一会儿是什么,我觉得我当时是一定可以走那个路的,但我觉得那个一定不会长久。

系列主题丛书《鲤》从2008 年6 月起每两月一期,至今仍在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有人批评80 年代作家的时候说:你们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经验,却非要展示那么大的视野。所以有人会把你的《誓鸟》和《茧》放在一起,进而去表扬你的进步。
张悦然:坦白说现在看那个年龄我写的《誓鸟》,不管它有多少缺憾,但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觉得那个时候小说寄托了我对热带、岛屿,对海洋等很多东西的感情。
但在那之后我想让自己慢下来。从2003 年出第一本书,到2006 年我已经出了三年书,三年的时间里,我出了两短篇集和三部长篇,这个创作量你不觉得是个非常恐怖的事吗?我觉得这个量是个巨大的消耗。我当时意识到情感是要有经验作为载体的,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有非常充分的情感,但我没有生活经验,我的经验非常苍白,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留一下感情等经验来补充,这样我才能让两者结合成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特别空幻的情感爆发,让情感就这样消耗掉。
《茧》推出已经大半年了,我注意到一条反馈是有人说这是80 后第一次在严肃文学中去反思20 世纪90 年代。
张悦然:《茧》涉及了两段历史,一个是60 年代、一个是90 年代,但我对90 年代的历史更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们是孩子,包括你也在大学的校园里,但你能得出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变化。包括信仰和理想主义的崩塌。之所以会转向物质和市场经济,就是因为这种崩塌。我们在大学里长大,对于这种状态看得更清楚。我现在都记得,我爸爸每天带回来的班里同学的毕业纪念册,每一页都有学生的照片和留言,我一般都是抱着看班里哪个女同学比较美的心去翻。我对那个毕业纪念册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他的学生是70 后,大概是60 年代末到70 年代初出生的人,正是经历过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以为我将来上大学会变成70后那代人,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他们的留言写的都是“远方、理想、不要抛弃梦想,我们新的驿站在什么地方”之类的,他们是相信真的有理想这个东西。
你现在的学生毕业会写什么?
张悦然: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一定不是那个时代的调调。我在小说里也有写我很喜欢“谈心”这个词,我觉得它特别有90年代的感觉,那个时候心还是能够“谈”得出来的,“谈”的那种状态就是种心的交流。能“谈”,人需要先静下来,现在这种状态我们都是在聊,聊天儿,不再说“谈心”,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变化。哈哈,我觉得咱俩不应该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怀旧模式。

《红鞋》2004 年7 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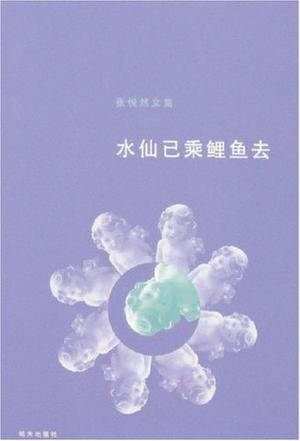
《水仙已乘鲤鱼去》2005 年1 月作家出版社

《霓路》2007 年6 月 明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