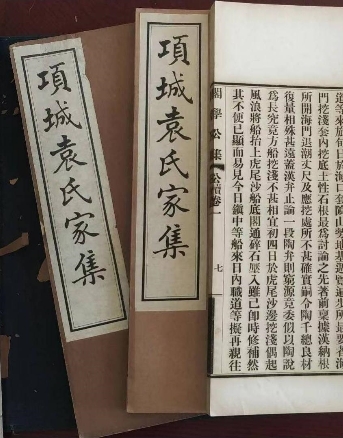《散文》2025年第5期|干亚群:等台风
不同的夏天,有一件事是重复的——台风。可它具体什么时候来,又不得而知。
穿着短袖的门卫老伯,在喝完最后一滴酒后,捏着蒲扇,一脚高一脚低地踱到值班室,打开那台缺了一根天线的黑白电视机,有时雪白一片,狠狠拍打几下,闪出几个人影,打着哆嗦,背后噪起一片沙沙声。再左右拍打一番,电视机里的人影总算立住。这一招,他是跟阿其医生学的。
门卫老伯手里的蒲扇啪嗒啪嗒,扇起一阵阵风,顺带也赶赶蚊子。他看新闻,虽然听不太懂普通话,但他分得清国内与国际,国内是机器开得轰隆隆,国际上炮声在轰隆隆,打不完的仗和吵不完的架,偶尔也会提起“克林顿”,说这男人不得了,居然会讲外国话(英语),不过,头发烫得跟阿飞似的,不好。我同他解释人家的基因如此。他一脸蒙,说:“基因啥东西?”我正思索如何跟他启蒙基因,边上的阿其医生说:“人种。”直截了当。门卫老伯恍然大悟,几个“哦”字配合着他脸上舒展的皱纹。
那时,我还没买电视机,想看节目,也得坐到值班室。有时,窗外雪花飘飘,我抱着一只热水袋,跟着连续剧荡过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春天的时候,大多也是我一个人看到深夜,出来常常淋一身雨。
因为夏天的傍晚时间显得有些拖沓,夜色给暮色留下一道很宽的缝隙,就像厨房的门,总也掩不实,上半扇看起来关上了,下半扇豁着一张嘴,风可进,月光可进,狗猫也能进。我很喜欢这段光景,饭已食,衣也洗了,剩下的时间去医院背后的小路上走会儿路,不能说散步,一说这个词,门卫老伯跟我急,说那是城里人的词,农村人只有走路。
等我走路回来,顺便坐到值班室看一会儿电视,大多时候是国际新闻了,又是哪里紧张了,哪里开火了。
新闻结束后,我想门卫老伯也该起身了,他一起身,我便可以换台了。谁知,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还端正了坐姿,手里的蒲扇也不摇了。电视机里是短暂的广告,有时是饮料,有时是酒,都没喝过。待广告热闹过后,开始天气预报了。门卫老伯的眼睛闪了一下,我感觉他的老花眼努力撑起一缕光。貌似我跟门卫老伯一起在看电视,其实还是他一个人在看。我只是在等他离开。
待天气预报结束后,门卫老伯如释重负地站起来,跟我说,明天没有台风。然后,他摇着蒲扇,啪嗒啪嗒,噗嗒噗嗒,手上的蒲扇与脚下的拖鞋,拖出了整齐的节奏,后面跟着一个影子,拐弯时,影子折出三角形,随后消失。
电视机里还在播放各省的天气情况,但只有字幕。我会一直等到“浙江省”,等它被升上去,不见了,我才换台。
那时,我行过最远的路程是到杭州,坐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心里万里无云,在西湖边上骑着自行车,过断桥,过苏堤,遐想与那些穿着长衫的先生们相遇。
所以,省外的那些天气,于镇上的我而言,比生活的边角还要边角。
那晚,门卫老伯准备起身,跟老中医似的,脸上慈祥而俨然,还有那句“没有台风”的诊断。我突然来了兴致,问他,我们属于华东还是华南?门卫老伯摸摸脑袋,上面覆盖着白发,仿佛覆盖着一生的智慧。他说我们属于华南。我笑了,笑得毫不客气。我说,不是。门卫老伯一惊,两只混浊的眼珠子几乎跌出沧桑的眼眶,弄得我差点伸出手去接。这时,阿其医生陪着病人过来配药,门卫老伯趁机叫住他,把刚才的问题掼给他。阿其医生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华东。门卫老伯的神色紧了紧,喉咙里咳嗽几下,手里的蒲扇往身上拍了几下,一边说着三话四话。
第二天,门卫老伯串了中药房与西药房,还晃到了内科与外科,临近下班,我诊室门口出现他的半个身影,说是答案太多了,明天再理理。说完,半个身影也不见了。自然,我也没等到他的“眀天”。
其实,对他来说,只要没有台风,我们华在哪里,并不要紧。
有次,我好奇地问他:“你那么关心台风干什么?你又不种田。”他说:“台风每年要来,什么时候来,心里一点也没数,就像悬空荡着。”我理解他的意思,台风不来,他的心一直担着,提着,直到它来,他才能从半空中被解救出来。
等台风成了门卫老伯在夏天的常规,如同我们替病人看病时要量血压一样。
在乡下,像门卫老伯这样年纪的老人,肚子里有看云识天气的俗语,什么“朝怕南云涨,晚怕北云堆”“雷打天顶雨不大,雷打云边降大雨”。尽管它们是民间的,但从一张张沧桑的嘴里过去,它们自带资历。可到了台风这桩事上,他认为那些谚语不管用,就像药物,有时一片够了,有时得加大剂量,具体要看病情。
也不知经谁提醒,他隔几天去镇政府,有时农办,有时工办,连教文卫办也去,向他们打听台风何时来。门卫老伯毕竟是医院里的人,至少还有人会敷衍他,或给他泡杯茶,他也不客气,端着茶杯从一个办公室串到另一个办公室,无论熟不熟悉都会跟人搭讪几句,这几句里一定有一句是叮嘱别人要健康卫生,说是病人他看得多了,那痛苦,就像身体内刮了一场台风。末了,他问别人有台风消息吗,工办的人让他去问农办,说是他们管着看天吃饭的事,台风消息更准确。于是他踱到农办,见有人在,挑个角落坐下,进来的人给办公室的人分烟,自然也把他当成办公室里的人。他也不急,慢慢地抽,在边上看别人忙碌地进出,待来人一个个出去后,他上前问台风的事。获悉近期没有台风时,他呷一口茶,送出健康卫生后,便起身走向另一个办公室,也是最后一个——教文卫办,里面的阿姨们一见门卫老伯,打招呼,端椅子,续茶,几乎全室总动员。热心的她们还会送他搪瓷杯、日历本,甚至安全套。门卫老伯尴尬极了。阿姨们替他解围,说是可以送亲眷的。门卫老伯腋下夹着日历本,手里捧着搪瓷杯,杯里装着安全套,嘴里唱着越剧,荒腔走板而心满意足地回了医院。
我惊叹于门卫老伯的比喻,把生病当成刮台风。可不是,那阵痛袭来,不亚于台风的肆虐,几乎可以穿过任何脏器与骨骼,还能变换着动作,有时刮,有时拔,有时拉。门卫老伯的脸慢慢绽开来,然后,保持着不动,好半天,他都带着这样的表情,似乎那笑嵌入了他的肉里,成为脸的一部分,想摘下来都难。
院长曾在开会时强调,我们对待病人要热情,态度不能生硬,尤其不能板着脸,要向门卫老伯学习。会后,外科的谢医生不服气,趁院长外出开会把门卫老伯叫来,让他给我们示范微笑。门卫老伯搓着手,脸上一阵紧一阵松,哭笑不得。防疫科的徐医生起哄,说是门卫老伯穿上白大褂,找他看病的人一定比任何人都多。
只有我知道,如果不表扬门卫老伯那个经典的比喻,他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
日历一天天翻过去,夏天过完了一半,终于,门卫老伯等来了台风的消息。他拍着胸脯,保证着消息的可靠。这段时间也真够难为他的,台风的事好像熬干了他的脂肪。
这天,院长正好去县城开会,也没电话,只有传呼机。他那个急,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好像台风已经撵上他的脚跟。他不停地跟刘会计说:给院长打个电话,台风要来了。刘会计打着算盘,头也不抬,说:外面是猛日头,你不要瞎讲。门卫老伯跺跺脚,但也无可奈何,每个月的工资需在她这里领,虽然刘会计不是医院的业务主干,但上上下下都待她很客气,久而久之,刘会计也养成了气场,说话的口气里含着微量金属。
于是,门卫老伯推开了防疫科的门。这门算是推对了。徐医生是搞防疫的,台风来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外面风吼雨急,他岁月静好地看报纸,偶尔也写点小诗,怎么读都像是小半篇作文,无非是用斜杠替代了标点符号。台风过后,他的手脚不停,挨家挨户地分发消毒片,还要教村民怎么使用,有时他回来时,头上的星月都出来了。徐医生虽然离诗人很远,但他离诗很近——这句话是我说的,被徐医生反复写进个人总结。
徐医生听门卫老伯一说,跟刘会计要来电话机的钥匙,嘀嘀嘟嘟打了几个电话。待他归还钥匙时,院长的电话也来了,说是开会时领导特别强调了,各家医院要做好抗台准备。在边上的门卫老伯听到院长的话,眉心拧出一个“川”字,说,台风能抗吗?徐医生根本没心思停留在“防”还是“抗”上,脚底生风,去落实院长的指示——防止药库进水。
徐医生叫来没在看病的医生们,七手八脚把药库里的药箱全搁到长脚的柜子与凳子上,即使进水,也浸泡不到它们,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油毡。他还跑到每个科室去摇门窗,如果有松动,赶紧换插销。这时天上堆起了黑云,风开始紧一阵慢一阵,跟分娩的阵痛似的。我查看了下产包,还有两个,应该差不多。天气越恶劣,我心反而笃定,产妇都留在了家里。这种天气,连胎儿都嫌弃。
也真是,我从来没有在台风中接过生。
门卫老伯拧开自己的那台电视机,把开关拧得啪啪响,没有任何消息,里面有人演天上的事,但没人说天气。他只好放下电视机,还得跑镇政府。这次他直奔主题,找到广播站,知道那里会随时播报台风情况。等他回到医院,其实风已经像台风的样子了,急吼吼地在门窗外徘徊,树已经变形,我开始想到一个词:撕心裂肺。
还没到下班时间,尽管没有病人,大家还是守着诊室,没有提前离开。只有外科的小方医生显得焦躁不安,白大褂已经脱了三次。他有一个正在谈的女朋友,是小学的老师,长得小巧玲珑,有点像翁美玲,也是巧了,也姓翁。小方医生追得很紧,但这位美丽的翁老师一直若即若离,有时,她来医院配个药什么的,小方医生屁颠屁颠。翁老师最怕打雷刮大风,遇上这样的坏天气,小方医生两腋生风地奔向学校,脸上的笑,那是一窝一窝的。
门卫老伯不时伸长脖子看天,那台小电视机被他搁在小桌上,一会儿把桌子拉到门口,一会儿又把电视机捧下来放在门口。我觉得很怪,悄悄问他的老伴菊婶婶这是做啥。菊婶婶没好气地说——他神经。
台风有术语,叫“登陆”,它如果一直悬在半空,这风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它何时过去,跟何时来一样,也需要等。在等的过程中,大家只能顺带做点事,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医院的门被门卫老伯早早关上了,这时间,还有这天气,估计也没病人来了。住在医院里的医生们合了门,门后的锅碗瓢盆,还有人间烟火,被渐渐低下来的暮色挤成一张纸,在风声中抖落一地的忐忑。我窝在寝室里看书,看不进去,跟门卫老伯所说的那样,心悬空荡着。我合上书,对着天花板发呆,雨点疯狂地敲打着瓦楞,像戏开演前的鼓点。
夜色来得很快,我一直没开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醒来已是后半夜,居然月明星稀。我愣了好久,才确信台风过去了,月光溶溶,像是洒下了一钵清水,照得世间宁静又祥和,似乎,台风把坏东西都刮走了。
早上,医生们陆续来上班,也没人提及台风,就像往常一样,临近下班,我们又被徐医生叫去,把药箱搬下来,门窗一阵吱吱嘎嘎,仿佛憋了一肚子气。往常,门卫老伯对分外的事是积极的,跟我们一起扛药箱抬盐水瓶,但这次他缺席了,一整天没看到他人影。
傍晚,我去拿饭盒,见他独自坐在小马扎上,神情有点沮丧,仿佛一场台风把他的元气刮没了。他告诉我一件事,听起来像个民间故事。他说有个邻居,家里的一台西湖牌电视机被台风刮到屋外,等台风过后揩净泥污,居然还能播放,于是写了一篇报道,被《浙江日报》刊登。这新闻被西湖牌电视机厂知道,奖励了他五百元,这笔钱于当时的家庭来说,相当于一年的收入。
门卫老伯的脸总算展开了,几声嘿嘿里有了生气。
【干亚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给燕子留个门》《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庄》《树跟鸟跑了》《带不走的处方》等。作品常见于《散文》《作家》《上海文学》《天涯》《美文》等。曾获得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三毛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储吉旺文学优秀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