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畀愚:被贴上《叛逆者》带来的标签是一种无奈,但好在很多东西都是会褪色的
根据“人民文学奖”得主畀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叛逆者》虽然已完结,但与之相关的各种热议却依然不止。与此同时,畀愚的另一部长篇力作《江河东流》也正式上市。该作品是畀愚“对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以电影画面般流畅灵动的文字,精彩绵密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名旧军阀儿子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由苦难贫弱、倍受欺凌到逐渐觉醒、奋起抗争的史实。那么,畀愚在构建此类故事时,想传达给读者什么,又是用怎样的手法去吸引读者的呢?他是如何看待《叛逆者》给自己带来的“标签化”?另外,他的写作生涯因何开始?阅读喜好又是什么?近日,《读者报》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畀愚。

《江河东流》让自己“从青年过渡到了中年”
畀愚,29岁开始创作小说,从青年工人转身为青年作家,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出版有小说《碎日》《罗曼史》《欢乐颂》《叛逆者》《通往天堂的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江河东流》等。不过,虽然有如此多的优秀作品,但“畀愚”这个名字却不太被广大读者所知,直到《叛逆者》被改编成由诸多明星参演的电视剧。
“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如今,电视剧《叛逆者》已在热血、澎湃的节奏中收官,但网络上围绕《叛逆者》的人物刻画、故事情节、精神内涵等不同层面的持续性讨论,让剧中的逆行精神与青年力量打破时空壁垒,成为勾连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更是在众多年轻观众心中埋下了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种子。这,就是优秀文学的力量。
正如畀愚所说,《叛逆者》这类题材的作品,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认知并回望那个特殊年代。这些关乎信仰、情怀、理想的继承,是十分要紧和迫切的。而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江河东流》,以20多万字的篇幅写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蕴藏着这种特有精神内核的小说的延续。
《江河东流》以第一人称“我”(孙宝琨)为叙述主体,切入历史、参与历史,纵观了整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将一段近百年的历史重新构造,塑造了两代军阀和诸多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以高密度的故事情节,暗示了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个人命运的渺小和顽强。
谈及这部作品的创作,畀愚坦言“过程并不令人愉快”。原来,《江河东流》其实是畀愚的无心之作。有一次,他接到单位的短信,问手头上有无写作计划?于是就随手回了句“准备写一部《我的革命生涯》”。就这样,畀愚在没有规划的情形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畀愚说:“创作几乎一直是处在断断续续之中,一直被琐事干扰。断开了,还得继续抱着创作中必须要有的那股热情,这是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一直写到过半,才忽然发现我其实在写的并不是那个我以为的年代、我以为的那个人物。其实,很多时候这会让我觉得好像是在创作另一个自己,是作者孤身在一个无序的时空里梦游。也正因为此,常常会发生白天的所闻所感,隔夜就会把它写进小说,而更奇怪的是,它竟然没有半点违和之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学与虚构的力量吧?同时,它也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有了点辩证的意味。”
小说《江河东流》写了整整两年。对畀愚而言,这部小说更像是一座桥梁,终于让一个创作者从青年过渡到了中年。畀愚解释道:“这是个反复接纳与反复领教的过程,但既便是到了此刻,我仍能体会到沉浸在那个人物中的那种感受,甚至有时一开口就会不由地吐出几个字的脏话,好像真有孙宝琨附体了一样。”
不过,畀愚却并不十分喜欢小说中的孙宝琨这个人物。在畀愚看来,孙宝琨的无知与任性恰好是自己感兴趣的无知与任性。“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用来磨灭我们的无知与任性的。孙宝琨就是一只井底的小蝌蚪,他不停地挣扎,与不知道是谁的人抗衡。他试图要违背整个面临的现实世界,甚至是他自己,那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世界必然与之背道而驰。而作为创作了这个人物的作者,其实我更想探究的是他的余生。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种全新的人生。”
小说就是引导读者,给人以思索的空间
透过《江河东流》的书名,很多读者都感受到了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感叹,这是否就是畀愚所要表达的呢?畀愚对此回应道:“其实这也是所谓历史留在大部人心底的感受吧,那种俱往矣般的沧桑感。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书的封面上还印着两句诗:‘大江东去浪淘沙,一壶浊酒喜相逢。’事实上,这部小说付梓时还在跟责任编辑反复商讨这个书名,我们都觉得它应该还有一个更加合适的名字,只是都没能想出来。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除了命运的无奈与对人生的感叹,它还隐藏着某种唐吉诃德似的精神,像江流一样一往无前,且又泥沙俱下。孙宝琨这个人物在民国那个时代也许可算是个另类,他的无知与无畏却有着江河拍岸般的执著,最终向我们证明了,所有的江河终归会流向大海,不管它来自何方,不管它怎样的百转千回。这就是历史的洪流,也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这是《江河东流》的第一句。接下来,小说继续写道:“乌尤城的大街上热闹的是剪辫子。革命军挥舞着白旗,臂上缠着白色布条,就像出殡那样拥过大街小巷,他们都是我父亲手下的士兵。……我喜欢看那些被剪掉辫子的男人。他们有的惊慌失措,拔腿就跑;有的追着革命军,死活都想要回他们的辫子,结果被痛打一顿,捂着脑袋蹲在街边痛哭流涕。”小说的开篇就把基本信息都呈现给读者了,几乎不做铺垫。这种看似有些独特的写作方式,畀愚坦言:“可能是长久以来的写作习惯吧。我就属于那种不太会对事情作过多解释的人,直来直去,喜欢简单,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情,尽量不去说第二句。以前就有人说过,我常把一些长篇容量的小说写成了中篇,而且很少有心理与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对人物与事件也基本上不作铺垫。这其实是我个人对小说创作的一点小探索,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不断地践行着。因为,小说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比较个人化的东西,或者说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东西。小说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引导读者,给人以思索的空间。小说既然是作者呈现的一个世界,它是虚构的,是不设大门的,可以让任何人自由地出入或滞留,让他们自由地思考。所以,我觉得作者没有必要像电影中的旁白那样,在文本里去告诉人们这个人物心里在想什么,更没有必要担心读者有可能会误读而去作什么注释,或者是告诉读者,我这个作者是怎么想的。因为,作者创作的这些故事与人物,本身就是作者发出的声音。你可以自由地创作,读者也应该自由地阅读、思考与判断。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写作者与读者一起来丰富一部作品。我把它看作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
不太在意被贴上的标签
在《江河东流》中,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贯穿其间,比如讨袁、北伐、抗日,但畀愚却仅仅只是提及了这些事件,可以说既给了读者以真实感,又弱化了大历史,而回到故事本身。常言道,小说的魅力在于虚构,畀愚更偏爱把虚构的人物与事件放在真实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创作这类题材时。“历史的沧桑感、它不逆转的惯性,像车轮一样滚滚而来,无情地碾压过一切。我希望读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不管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文学的世界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因为历史在发生的瞬间,已经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而书写与表达他们则是作家的责任,也是写作的意义。我相信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的。”,总有一个地方是息息相联。
畀愚给《江河东流》的开篇和结尾作了一个特殊的安排:主人公孙宝琨从“不爱念书,喜欢革命”到“在学校教书,回归平淡”。对此,畀愚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考量:“在那个时代里,‘革命’应该是个最关键的词。整个所谓的民国时代也几乎是在革命与被革命中完成。当然,我在这里指的革命,更多是指暴力革命。我用‘我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这话作为小说的开端,其实也是预示一段动荡岁月的开始,不管对那个时代还是对那个‘我’而言。最后,‘我’在经过了那么漫长而跌宕的那段人生后,选择做了一名老师,也是一种预言似的。它不仅要告诉人们和平的到来,它还告诉人们,强权与武力也许可以改变世界,但改变人心的却是教育与教化。”
畀愚的历史题材作品很多都具有画面感,这是写作风格还是为作品影视化做铺垫呢?畀愚说:“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有的吧。我喜欢看电影,有时也会考虑文字表达与镜头语言之类的问题。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写了十年,这也是我尝试小说电影化创作的十年。这个效果现在开始显现,读者也开始喜欢这类小说作品。但确实也有人指出过,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为转化成影视而创作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有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时会发现,它的艺术性、思想性,那种直抵内心的力量完全不亚于小说。同理,小说也可以像电影一样深入人心,它需要广大的读者。这是我努力想做与在做的。”
从事写作这么多年来,畀愚几乎没有开过一场新书发布会或者座谈会,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调。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叛逆者》走红后也给畀愚带来了与之相关的标签。但标签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在畀愚看来,小说跟人一样,一个小说自有一个小说的命运,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或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作者能决定的。“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坦然地面对。从我个人来说,我不会给什么贴标签,也不喜欢被贴上标签,但有时这也是一种无奈。标签在很多时候好像已经成为了某种特征,但好在很多东西都是会褪色的,标签也一样,不需要太在意。”
“有点小传奇”的写作生涯
不管怎样,畀愚就这样火了。于是,很多人都想探寻一个小说之外的作家畀愚,比如写作生涯、创作瓶颈、阅读习惯等等。
谈及自己的写作生涯,畀愚笑着说道:“这还是有点小传奇。我几乎没有过那种文学青年的经历。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可能只是比当时的同龄人多了点小爱好吧,就是看书与画画。小镇上有个工会图书馆,每周三、六的晚上开放。我记得那里的文学期刊也就四种:《收获》《当代》《十月》与《花城》,看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小说自己也可以写,就开始尝试写作。当时,我还给自己定了个两年的期限,在这个时间段里不能写出点名堂来就放弃,好在老天厚爱,第二年就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发在《清明》杂志上,叫《单五一的最后一天》的短篇,讲一个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接着是《上海文学》杂志连着给我发了五个中短篇,我的责编是金宇澄。当时打电话还比较麻烦,基本上都是靠通信。我记得有次他在信里让我写个中篇试试,我就写了《六月的阳光》。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由此,我也就从小镇青年成了青年作家。”
阅读对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平日里,畀愚非常喜欢阅读。“我喜欢看一些史实与传记类的,人物的,事件的,小说作品反倒读得不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卫生间里放过三本书,一本是《百年孤独》,两本是《拍案惊奇》。每天都翻,翻到哪里就从哪里看起。后来翻旧了,又去买了这三本。”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在畀愚看来,我们阅读历史、了解历史,其实也是为了便于更清晰地看待我们正在面临的与将要面临的。“不过,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历史书籍。如果一本书就是作者创造的一个世界的话,只要是没看过的,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除去写作,在畀愚身上,“几乎就想不出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喜好的事情。以前茶都不喝,现在开始喝茶,但对茶叶也没什么认知,有什么就泡什么,泡什么就喝什么。有时,写累了,实在找不出可以排解的,就上菜场去买一堆菜回来,做上一桌。可能对于我来说,跟写作关联的也就剩下做菜了。”
谈及接下来的写作计划,畀愚说:“我正在尝试着写悬疑类的小说,当然文学性仍是前提。悬疑的魅力在我看来是两方面的,一是故事本身,二是写作技巧上的。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小说里也是有悬疑成份在的,只是不明显,没有放大它的存在。有段时期,我想写李商隐,后来放弃了,因为发现有不少人都写过了。我是特别想写一部全面虚构的历史小说,一直在想,差点就动笔,结果却发现没那么简单,还是再等等,再积累一点。希望这一天早日来临吧。”
 更多
更多

姚鄂梅:以笔为杖探向人性深处的暗礁与微光
“年轻时,写作是青春的自发倾吐,像《像天一样高》里对诗歌时代的追忆,那是没加任何雕琢的赤诚。随着年岁的增长,它逐渐蜕变为‘智慧型’的自觉表达。”
 更多
更多

“人民文艺”的香港之旅
1946至1949年间“人民文艺”在香港的历史际遇,尚未被充分关注……
 更多
更多

散文 | 山寨夜色
村里能出去打工挣钱的劳力,都出远门了。夜晚的山寨,再也寻不回我们小时候的热闹光景。堕谷村在山里算是个大寨子,三百多户人家,大部分还留着人。白天下地干活和下午收工的时候,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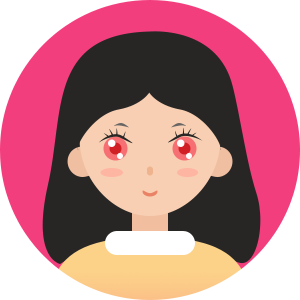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散文 | 西大湖畔好村庄
西大湖有一千多个泉眼,是黑河岸边的天然湿地,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坐落于泉水之上的村庄明永上崖近年来依托自然条件和黑水国古城的悠久历史人文,改造原居民破旧民居院落,建成了三

散文 | 神农架散记
神农架观感

散文 | 想起那些吃杏的时节
留在作者小时候吃杏子的记忆,读来使人如身临其境一般,文章叙事清楚,脉络分明。也体现了作者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之情。

随笔杂谈 | 抬头的铺路石
在青石板铺就的古道上,躺着无数沉默的石头。它们被岁月磨去了棱角,被车轮碾平了脊背,在晨雾与暮色中编织成一条通往远方的银灰色绸带。这些铺路石从不抱怨,任凭牛车沉重的木轮从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