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邱兵最新故事集《鲟鱼》出版 邱兵:写下我的故事 我的记忆 我的一去不返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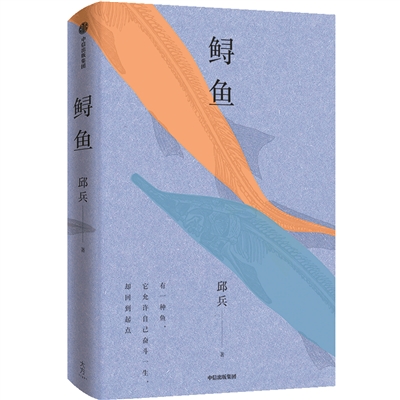

邱兵的文字有他的声音。
阅读邱兵最新故事集《鲟鱼》时,总能从他的文字中想象到他的语气、音调和态度。此前,我从未见过他,但我一直知道这位资深媒体人的“传说”。邱兵,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文汇报》记者,2003年创办《东方早报》,2014年创办“澎湃新闻”,2023年发起“天使望故乡”写作计划,2024年出版非虚构故事集《越过山丘》。近日,他又出版了新书《鲟鱼》,并计划推出“天使望故乡+”以及视频播客。
直到采访他时,我更加明白,文字的确不会撒谎。他倾听问题时很认真,回答问题时却又逗得大家狂笑,而在欢快的氛围中,我仍能从他的回答里感到几分冷静的思考。我想,邱兵讲话时就是如他的文字一般坦率,读者会被他的坦率逗乐,而后他又立刻用真诚的态度,讲述自己近几年的人生经历,打动着看故事的人。
邱兵说,这本新书最初的书名是一个长句子,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而出版时又短到只有一个词——《鲟鱼》。在我看来,这两个名字有着同样的内核,都在讲述着邱兵这些年的思考,以及他现在的状态——航行。我们的对话,就从书写一群鲟鱼开始……
现在 终于 我又坐在这里
故乡不再只是存在于记忆之中的地方
邱兵像一条鲟鱼一样,正在记忆中航行。
在邱兵笔下,他书写了与朋友之间的往事,自1988年起,记忆游过了2010年、2014年、2018年等时光,最终在2022年画上了句点,其中数次提到他曾见到过的难以忘怀的场景——一群正在逆流而上的鲟鱼。1988年,20岁的邱兵在葛洲坝排队时看到水面冒出十几条中华鲟,它们“体积非常大,一条得有四五米长,似乎必须要经过大坝,不停地腾空飞起”。
之后,邱兵才知道鲟鱼为了去到它最初的地方,总要奋不顾身开启一场洄游之旅。“每当夏秋两季,生活在长江口外浅海域的中华鲟洄游到长江,历经3000多公里的溯流搏击,回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产后待幼鱼长大到15厘米左右,又携带它们旅居外海。它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当鲟鱼洄游到江河中的时候,它们总是会回到父母曾经交尾的那片水域,每一条鲟鱼都跟随着自己父母的轨迹……据科学研究说,不需要任何指引就能够找到自己出发水域的长江鲟鱼,世界上还有57条,我想我一定是其中之一。”
2022年底,邱兵沿江而上,从上海回到家乡重庆巴南鱼洞镇。“总有人说回不去的故乡,而我是‘被迫’回到家乡。那时,我的母亲离开了我们,父亲的身体也开始抱恙,曾经强壮的身体,现在也要开始用上轮椅了。之后,我要在重庆过完夏天和冬天再离开。这种长时间待在家乡与以往工作时回家探望几天的体会,有很大差别。我总是见到童年的朋友,像是回到了童年时的生活,现在也更加能融入家乡的生活了。故乡不再只是存在于记忆之中的地方,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正如鲟鱼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这两年,邱兵一回家就能听到许多故事。曾经,他对这些家长里短并不太感兴趣,而随着心境的变化,他的姐姐和父亲所讲的身边人的事情,逐渐让他听得颇有兴趣。这一过程中,他对父亲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坦率地讲,我父亲的脾气很怪,很霸道,我们曾经在家庭中很难与他有一种平等的沟通。每次我回去的两个月,他每天都想出去,我只能推着轮椅,带他散步,与他聊天。最近他的听力下降很快,我们就用小黑板进行沟通。如果没有这两年的时光,那么他对我而言仍然是很陌生的。当他聊起自己曾经的公安工作,讲起他如何识人,如何探案的时候,我才逐渐有耐心听他讲,有动力去了解他。与他走在路上时,他的老同事、老相识以及我们的左邻右舍都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我想我的父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他不靠权位赢得尊重,而是在生活的细节中得到他人的赞赏,这是他留下来的道德财富,也给我树立了道德标杆。”
每次回家,邱兵从几十年前的老大桥进入镇上大街时,都能看到“孝善鱼洞”四个大字。邱兵喜欢“孝善”两个字,他认为这是做人的标准,“能落实好这俩字,这人差不到哪里去”。
“长江从孝善鱼洞流过,历经一个大的转弯,往东北方向而去。童年每一个寂静的时刻,我总是喜欢坐在长江边上放空大脑,看江水缓缓流淌。现在,终于,我又坐在这里。”邱兵写道。
天使望故乡
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 在文字中寻找共鸣
在人生中航行时,邱兵总是不停地转场。
作为资深媒体人,邱兵总是在不同阶段接触不一样的传播介质,比如他经历了从纸媒到新媒体再到短视频等阶段。在一次次转场之后,许多人正在着重关注着视频这一媒介,邱兵却再一次转向了文字。“可能是机缘巧合,我与好友王帅都在关注着视频,但是我们本身都比较喜欢文字。写作,是我闲暇时休息的方式。曾经做总编辑的时候,总爱指挥编辑和记者,甚至有时候会怪以前的同事不会采访。对于写作这件事,反而没有太亲力亲为。因此,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写作的,同时也没有勇气去写。当我与王帅聊天时,我说我们也来写点吧,只要真实的表达就可以。我们一拍即合,建立了一个公众号。”邱兵回忆道。
2023年,邱兵与王帅发起了“天使望故乡”写作计划,并召唤朋友们纷纷投稿,在两年多时间里,已成为李敬泽、罗翔、王帅、陈年喜等许多文化圈名人的聚集地,吸引了众多读者。“在路上看见欢乐和哀伤的岁月”是该公众号的简介,也是这个写作计划的宗旨。
“有时我们发表几篇普通的文字也会得到呼应,我没有想过得到的回应可以如此热烈和积极,所以我真是因为读者的鼓励,才能够持续地写作。我想,‘天使望故乡’的文字是一种对往日的怀念,同时抒发了我们共同的情绪。比如,有的读者也同我一样经历了亲人的离别,或是正处于生活的低谷中,他们会在文字中寻找共鸣。我常常看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我们读者的评论是很真诚的,让我感到他们对文字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更重要的是,不是我一个人在写,而是更多的人正在参与进来,他们的表达并不是负能量的文字,而是温和的书写,发自内心,带着思考,同时夹杂着诸多情怀。”邱兵进一步解释道。
在邱兵最新的一篇文章中,与读者谈起《鲟鱼》这本书,再次表达了一以贯之的态度,他写道:“我一直对自己说,能够用最简单的字,绝不用复杂的语言,因为它只是一本最平凡的书,一本如老友般交谈的书。”在“天使望故乡”中,邱兵写下的每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的作者简介均为“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一动不动的生命有个什么意思呢
每个人都有心灵密码 推动着我们去挖掘内心深处的情感
“折腾”一词,早已注入邱兵的血脉之中。
当年,邱兵从《文汇报》离职,创办《东方早报》,又创办“澎湃新闻”,他直言自己一路下来,都是在“折腾”,自己早已适应这样的状态。“我听过一句话,意思是人有两种,一种人的人生是活了一万天,而另一种只活了一天,但是重复了一万次。这句话尽管有些‘鸡汤’,却让我很感动。回首这二十多年,如此折腾,我肯定不只活了一天,我可能是真真实实活了几千天,经历了不一样的体会,尽管其中有低谷,也有痛彻心扉的感悟,但于我而言都是极为宝贵的。”
如今57岁的邱兵,也曾有过退休的想法,只不过当他每每想到“躺平”,脑海中总想起一位已经离去的老友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记住我留给你的最后的话,乌龟可以活几百年,因为它一动不动。但是,一动不动的生命有个什么意思呢?”因此,邱兵仍在“折腾”。
今年,邱兵将推出“天使望故乡+”项目,通过MOOK(杂志书)的形式,记录当下的时代。“天使望故乡+”预计持续十年,在这个十年之约中,每两个月围绕一个主题,邀请各领域的专家、专业作者和素人写作者,进行访谈和创作。目前,计划推出的第一辑MOOK是《100个中国人的梦境》,参与创作的专业作者包括胡泳、毛尖、罗翔等。他们围绕着梦境本身的书写,进行深入讨论,或引申为“梦想”的主题。“我认为这是一种记录当下生活的方式,从细节入手,挖掘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但这并不是文艺杂志或是报告文学,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媒体平台。我们第二辑则计划推出《100个中国人账单账本的故事》,第三辑的内容可能是以音乐记录时代为主题。我们邀请罗翔老师写自己的歌单,他一点儿都不抗拒,因为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喜爱。甚至给我们交稿之后,他突然又想起来一首歌,还要再加入文章之中。我想,这就是某种心灵密码,推动着我们记录和书写。”邱兵介绍道。
此外,邱兵还尝试了“视频播客”的录制,计划在本月发布。在录制第一期的时候,邱兵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期采访用中文写作的意大利人亚历,去年他出版了《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成为年度畅销书。在访问他的时候,一进入现场,看到三个大灯照着,我就蒙了。总共录制了五六个小时,但是我没说几句话。原本我还准备了一些‘梗’,休息时试着讲了一下,同事们都觉得不好笑,冷场了。我心说,这下坏了,我还准备了好几个呢。在这次之后,我明白这件事也是需要天赋的。因此,我要再松弛一点,把案头工作做得更充分些。”邱兵笑道。
现在网络流行语总说“五六十岁正是闯的年纪”,邱兵虽然认同,但也苦笑道:“要知道,我们这个年纪闯起来,还真的挺累的。”最近,邱兵给读者做《鲟鱼》的签名本时,一直从中午签到了晚上。“我一直重复着一个动作,持续签完像两座山一样多的书。保持一种姿势的时候,我的腰会很不舒服。我那时候就想,真的是老了,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我一定很轻松地签完。正如我曾说过的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坚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所坚持做的事情是我一定想要做的,不然我会后悔的。”
我打开电脑 我要写作
成为地球人 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不同的好与不好
邱兵的心里有一道坎,他想用文字追寻答案。
“我为什么要写作?”邱兵自问。他在《鲟鱼》中提到:“初夏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梦到自己突然就死了。”生死的问题,从他的人生低谷就一直围绕着他,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坎。“我写作这本书的前后两年,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间。亲人离去,事业危机,生活动荡……我有哥哥和姐姐,但是在2020年初,我的大哥突然离世,他只有六十岁;2022年,我的母亲离世。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突然就不完整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对于这个问题,我总是绕不出来,总在围绕着它进行书写。所以,我写下的这些很简单的文字,希望让普通人也能够很顺畅地阅读,或是通过文字让大家在心中一同触碰这样的话题。”
邱兵的写作紧密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讲述着家人、老友以及媒体同仁的真实故事,属于非虚构写作范畴。他认为,这更像是职业习惯,去追求更真实的表达。“由于自己的想象力有限,以及内心的记忆很难扭转,因此我的创作一定是基于现实的。就像是我们写新闻时追求‘五个W一个H原则’,我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一些个人情感的元素。比如,我写父亲、写我曾经的总编辑、写我的朋友‘谢老’等人物,他们都是一类人,身上都有一种极为‘纯粹’的气质,他们有时或沉默或旁观,且不被商业和流量所裹挟,是他们让我深切感受着理想主义者的光芒。在我低落的时候,我将烦恼告诉他们,而我得到是一种使我安静的力量。”
除了写作,邱兵这些年通过阅读在心灵上得到了一些鼓励,他重读了《百年孤独》《了不起的盖茨比》《遥远的房屋》等书籍。于他而言,阅读是一种放空和排解,让自己沉浸在这些故事中,探寻别人在人生低谷中是如何度过的。“在《东方早报》的时候,同事总嘲笑我不读书,是个‘文盲’。偏专业的社科类书籍,我看不太懂,只能多读点文学类的书籍。在读到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巴顿奇事》时,记得他说五十岁是人生最好的年华,我想,我要在最好的年华里做最好的事情,尽管我的腰已经很不舒服了。”邱兵笑道。
如今,邱兵还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地球人”。只不过,他总是要像鲟鱼一样,继续航行,时而从家乡起航,时而返回起点。“我从一个重庆人,变成了一个新上海人,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上海重庆人,如果加上每年在北京工作的一两个月,去波士顿陪女儿的一两个月,我变成了一个地球人。我觉得,在身体状况尚能支撑的前提下,颠沛流离的地球人的生活很好,因为他经历各种体验,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不同的好与不好。同时每年还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让人生不留遗憾。”
而关于邱兵为什么要写作,他自己的答案是:
我的梦在初夏的清晨醒来,那些眼泪和遗憾挥之不去。
我打开电脑。
我要写作。
写下我的故事,我的记忆,我的一去不返的时光。
某一天,这本书会在女儿的枕边,她每天都会读几行,哭着、笑着、叹息着,然后,这些文字会偷偷走进她的梦境。
一直到又一个美好的清晨。
“爸爸一直都在。”
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理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