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约翰生:鲍斯威尔的诗心与史德
一、 谈客约翰生与《约翰生传》的传记价值
1778年4月20日,鲍斯威尔赴约翰生家座谈,聊到了友人兰顿入不敷出的家政状况,约翰生行云流水的句式和恰切熨帖的譬喻令鲍斯威尔叹服,在《约翰生传》中转述该场景时,鲍斯威尔插入了珀西的评价:“约翰生的言谈有力而清晰,可以把它比作一尊古代的雕塑,每一根血管和肌肉都清晰凸显。一般的言谈就像一种低级的铸型。”珀西把言谈与铸像的固化过程相类比,不仅把握了约翰生关于言谈必须有“介于流俗与清雅之间的得体”的诗学主张,更提示了谈话作为书写的重要补充,施加于社群趣味的“古代雕塑”般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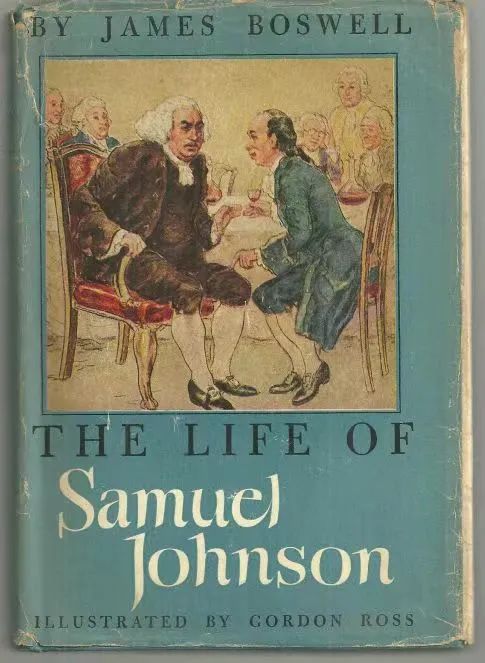
鲍斯威尔与《约翰生传》,图片源自Yandex
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酒馆、咖啡屋及名流的客厅是人际交往及知识流通的公共领域,及至约翰生时代,才俊人物麇聚于特定处所,形成文化趣味与政教背景相近的小团体(coterie),具备了不亚于报纸杂志的知识生产力,譬如,定期聚首“土耳其人头”(Turks’ Head)酒馆的“约翰生俱乐部”、集结于蒙塔古夫人客厅的“蓝袜社”等。时人对奥古斯都时代修辞技艺及雄辩才具的效法使交谈成为关键的文化行动,如约翰生所言,“一把酒馆的椅子就是人类幸福的最高宝座”。交谈不仅因为展示了成员风度(manners)而有利社团融合发展;也可以用于厘定趣味标准、评判文学素养以筛除混迹其间的异见分子。
纵观全书不难看出,《约翰生传》逐年纪事时倚赖的是对社交言谈(书信不妨视为谈话的特殊形式)的摘录。据此,科辛认为《约翰生传》不过是一部妙语的摘集。对于摘记过于庞杂的指责,鲍斯威尔不但将琐碎视为传记的特殊价值,更援用了普鲁塔克及培根等权威为“琐事的典型性”辩护。其实,《约翰生传》倚重言谈摘录有特殊原因。约翰生本来就“不愿写作”,在获得年金后更逐渐转型为谈客(conversationalist),因此,谈话确实是读者理解他的重要途径。斯雷尔夫人甚至认为“言谈的复述与摘录几乎是替约翰生作传的唯一途径”。此外,约翰生特别注重“著述一致”,并且认为自己“通过谈话做到的善事与通过写作做到的一样多”,晚年他还有“读书不如闲谈”的看法,可见约翰生对言谈“书替”价值的重视。《约翰生传》中既有揶揄谢立丹演说的影响好像“在多佛尔点燃一支小蜡烛要照亮加来”此类加里克称为“紧紧一抱,摇得你哈哈大笑”的冷隽幽默;也有“爱国者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也就厌倦了生活”这样充满智识穿透力的警句。不少妙语即便当下读来仍旧令人耳目一新,难怪鲍斯威尔为了同约翰生谈话,甘愿饿着肚子。
当然,《约翰生传》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除了它庞大的资料体量和极为翔实的谈话记录外,还有以下不容忽视的优点:第一,正如作为早期阅读反馈之一的《每月书评》(Monthly Review)那篇匿名批评说的那样,《约翰生传》采用了区别于既往作传技法的“新颖模式”。《约翰生传》擅长描摹“生活场景”(life in scenes),赓续了约翰生在《萨维奇传》“莎翁集序言”及《诗人传》中的文学传记笔触,尤其注重以生活场景再现“激情主导”下传主命运的曲折走势,突破了传统传记叙事的脸谱化体式。此外,鲍斯威尔认同约翰生关于传者与传主“共时经验”的“事件目击”原则,认为传者具备隔代传记家缺失的临场优势,能够以更为直爽的主观介入抹除隔代传记因时空距离可能导致的隔阂,因而《约翰生传》塑造的场景栩栩如生。比如,《约翰生传》曾经记载盲女威廉斯因为沏茶时斟得杯满不溢而沾沾自喜,但鲍斯威尔猜想她是以手指伸入杯中才能有此效果,寥寥数笔便将约翰生身边关键人物的习性描摹得淋漓尽致。再如,鲍斯威尔在1775年某次聚会中注意到约翰生收藏饭桌上的橙皮,好奇之下追问无果,可叙及1783年时,他回溯并解答了未解之谜——为了晾晒止咳药物。此外,诸如受难日早茶不加奶的习惯,两人最后一面时约翰生的临别动作等细节都是传神的点睛之笔。这类巴特(John Butt)赞为“切割钻石之技艺”的“两寸牙雕”笔法使得《约翰生传》具有斯威夫特伦敦日记那样的“奇怪的吸引力”——马隆(Edmond Malone)称,“有关人和事的奇妙的信息,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书籍中再找也是徒劳”,点明了《约翰生传》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第二,鲍斯威尔在《约翰生传》中多次表明,虽然对约翰生极为崇拜,但秉持求真原则,他力图呈现真实的约翰生,要以弗兰德斯画派的明暗对照(chiaroscuro)笔法描摹“混杂在这颗巨星躯体中的所有阴影,标明这位文学巨人的所有小小的怪癖、轻微的瑕疵”,比如,约翰生粗鲁骇人的吃相、呢喃自语的怪癖、乖戾暴躁的脾气等。《约翰生传》对约翰生的观点行为并非时时附和,反倒有讲真话甚至进行论辩的独立精神。比如,鲍斯威尔不但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权辩护,更指责约翰生对奴隶贸易的看法是“不知情的热心”。再比如,尽管约翰生对斯威夫特颇为怨恨,他却毫不掩饰对斯威夫特的喜爱。此外,约翰生因为同小说家理查逊私交甚笃,就攻击菲尔丁是个“榆木脑瓜”,认为“理查逊一封信里对人心的认知比整部《汤姆·琼斯》里的还多”,对此鲍斯威尔公正地指出,“《汤姆·琼斯》经受住了舆论的考验……一种生动真实的创作技巧贯彻始终”。《约翰生传》还多次指出约翰生对演员及苏格兰民族的偏见,种种揭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得约翰生形象“妍媸毕露”(warts and all)。
第三,鲍斯威尔曾表示将会遏止坊间流言并更正他人传记中对约翰生形象的歪曲。凭借执业律师对证据准确性的照勘能力——“为核查一个时间,跑遍伦敦”——他使用材料时确实表现出记者式的严谨。《约翰生传》确实澄清了不少人们误归于约翰生的“荒谬或恶毒的言论”。除了纠正“多德牧师案”“亨利·赫维落狱”等公共事件中人们的误读,《约翰生传》还纠正了人们对约翰生“视力不佳”“脾气粗暴”的误解。更重要的是,《约翰生传》深入约翰生人格的隐微之处,为读者理解约翰生提供了不少讯息。比如,在惯常认知中,约翰生以才思泉涌及“倚马千言”著称,既有“搅动茶杯沉思片刻的即席创作”,亦有“立等可取”的快笔美谈,《约翰生传》却揭示了约翰生辛勤积累素材、刻苦准备底稿的一面。
像常被忽略的副标题“全面展示大不列颠近半世纪,亦即约翰生活跃阶段的文学状况与士人风貌”所说的那样,《约翰生传》以广阔的社交言谈场景展现了约翰生时代英国人精神图景的多重风貌。但是“以言观人”需要同时考虑谈话的语境和谈话者的个人偏好。约翰生作为谈话家最突出的个性是“为胜利而谈”,时常刻意站在错误一方卖弄辩才。约翰生的莫逆之交泰勒对他交谈时碧海掣鲸的好斗形象曾有如下概括:“言辞横扫千军,但是没法跟他争论,他干脆不听你讲话,由于嗓门比你高,不把你吼倒决不罢休。”因而约翰生不仅有失势时的“诡辩野招”,也有冷静后为言不由衷道歉的情况。此外,出名后来访者如云,约翰生注意到有人当场记录言行,因而说了不少因虚荣心作祟才讲出口的惊人之语。鲍斯威尔也觉察到约翰生在“大庭广众之中被激得热情洋溢之时”与静思之后对同一事物的矛盾态度,故而指出不能通过一次谈话就“断定约翰生对某事的看法”。大概因为坊间对自己言论歪曲得厉害,晚年约翰生曾对友人抱怨:“我是个被误解得很厉害的人……有时候开玩笑,意在言外,人们容易相信我是当真的。”我们也应该追问一句:鲍斯威尔是否也有误解约翰生的时候呢?
二、 鲍斯威尔的传记技艺
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界虽然掌握了一些信息,但并不了解《约翰生传》成书的具体过程。因为《约翰生传》在写作过程中一直由以学术严谨闻名英伦的马隆从旁协助,所以读者赞叹鲍斯威尔记忆力惊人之余,大多相信他在《约翰生传》中不断申说的“据事直书”与“逐字誊录”。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拉海德堡文献”(Malahide castle papers)及1931年“费特凯恩文献”(Fettercairn papers)的面世为学界重审《约翰生传》的生成史提供了新材料。通过校勘比对同一事件在鲍斯威尔随身携带的备忘录,事发当晚或数日后根据备忘录整理而成的日记,以及依托日记扩写成书的《约翰生传》这三类文本间的衍变,研究者指出了两大问题:第一,备忘录采用极简的速记,日记与《约翰生传》则根据速记扩写;第二,从《约翰生传》篡改他人材料的程度或从它对备忘录的扩写来看,《约翰生传》都更像一部“文艺作品”(work of art)——比如备忘录中“《伊瑞涅》首演。嘘声。谋杀云云。普里查只得活着退台”的十几字速写,在《约翰生传》中扩写成一百二十余字的鲜活场景。此类戏剧化改写令泼特承认,《约翰生传》相较日记的平实,已经是“富于想象力的重构”,并且对原初场景的“诗心笔法”正是《约翰生传》的主要特征。可见,如范存忠先生所言,《约翰生传》在“涂抹、添注、改削”等编辑技法上确实“花了不少工夫”。在参照谈话场景的第三方记录等旁证文献后,我们不难看出《约翰生传》的编辑功夫主要体现在为尊者讳方面:为塑造约翰生对发妻的深情,就对他与德穆兰夫人的暧昧采用曲笔;为掩饰约翰生年少时对同学的霸凌及社交时的粗暴癖性,就对他人提供的材料避重就轻或者按而不表。此外,《约翰生传》中还有不少穿凿附会的“对话”,乃至将他人言论移植于约翰生头上的“张冠李戴”现象。
如果从现代传记的批评标准来看,《约翰生传》在布局方面无疑有结构失衡的问题:全书仅用约六分之一的篇幅处理约翰生前五十四年的生命历程。由于常年住在爱丁堡,缺乏第一手资料,鲍斯威尔在论及约翰生晚年的时候,出现了意识流式的叙述跳跃和来路不明的材料。此外,《约翰生传》还“夹带私货”,在正文及脚注中堆砌了不少略显冗余的“离题叙事”和“自传材料”。正如格林所言,这些重复罗列的材料既包括借题发挥的托利党政治宣言,也包括情不自禁插入的布道文赏析、夸示孟浪与诗才的作品小览,还有一板一眼的宗教观点论析。对于堆叠材料的作传方式,斯雷尔夫人在《约翰生轶事》开篇有一段评论值得引述:
对一部传记而言,要素过多和材料稀缺可谓同样有害。事件种种可能所引发的矛盾情状会令读者困惑不已,进而无从分辨真伪。约翰生曾哀叹人们关于巴特勒叙说太少,我大抵更有理由感慨对于约翰生世人却谈论甚多;不可尽数的材料只会让人如坠云雾,正如多数情况下,镜片的交叠亦不能使人看得更加清楚。
虽然《约翰生轶事》比《约翰生传》早五年面世,斯雷尔夫人这段话却可以看作对鲍斯威尔的“诗心”笔法和夹带私货的“私心”的预告性批评。有趣的是,斯雷尔夫人的“约翰生传”也经常枝丫旁出,因堆砌冗繁的离题话招致了不少批评。可见时人作传夹带私货似乎较为常见,而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文学琐事及聒噪的离题话也别有价值,一来可以为公众带来“乐趣与教益”,二来可以为读者品评人物提供隐匿线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私心”称作一种“亲切的偏私”(amiable partiality)。
三、 鲍斯威尔的“史德”
1778年4月的一次会面中,约翰生用缓慢而清晰的语调朗读了罗伯逊《美利坚史》的片段来考察鲍斯威尔速记的效果,鲍斯威尔发现自己的速记方法要求一种损害原意的“对词的刻意安排”。但他“刻意安排”的不仅是字词,《约翰生传》中不少谈话的契机和内容都有“编导”的嫌疑,比如,对两人1763年5月16日历史性会面的谋划,以及对1773年“苏格兰边岛之旅”路线的设计。
熟读鲍斯威尔《伦敦日记》的读者当然不会被《约翰生传》中仰慕约翰生道德文章的那位有志青年蒙蔽。彼时二十出头的鲍斯威尔之所以“南漂”,一来是为了逃避父亲的催逼,不愿继承家业学习法律,二来是为了“观察人性,研习举止”以便老年时能“忆往昔”。总之,鲍斯威尔寻访名士有着社交虚荣和现实利益的多方考量,拜谒约翰生也不是他的伦敦之旅的首要目标,这从他拜谒的名流——威尔克斯、麦克弗森及谢立丹等——都是约翰生绝交之人上可见一斑。从欧陆求学归国后,在鲍斯威尔那份“报人的猎物”(journalistic conquests)名单上,约翰生也非核心人物:这个单子上的名人还有保利将军、休谟、卢梭和伏尔泰等人。
随着交往的深入,约翰生怪异骇人的外貌举止同他技惊四座的言谈能力间的反差,他博采沉奥的学识、光怪陆离的经历和深邃明澈的洞察力,也即卡莱尔称赞的“英国最伟大的心灵”——或许还有两人因忧郁症而产生的同病相怜——都使得约翰生最终成为鲍斯威尔进行人性研究的核心样本。当然,鲍斯威尔在发现并制造“英雄话题”方面也具备记者的才干:除了诸如拿笔偷记座中言谈此类斯雷尔夫人嗤之为“毫无教养,易作奸谤”的恶习外(造访保利将军时他还因此被当成间谍),在套取材料方面,鲍斯威尔还“有一种不露声色便可激怒他人的技巧”,时常“装出一副蒙昧无知的样子,激他(约翰生)说话”。当然,以约翰生的社交阅历,未必对此类“人性测验”毫无察觉,或出于谈兴,或出于反向考察的兴趣,他也会耐着性子回应,但更多时候,尤其鲍斯威尔的盘问和“窥视癖”触碰约翰生的道德底线和心理防线时,两人的谈话大多以约翰生的恼怒及对谈的遽然中断收场。
其实,《约翰生传》中散布的“人性测试”和“驯兽师”式的话题引导,可以视为鲍斯威尔对时兴的“活体解剖术”(vivisection)的社会学移植。它接续的或许是17世纪以来“人与风俗”的科考潮流,其典型表现就是1776年5月那场“心智化学”实验。在那次著名的“威尔克斯会谈”中,鲍斯威尔终于满足了让两位宿敌共处一室的“愿望”。在一众来宾的嘈杂声中,鲍斯威尔观察到约翰生得知威尔克斯在场时“难以自控”,只好坐到窗边阅读以平抑心情,鲍斯威尔写道:“他的感受,我敢说,别扭极了。”而得知鲍斯威尔想故伎重施观测自己在另一敌手麦考莱夫人面前的表现时,怒不可遏的约翰生痛斥鲍斯威尔“十分缺德”。后续交往中,一心探究人性的鲍斯威尔即便远在爱丁堡仍然要用断交书信来考验约翰生与他的友情,并在约翰生为十余年情谊交出令他满意的“答卷”后表示:“我永远不会再考验你了。”
鲍斯威尔获取(制造)材料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既有向约翰生几番索取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信的原件,以及逼迫他以法律文书形式对《隐士》表态这类不知分寸的行为;也有尾随伯尼纠缠讨要书信的越界举措;更有未经允许公开信件,命妻子偷看约翰生日记,乃至亲自偷看并想偷走约翰生自传手稿这类不义之举。如果说上述做法可以视为求资料心切,那么肆意删改他人材料,因1793年法国革命情势移变就改动初版内容等“小动作”,则无法再用“为史实而不顾史德”来解释了。
如斯托弗所言,“传记是艺术而非科学”,不同写者和读者对同一份传记材料的差别对待体现了智识与道德及共情能力的个体差异。然而,正如“真相是史家第一职责”,作为批评者,我们仍旧须审视《约翰生传》或出于私心,或由于史德有亏,或因为史实有缺而“误造”的约翰生形象。对约翰生社交“仲裁人”形象的夸大应该是《约翰生传》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在《约翰生传》描述的各类谈话场景中,约翰生通常被塑造成“文学可汗”,不仅主导席间话题,通常也裁定结论。然而,伯尼记载的“格雷维尔会面”或许更接近实际情况——会谈中约翰生雕塑般盯着炉火一言不发,并不主动发起而更愿意续接他人话题。与《约翰生传》中以雄辩高谈使众人服膺的“独语者”形象不同,当时社交场中不少人对约翰生的言论并不买账,他也有被人反唇相讥而无地自容的时候,甚至发生过火药味十足、“被回跺一脚”的事件,缺席的鲍斯威尔自然没有记录这些场景。哥尔德斯密斯就曾抱怨鲍斯威尔美化了约翰生的社交形象,认为他将本是“共和国”的社交场说成了“君主专制”。鲍斯威尔对此事还颇有腹诽,大概是没能理解约翰生的忠言——“泰尔斯把我描写得最到家:‘先生,(他说)你像个鬼魂:人家跟你搭话前,你从不主动说话’。”
再如,由于麦考莱断章取义认为约翰生对旅行抱有“无知的偏见”,学界渐渐出现了约翰生不喜(跨国)旅行的言论。其实,在18世纪,旅行花费高昂,并非易事,而早年手头拮据的约翰生忙于生计根本无暇出游,而且,仅就约翰生“退休”后每年夏秋的乡间旅行及他对旅行意义的反复申说便足以修正讹传。此外,鲍斯威尔在约翰生负笈牛津及因贫辍学的时间问题上,轻信了亚当斯的口述,并未核实就认定约翰生在牛津求学至1731年秋(计三年),这一说法后来由克罗克考订并更正为1729年冬(计一年),但麦考莱偏偏对此熟视无睹,这又导致中译者误引为鲍斯威尔“秉笔直书”的一桩功绩:“不是我国各种介绍约翰生的文章中说的‘一年’。”其余如约翰生的“视力”“吃相”“骑术”等,《约翰生传》中的描述也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且对同一事项的论述有前后不一之处,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批评者须仔细辨别的。
四、 制造约翰生
鲍斯威尔一方面在《约翰生传》中申明要不虚美不隐恶地呈现真实的约翰生,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掩饰神化约翰生的意图。1785年4至5月,他先后致信友人表示《约翰生传》将会是保存“文学法老”约翰生木乃伊的金字塔,并预备为约翰生织造神圣的花冠。《约翰生传》的扉页引用了贺拉斯称颂卢基里乌斯(Gaius Lucilius)的诗句:“如此,这位长者的一生便如同雕刻在铭碑上那般清晰地显现了。”从中读者可以窥探到鲍斯威尔为约翰生“造像”的用意:将精心雕刻的约翰生神像供奉在庙堂之上,使其流芳百世,追附骥尾的《约翰生传》自然也就有不朽的造像之功了。从卢基里乌斯到贺拉斯,从贺拉斯到约翰生,再从约翰生到鲍斯威尔,“年长诗人”间的代际轮替似乎暗示着《约翰生传》也嵌入了那条由古今重要诗人诗作连缀而成的存在巨链中。这种隐深的精神自传特征凸显了《约翰生传》超越“造像不朽”,追求“立言立德不朽”的意图,并且这不朽同时属于传主与传者,如此设计可谓用心良苦。
蒲隆先生捕捉到了鲍斯威尔隐秘的动机,特地借《阿Q正传》文首的“不朽之笔传不朽之人”一语来比喻鲍斯威尔为约翰生作的传。如前所述,鲍斯威尔“制造”约翰生恐怕并不仅是出于“良苦用心”,他用“诗心”笔法雕刻的约翰生像虽不至于面目全非,但也有走样的地方。比如《约翰生传》中,约翰生对演员及女性莫名厌恨的刻板形象便让格林感慨,金刚怒目的“大道德家”劝退了不少试图走近的学生。虽然《约翰生传》没有记录鲍斯威尔和约翰生关于“保存名誉”的一次对谈,但同为俱乐部成员的温德姆多年后向伯尼补叙了这次谈话。谈话中约翰生对鲍斯威尔说:“世上保存名望的方法不过两类,一是‘糖渍’(by sugar),二是‘腌制’(by salt),至于第一类‘谄媚曲辞’,鲍仔(Bozzy)你不得其法,而我会让你浸泡到醋坛子里,利索地一举腌好。”“鲍仔”这次倒是听懂了老师话里的深意,没有把谈话写进《约翰生传》中。
如克林汉姆指出的,鲍斯威尔将约翰生“木乃伊化”有不愿失去代理父亲并延续“英雄崇拜”香火等原因。又或许,鲍斯威尔单纯因为对约翰生那“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完美依恋”而一心想把英国“约翰生化”。无论如何,对于这种崇拜和依恋,罗伯逊的洞见一语中的:“你们有些人害了他,你不应当崇拜他……在批评方面,在言谈的机智方面,他无疑非常优秀;但在其他方面,他并不比别人高明。”对此,鲍斯威尔回答:“我身不由己要崇拜他。”正如《每月书评》1792年5月刊的匿名论者所言:信徒对神的膜拜,时常引领着他落笔之时那偏私的情谊之手。
约翰生曾断言,时间与普通读者才是文学声誉的最终裁判。《约翰生传》付梓后,麦考莱1831年发表的《塞缪尔·约翰生》一文偕同10年后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文将《约翰生传》提升至不朽的地位,其后该传记近百个版次的编者又在前言中众口一词地复述了约翰生与《约翰生传》的不朽神话。1963年,“斯雷尔夫人点评本”的编者盛赞麦考莱的“先见之明”,同时再次认同《约翰生传》令约翰生与鲍斯威尔并垂不朽。只是,这位编者有所不知,早在1950年,美国“每月图书俱乐部”的评委之一,作家费舍尔便致信俱乐部创始人舍尔曼,称《约翰生传》对普通读者而言实在味同嚼蜡,其文名被英国文学教授们严重夸大,随信她还附上了《出版之乐》主编调研数百位图书馆员、编辑、作家、评论者及教师后排出的“十本最无聊之书”及阅读调查报告,名单中《约翰生传》赫然在列。有趣的是列在名单上的还有约翰生最喜爱的三本书:《天路历程》《堂吉诃德》《帕梅拉》。2020年,书商莱瑟姆在《书商故事》中称,书店采购《约翰生传》是“碍于文名而非销售需求,每年仅零星售出少许”。这些是不是说明,《约翰生传》及鲍斯威尔、麦考莱和卡莱尔等人以“强大的防腐剂”精心制造的文化图腾“英雄约翰生”开始腐朽了?
五、 走近约翰生
我们有可能复原历史上的约翰生吗?答案或许如鲍斯威尔所言:“世人必须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摇摆。”《约翰生传》在“诗心”与“史德”的平衡木上艰难地摆荡,将“诗艺与谎言”“历史与真实”等古老命题推到我们面前。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早年撰文《约翰生的眼镜》,指出后人评读前人时,因阐释惯性及语境差异,总有虚焦散光的时候。随着时代风潮的改易,约翰生形象也像“移动冰山”似地不断漂流,就像蔡田明所说,我们大概也只能不断“走近约翰生”。在《约翰生传》的一面之词与其他“不讨喜的”传记材料之间并不一定要做出克利福德所谓的“关键决断”,更为真实的约翰生或许正游走在二者之间未被照亮的地带中。
这些“不讨喜的”材料,当然包括了霍金斯及斯雷尔夫人、伯尼乃至苏华德(Anna Seward)和墨菲等约翰生密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外传”(apocryphal)材料,但同样也包括鲍斯威尔的《赫布里底斯游记》乃至《科西嘉游记》等“前传”材料。《约翰生传》展现的主要是咖啡屋、沙龙等公共领域中以男性视角传递的约翰生形象,斯雷尔、伯尼等人的回忆录则以女性眼光描摹了家庭生活场景中的另一个约翰生,这类材料加上约翰生存世的4卷书信和2卷“日记、纪年、祷文”,为读者深入约翰生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可能。由于仰赖社交谈话,《约翰生传》虽然录有“格林尼治划船”“水坝推死猫”“为爱猫霍奇买牡蛎”等几处户外场景的事件,但更多时候,它的叙事场景都固定在室内的茶桌边与沙发旁。“外传”材料却收录了不少未见于《约翰生传》的户外事件——出游时的草地赛跑与跨栏比赛,约翰生不顾众人劝阻从山顶滚落山坡,放生友人抓获用于餐宴的野兔并大喊“快逃命”等场景——进而营造了神态鲜活的“可爱版”约翰生。20世纪以来,此类材料或多或少都有面世,现代传记作者也相应取用并借以修正《约翰生传》中的约翰生形象,比如里德(Aleyn Reade)、克利福德及格林对早年约翰生的描述,贝特、韦恩(John Wain)、诺克斯(David Nokes)和马丁(Peter Martin)等人各有侧重的“重述”,都是读者走近约翰生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如果有热心读者愿意去翻看麦考莱那篇评论克罗克“《约翰生传》编校版”的文章,或许会对开篇的陈述句感到吃惊:“这套书真是令人大失所望。”当然,我们不必被麦考莱的辉格史家气魄所牵绊,而应有自己的判断。一如鲍斯威尔坚称“信笔直书”,麦考莱自言“月眼观书”,两人各有各的动机。尤其在鲍斯威尔的私人信札公开后,麦考莱对鲍斯威尔是约翰生的“寄生虫”,《约翰生传》乃“白痴的偶得”等不负责任的攻讦早已不攻自破。鲍斯威尔矛盾重重的“诗心”与“史德”凝于《约翰生传》中,即便因英雄崇拜“制造”了略微失真的约翰生,《约翰生传》仍旧颇具文学史(譬如对浪漫主义诗学的预见)和心灵史的价值。或许因为没能谨遵师命去遏止“饥渴的想象”,反而将约翰生(连同自身及《约翰生传》)涂满防腐香膏供奉在“金字塔那幽深黑暗的洞中”,于心有愧的鲍斯威尔在妻子过世后不久记下了一个不安的梦:“我觉得自己正在一个房间里,约翰生突然走进来,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我对他说:‘亲爱的先生,您应当没有什么责备的话要说给我听吧。’他严厉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责备的话要说给您听吗,先生?’我在惴惴不安中醒来。”或许此类自我审查的“惊觉时刻”,正是《约翰生传》居于“琐事的典型性”之上还能传达给读者的另一种教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