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在上海的屏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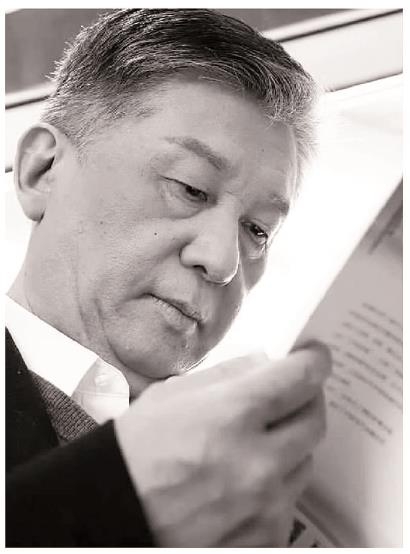

从文学履历上来看,孙甘露是一进门就找到了开关的人,但他仍然在革新自己的创作,从成名作开始,到《呼吸》《上海流水》《千里江山图》,创作和生活中的每一次改变,仿佛仍然在重复这个走进黑屋子的游戏。
如今,作家以外,孙甘露又多了一个身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抬头望见文学史里提到的人,生活中是如此平和儒雅,用学生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反差萌。
1 他把上海看作爱人
祖籍山东的孙甘露,幼年时随父亲的部队南下上海,上海几乎是他写作的唯一对象。他把上海看作是爱人,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是,她还有一个只有你会这么叫的名字,独属于你个人的。众人知晓的上海是一座公共花园,繁华的上海,文艺的上海,市民的上海,革命的上海,它们组成一道锦绣绵延的屏风,孙甘露从少年时代就穿行其间,“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一度喜欢上了黄浦江上的渡轮,花几分钱,随着人流来回摆渡令我沉思我一无所知的事物并且获得慰藉,江面在四季中的形态以及风雨中水面那令人窒息的味道,是最初令我产生迷惘之感的东西。流水天然地变成了一个象征,它的波澜和雾气绵绵不断向两岸涌去,似乎要使潮湿的南方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
我怀着猎奇的心理,重走过一遍孙甘露书中的上海,跟随外出工作的摩托车队伍,坐上两块的轮渡,眺望着窗外的集装箱、仓库、浮桥与鱼市场等,两岸状似人烟稀少的乡村中国,破败瓦房是等待拆迁的样子,散发着郊区式的孤寂。来到东方明珠耸立的外滩,这是孙甘露说的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一个被不厌其烦地四处展示的建筑群,也走完了孙甘露经常谈论的郊区与市区的辩证法。紧接着,我走到浦东美术馆,在敞亮的落地窗前观望着更近的塔以及江面上的巨轮,雾气绵绵,潮湿的空气四处与万物接壤,人在其间显得渺小而后退,仿佛置身《千里江山图》中的清晨,看得到想象中山峦江河的景致跌宕起伏,让人心潮起伏,也让人慵懒。孙甘露在《自画像》里说道:“一种松散慵懒的生活,与争分夺秒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顺着他的作品地图游荡上海,仿佛做了一天上海的吟游诗人。
走过思南路,看思南公馆里的名人轶事,传奇与故事还在上演,人生代代无穷已。2011年8月,上海书展的上海国际文化周活动在公馆里如期举行,作家们在这里阐述着自己的文学理念,市民随时走进来坐下听一听,他们成为朋友,成为周末聚会的方式,“思南读书会”品牌应运而生。孙甘露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召集了一帮青年作家、评论家,打造了一间城市书房,天南地北的作家、艺术家在这里停留,“思南读书会”给上海增添了一抹暖色,成了新的打卡地。最后我来到人民公园邮局,回到孙甘露青年时代的工作场所,曾作为邮差的他奔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传递出信使之函,作为写作者的他,传达的是一种复调的声音,有时代的风尚,也有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摩擦的声音,不仅有此地,还有异乡,上海作为一个移动的能指,“在”与“不在”交织在远景的幕布上。
2 一幅古画延伸出的江河湖海
2022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文学界期待已久的作品《千里江山图》,书名与北宋徽宗年间王希孟唯一存世的画作同名。《千里江山图》与李洱的《应物兄》曾经一起成为文学界难产作品的段子,十几年来被作家们作为谈资、趣闻,当然也带着对写作者的敬意。
孙甘露多次谈到过画家朋友徐累、孙良推荐给他看《千里江山图》,他个人喜欢看画展,在他的意识中,一幅名画背后实际上是一些历史上重要的时刻、人物、历史事件,充满了热血、能量或者是一种激烈的动荡,被艺术家呈现在一幅作品中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就冷却下来了,他更看重我们怎样看待画作背后表现的那个东西,《千里江山图》可能就是回到冷却的后台。
《千里江山图》扉页上的“一九三三年”是冷却时代的印记,1933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以及国民党疯狂围剿中央政权之际,上海春寒料峭,工农革命处于低谷。党中央总部把革命果实从上海撤离到瑞金,避免了红色血脉遭受灭顶之灾,这三千多公里的交通线征程被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隐喻着革命火种和不息的信念。
《千里江山图》有谍战小说标配的特殊时空,悬念重重,情节波澜起伏,阴谋与背叛,信仰与理想,也有先锋作家对人物和构思别样的处理,十二罗汉式的游戏构造,极具现代感和时代性。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十里洋场下,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以梦境和背影出场,他们不再沉湎内心,而是直面时代,躬身入局,从形容词的世界脱身而出,化身为真实可感的名词和有逻辑可推理的动词。《千里江山图》的开端即是中场,仿佛切入了时间的河流,腊月十五浙江大戏院,对面是四马路菜市场,戏院门口的电影海报,从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看到的游乐场、跑冰场、弹子房和书场,还有次要人物的一份闲情,“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谁也不曾想到这样慢悠悠地享用早餐的人,即刻就要去菜场东面的一条夹弄里开一次十万火急的会,紧接着特务闯入集会现场,有人逃脱,有人还没有到场,有人只能迎接随后的抓捕与审讯。生活表面的松弛与底下的紧张动荡,小心翼翼地探寻着上海和时代的秘密,也触碰着现代读者多次元生活中交叠共存的心绪,像一场穿越时间的相逢。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再次盘活上海地图,从浙江大剧院、四马路菜市场开始,跑马总会、公益坊、顾家宅公园、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工部局立格致中学、同春坊、肇家浜、闸北、漕河泾、小闸镇等,他给人物设定了有质感的上海生活地图,这些地标集合起来,以工笔的手法潜入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故事中。从《我是少年酒坛子》到《千里江山图》里的街道,真实的街道路线贯穿到虚拟的空间里,是他对现实主义小说技艺的接续,蛛网式的大街小巷在小说里形成一种卫星定位式的存在和真实性的压迫感,借着人物之口,仿佛是孙甘露在对这个城市自言自语,“上海的马路他熟悉得像自己的手指”。信手拈来的熟悉,或许得益于作者早年当邮递员的人生经历,多年后,他把路途中的历史、记忆和想象编织起来。读者也跟随书中的路标,躬身入局,充当试图识别敌方的地下组织员,在上海的迷宫中寻找谜面,通过骰子和茄力克香烟来侦察真相,通过人物代号“老开”、“西施”等来破译时代和自我的密码。读者在小说里纵横之后,深感那些在上海龙华监狱牺牲的前辈们,或许肉体湮灭,但他们的灵魂走进了当代的千里江山图里,在江河湖海里重生。
3 写作就像进入一间黑暗的屋子
从1986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算起,孙甘露进入写作这一行当已经有三十六年,从新锐先锋作家到策划《上海壹周》,从时尚名人到作协领导,分管文学界鼎鼎有名的沪上杂志《收获》《上海文学》《萌芽》《思南文学选刊》,策划市民喜爱的思南读书会,加入华师大创意写作专业,如果说他对文学熟悉,似乎略显轻薄,文学对他来说,就是生活。谈起自己熟悉的生活,人们总会多一份自如和即兴。对于很多中文系学生来说,孙甘露有时候基本等同于一个名词解释,辐射范围包括“先锋小说”“反体裁”“反小说”“元小说”与“不可索解性”。
面对新时代的文学爱好者,他不讳言文学需要一定的天赋,当然他也充分强调创意写作专业的必要性,文学需要后天的打磨。天赋固然重要,但日常的训练和有意识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也是写作的重要环节,在有经验人的指点下,我们的写作会少走一些弯路。
他说写作就像进入一间黑暗的屋子,“里面有灯的开关的,但是你不知道开关在哪里。有一些情况下,我们不是很幸运,把整个房子摸了一遍之后才找到开关。其实,如果有人指引你,你找到开关,轻轻一碰灯就亮了。有的人也可能比较幸运,一进门就能伸手摸到开关”。
如今,创意写作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地进入黑屋里,以个人的方式滑翔在阅读与创作作品之中,流连在前辈书写的词语花园里,体会着孙甘露曾有过的生命体验。
王朔曾说过一句话,“孙甘露的书面语最纯粹”。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他的每一次写作多少都带有异数的色彩,不同于自己,也不雷同于他人,在遣词造句和修辞布局里撒播反叛的种子,也享受着语言游戏拆解聚合的愉悦。
《千里江山图》可以看作先锋小说家的一次告别,而不是公众所期待的向现实主义的转型,他用“上海”和“谍战”两个关键词,创造了比真实还真实的阅读感受,同时又潜藏了最个体的生命经验,因为上海和谍战都是广博的,都是打开的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