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里的“器”与“道” ——吴仕民长篇小说《御窑重器》读解
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甚巨,然而在这些发明之外,中国瓷器的悠久历史及精湛的烧造技艺亦独领风骚,令世界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即使是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晚清,翰林院编修徐琪在上书光绪帝时亦曾有言:“顾中国丝茶而外,其余百物,皆不及外洋之精,独磁器一门,外洋虽竭力仿造,皆不能及。” 美轮美奂的瓷器历经时间的淬炼与空间的旅行后,光耀世界,既代表着东方大国的形象,又凝聚着民族文化的密码。以至于在英语世界中,西方人以大写的China指称中国,又以小写的china称呼瓷器,据此可见中国瓷器的影响力。因之,《御窑重器》这部以制瓷工的瓷艺传奇为素材的小说,天然便具有了“中国气派”和“中国格调”,是典型而独特的“中国故事”。
在《御窑重器》之前,吴仕民已接连完成了《铁网铜钩》《旧林故渊》和《佛印禅师》的写作,尽管这些长篇小说的题材和内容各不相同,但贯穿其间的则是对中华文化的追溯与探寻,并将深情的笔触探入到丰厚的地域文化之中,力图在对传统的回溯中发掘可资转化的精神资源,进而在消费主义时代彰显信仰与民族大义的魂魄。而且,地域文化的寻根与民族精神的彰显,使得他的写作既富有个性风格,又具有宏大叙事的广度与深度,显示出作家丰沛的创造活力和浓烈的家国情怀。
《御窑重器》从晚清御窑关闭前最后一批瓷器的烧造起笔,叙写了御瓷制造过程中的重重艰难及种种奥秘。尔后,通过重器龙凤双尊的流离,将大历史中载浮载沉的匠人良工和世态人情进行深描,在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中,对瓷器历史、地域风情、文化传统和人性等宏大命题进行探讨。在空间地域上,小说由江西景德镇辐射至北京、东北乃至日本,在时间上则横贯晚清至整个民国时代。在此期间,“重器”与“良工”彼此成全又时聚时散,历史的常与变,时代的新与旧,人世的悲与喜,构成一幅动态而又传奇的“清明上河图”。
吴仕民在下笔为文时,总会耐心细致地完成“格物”的工作,《御窑重器》中关于瓷器的历史、制瓷工艺、专业术语和行业禁忌等都如同科普、考古般精确而严谨。为了贴近历史原貌和再现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作家通过实地调查走访、查阅文献史料和打捞原型素材等方式方法,准确而精致地写出了瓷器行业的历史风貌。小说对瓷器工艺和文化历史的细心勾勒,不仅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边界,而且让在时间洪流中沉浮的器物以别样的面貌生动地呈现人间。不可否认的是,或许是因为陶瓷历史的悠久,或许是瓷器文化的精深,更或者是专业知识的浩繁,当代作家鲜有以制瓷作为书写的领域,因而本书便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御窑重器》固然围绕着瓷器行业及其传统展开,但在国之“重器”的设计制造和颠沛流离中,则由物及人,以物写人,致力为制瓷行业的良工巧匠作传。小说对瓷器行业七十二道工艺中的专业人才作出了立体、生动的摹写,诸如绘瓷大师王青、拉坯鬼手牛头、制釉高人鄢老板、把桩师傅刘胜远、仿造高手徐一涛等。这些活跃在景德镇制瓷行业的圣手,如同《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般各怀绝技,作者以传奇、浪漫甚或夸张的笔法极写人物的典型性格。形形色色奇人轶事的讲述,发散出民间烟火的亲切气息,有效地化解和平衡了行业文学自带的隔膜、滞重、端肃的面相,流溢出传统小说消遣娱乐的功能。此外,小说中亦有大量笔墨集中于民间道义的宣达与褒扬。例如,景德镇的制瓷人对辞世的孤寡同行充满了温暖的情义——“每逢清明节,老板会带着香烛果品,率领员工对着义冢行礼祭拜,表达对故去同行的缅怀与追念,也是对孤魂野鬼的怜悯与安抚。设义冢而拜,充满人世间的情义,闪射着人性的温暖,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永逝者,如果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御窑重器》的主题是重大而有深度的,在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风俗画式的追溯和怀旧外,还浓笔重彩地写到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人与器物犹如浮萍似的境遇与命运,由此强有力地阐明了国家与个体间休戚与共的命运,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演绎。吴仕民将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时空观援引进古老的行业中,而对“赛先生”和 “现代性”的追求则彰显出作者对救亡保国和弘扬传统的自觉承继,字里行间充溢着感时忧国的济世情怀。在“器以载道”和“器以藏礼”的传统中,器物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是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之物,还在于它代表着的礼乐文化和家国精神。诚如主人公方浩所感知的那样:“这龙凤双尊虽然无口无舌,永远是沉默无语,但身上却凝聚着千言万语:山河的圆缺,国家的兴衰,人性的善恶,都融在了瓷胎里,刻进了釉彩中”。然而,志士仁人付出生命代价守护的龙凤双尊依然被无耻的侵略者和盗抢者所占有。由此可见,国之重器的遭遇与归属,端赖国家的强盛与民众的觉醒。否则,即使我们造出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也不能以方正之心持之,更不能抵挡侵略者的强取豪夺。作者这是一个郑重而精巧的设问。
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小说中那些潜心于陶瓷制作的方正之士也往往遭遇梦想破碎的结局。被称为“青花大王”的瓷画大师王青技艺满身,大名远播,但一生充满憾恨,早年的青云之志与晚年的慈善之举均没能够遂愿。而王青的爱徒方浩则为“开眼看世界”的新派人物,他曾学跨中西,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热切愿望,他迫切地希望关闭御窑,建立起适应现代潮流的瓷业公司,试图通过技术革新和兴办陶艺学校达到去旧疴而入新境的理想愿景,但却是山重水复,徒唤奈何。
在战争的漩涡中,理想的实现似乎遥遥无期。巴赫金的“人在历史中的成长”的论断指出了个体与社会历史的共生关系。在历史风云面前,个体显然是渺小的,方浩虽冲破重重阻力,以实际行动锲而不舍地坚守育才兴陶的初心。可战火的蔓延与国家的贫弱,令方浩实业救国的抱负成为泡影。小说的结尾,方浩立于被炸毁的柴窑瓦砾中,不得不再次面对瓷业学校面临倒闭、瓷业衰落的事实。此种情状恰如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的沉痛之言:“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民生凋敝,社会极荡,文明式微,回首犹如飘萍般的过往,方浩的困顿、颓唐和幽怨像密不透风的悲云惨雾漫天缭绕。然而,在“黑暗的闸门”前,我们的主人公大志不改,仍旧升腾起对民族、国家浴火重生的强烈企盼,在“焚其旧叶,吐我新烟”的自我勉励与召唤下,将坚定的目光投注在光明的未来。
 更多
更多

一个乡村书写者的局限与追求
“就算不是涉及乡村的题材,我的写作也是注重在自身感受,不粉饰与伪善的。我的写作当然也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而我也是人民的一员。”
 更多
更多

构造“记忆之场”:《革命烈士诗抄》出版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非常大的一部诗歌选集。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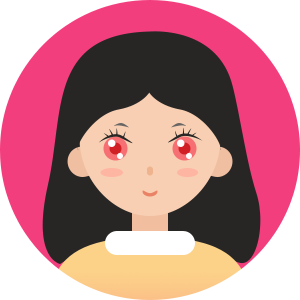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散文 | 一把雨伞和一棵杏树
一棵旺盛且勤劳的杏树,因为与我有关的一把雨伞而腰斩了,我内心充满了愧疚。

小说 | 刘老太太
固执的刘老太太用健康去交换农村所谓的“争一口气”,结果气是争了,体面地盖起了二层的楼房,但却彻底地失去了健康。失去健康的刘老太太连一只麻雀都羡慕。

散文 | 故乡的童年时光
故乡的青砖灰瓦下,鹅卵石巷道是儿时的乐园,留有我童年的足迹。故乡的山峦、溪流、田野、学堂在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烙印,那亲情与乡音是生命中温暖的底色,是一生的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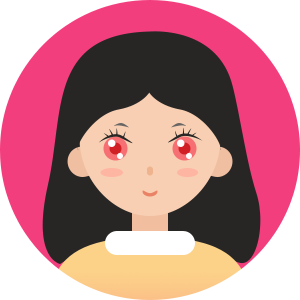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诗歌 | 繁文缛节裹挟的人(组诗)
婚礼,旧藤椅,遗漏的情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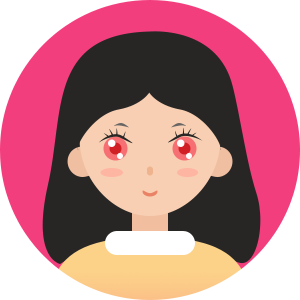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诗歌 | 夏日的自由
组诗《夏日的自由》,共 八首,以夏日为时空背景,以“自由”为精神核心,呈现出一个自由与真实交错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