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平沪通车》:信任危机与欺诈游戏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 李思逸 2020年07月10日09:04
原标题:张恨水《平沪通车》中的信任危机与欺诈游戏
摘要:本文透过引入铁路旅行的经验视角,分析、解读张恨水《平沪通车》中的艳遇与骗局,以此揭示现代主体面临的困境。车厢作为新型的移动空间,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生产叙事的装置;车厢内与陌生人的邂逅既是铁路旅行的普遍经验,也是建构现代主体的重要机制。在此脉络下,《平沪通车》不只是一个包含传统道德说教的现代传奇故事,其对铁路旅行的刻画指向了现代社会中抽象体系与陌生他者所蕴含的风险。男主角胡子云上当受骗并非是因为固守传统,恰恰是遵守了现代的规则,才在理性的推论中得出了不合理的结果。张恨水塑造的女骗子柳絮春,除了象征现代性的欺瞒与可怕外,更是体现了现代主体的本质特征——颠覆流动、无法界定。
关键词:铁路旅行、车厢邂逅、张恨水、《平沪通车》、现代主体、陌生他者
一、车厢中的艳遇与骗局
《平沪通车》是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部以铁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其最先于1935年开始在《旅行杂志》上连载,几乎每期一章,实现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与现代大众媒体的完美结合。该作文笔老练、叙事流畅,充满对于世间人情冷暖的细节刻画以及出门在外的谆谆教诲。上海百新书店于1941年将其单独成书出版,短短5年间就重印7次,当时的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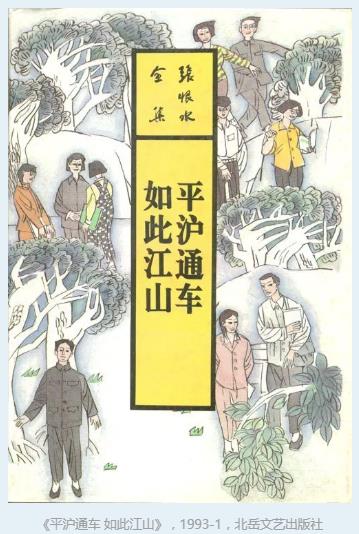
故事背景设置在1935年1月3日下午3时5分开行的由北平(北京)直达上海的列车上——与现实中的列车时刻表完全一致。男主人公胡子云是上海的银行家,头等车厢里的乘客。他在餐车里邂逅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摩登女郎柳絮春,后者因未买到卧铺票而发愁。两人眉来眼去试探之间开始攀谈,胡子云发现这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子居然还算是自己的远方亲戚。面对这位婚姻不幸的新派女子,胡子云难免见色起意,邀请柳絮春去自己的头等包厢内休息。柳絮春举止优雅、通晓英文、为人大方,胡子云像着了魔似的对她积极追求。在这段艳遇中,不仅势利的茶房,欺软怕硬的查票员扮演着不少戏份,更是穿插着与其他车厢乘客们的故事:隔壁头等车厢内携带爱犬的大少爷齐有明,二等车厢内胡子云的旧友、为人世故的教授李诚夫以及曾有几面之缘的余太太,三等车厢内柳絮春曾经的同学、清贫恩爱的张玉清夫妇等等。就在二天二夜的旅程即将结束,火车快到上海站时,自以为会抱得美人归的胡子云方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皮箱里的十二万巨款不翼而飞,柳絮春也趁他睡着之际在苏州站悄悄下车。借助茶房的报告和齐有明的消息,胡子云才恍然大悟自己中了骗局,那老鸨出身的余太太更是女骗子柳絮春的同伙,而三等车内所谓曾经的同学跟柳絮春其实并无多少交际。小说结尾是数年后,已经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胡子云再次搭乘此趟列车由上海前往北平,只不过这次他成了三等车厢内最底层的乘客。当列车又经过苏州站时,往事不堪回首的胡子云看到车窗外年轻貌美的摩登女郎不禁陷入疯狂。他跳下车去警告女郎身旁大亨模样的男子小心女骗子,却被人视作疯子,为继续前行的列车所抛弃。[1]
早在1913年上海至北京就有每星期开行一列的旅客火车。自1933年起,改为每日对开一列,旅客要在南京下关至浦口间乘渡轮过江。1934年开始采用火车轮渡的方式,即乘客可以留在车厢内随原车一起过江,运行时间缩短至36个小时。[2]至此,北京和上海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嵌入进一个完整封闭的铁路系统中——人只要待在车厢内,无关承载其下的是铁轨还是轮船。小说中的“通车”便是寓意在此,作者借余太太之口评论道:现在这样出门算不了什么,只要在北平前门上了火车,就算到了上海北站。这趟在线的列车设备自然是奢华讲究——头等客厅车和餐车的内部样貌可借当时报导的照片加以领略(图1及图2);[3]服务水平臻至一流——《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乘此线自上海北游后,称沪平通车“引起旅客无限的好感”。[4]

男性乘客在车厢内邂逅陌生美女的故事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已多有出现。除了刘吶鸥的《风景》,更早还有另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朱瘦菊的小说《新歇浦潮》,其中第八十二回就有“彭公子车厢逢艳侣”的情节。但车厢内的美丽女子以一种类型化的新女性形象出现——身着高领皮大衣的摩登女郎则是1930年代的文化产物。当时《大众画报》曾刊载广州一个名为“羊社”的文艺绘画社团之作品,有一幅漫画《车厢内的自由神》便是描绘这种西化的时髦女性(图3)[5],与《平沪通车》对柳絮春的文字描述及所配插图如出一辙(图4)。[6]

车厢里的摩登女郎其实是猎取钱财的女骗子,这样的桥段在当时新闻报导中屡见不鲜。陈建华发现上海小报《福尔摩斯》1928年刊载的一则新闻《宁沪车中之美人计》即是一例,其中陌生男女在车厢中相互凝视、藉由茶烟之事开始交谈的套路与《平沪通车》的情节极为类似。[7]除此之外,像《火车中之新骗术》报导的是南洋一位商人在火车中被美艳的泰国少妇用咖啡迷倒,丢失钱财而大发神经病。[8]《火车中又发现漂亮妙龄女贼》讲的是南京至上海特快列车的头等车厢中,一位有钱少爷邂逅一位陌生女子,两人同样是以借火吸烟为由,互通款曲。该女子打扮时尚,风姿绰约,交谈之中更是显得对于国家大事、社会民生等颇有见解。少年对女郎崇拜至极,心神荡漾,以为遇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而极力示好。等到他钱财尽失,女郎也自中途下车后,才意识到其“实乃一神技之女偷也”。[9]无可否认,《平沪通车》的故事和这些新闻报导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反映的是某种客观事实,况且这些新闻本身都有太多可疑之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女性刚进入现代公共空间时,其作为被害者的机率要远远高于自身成为加害者的机率。街头、公园、车厢,女性在这些公共场合不单是可能和男性一样遭受意外,还会因为自身性别的因素而面临更多的不安与威胁——这是男性漫游者和冒险家无法想象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都市和20 世纪初的北京城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男性作者主导下的新闻报导、旅游指南以及通俗小说,都在极力告诫女性新的公共空间对她们来说是如何危险并时刻提醒作为女人自身的脆弱无力。[10]与需要男人保护的柔弱女子相对应的,则是文本中常出现的另一女性形象 :会祸害男人、谜一样的危险女人。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女性读者的规训,那么后者则是面向男性读者的教诲。车厢中的陌生女人永远都是时尚漂亮、充满诱惑的,她们时刻都懂得利用自己的女性特质去勾引、欺诈、诬陷、偷窃那些处在蒙昧和被动之中的男性乘客。所以火车上的骗子一定是由美丽而狡诈的女人担当——她们不可能逾越自己的性别特质去干男劫匪的活,虽然有时会和他们共谋。[11]柔弱女子和危险女人都有着被男性作者物化、类型化的倾向,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公共空间中女人的污名化。但这并非需要我们去彻底质疑车厢中骗男人钱财的摩登女郎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只是必须谨记这种“真实”及在文学中的再现同时也是男权意识形态的产物。正如女性主义学者伊莉萨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论述的那样:男性作家及其笔下男主人公挥之不去的焦虑和痛苦是和性的观念紧密联系的,在都市环境中体验无限可能的同时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此现代女性在城市中总是被再现为引诱者、妓女、堕落的女人、女同性恋,但也具有遭受危险时的善良女性特质,以及战胜诱惑和苦难的英雄女性特质。出现在现代公共空间中的女人是城市的闯入者,是混乱和问题的症候,是城市中的斯芬克斯(Sphinx)。[12]
恰好周蕾(Rey Chow)为《平沪通车》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版本的解读。在她看来,这一铁路旅行中艳遇变骗局的故事关键是神秘危险的女性他者与现代性的结盟,并被越来越商品化的现代世界赋予了合法地位。胡子云沦为这场欺诈游戏的输家,是因为其自身作为传统的男性沙文主义者,既被新的世界所抛弃又无法回到旧世界中去。尽管他曾尝试对这新的世界进行解释,却意识不到光晕(aura)消散的现代世界危机四伏,只能落入他者的陷阱。而柳絮春之所以成为赢家,恰是因为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女性身份——她能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不仅是因为艳遇中性的角力,更是因为她自觉地自我贬损为窃贼、妓女、一个西化的女人。柳絮春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火车的运作遥相呼应:冷酷无情、充满效率,从不等待别人。[13]这种解释背后有着强烈的个人身份政治姿态:鸳鸯蝴蝶派的通俗作品长期被现代文学史占据正统地位的五四作家所轻视,这为周蕾设定了一个从边缘位置出发的契机。她发现这些作品中所具有的感伤、煽情、说教,以及碎片化、戏仿性的叙述正代表了一种女性化现代性特质,以此挑战占据中心的、代表男性特质的五四作家,把价值完全颠倒过来。周蕾对《平沪通车》的阅读不乏启示,却因为对抗性太强——太过在意一种中心/边缘、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常常将文本进行过度阐释。银行家、头等车厢乘客胡子云,明明具有显著的理性计算能力和丰富的现代旅行经验,却为了符合上述公式,而被划为传统中国的代表。同样,柳絮春成为车厢中的女骗子是否是因为女性主体意志的选择我们不得而知,她所动摇的更像是现代的理性规范而非一种想象的传统。简言之,如果我们重视的是传统/现代,男性/女性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不是这一关系本身,那么结果只可能是颠倒了中心/边缘位置上的对象而没有真正颠覆这一权力模式。
鉴于此,我将从信任危机和女性主体两个角度对《平沪通车》予以新的解读。首先,车厢不只是艳遇发生的背景,铁路也不只是现代性的象征——它们都切实地参与进了这场与陌生人的邂逅。骗倒胡子云的不只是扮演摩登美女的柳絮春,还有车厢、铁路及其背后整个的现代抽象体系。其次,柳絮春的多重身份扮演及女骗子这一匮乏的主体称谓,正说明主体本质上无法界定、并不绝对存在。她的颠覆力量并非来源于和传统男性对立的现代女性建构,而是作为她者在永远成为主体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展演行为(performative acts)。
二、现代主体的困境之一 :抽象信任
齐美尔(Georg Simmel)将男女之间的艳遇视作现代性冒险经验的典范,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了欲望的强力与理性的妥协。冒险家们要想成功,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之外,还必须祈求外在于个体之上、不可计算的运气。[14]彼得·贝利(Peter Bailey)受此启发,对维多利亚时代火车中的艳遇及其文学表征进行了探讨。车厢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男女激情冒险的最佳场所:乘客在其中暂时摆脱了家庭、工作的身份束缚,与陌生人一起心照不宣地进行角色扮演游戏。与维多利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性的压抑形成对比,车厢成了跳脱这些教条规范的“法外之地”,上演着快餐化的现代“狂欢节”(Carnivals)[15]。马修·博蒙特(Matthew Beaumont)则延续弗洛伊德的脉络,将车厢定义为一种“诡异地方”(locus suspectus),关注西方现代文学和电影是如何以车厢中的犯罪来表现个体的自我异化。而车厢在作为犯罪现场的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经验的原处情景。[16]结合这两方面来看,艳遇和犯罪,快乐与毁灭,从来都是车厢一体两面的存在方式。
《平沪通车》里艳遇最开始在餐车上发生。根据文本所述,餐车处在连接三等车厢和头二等车厢中间的位置。不过按照列车的规定,只有头等和二等车厢内的乘客才可入内。这以资本为门坎划定的特定空间给里面的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也限定了胡子云去想象另一位陌生女子身份的范围:女学生?姨太太?都不像,但总之是属于阔人之流的摩登女士。而犯罪进行的现场——头等车厢却是整列火车上最为奢华和安全的私密空间。当列车停靠在较大的车站时,茶房为了讨好胡子云表示自己会帮他把房门锁紧,叫他不用担心只管下去走走。对于这种金钱买来的安全与舒适,胡子云自然视作理所应当,但同时又更愿意把它想象成是对自己做为一个现代文明旅客的奖赏。小说中借胡子云之口抒发的两处议论,极为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有钱人心态 :
并不是因为我有饭吃,我就说花不起钱的人不好。的确的,公众场所,总是花钱多的地方,秩序要好些。譬如电影院,卖一块钱门票的影院,里面是咳嗽声都没有,一毛钱门票的电影院,那里面就像倒了鸭笼一样了。[17]
现在青年人,动不动就说铲除阶级,这是谈何容易的事。你看,就是当小贩的,他们也分阶级,有力量的,自由自在的,在站里面作买卖。没有力量的,就在木栅栏外面等候主顾了。[18]
这种悠然自得的优越论调,和日后胡子云在三等车上遭人嫌弃,因为一身破烂而不敢去和他人计较等穷困潦倒的情形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此时还未遭罪的胡子云自然不会考虑这些,在与李诚夫、余太太的谈话中,他极力想表明自己之所以高人一等,不光是因为有钱,还因为自己的行为举止算得上是“火车上的典型旅客”:一个讲卫生、守秩序的现代文明人。不用说,在胡子云眼中,柳絮春除了有钱外,举止文明、态度大方,当然也是属于这种“典型旅客”的范畴。可见美色只是诱因,真正让胡子云安下心来敢于对柳絮春展开追求的是后者的言谈和行为。这种有关现代文明旅客的想象无疑在艳遇和骗局的顺利进行背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类似,平沪铁路的运行时刻、经停站点以及沿途的地方知识,这些看似客观的信息也在两人的交锋中有着偏向柳絮春的嫌疑。余太太在和柳絮春的两次秘密对话中,断断续续地涉及火车沿途经过的城市:“以不过苏州为宜”,“镇江最好”,“常州无锡都没有镇江好”。对于读者来说,已经隐约猜测到她们是在确定下手的地点和时机——这些都是列车会停留较长时间的站点;但对于胡子云而言,这些车站的名字不过是旅途路线上的符号而已,况且他对这些地方更是了若指掌——比如小说中各个地方的名胜特产往往以胡子云的视角来为读者介绍。张恨水通过此种叙述手法一方面让艳遇/骗局的发展配合真实的铁路运行状况使读者信服,另一方面借文中人物的论述为当时《旅行杂志》的读者提供实用的出行信息。那么令读者难免疑惑的是,为什么一个旅行经验如此丰富、掌握了沿途信息的乘客胡子云仍然还会上当受骗?真的是因为他色令智昏,失去理智了吗?其实不然。因为《平沪通车》的整个故事都是在提醒读者胡子云之所以上当受骗不是因为他缺乏经验和常识、没坐过火车,恰恰是因为他太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相信自己积累起来的旅行知识,反而落入了陌生人的圈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浦口渡江那一段:火车轮渡时,柳絮春借口要去下关买咸水鸭而从浦口下车,实际上是为了和余太太商定最终的地点。胡子云对此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这位小姐的举动有名士气,很脱俗。在旁附和的李诚夫由此推断柳絮春一定是老走平沪路的常客,解释道:“这一渡江,现在虽是省了旅客下车上船,下船上车,可是这渡江的时间,实在是长得很,几乎要达到四个钟头。所以由北方到南京来的人,虽是坐在车上可以过江,也不愿坐了车过去,总是由浦口下车,坐了渡轮走,因为这样走,至少是要早三个钟头进城的。”“老坐这趟车的人,到了浦口,立刻过江,到下关去洗个澡,还可以到馆子里去吃餐晚饭,从从容容的由下关车站上车来一点也不误事的。”[19]李诚夫此番谈话事实上是针对《平沪通车》当时的读者而言,既说明了“通车”一事的来龙去脉,又为潜在的旅客给出了打发时间的建议。但在艳遇/犯罪的发展脉络里,这一旅行常识却成了麻痹胡子云、掩护柳絮春行骗的助力——为什么要去怀疑任何一个正常旅客都可能做的事呢?这不仅体现了张恨水在情节铺陈上的巧妙,更让整部小说超越了规训旅客行为、传播旅行信息的导览范畴。因为不论是之前文明现代的“典型旅客”之规范想象,还是现在有关铁路旅行的常识,都不足以保证乘客在车厢中的安全。一个看似正常的陌生乘客可能是对“我”图谋不轨的骗子,而“我”所获得的知识、积累的信息同样会被他/她加以利用。所以在与陌生乘客的相遇中,知识与经验都不可靠,唯一能做到的是抑制自己的欲望。这并非是欲望本身要为车厢中的罪行负责,只不过追求欲望所要承担的风险远远大过理性计算的考虑。鉴于艳遇和犯罪进程中的不可测控因素,主体只有以节制欲望、限制与陌生他者深入交往的办法将这两扇门同时关上。
不得不承认,胡子云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了理性谨慎、时刻计算的现代人特征。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真正对柳絮春放心过。在邀请柳絮春进入自己的头等车厢后不久,胡子云就趁她出去时偷偷查看她的皮包以探听她的底细,想知道里面是否藏有什么秘密。随意放置的钱票让胡子云相信这是阔少奶奶对金钱不在乎的表现,一枚不戴了的订婚戒指印证了他之前有关柳絮春婚姻出现问题的猜想,而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上面有着在杭州的具体地址更向他证明柳絮春不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她有着自己的关系网有着自己的身份。从事后的角度看胡子云确实不是一个成功的侦探,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的努力,以及他诸多推测中蕴含的合理性。另一处细节更为直接的说明,胡子云即使在满足了性欲、春宵一刻之后,仍然冷酷地盘算着自己和柳絮春的关系。“看她的样子,脸上也带了不少的聪明,处世的门坎应该是很精,何以她怎肯这样的,让男子占尽了便宜?是了,她虽说不在乎钱,然而钱这样东西,究竟是可以吸引人的。她必然是以我是个银行家,和我合作起来,无论怎么着,也可以得到一些银钱上的便利。现在她决不会沾我一文钱便宜的。久而久之,恐怕就谈到钱上去了……”[20]
这番思量既透露出胡子云“银行家”的本色,也让我们看到胡子云不是没考虑过柳絮春图谋自己钱财的可能性。他只是根本没料到骗局会来得这样快——36 小时的旅程中,更没想到居然就发生在火车上——安全的车厢、严格的制度、熟悉的线路、文明现代的乘客等等幻象转瞬就崩塌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骗局成功的原因简单概括为胡子云被一个陌生的摩登女郎骗取了信任——他的信任从来不只是针对另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夹杂着车厢空间、乘客规范、铁路系统、知识经验的“抽象信任”(abstract trust)。
“抽象信任”是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最早提出的概念。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是联系在同一个具体场所中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熟悉的在场(presence)和地域性活动中依据家庭氏族、宗教信仰等延展开来。但现代性的来临导致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社会关系从原本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并且在一个无限跨度的抽象时空中以不在场(absence)的方式重新组织。有限个体在无限的时空中必然会面临信息的缺乏,而信任即源于时空中的不在场。毕竟,我们不需要对一个永远为我们保持可见的对象或一个让我们彻底掌握的系统怀抱信任。因此吉登斯认为,信任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关。在现代社会中,信任被授予的对象不再是个体,而是抽象的能力;信任涉及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承诺和情感,而是包括象征符号、专家系统在内所有知识和信息汇集的抽象体系。抽象信任成了主体必须具备的能力用来处理时空中的不在场,而这问题背后往往指涉另一个主体看不见的活动,即他者的自由。[21]吉登斯还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抽象信任的产生不仅影响了本体论上的安全感——和主体漂浮不定的身份捆绑在一起,也与亲密关系的转变息息相关——在艳遇这种新型的浪漫爱情中,熟悉与陌生的两种状态快速地反复交替。[22]抽象信任所能获得的奖励只不过是使日程生活正常运转,它要承担的风险却是现代世界的动摇及主体自身的毁灭。小说最后安排胡子云数年后看到一个长得像柳絮春的女人从而陷入疯狂,这和他当初在车厢中意识到自己被骗时的镇静形成一种有趣的反差。他对火车的无可奈何,对铁路的无力责怪,对自己的懊恼,对女骗子的痛恨,都再次印证这个故事的教诲:物与抽象体系在现代性中永远处于免责的状态,主体唯一能做的只有节制欲望,提防他/她者。
三、现代主体的困境之二 :展演颠覆
胡子云的乘客形象象征了现代主体理性、秩序的一面,但却在一系列看似合理的过程之中推演出了不合理的结果:以抽象信任和经济资本建立起的身份看似稳固,实则脆弱不堪。柳絮春的形象代表了现代主体非理性、无序的另一面,然而这种混乱无序同样是以合乎理性、遵守秩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里面体现了现代性的狡计:正如非理性的对象也只能依靠理性的表达方式谈论自身,对现代秩序的颠覆其实也是现代性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省察柳絮春扮演的一系列不同身份来理解这一点。
当她刚在车厢中出现时,是一个没买着头等卧铺的摩登女郎;在餐车中和胡子云相遇时,她是一个看着洋装书、会英文、要抽名牌香烟的阔少奶奶;两人间的对话揭示了她是胡子云朋友的亲戚并且是一个婚姻不幸的新派女子;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胡子云感到她是一个体贴的旅伴;三等车里以前的同学,证明柳絮春是曾受过教育的女大学生;在面对穷苦乘客时的大方义举,又让柳絮春看起来像是个善良的妇人;她的言行举止也表露出自己是非常熟悉这趟平沪铁路的老乘客;作为胡子云欲望的对象,柳絮春是温柔的情人;但在最后胡子云人财两空时,才从别人嘴里得知,她是火车上有名的女骗子——所在地址无人知道,真实姓名始终不明,柳絮春这个名字当然也是假的。就算最终我们将她的主体界定为女骗子,这样的谜底也没有任何价值,等于什么都没说。女骗子,只是我们在掌握片面信息的情况下、对无法界定本质的主体给予的暂时称呼。我们甚至无法将女骗子归类进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等习以为常的分类范畴里。女骗子就像是一个占据着空位的零,拒绝着所有“女人”条目下的名词属性、分类卷标,但又可以作为一种流动的主体同时拥有它们全部——这正是柳絮春在车厢中的所作所为。
此外,即使确定柳絮春是女骗子,这是否意味着她在车厢中展示的一系列形象都是假的呢?倒也未必。我们在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柳絮春的多重身份和所具备的现代乘客的言行举止有多少是伪装出来的。只不过一个曾经的女大学生也可能是现在的女骗子,她对胡子云的“残忍”和对穷人体现出的“善良”也不一定互相冲突。张恨水提醒说:“女人的心,很是难揣测的,有时很厉害,有时又很慈悲。那管媳妇的恶婆婆,常是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妓女们常是把忠厚青年,引诱得他倾家荡产。可是对那街上素不相识的贫寒人,也常有把整张钞票施舍的事。”[23]表面上看,这仍是传统男权社会对于“女人善变”的想象与告诫,但结合车厢邂逅的语境和乘客主体的反思,这种提醒也具有了新的现代内涵:不要根据片面的行为去推断他者的本质,对主体的理解只能局限于她/他在具体情境中的再现活动。这就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展演理论反思现代主体的做法不谋而合。
巴特勒认为,女人作为一个主体,并不绝对存在,也不是作为既存男性主体的绝对他者而存在。其是在永远“成为”主体的过程中,通过不断重复的性别展演,借助具体情境中的言语述行来暂时地建构身份。[24]展演不只是表演,前者是主体针对他者进行的一切言语述行,后者更多是根据既定的规范或某种角色展开的活动。所以主体可以在再现中容纳个体扮演的各种角色,却没有一个先行存在、能被表征的本质。强调主体的展演性意在提醒我们,不要去想象一个隐藏在言语行为背后的内在自我,因为并不存在一种能脱离展演活动之外的本体论状态。[25]主体的展演活动,不仅关涉个体的自觉行为,更是涵盖了权力论述、身体实践、意识形态的质询、非人的物、抽象体系等诸多要素的协同运作。由此建立起的身份认同不可能是清晰直接的,也不会一劳永逸,必须要在不断的重复之中进行再次确认。如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巴特勒也特别强调没有两次完全一样的重复。因为在展演活动的具体情境中时空是变化的,经验是流动的,构建的身份每次都要重新被赋予意义、重新被置于新的情境之中,所以重复之中蕴含了颠覆与改变的可能。展演的颠覆力量不是和既定秩序的对抗,也不再于它对当下权力关系的破坏或超越,而是源于对现存资源、规范、角色的重复利用。[26]
女骗子柳絮春实在是上述展演主体的最佳代言人。她展示了一切令人信服的细节,但在本质的位置上永远是空无——谁都无法确定的陌生人。她对铁路秩序的遵守和利用,对各种乘客类型的重复展演,使她构建出的身份比真实还真实,比典范还典范。真假的判定原则在她面前失效了,胡子云却还在致力于弄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也许是积累起来的资本和符合理性、遵守秩序的生活让胡子云忘了真实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建构的,这只能等他丧失资本、陷入落魄时才会重新想起来。《平沪通车》的劝讽意味也显露于此,尽管我们对陌生人一无所知,尽管我们没办法检验信息的真假,但会被骗钱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真实也是承担不起的后果。柳絮春和铁路的共谋共生,让她的颠覆也落脚为一种游戏:胡子云的失败和柳絮春的胜利并不构成两种现代主体的取代关系,而是成了现代性内部的一种自我调整。资本从凝聚走向流动,界限从明确转为模糊,他者从陌生变熟悉并再次变陌生,在这些过程中铁路和现代性的体系始终是毫发无损的。所有的责任都被转嫁到主体自身的欲望上,所有的教训都被归结为亘古不变的箴言:他者不可信、小心陌生人,而火车永远继续向前开。有趣的是,这一现代性颠簸不破的真相偏偏是透过一部与理论无缘、欠缺正面批判力量的通俗小说暴露出来的,这或许再次印证了叙述的意义总是能超越自身的时代,与文字的反讽力量一起继续存在下去。
注释:
1.张恨水:《平沪通车》,《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1 期至1935年第9卷第12期。
2.《上海铁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铁路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116— 117页。
3.图1:“头等客列车内景各皮椅均可旋转”,图2:“沪平通车餐室内景”,转引自《记两路新备沪平联运客列车》,《旅行杂志》1934年第8卷第3期。
4.赵君豪:《北游旅程》,《旅行杂志》1937年第11卷第6 期。
5.图片引自容衍:《羊社漫画:车厢内的自由神》,《大众画报》1934年第6期。
6.图片引自张恨水:《平沪通车:第二章薄水相逢成了亲戚》,《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2期。
7.陈建华:《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5— 218页。
8.佚名:《旅行:火车中之新骗术》,《游历》1930年第8 期。
9.三叔:《火车中又发现漂亮妙龄女贼》,《风光》1946 年第 10 期。
10.参见Anna Despotopoulou,“‘Running on lines’:Women and the Railway in Victorian and Early Modernist Culture,” Teresa Gómez Reus and Terry Gifford, ed. Women in Transit through Literary Liminal Spac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47-60. Anna Despotopoulou, Women and the Railway, 1850-1915.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3-40. Weikun Cheng, City of Working Women:Life, Spa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ern Asian Studies, 2011, p.85-91.
11.Anna Despotopoulou, Women and the Railway, 1850-1915, p.29-30.
12.Elizabeth Wilson, The Sphinx in the City:Urban Life, the Control of Disorder, and Wome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5-9, 86-87.
13.Re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76-83.
14.Georg Simmel,“ The adventurer,” Donald N.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187-198.
15.Peter Bailey,“ Adventures in Space:Victorian Railway Erotics, or Taking Alienation for a Ride,” in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01 January 2004, Vol.9(1), p.1-21.
16.Matthew Beaumont,“ Railway Mania :The Train Compartment as the Scene of a Crime,” Matthew Beaumont and Michael Freeman ed., The Railway and Modernity:Time, Space, and the Machine Ensemble. Bern:Peter Lang, 2007, p.125-153.
17.张恨水:《平沪通车:第四章二等车上的典型旅客》,《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4期。
18.张恨水:《平沪通车:第七章大家心神不安》,《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7期。
19.张恨水:《平沪通车:第十一章浦口渡江时》,《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11期。
20.张恨水:《平沪通车:第九章甜言蜜语》,《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9期。
21.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Oxford, Boston and New York:Polity Press, 1991, p.21-36, 79-99.
22.Ibid., p.112-124,137-144.
23.张恨水:《平沪通车:第八章求人助者亦愿助人》,《旅行杂志》1935年第9卷第8期。
24.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1999, p.23-33.
25.Ibid., p.173-180.
26.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226-241.
(图片转自“现代中文学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