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沈善增

沈善增
在跨年的那几天,心情黯然,打开电脑想写几句诗辞岁,盘旋脑子里的,却是新近去世的多位朋辈师长。于是写了一联:“忍看师友登仙列,唯剩诗文作挽联。”诗写成后,颇觉得新年来临之际这么写有点不祥,就没有传给朋友们看,只是在心里暗暗祈祷,愿辞岁把一切晦气都辞去。但是,不祥的感觉挥之不去。新年以来,一月份走了刘绪源,二月份走了郏宗培,都是我的朋友,现在是三月份,沈善增又走了,难道一言成谶,真的唯剩诗文作挽联了?我为善增拟的挽联是:
弥陀转生犹沉痛:救人可救世不可;国学到底无是非:批判行还吾也行。
善增是一个有传奇故事的人,估计以后他的朋友们都会不断传说这些故事。我对此了解不多暂且不说。本文只想简单勾勒一下我对他的印象,当作是挽联的注释。沈善增本来可以做一个很不错的小说家。他出身市井,在福州路石库门弄堂里长大,有着典型的上海男人的乐天、聪敏、善解人意等优点,一篇《黄皮果》在实验小说蜂起的1980年代中期问世,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但他真正写出扛鼎之作的,是长篇小说《正常人》。小说也写得很正常,但是那个时候是寻根文学迅速崛起、先锋文学伺机而动的时候,批评界都受这风气的影响,希望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实验性作品,对于老老实实的叙事兴趣不大。我在撰文讨论他的这部作品时,还自作聪明地从刚刚学来的作家和叙事人分离的角度分析文本,尽力把它分析得“不正常”一些。善增当然也笑纳。记得他在送我的书上题词,其中就赞扬我“一眼看出,两种文本”。不过也可能他在窃笑我的过度阐释,只是不说穿而已。那些日子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经常在我家里聊天到深夜,他知道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听得也不累。我也曾经看好沈善增的创作,几乎讨论过他早期的所有作品。我甚至觉得他会是上海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因为一来他懂得那么多上海市井故事;二来是他有一种出自本能的高远襟怀,而没有一般上海作家很容易犯的狭隘自恋的毛病。沈善增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些毛病,他是有大襟怀的。正因为具备这个特点,他才可能在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作家创作班里一下子发现和推荐,许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像孙甘露、金宇澄、阮海彪等等,后来有些作家有了更大的发展,文名远在他之上。这里就可以看出沈善增的襟怀之大。过去有句话说上海人的性格:龙门会跳狗洞能钻。沈善增就属于上海人中会跳龙门的人。
但也许正是这种襟怀所决定的,小说创作渐渐就装不下他更加远大的向往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迷上了气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气功治病。这一点我也曾受益于他,从他那里获得许多气功知识。不过善增绝非一般的为气功而气功,他有更大的情怀,希望能够为普天下看不起或者看不好病的病人治病。他努力练一种气功,据他自己所说,是用气功把别人身上的病吸收到他自己身上然后再甩掉。我当然无从了解他所体验的种种身体信息是否都是真实的,但至少他自己是相信的。他不断告诉我,他利用气功治疗某某人的疾病,而这时他对文学创作已经失去兴趣了。我曾经与他争论过,我希望他赶快回到文学创作,多写几部小说,而他却认为,写小说主要还是自娱性的,仅仅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气功治病却可以救人一命,利于大众,所以更有意思。我知道他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选择的,为此他还写了一本《我的气功纪实》的书。他读了很多中医和气功的古籍,一步步接近了佛经。
这以后,因为大家都忙,我与沈善增的交往就不多了。但我始终是在他的朋友圈内。记得那几年主编《上海文学》,我受到一些争议,朋友中站出来公开为我说话的,就有沈善增。不仅如此,沈善增还影响了一位我素未谋面的作家,也出来仗义执言。为此我感念他,把他视为一辈子的朋友。不过那时候,沈善增对气功也不甚热心了。他被一个更大更有吸引力的向往迷惑住了。从研读佛经开始,他又一次无师自通地研究起老庄孔孟。沈善增本来是工人出身学写小说而成为作家,没有在学院里受过系统严格的小学训练,后来他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中文系文凭,但是要研究古典经籍还是有一定难度。《沈善增读经系列》花了他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这完全是靠他的聪敏过人和勤奋过人。他以极大兴趣投入研究,说他是为了弘扬国学倒也未必,他太聪敏和太富有想象力,他对《庄子》《老子》《论语》《坛经》等古代各种学派的经典都读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而且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还我”系列,既然要“还我一个真相”,那就是说,以前各派大家的解释都有错误。他开始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清理批判。这样的做法,如果放在以前某个特殊年代,也许会成为“工人也能学理论”、或者“小人物向学术权威挑战”的典型而得到高层关注,可惜,子不遇时,善增生活在一个风清月朗的时代,学术研究需要积累而非革命,他似乎掉进了一个无物之阵。小人物敢向学术权威开炮,学术权威未必有义务来搭理小人物,自然也没有谁站出来回应他的叫板。这给沈善增带来的郁闷是可以想见的。我因为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善增的各种观点也就姑妄听之,并没有特别留心过。但我以为善增起先进入国学领域,是一个聪敏人的童心大爆发,他读到了许多新鲜思想而引起了新鲜的感受,于是有了自己的理解。但是到了后来,他越是得不到关注,心理上就越走偏锋,滋生了较劲的念头。《还我庄子》《还我老子》《坛经摸象》等著述一本本问世,但他心内的寂寞也越来越加深。2014年他65岁生日,早上起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言:“免担孔孟丧家累,幸得老庄顺性游。福报怎求超此福,余生更为众生谋。”在这里我读到了他的焦虑。原来他的研究经典的热情背后,还是有着更大的“为众生谋”的原动力,这与他热心气功治病救人如出一辙,只是谋福的范围更大,近乎“救世”了。要说到救世,那就难了。
沈善增晚年多病,目力渐差,但他写作更加勤奋,常常利用博客、微信发表观点。他迷恋于此道,而且相信新媒体更有利于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那几年他写了几部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论著,他自己比较看好的是《崇德论》。他认为这部著作能够在挽救世道人心中发挥一点作用,于是不遗余力地推广这本书的观点。我不想否认善增晚年的研究和写作都有点急功近利,但这种功利心是与他一以贯之的“为众生谋”,以及随着身体的每况愈下而生发出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联系在一起的。他太迫切希望人们来了解他的很多想法,来倾听他的许多见解,在他晚年开设的一个题为“瓢饮”的专栏里,他谈天说地,内容广泛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诗词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谈。我在近几年与他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是他每天一篇“瓢饮”文章,我是必读的。读之后也常常为他担心,总感到他被巨大的焦虑所困扰,为之也常常劝他。甲午年阳历10月8日,读了善增的《六五自寿诗》后,我曾与他唱和:“人生收获在金秋,稻穗沉沉德化周。庄老还君新地界,弥陀渡世赖天酬。宅心伊甸何家丧?沉气虚中任我游。身在江湖疏问庙,鹏程走狗两非谋。”第二年(乙未)8月3日,又一次送诗与他:“弱水三千起一瓢,伏中挥汗涌文潮。谈天说地君真健,养气明心病自消。释道孔为家学问,诗书气作国之骄。善增日日添增善,胜过磻溪老钓猫。”我在诗中对他有赞扬也有规劝,善增是理解的。他最后一次来看我,坦率地对我说:“我自己最吃亏的,就是没有在高校里工作,我没有平台,也没有经费,更没有学生助手,我有一肚皮的想法,都是好东西,可是实在来不及写出来,没有人帮我啊!”这是他与我最后一次面对面时说的话。再后来,“瓢饮”文章就渐渐少了,终于不见。
善增生前讲究佛缘,某个朋友去世,他总会来对我说,某某的灵魂到过他的家门与他告别了。复旦几位师长弥留之际他都不请自来,穿梭于生死场间,尽了自己的招魂之力。他现在这么突然间撒手而去,我想也不能让他孤单单地远行,他毕竟是一个喜欢热闹喜欢轰轰烈烈的人。于是写下以上文字,我想告诉亡灵,他的离去,对在世的朋友,是一个难以弥补的大悲恸。我感到了真正的人生之痛。
2018年3月28日写于鱼焦了斋
 更多
更多

理解《红楼梦》的伟大,自然心生敬畏
在白先勇眼中,《红楼梦》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书”,是“越看越了不得的东西”。
 更多
更多

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镜池在北平来去匆匆的一年
山河破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人能够置身事外。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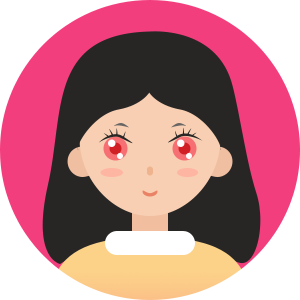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散文 | 一把雨伞和一棵杏树
一棵旺盛且勤劳的杏树,因为与我有关的一把雨伞而腰斩了,我内心充满了愧疚。

小说 | 刘老太太
固执的刘老太太用健康去交换农村所谓的“争一口气”,结果气是争了,体面地盖起了二层的楼房,但却彻底地失去了健康。失去健康的刘老太太连一只麻雀都羡慕。

散文 | 故乡的童年时光
故乡的青砖灰瓦下,鹅卵石巷道是儿时的乐园,留有我童年的足迹。故乡的山峦、溪流、田野、学堂在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烙印,那亲情与乡音是生命中温暖的底色,是一生的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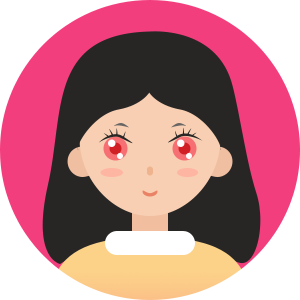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诗歌 | 繁文缛节裹挟的人(组诗)
婚礼,旧藤椅,遗漏的情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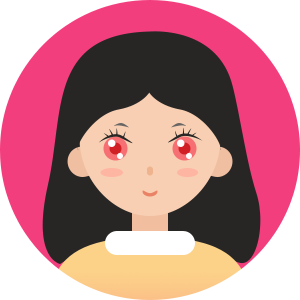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诗歌 | 夏日的自由
组诗《夏日的自由》,共 八首,以夏日为时空背景,以“自由”为精神核心,呈现出一个自由与真实交错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