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记忆里的痛
一
向西,向西,一直向西。
我的祖母放弃故乡的一切,在她暮年的时候,几经碾转倒车换车,从山东胶东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新疆。她品尝了人生第一次晕车呕吐的滋味,放弃了她深爱并熟悉的故土,来到西北边陲哈巴河这个在她看来遥在天边的小镇,来与她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团聚。
灰黄的戈壁泛着滚滚热浪,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像丢了魂,步履艰难地低头拉着一辆吱呀乱叫的架子车,车轮碾压在细软的沙上,身后两条深深的辙痕像蛇一般蜿蜒在戈壁滩上。戈壁滩安静的能听见虫鸣,三、四只讨厌的苍蝇扇动着翅膀在牛屁股上肆意飞舞,慵懒的老牛终于被它们扰得忍无可忍,它狠狠地甩动了两下牛尾巴,这几只苍蝇瞬间仓慌而逃。
祖母坐在车厢里,惊恐地张望着这无边无际的戈壁沙漠,那年祖母七十四岁。
七十年代,父亲带着全家到了新疆,祖母却不肯走。她说:她要看家,替她的儿孙们看好家门,等到儿孙们在外面飘泊累了,回家有落脚的去处。
祖母把故乡当成真正的家,故乡以外的地方,只不过是家人们的暂住地。祖母认为:只要故乡老屋在,这个家就会在故乡继续延续,在外的游子无论走得多远多久,终有一天会叶落归根。她自甘做了那个留守的人,因为在她看来,这件事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和辛苦,她当自不让地做了那个最辛苦的人,割舍下对儿孙的思念,把痛深埋在心底。
祖母在故乡独居许多年。父母不放心祖母亲一个人在故乡生活,说服祖母把九岁的我留在她身边与她作伴。我陪祖母度过两年时光,在那段日子里,祖母努力给我最好的生活和最温暖的关怀,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让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不缺失父母的管教,祖母执意让父母把我接走。我记得,在母亲带着我即将离开故乡的前夜,祖母像丢了魂,她坐在天井的角落里不肯进屋,快到天亮的时候,却一声不响地出了门,直到我们走,她也没回家。我眼含泪水四处找寻祖母无果,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村庄……
多年以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内心仍不由的颤栗,坚强的祖母她定有千万种不舍,不见才是最大的心痛,对祖母来说,这是多么艰难的抉择!
人生最大的痛,莫过于痛心,我想那一刻祖母是最坚强的!
祖母目不识丁,她独居在故乡,却总捎信给我们报平安,嘱咐我们保重,说我们安好,便是她的好,我知道她对我们有着彻骨心痛的牵挂。她给我们的家信,找人代写,送人两枚鸡蛋或一个苹果做为答谢。我陪伴祖母那两年,祖母捎给我父母的家信全由我代写,祖母说一句,我写一句,无非就是些家长里短,今天生产队里分了多少口粮,昨天锄完几亩地的花生云云,写信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我就用拼音代替或是查字典,因为隔三岔五写信的原因,我的识字水平和写作能力提升得非常快,上二年级,就能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作文,让任课老师对我刮目相看。
祖母在故乡的生活和身体无论多么糟糕,她在给我们的信里从不提及,而是在信的末尾总缀加一句:家里一切都好,忽挂念!记得有一次,祖母病得厉害,发高烧好几天下不了炕,她躺在炕上让我写信给我父亲,我坐着小板凳伏在炕上代她写信,照例是祖母说一句我写一句,祖母声音低弱,脸色黄灰。
“家里一切都好,我身体好,孩子也很好。”祖母让我在信的最后缀上这句。
我执笔望着祖母,“奶奶,您明明病了,怎么还说身体好呢?”我不解地问。
“就这样写,别让你爸妈担心!”祖母嘱咐我。
“您病了,不但不给我爸妈说,反而说身体好,您这是撒谎呀?”年幼的我、不谙世事的我竟然对祖母这样说。
祖母伸出粗糙的大手慢慢摩挲着我的头顶,她灰黄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就这样写,大老远的,别让你爸妈担心!”祖母说,声音低哑。
祖母对她远在他乡的儿孙只报平安,却把伤痛留给自己,从来不说给我们,生怕我们担心。
那次祖母病得厉害,长时间不见好,为了早点好起来,我发现祖母竟然背着我,在大半夜里拖着病重的身子跪在炕上乞求神灵赐她灵丹妙药,别让她就这么死去,她说她不怕死,最最让她牵挂的是远在他乡的儿孙,还说更不能丢下年幼的我。那天,不知怎的,喜睡的我就醒着,看见祖母灰黑的背影在暗黄的月光里显得悲凉,她平常梳得整齐的发髻,蓬乱披散……
在我眼中,一度坚强的祖母,她竟有如此凄惨的光景,我惊讶的同时心痛不已,咬着被角偷偷落泪。
祖母在故乡的坚守,终于在她孤独地度过七十四岁生日之后被摧毁,她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卖掉故乡老屋,到几千里之外的新疆与她的儿孙们团聚。祖母或许终于明白儿孙们已经在他乡落地生根,只是把故乡当成一种念想,故乡的她是儿孙们最锥心扯肺的挂念;或许那种长离别的相思之痛,让祖母再难忍受,才痛下决心离开故土,在年老该是落叶归根的时候却连根拔起离别故土;或许还有更多的或许……
我想祖母的决定何其两难,她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有难以割舍的痛。
二
祖母生于清末,她有一双那个年代少有的大脚,穿三十七码的鞋!因为有一双大脚,她算得上那个时代的丑女子!女子长一双大脚不但丑陋,而且是件了不得忤逆之事,三寸金莲是衡量美女的标准,大脚的女子连婆家也不好找。
祖母嫁给祖父,其间也经历了很多曲折……
我曾经问过祖母:“奶奶您的脚咋这大?您没裹过脚吗?”
“我裹脚了呀!”祖母笑吟吟地对我说。
“啊?您裹脚了?咋还有这么大一双脚呢”我不信奶奶裹了脚,“您看沟上大奶奶的脚,才这么长一点。”我伸出食指和拇指给祖母比划。”我所见的祖母辈的女人都是小脚老太太,脚像烟盒大小,尖而弓着,脚面厚肿,脚趾坏死,除拇指外,其他四个脚趾成扁状贴压在脚底,其模样令人恐怖而又可怜可悲!
“裹脚疼得很,我就哭闹着不让裹,所以才有这么一双大脚。”祖母伸出脚来,向我晃了晃。
“那个时候您不裹脚,他们咋肯放过您呢?”我疑惑不解地问奶奶。
祖母把老花镜滑到鼻尖,她盯着我笑呵呵地说:“俺从小没了娘,家里穷,没钱缠脚,到俺十二岁的时候,俺爹才让邻居大婶帮俺裹脚,裹脚布把俺脚缠得生疼,脚趾头都快断了,俺就拼命地哭闹,但是哭闹根本不顶用,俺索性忍着不哭,等俺爹和邻居大婶走了以后,俺就拿剪刀把裹脚布给剪了……”说起这段往事,祖母甚是得意。
“老太爷愿意啊?”我问。那时候女孩裹脚是人生的必修课,她们都要经历同样的苦痛,父辈们决不会因为孩子的哭闹而放弃约她们裹脚。
“你老太爷当然不愿意。”祖母说,她的脸上没了笑容,神色变得沮丧,“为这事,俺还挨了俺爹地揍,我是宁可挨揍也不缠脚,那脚缠的痛死人啊!”
“那你怎么办呢?”我刨根问底。
“我就哭着求你太爷,哎,你太爷也哭着求俺,无论你太爷如何给俺说好话,我就是不裹脚,最后你太爷就给我讲,你如果不裹脚,以后就是个丑姑娘,长大了连婆家也找不着,你不能怪爹啊!”祖母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变得暗淡。
“那时候的人真可笑!”不懂事的我说了一句不疼不痒的话。
祖母苦笑着摇了摇头。
祖母一生可能会因为一双大脚倍受岐视,然而阴差阳错,在后半生的日子里,祖母却凭一双大脚把人生活得无比精彩,不像沟上的大奶奶,整天盘腿坐在家里的铺里垫上,那里也去不了。大奶奶年龄跟祖母相仿,拥有一对三寸金莲,走路连步子也迈不开,颤颤巍巍向前一点点挪动,看着大奶奶的模样,我心里替大奶奶倍感憋屈。
大奶奶腰弯背驼,身子上大下小呈锥形,踮一双尖尖的小脚,总觉得她随时会倒下。我常常假设大奶奶摔倒的样子,她摔下去一定非常沉重,像她这种情况,她摔倒又怎么能够爬起来?出于对大奶奶的好奇,我经常悄悄跟在她身后,想看看大奶奶摔下去的样子,心里也生怕她摔倒爬不起来,我可以拉她一把。
大奶奶曾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大小姐,缠出一双畸形的小脚,自然是大小姐从小要做足的功课,将来才能以此为美嫁个好夫君。我真正赏识过大奶奶那双小脚的真容,它深深触痛我柔软的神经。解开那细细长长的裹脚布,我惊悚地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小小年纪的我,痛得满眼泪水。那是一双怎样丑陋的小脚,完完全全的畸形,足骨变形,脚形尖小成弓状,脚指头全部折在脚心,四个本可以非常秀美的脚指被压成扁状,死气沉沉地与脚底粘在一起。
我痛惜地蹲在大奶奶脚边,抬起婆娑的眼问她:“大奶奶,您疼吗?”
“不疼。”大奶奶摇摇头。
“怎能不痛呢?都成这样啦!”我吃惊地问道。
大奶奶叹了口气对我说:“现在不痛了,脚趾己经都坏死了。”
“大奶奶,你怎么不学我奶奶啊?不让他们这么害你!”我忿忿不平地说。
大奶奶无奈地摇摇头。
我可怜大奶奶的一双小脚,我心痛地抚摸着大奶奶弓起的脚背,问道:“您当时一定疼死了吧?哼!如果是我就不让他们这么害我!”我坚定地说。现在想来当时年幼的我,话说得是那样无知,一个弱女子怎能逃脱了世俗?一个人的力量又怎能与社会抗争呢?
我见过一张大奶奶年轻时的照片,眉清目秀,端庄秀丽。现在想起我都叹息大奶奶:“可惜了,真可惜了大奶奶的美丽!”大奶奶的脚原本应该是一双美足,会让她的身材更加窈窕,然而这双变形的小脚却让大奶奶秀美的身姿没有了婀娜,造成了失调的锥形。
失落的大奶奶摸着我的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怎比得了沟下的奶奶,她这辈子可活了自己的模样,俺呢——”大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生生的让这双小脚把我绊在家里,沟下的奶奶过得日子泼辣啊!”大奶奶说的沟下的奶奶指的是我祖母。
我看见大奶奶眼神里对祖母的羡慕,是倾心而没有半点的造作。一双小脚把模样俊美的大奶奶活活弄成残疾,我对大奶奶生出许多怜惜,如今,每每想起大奶奶,我的心里就充斥着那种让我欲哭无泪的痛楚。
三
大奶奶的丈夫是我爷爷出了五服的堂兄弟,村里几乎都是杨姓,为了便于区分称呼,我按照奶奶们居住的位置区分来叫她们。我们居住的村子属丘岭地貌,一条自然形成的大沟,大奶奶住在沟沿上,祖母住在沟底下,我便称大奶奶为沟上的大奶奶。
其实称呼大奶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她是我堂爷爷的大房女人。堂爷爷娶了两房老婆,大奶奶是大房,是堂爷爷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娶回家的千金小姐,却因为不能生养,她建议堂爷爷再娶一房女人,给堂爷爷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大奶奶知书达理安静贤惠,深受堂爷爷的尊重和喜爱,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中,堂爷爷不得不再续一房小妾,二房奶奶进门一口气给堂爷爷生了四男四女八个孩子,大奶奶没有一句旁话,一声不响地把孩子接到自己跟管教拉扯。
即使二房奶奶为堂爷爷生下八个子女,在杨家功勋卓著,堂爷爷依然把大奶奶的位置摆在首位,从没有过动摇过其他念头。堂爷爷长期与大奶奶住在一起,偶而会到二奶奶房里小住,自从有了八个孩子以后,堂爷爷去二奶奶屋里的时间屈指可数,即使去二奶奶屋里,也是为了生活上的琐事,并不留宿。
堂爷爷脾气暴躁,稍不顺心对二奶奶非打即骂,二奶奶逆来顺受,对堂爷爷的打骂从不言语,反而是大奶奶从中调和劝说堂爷爷。或许是旧观念作祟,或许堂爷爷真正爱着大奶奶,爱得刻苦铭心。他从不打骂大奶奶,甚至没用高声对大奶奶说过话。
大奶奶和二奶奶相处的极为融洽,两人互为姐妹,二奶奶对大奶奶是尊重,大奶奶侧对二奶奶是疼爱,她们共同养育的八个子女在外人眼里对两位母亲没有亲疏。
堂爷爷按照旧习俗给二奶奶在村西盖了瓦房,他和大奶奶住在我家老屋沟沿上的小屋里,小屋收拾的整洁干净,小院里一尘不染。院墙外面长了一溜槐花树,院子西面种了几畦小菜,扁豆的藤蔓开着黄白色的花爬满架,槐花的香味弥漫着小院。春天大奶奶就会从屋里来,搬了把太师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孩子们在小院里来来去去,八个孩子有四个孩子住在大奶奶跟前,另外四个孩子住在二奶奶那边,孩子们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大奶奶安排。
二奶奶比堂爷爷小二十岁,是穷人家的女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十块大洋便将二奶奶嫁到堂爷爷家做小。从我记事到离开故乡的那段日子,每天几乎都能见到二奶奶从我家门前路过,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从没阻挡了她的脚步,她是到堂爷爷和大奶奶住的屋里来,我想她大概是给堂爷爷和大奶奶请安吧!然而二奶奶却从来不说是请安,她总是笑着给我们说:我来看看大姐!话里满是情愿和坦然。
即使到了21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多岁的堂爷爷百年后,他的家庭格局依然如此,堂爷爷离世不久,大奶奶也随他而去,留下一生在婚姻中作配角的二奶奶寡居在村西头的那间老屋里,直到堂爷爷去世十五年后,二奶奶也撒手人寰,到阴间去追随她把一生都倾情付出的夫君。我不知道二奶奶这辈子是不爱过堂爷爷,她爱堂爷爷吗?堂爷爷爱她吗?我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爱情。
无论是大奶奶还是二奶奶,她们在分享婚姻和爱情的时候,应该有苦涩酸辣,犹如剥洋葱般,泪流满面地一层层剥完。之后才发现心里空的。她们表面上心甘情愿,内心应该是撕扯的痛,亦或是有许多许多的不甘心,在婚姻和爱情里她们当了彼此的配角,共享一个男人的婚姻,这是何种的宽容和大度!其中又包含了多少无可奈何,她们可以在黑夜里孤守枯灯,能在自己的男人或是爱人与另外女子承床第之欢时而无动于衷,这种无法言表的痛才是最大的痛啊!
四
二奶奶生于民国之初,虽然裹过脚,但是脚并没有像大奶奶那般走形变样,还能找出原来的模样。其实二奶奶的足能保持原有的模样,重要的原因是她生于穷人家,一家人只忙乎生计,哪有心思顾及她裹脚呢?裹脚是件极费时又费钱的事,因此,穷人家的女孩子无意中在缠足上比大户人家的女子少了许多的痛苦。
缠足前要准备蓝色的裹布六条,每条大约是八尺到十尺,而且要浆好,以防缠在脚上挤出皱折;平底布鞋五双,鞋形瘦尖,鞋子大小宽窄要随着缠脚的过程慢慢缝小、缝窄;睡鞋三双,睡觉时穿着,以防裹脚布睡觉时松开;还要准备针线、棉花和小剪刀,裹脚布缠好后,要用针线密密匝匝缝好,穿鞋时脚骨凸出的部位用棉花垫着,免得把脚磨出生鸡眼,小剪刀用来剪脚趾或抠鸡眼。
缠足的过程既复杂痛苦又漫长。将大拇指之外的四个脚趾朝脚心拗扭,在脚趾缝间撒上明矾,防霉菌感染,再用布包裹,裹好后用针线缝合固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让两只脚慢慢习惯这种拘束,等女孩子习惯了以后,再试着将脚慢慢缠紧,先将第二和第五个脚趾向脚下蜷屈缠到脚下,连带将第三和第四个脚趾也蜷屈到脚底;每次解开重缠时,都要将四个脚趾向脚心挪,四个脚趾关节扭伤,然后用裹布勒紧,为了将脚裹尖,避免脚尖太粗,一直缠到小趾压在脚腰底下,第二趾压在大趾趾节下才算可以,缠好后用针线紧紧缝住,然后硬塞进尖头鞋里;裹尖完成以后,下一步是裹瘦,把小趾的外把骨向下向内推蜷入脚心,把足趾压入脚心更多,缠到最后,要把第三、第四、第五个脚趾触到脚掌心内缘,裹脚工作才算完成。
裹脚的经历痛苦难当,但是女孩必须忍受。八个脚趾严重扭伤甚至脱臼,扭伤脱臼的脚肿得厉害,整个脚变成瘀紫色,在裹脚布里又涨又痛,痛到寸步难行,因为裹脚布勒得脚血液不循环又不透气,脚往往溃烂,解开裹脚布时,溃烂的部位和裹脚布粘在一起,撕下裹脚布,脚上血肉模乎,令人不堪入目。溃烂严重又处理不当,会导致脚趾腐烂脱落。裹脚前前后后得一至两年时间,其间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祖母却因为家里贫穷,没有在幼小的时候裹脚,在她有力气反抗时却幸免逃过了一劫。祖母出生在一个走街穿巷卖地瓜为生的穷人家,又早年丧母,经常连肚皮都吃不饱,让她拥有了那个时代丑女的标志——一双大脚。
祖母因为贫穷无意间拥有了一双大脚,她的后半生与同时代的女子相比,活出了人生精彩,算是上天对祖母的眷顾。祖母生活的自在,让禁锢在屋里的大奶奶眼羡不己。祖母因为有一双能跑路的大脚,家里吃不饱肚子,她能跑到田地里摘枣儿,也能到坡上割回一捆捆山草扛回家,然后推到集市上卖给盖房的人。
后来,祖母还能和没裹足的年轻妇女一起到生产队下地挣工分,放工后,她在地头搂一篓野草枯枝背回家烧饭……在我这个小小人眼里,祖母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忘不掉,祖母在三伏天穿一件青布偏襟大褂,挽起衣袖站在锅台边,手里拈一疙瘩玉米面团,在手掌里三下两下摊平摊薄,贴在那口锅底冒着水气的大黑锅里,锅边贴一圈金黄色的玉米面饼,玉米面饼服服帖帖地粘在锅上。祖母脸上淌着汗,汗珠从她脸上滚落下来,在锅台上摔得粉碎。木制锅盖里冒出袅袅白气,随着一缕缕白气,屋内弥漫着玉米饼的香味。
祖母和大奶奶的性格截然不同,大奶奶安静的如一湖没有涟漪的水,温柔娴淑,安安静静;祖母却像是火辣辣的骄阳,泼辣能干,风风火火。一柔一刚两个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却因为一双脚,美丽的大奶奶没了灵魂,整天窝在屋里,见不到天;泼辣的祖母活出了自我,做了独立的女人,她不依附任何人,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祖母闲暇的时候就去找大奶奶聊天,把外面遇到的精彩事情说与大奶奶听,大奶奶不言语,听着听着入了神,却两眼发直发呆。祖母敬重大奶奶,跟大奶奶说话慢言细语,生怕惊扰了安安静静的大奶奶,遇到思想上有分岐的事情,祖母总顺了大奶奶的意思。祖母有着不服输的坚强性格,但是她对大奶奶却不同,像是捧在手心里一件细致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怕伤了大奶奶。我搞不懂一向风风火火的祖母在大奶奶面前竟然变得如此柔情似水?或许祖母缘于是对大奶奶大家闺秀精美举止的仰慕,或也许是对大奶奶一生禁锢在屋内的同情,也或许两者都有或者还有其他,祖母没说,我也没问过。
五
祖母始终穿青布偏襟衣服,小腿处打一条黑色绑带,从没间断。她偶尔也戴一顶黑色平绒的圆帽,帽子正中间镶嵌一块绿色玻璃扣,胶东老太太普遍戴的那种帽子,到新疆后,只在电影或电视里见过这种帽子,新疆老太太没戴过这种帽子,
祖母每天总是早早起炕,她不识表,家里也没表,然而她却有着比闹钟还准的生物钟。她每天起炕洗漱完毕,鸡舍里的公鸡准会打第一遍鸣。祖母会将猪圈旮旯里集下的尿液挑到村北的菜地给菜追肥。
我在她身边,她非常注重我的成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质贫乏,那时候虽然已经能够吃饱肚子,但是要吃好吃的有营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和祖母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却吃两种饭菜——我吃细粮,祖母吃粗粮。她要么用铁碗给我蒸一碗白米饭,要么去集市上给我买两个白面馒头或是半斤猪头肉,她自己从来不吃一口,全给我吃。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她眸子里满满的笑意,假如我不吃或吃得少,她就会不高兴,故意拉脸给我脸色看,逼我吃东西。有一次,她又给我买回油饼,督促我多吃,我看着坐在一旁的奶奶,问道:“奶奶,油饼可好吃啦!你咋不吃呢?”
祖母看着我回答:“奶奶吃惯地瓜和玉米饼子,不爱吃这种油腻腻的东西!”
“哦!是这样啊!”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时,我真以为祖母喜欢吃地瓜和玉米面饼,总是无知地把地瓜和玉米面饼让给祖母吃,表达我对祖母的关心和孝道,再年长几岁后,才明白自己行为的愚蠢,“不爱吃”只是祖母的措词,一个善意的谎言。
那年我上二年级,过六一儿童节,各村小学要集中到公社演出,我被老师挑选上演节目。老师让我们这些演节目的学生穿裙子,如果没有裙子就不能参加演出。我把老师的话给祖母说了,因为我没穿过裙子,家里也没裙子。
“演!一定要演!你演节目演得最好,下午上学的时候,你给你老师说你有裙子!”祖母连声说。
“奶奶,我没有裙子,我也从没穿过裙子啊!”我疑惑地问祖母。
“奶奶说有就有,要相信奶奶的话,你一定要参加演出。”祖母认真地说。
我茫然地点点头。
我没有裙子,我不知道祖母会用什么方法给我变出一条裙子来?做条裙子肯定是不可能的事,买布需要布票,祖母手里那点布票早给我做了衣服,她哪里还有布票可以买布呢?
我虽然相信祖母的话,但是总放心不下。
傍晚,放学回家,祖母不在屋里,我蹲在堂屋自个抓石头玩。天黑了,煤油灯在炕上的灯窝里忽闪着豆大的火苗,跳动的火苗只能照见炕上,屋里黑黝黝的,祖母没回来,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吓得缩在炕角,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被祖母叫醒的时候,祖母手里端一碗飘着葱香的疙瘩汤站在我面前,汤里卧了两只荷包蛋。
“饿了吧?快起来吃!”祖母微笑着对我说,她把碗递到我手里。
我接过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祖母看我吃完疙瘩汤以后,她打开红布包拿出一条粉底绿花的绸裙在我面前抖开,啊!好漂亮的裙子!我眼前一亮,高兴地叫起来。
“这是从你表姑家借来的,你穿上肯定好看!”祖母高兴地的说。
我如愿地参加了节目,并且还获得了一枝铅笔的奖品。
那时候,我只知道表姑住的村离我家好远好远,具体有多远我没有量上的概念。长大后,我才知道表姑家离我家三十里的路程,那次祖母全靠她一双大脚走了个来回!
六
祖母卖了她住了几十年的青瓦小屋,带着她所有的行囊一路向西,来到在地理地貌饮食风俗与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胶东有着天壤之别的新疆,这对于一个在暮年的老人来说,是下了何等大的决心!可是祖母没有向我们流露出任何的不适应,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地融洽和谐,没有不接轨不适应不合拍!
在新疆生活的日子,祖母一如既往的早早起床,到田地里捡葵花杆、玉米秸,将葵花杆、玉米秸一捆捆背回家,她捡的葵花杆和玉米秸在我家院子里堆成小山,曾经为柴不够烧担忧的祖母,卯足了劲往家里捡柴。全家人反对她这样做,我更是反对。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担心她干这么重的活,身体会吃不消,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她这样做事会被外人误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对她不孝敬,让老人在外面拣柴烧云云等口舍。祖母非但不听,反而愈演愈烈,她不但往家里捡柴禾,而且跑老远拔猪菜,割羊草。我因为怕丢面子,说她又不听,便对她十分生气,故意疏远她,不跟她亲近,希望以此逼她让步。
我错了,祖母并没有因为我的态度而就范。现在想来,如果祖母顺了我的意思,就不是我祖母的性格,后来祖母竟然发展到背了玉米甜筒去街上卖,她孤零零地坐在市场里等着有人买她的玉米甜筒,凌厉的风吹散了她的白发,她站在风里,我远远地瞧着她,对她既心疼又气恼。祖母卖玉米甜筒回到家里便坐在床边数那些皱皱巴巴的毛票,我对她犹为生气,故意把家什弄出直响,向她表示抗议,为了不让她去卖玉米甜筒,我把她装甜筒的布袋藏起来……即便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阻止了她的行为,年老的祖母依然如故地在外面抛头露面工作。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发生了,在十月份寒风入骨的时候,她拿一把菜刀去给人家农户砍甜菜,一天只挣两块钱!我忍无可忍,对她大声喊道:“如果您缺钱,我给您!您别在外面给我们丢人!”
祖母看着我怔了半天,她轻轻回了我一句:“俺有手有脚能干活,俺可以养活自己,凭啥要你的钱?再说,我在外面干活不偷不抢,给你们丢什么人呢?”
我说服不了祖母,生气地夺门而去。
我彻底和她成了路人。有一次,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碰见从农户田里干活回家的祖母,我生气地扭头装作没看见她,骑自行车从她身边飞驰而过,身后丢下孤零零的祖母,这一场景成了我今生每每念起她的痛,这之后,祖母再没给我弥补她的机会!现在我常想,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是何等自私,为了顾及脸面和外人那些无聊的说词,竟然让老人放弃他们的追求和爱好!
祖母安静地走了,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给儿孙们添一丝麻烦,用她的大脚走完了她的一生。她安详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整整齐齐的棉被,还有她的青布偏襟棉袄!那是个满天雪花飞舞的日子,那满天的白蝴蝶,一片片扑扇着美丽的翅膀悄然坠地,再没有飞起来,雪化成水,入了泥。
收拾祖母的遗物,在她偏襟衣衫的腋窝处竟然塞了五百七十八元人民币,卷成卷,里面还掖着一张胶东的旧火车票。我泪溢满眼眶,忽然明白祖母为什么到老都在拼命地工作,她把对故乡相思的痛深埋在心底,幻化成一张不能归程的旧火车票!
“远离家乡,不甚唏嘘,幻化成秋夜,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王力宏的一首《叶落归根》碎了我的心。年迈的祖母选择了离乡飘零,当年的她内心又有多少悲苦心痛?她用忙碌去忘却,而自私的我却没有读懂她,竟然在她永远离开我后才明白这个道理。人生哪里有倒行车?如果有,我愿意搭一程,让我挽着祖母的手一起去田地捡柴割草,让我陪她在萧瑟的风中卖玉米甜筒!
祖母啊,我知道你在想念大奶奶,想和她再说说话,把你在新疆的种种向她诉说;你还想去住一住那三间青瓦老屋,愿意伫立在门前,翘首期盼在他乡的儿孙们归来;你还想赤着一双大脚淌过沟底那条清澈的小河,在河里浆洗你的青布衣裳。你内心的苦和痛,从来不给我们言语,却总对我们说:儿孙就是你的根!祖母啊,祖母,我不知道你是否情愿把自己留在大西北不毛之地的戈壁?又是否情愿远离山青水美的胶东,愿意与白雪为伍和寂寞为伴?
又是四月断魂季,哈巴河竟然飘着雪花,我不知道是雪负了冬,还是新疆的春负了雨,本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然而这些白色的小精灵却翩翩落满你的冢,我欲捉住这秀美的蝴蝶,它却折了翅,在我的手心里化成了水,断了我的魂。
作者:杨梅莹 女 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更多
更多

格非、杨好:生活充满烦恼,但人可以快乐
两位作家认为“没有经验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一个好的作家,有很好的修养,有很强的思考力,才能捕捉住神来之笔。
 更多
更多

李今:为建成资料、档案中心的文学馆亲历散记
40年后,不能不忆起从零起步,初创时期的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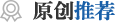 更多
更多

诗歌 | 崖头如碑(组诗)
崖头上的老人与崖头下的村庄 是两个世界,中间一条石板路间隔

散文 | 薄荷的里下河奇旅
在里下河这片钟灵毓秀之地,我,薄荷,悠悠然开启独属于自己的奇妙旅程。

散文 | 梅雨有信
原来这江南的梅雨信,不过是大地蘸着无尽水痕,写给凡间的一封封情书。它无声低语:且让日子慢些,看草木吸饱水汽,山色渐渐朗润,待云开雨霁,自有明媚铺陈开来——生命之丰润,恰在

散文 | 情因黄河起
恍如隔世,在横亘着新与旧的堤坝上,俯视星空下古老而又年轻的黄河,仰望黄河上璀璨的星空,与时间老人默默对视,与万物共怀的依是归来的羞涩少年。

散文 | 忆母亲——井水浸透的端午
母亲将溽热的端午喧嚣、活色生香的故乡光景,连同她深沉无言的爱,如同箬叶包裹的糯米,一并封存于时光的静水深流;那井水的寒凉浸透了粽子的糯软,也浸透了记忆深处母亲温热的指尖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