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游戏化编码及其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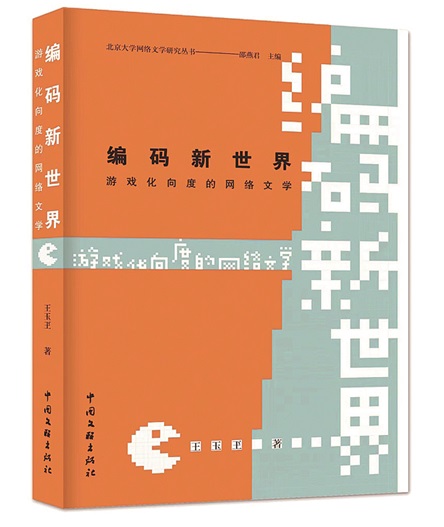
《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王玉玊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3月
游戏研究是新兴的跨学科热点,其与文学的关系也受到日益增多的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关注。王玉玊的《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借鉴东浩纪的“游戏现实主义”,提出了“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的概念,继而从“互联网一代”的经验出发,将游戏作为中介,指出了游戏结构及其蕴含的思维与实践方式对当代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深刻影响。“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是以(数码)人工环境为第一依托的文学创作,其独特性不仅使之和现实主义的传统文学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甚至也和现代主义迥然不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体现了“二次元存在主义”的精神底色,其逻辑植根于后现代生活,体现了后现代心理,是“数码一代”对其生存状况的思索、再现或戏仿。
“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工环境”,其“两大支柱”——人物与环境——均和传统文学不同。“人工环境”为“游戏”与“文学”两大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榫接之处,也为网络文学搭建了一个传统以外的操演舞台。艾布拉姆斯(M.H. Abrams)的《镜与灯》从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缝隙处发现了“世界”这一中介要素。较之通常现实主义以“自然”指代“世界”的方式,“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将“世界”从“自然”变为了“人工环境”。换言之,如果“自然”是现实主义的舞台,是“典型人物”得以形塑的“典型环境”,那么作为“人工环境”的“世界”则是数值化的、和人物分隔的,其不再是“自然”或“舞台”,而是叙事的一个部分。较之“典型人物”对“典型环境”的依赖,“人工环境”具备特定的生发叙事的“半自律”特征。因此,“人工环境”预示了叙事的转变。立足东浩纪的说法,其中存在突出的“数据库消费模式”——人物是被投放的“程序”的组合(即“萌元素”),“萌元素”塑造的人物代替事件作为故事的基本单元。21世纪第二个十年“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的如此特征,是因为吸收了日本的“ACGN”文化资源,而“ACGN”包含的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之中,“轻小说”中的“美少女游戏”(galgame)影响尤深。
除了叙事模式转变,“游戏化”的“人工环境”为网络文学带来的另一种最直接的变化是“真”与“实”的脱钩。网络时代的想象力环境促进了我们对“真实”与“虚假”的再次认识——“真实”的不一定是“现实”的,也可能是观念建构的。“人工环境”的规则(设定)体系制造了某种作者与读者皆知其为假,而又从设定出发信其为真的“或然性真实”。此种能够创造游戏/文本之内“真实”的规则(设定)体系,便是“游戏性”。根据渡边修司的定义,“游戏性”是“效率预估模型”,或曰“游戏设计机制”(ludo);作为计算机编程控制的“输入—运算—输出”过程,“ludo”也是游戏的底层逻辑。为了使玩家更容易理解“ludo”的规则或机制并培养“代入感”,游戏的设计者往往会为其机制附加“叙事性”(narrative)。如雅达利(Atari)公司1976年发售的“打砖块”(Breakout),其“游戏性”是大众熟悉的以弹球的方法消除方块,而其“叙事性”则鲜少被提及——如其标题,为“囚犯越狱”。游戏的“游戏性”(游戏规则)和“叙事性”(游戏叙事)嵌套结构决定了许多网文的结构特征,如“升级文”的经验、数值、副本,便是以一套符码兼容了两个系统——“设定之系统”与“故事之系统”。然而,游戏性第一、叙事性第二的机制也体现为游戏向文学的渗透。
王玉玊敏锐地发现,游戏的体裁特征是“互动性”而非“视觉性”,而“选择”又是“互动”机制的内核。如是,她提出“二次元存在主义”的观念转向,其关键是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自由、选择与责任——“我选择,我相信,我行动,我创造,我负责”。同时,她认为“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动摇了“现代性”这一宏大叙事的根基,即挑战了“现代性”的时间观。汲取自galgame的“平行世界”与“世界线”设定模式挑战了“一往无前”的“现代性”时间观;而基于弹幕技术的“共时感”也体现了一种以“网络趣缘社群”为单位的“共同体”构造。趣缘社群“以极端个人主义的方式向往一种共同奋斗”,被认为是本尼迪克特(Benedict Anderson)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提纯。
游戏化的“人工环境”中,“自由选择”无疑赋予了玩家/读者以核心的位置。“游戏化向度的网络小说”中的“人工环境”和趣缘社群互为因果,一方面参与社群的共同创造,另一方面也为社群的共同创造强化。但是“自由选择”作为游戏的核心机制,其自身也存在某种紧张。我们既然承认程序(设定、规范)作为“游戏性”的“第一性”,玩家/读者便无法获得“绝对自主”;“设定”“规范”也并非先验的,而是制作人规定的,其设定与规范的渊源也必然深植现实世界之中,且其认同赖以建立的“丰富性”与“合理性”也必然借助现实逻辑。德斯潘(Wendy Despain)区分了“沙盒式”(sandbox experiences)和“导轨式”(on rails experiences)两种游戏体验或游戏模式;仅就galgame而言,可视/互动小说(visual/interactive fiction)自然是“导轨式体验”,“多样性”“开放性”甚至“完全自由”的判断和抉择也无法超越既定的游戏模式与叙事框架,是为“系统的辖制”。如果说“互动”的中心是以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话”(conversation),那么游戏提供的仅是“触发—接受”的单向通道;“自由”的表象也不过是将其扩充为“触发—(选择)—接受”,而“选择”是“选项内的选择”,并不是无限的或超越的。对于游戏者而言,UI(user interface)的外衣之下隐藏了“设计者设置—游戏者触发/抉择/接受”的限制性结构。故而,即便非线性或开放性的“沙盒性”游戏,其游戏性或叙事性中也不存在“无限开放”的“自由抉择”。一些非线性或开放性游戏甚至也会出现阿什莉·伯奇(Ashly Burch)和安东尼·伯奇(Anthony Burch)称之为“游戏机制无视玩家”的时刻,或杰斯珀·尤尔(Jesper Juul)称之为“(玩家被)解除代理权”的时刻——如《荒野大镖客》(Red Dead)的前期是开放的,玩家能够做出抉择(如决定行善或作恶);然而无论如何抉择,主线中约翰·马斯顿一定被“强制执行”以实现救赎(象征“西部时代”的终结时刻),正如其墓碑上镌刻的“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解除代理权”揭示了游戏者和游戏之间的一大问题,受到系统的监视与控制而身处“不自由”状况的不仅是NPC(non-player character),玩家又何尝不是只能于系统允许的范畴内做受限的抉择?游戏如此,“游戏化向度的网络小说”恐也亦然。
如此,“系统的辖制”又凸显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为天地万物赋值”是“数码一代的独特经验”,也是“游戏化”网文的“爽点”来源,那么,“游戏化”(gamification)除了为“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奉献“人工环境”的资源,也蕴含着自身的问题或危机。“游戏化”的概念是“使用游戏机制和游戏化体验设计,数字化地鼓舞和激励人们实现目标”。一方面,诚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之说,媒介的变迁预示了“对身份进行游戏的新可能”,因为其能“使关系中的现存等级失去稳定性”;另一方面,“去等级化”先天蕴含了“再等级化”的危险。例如“数据库消费”的倾向指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偶像工业,“暴露了自己的工业流程和游戏规则”。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观之,“数据库”提供的“萌元素”特征为标准化、程式化、齐一化,其中“绝对自由”的诱惑和“消费主义”的风险难分难解;换言之,当代生活之中“宏大叙事的隐退”本身就伴随着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垄断资本的文化工业使游戏不再完全是个人的领域;根据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也是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再现。杰斯珀·尤尔担忧“激励—优化”的“游戏结构”用于非游戏环境时,极易沦为“过时的官僚集团”。游戏者戏称的“肝”(即“爆肝”,指付出时间)或“氪”(即“氪金”,指花费金钱)便是从“游戏化”的现实中尝试获取文化/象征资本(如级别、道具、装备),如此“数值”这一“爽点”便多少投射了清教徒式的资本精神。
“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也从游戏的维度指出了技术与文学关系的潜能。但是,科技及其带来的范式更迭并不是评判的至高标准,科技终究要服务于人。一旦自足的拟像(Simulacra)即大众媒介营造的仿真社会被视为“赛博空间”的“绝对自由”,弥散其间的消费主义微观权力也将持续“操演”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从而消弭现阶段“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抵抗和解放的潜能。如何以数码环境下的“人工环境”及其时空机制挑战垄断资本的文化工业,恐怕是游戏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均需探索的全新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