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暗夜里飞翔》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杨秀玲 2019年02月27日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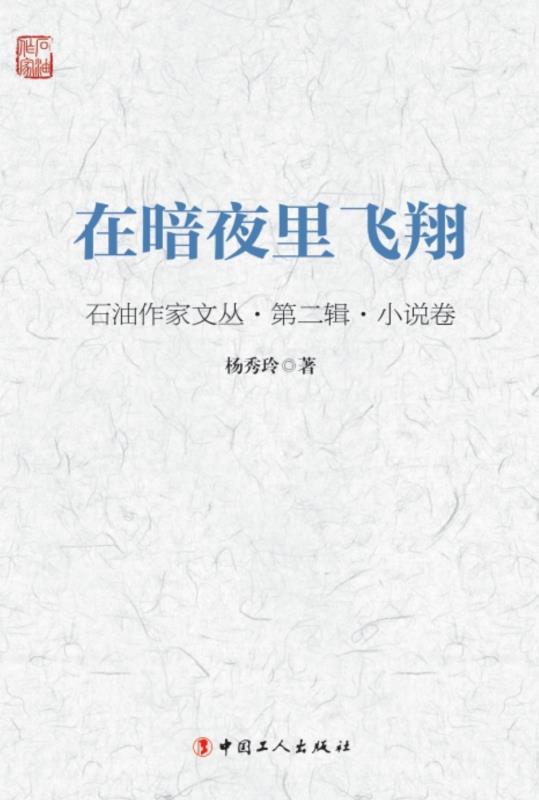
《在暗夜里飞翔》
作者:杨秀玲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08-7059-1
定价:36.00元
内容简介
作品集微距离放大不同的石油人生,展现石油人的精神底色,直面人生的悲观与人性的无奈,体味心灵的高洁与精神的坚韧:满腹心酸的母亲,挺立戈壁20多年的粗糙汉子,单身幼儿教师,空巢老人,为石油奉献终身的父女二人,“油二代”小两口,大戈壁上的一棵树、小沙蜥和流浪狗.......每一个生命,都在拂去时间的灰尘,发现和找寻石油人真实的内心,宛如叩问的灵魂在暗夜里飞翔。
作者简介
杨秀玲 祖籍山东禹城,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新疆和田。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石化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曾获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中国石油第六届文学艺术大赛小说一等奖,首届喀什噶尔文学奖等。现居新疆。
目录
奔跑的抓饭/1
背景修改下的余音绕梁/31
在暗夜里飞翔/71
1982年纸条/116
沙蜥秀儿/143
谁能给我一个拥抱/166
证据/187
紫色手帕/205
另一种存在(代后记)/251
代后记:另一种存在
我是个习惯向后看的人。我成长的生活环境,让我的眼界、思维及胸怀都不足以对前方做出高瞻远瞩的思量和规划。为此,我多年的写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包括这次出版小说文集,也是对自己十几年小说创作的又一次回头看。在一周时间内,我整理书稿重新阅读了自己40多个中短篇小说,看完倒生出了一种胆怯——这水平能出书吗?但这是我的第一本文集,总算对自己十几年的小说创作有一个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交代,拿出来瞎好是本书。我的选择思路很清晰,作品尽可能体现石油特色,地域特色和自己的创作特色,最终选了3个中篇6个短篇小说。
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中国第一个被废弃的油田——新疆依奇克里克油矿。我的整个童年以精疲力竭的依奇克里克油矿的衰落为背景,荒凉寂静可以听见燥灼灼的阳光落地有声,静谧辽远可以清晰窥视我那些过早忧伤的心绪。童年的路上铺满磕头机一样庄重含蓄的肃穆光阴。10岁,我随父母从依奇克里克整体撤离到现在的居住地——新疆喀什地区奎依巴格镇石油基地。作为土生土长的油二代,我22岁前没去过比奎依巴格镇大的地方,也没见过地里的庄稼长什么样子,我生活在一个城乡两不靠的狭窄地带,所有的思维和交流都来自于石油基地这样一个井底之蛙的天空。
我从小是个腼腆羞涩笨嘴拙舌的孩子,与人交往和言语表达是我的极端短板。我很想倾诉,总不知如何倾诉。我父母常年订《少年报》《儿童文学》给我们几个孩子看,八九岁时,我在一些文章上看到了许多我心里想说却无法圆满表达的话。我惊喜地发现,倾诉还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文学的神奇,它可以让我从别人的经历里看到自己。
我最初的写作欲望来自于阅读。奎依巴格石油基地的偏僻落后,使阅读成为我青春岁月的最好精神慰藉。20岁,我成了小石油基地的一名幼儿教师,开始尝试写作,又羞于让人看我写出来的文字。很快我找到个周全的办法——写一些很短小的童话,读给幼儿园的孩子听。那些四五岁的小孩子每次都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打断我跟我讨论童话中那些小猫小狗的细节,比如小猫的眼睛什么颜色,小狗有几根胡须等等。这些小孩子是我文学作品最初的读者,但在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意义远大于一般读者。十五年的幼儿教师经历,后来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证据》《素色手帕》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是幼儿教师,她们在生活中所流露出的感伤、淳朴、善良和倔强以及有点“二”的坦白率真满不在乎,都掺杂着我对幼儿教师工作的细腻感受和回味。
26岁,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日常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文友投给《新疆文学》,居然发表了。这篇小说的发表让我自以为是起来,第一次写小说就能在省刊发表,看来写小说没有多难嘛!接下来我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小说,越发不知道自己姓啥叫啥,心想自己这么有才,怎么能困在奎依巴格镇这个小犄角旮旯里不为人知呢?那时我的文学观功利而世俗,我幻想用文学这块敲门砖让自己走出封闭偏僻的奎依巴格。
奎依巴格,喀什地区泽普县的一个小镇。它翻译成汉语,原本跟果园有关,但不知怎么演绎成“理想花园”这样诗意而有抱负的地名。奎依巴格镇狭小肮脏又偏远落后。如果不下雨,这里所有的植物叶面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尘土,以至于我每次在内地看到任何一种植物,都觉得那植物绿得张狂妖娆咄咄逼人,想到自己每天也如覆盖在灰尘之下的植物一样灰头土脸无知无觉过日子,从未释放过自己该有的颜色,心里不免失落沮丧。时至今日,奎依巴格的巴扎天依旧有毛驴车坦然穿梭于汽车和人群之间,马路边还有卖表面滚满白砂糖、像五彩玻璃球一样没有任何包装纸的水果糖,许多黑脏的大手在糖口袋里一捧一捧地往外抓糖称重。
我在急切突围想走出奎依巴格的万丈豪情里愤懑不平急功近利地写小说。可惜,此后投出去的小说都石沉大海渺无音信。无利可图的文学创作让我恼羞成怒——我不写了!我扔下所有的思考所有的创作安心过一个家庭主妇该过的安稳小日子,一扔就是十年。
所幸我没有扔掉阅读。十年的阅读,让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肤浅狂妄和可爱,也看到十年来自己的落寞沉静和执着。我在应该狂妄的20多岁不可一世地狂了一把,又在不该狂的30多岁稳稳地看了十年书。我突然明白了,写小说是客观理性认知自己和社会的缓慢过程,它改变不了任何客观事实,但它的的确确又真的对人有所改变。我又开始小说创作,在抒情的审美世界里独自享受文字馈赠的愉悦,仿佛与初恋情人重逢。
我不再无端端憧憬和梦想什么,生活已多少开始偶露狰狞。小说创作顺理成章成为我抒发苦闷寻求慰藉的生活方式。在精神生活极度单调的奎依巴格,我精神抖擞絮絮叨叨地写着各种小人物的一些小疼痛、小欢乐和小庸俗。我尽量用世俗视角,尽可能匍匐在地,我慢慢体会到,越从小处着手,越能体现小说这种文体的长处。因此,我的小说中出现了刘军、李莉、程刚、老梁、何小青、依不拉音、张晓红、李红梅这样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都深藏着石油人文化基因的承续,凭藉着各自内心不同的丰富情感,对石油人的奉献心理认同、行为价值取向起到了或大或小的导向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潜在的、渺小的,但以小说的方式呈现他们,也说明他们存在的普遍性。这种选择,既包含对小说的理性认识,也是无奈——我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足和平静的按部就班秩序里,没有经历过任何大风大浪,没有遭遇过什么痛心疾首的人生教训,眼界视野窄小,我只能在身边的琐事上做文章。
小说创作让我进入一个美好世界,它记录下我的思考和心路历程,驱逐寒冷珍存温暖,感受充满渴望与期待的懵懂甜蜜。2015年,我写《背景修改下的余音缭绕》这个中篇小说时,被塔里木油田借调编撰《企业文化辞典》。白天我翻阅整理资料,目不转睛对着书本和电脑,晚上回去接着写这个中篇。那段时间,我的世界充满文字,我眼睛睁开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面对数不清的文字。《背景修改下的余音缭绕》写得很慢,大概一天写一千字。有时写得焦躁,就站在窗前,居高临下看窗外的车水马龙和人声鼎沸,不由微笑,有谁知道一个个夜晚还能够以另一种存在悄然打开?又有谁知道这样的存在可以任凭思维天马行空自由翱翔还有恬静淡然安之若素的妙不可言?40多天后小说完稿,我甚至有点留恋那一个个没完稿的夜晚。
写作也让我不止一次地疼痛、感伤、甚至气急败坏,且不说写作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焦虑,单说一次次修改、被否定、再修改甚至保留人物和情节重新再写的抓狂就让人崩溃。《在暗夜里飞翔》完稿是个近五万字的中篇,发表前的一年里,修改不下十次,不但修改细节情节,连结构都做了多次调整。小说中最后出现的王莉莉,一个像茉莉花一样纯洁芬芳的女孩子,初稿里本是个靠色相骗人钱财的暗娼,我改到不知是第七稿还是第八稿时,突然很疑惑自己心理为何如此阴暗,对于这些蜷缩在黑夜般深邃戈壁上遥望美好生活的人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投一束光亮进来。《在暗夜里飞翔》这篇小说本就是为了明晰那些被误读的石油人生而写。小说修改到最后,王莉莉成为一个美好事物的标签被定格在戈壁上,何欢痛不欲生抑郁自杀才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程刚、老梁这些卑微、朴实、无奈和悲壮的石油人生的疼痛也跃然纸上。这些疼痛让我一次次重新审视人生、打量生活、思考人性,也让我避免了写作者容易出现的浅薄。我就这样沉醉在小说创作的世界里,在不知道什么流派,也没什么圈子的单纯氛围里,坚持一个人默默地写小说。在经历了多次投稿退稿和持续沉静的创作之后,我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受挫平衡能力。
回头再看以前写的那些小说,很多都是实实在在的垃圾作品,对于石油小说的创作没有丝毫意义,可怜那些编辑们隔三差五就要被我折磨一番,但这些由数量堆积而成的文字,对我个人却意义重大。其中的煎熬、焦躁、进退两难、一筹莫展、无可奈何还有作品完成后的朦胧快感只有自己明晰。文集中的9篇小说,除《一棵树》因篇幅短小一气呵成外,其他小说都历经许多夜晚反复思虑磕磕绊绊才初见雏形。就连《一棵树》发表时,好几个文友问我,那一对相亲男女到底成没成,怎么没写清楚呢?我无言以对。《一棵树》写的是一种怀念,对戈壁上独特青春岁月的永久纪念,有温情,有壮美,有赞叹,有怀旧,唯独没有遗憾。我力图剥开故事情节的表层,深入挖掘一代石油人的内心感触。我的确不关心这两个相亲男女到底成没成,这并不是写《一棵树》的初衷。
这些人物原型都来自奎依巴格的石油基地。我在奎依巴格生活了30多年,这个有温度的时间长度理所当然让奎依巴格成为我的故乡。我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与我生活的奎依巴格息息相关,所有一切都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一点一滴浸透着我30多年的情感。它赋予我一些具有浓厚地域气息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比如沙蜥秀儿,名叫抓饭的流浪狗,大戈壁上的沙枣树,还有许多个刘军和李莉。
我许多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叫刘军和李莉。一是我懒得起很多名字;二是我始终认为: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个性鲜明、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可以帮助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自然也能够区分此刘军李莉非彼刘军李莉。不同的刘军李莉刻画出形形色色的灵魂和琐琐碎碎的人生,不同的刘军李莉在无情的现实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表现出不同的鲜明社会主题,抒发着普通人不同的悲欢离合和对悲伤困苦的无畏超越。诚然,我的大部分小说属于慢节奏,有些小说的故事情节还不严密不怎么好看,比如《1982年的纸条》《谁能给我一个拥抱》,但我更多的笔墨是扎实地展示特定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现实。《1982年的纸条》有个张文忠,在小说里是个一带而过却从始到终贯穿全篇的小人物。他的原型来源于我父辈第一代石油人,他们的来和去,他们的根与源,他们的喜和悲,都有着天高地阔的社会大背景,能让人们明显感觉到他们的辛酸、悲苦和沉重。这既是故事韵律的反复,也是小说情感的深化。我并不能完全地表达他们,但至少,我在自己的小说中能够真实地触摸到他们。
世界每天在变,总有些东西在尘土的遮蔽下不会改变,也总有些东西会成为永恒——比如,写作。我曾经问自己: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源自何处?当我自己写出的作品不断累加摆在我面前时,这个浅显的问题立刻被写作所承载的广阔包容完全覆盖。毫无疑问,写作是超越现实的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具象,但它泰然,宽厚,有种与世隔绝的沉静与安详,稳稳的,缓缓的,以一种神秘力量,把这个喧嚣的世界抛离得一点都不剩,同时又让日常生活呈现出触手可及的真实质感。
文学创作消磨了我许多大好时光,同时也恩惠了我,它体察我的内心,在文字间流露出我的倔强和感动,让我不断发出最微弱的光亮并始终置身于对文学创作的发现和热爱之中。这其间难以言表的欢愉,是真正体验了另一种存在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我想,我今后的小说创作会依旧执着于现实生活每个角角落落的探寻,一次次去擦拭时光的尘土,发现、追问和揭示那些让我有所触动的生活体验,以真诚的态度向这个世界描述我所理解的另一种存在。
剩下的,就是怀揣文学理想真诚而坦白的写作。
2018年5月20日
于奎依巴格石油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