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研究的集大成者——田本相和他的话剧研究
来源:文艺报 | 祝晓风 2019年10月25日08:25

主讲人:祝晓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文学博士。曾供职于光明日报社、中华读书报、中国外文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读书》杂志等单位。出版有文集《有声与无声之间》,新闻作品集《读书无新闻》,散文集《南开风语人》等。编著《知识冲突》,编辑《南开故事》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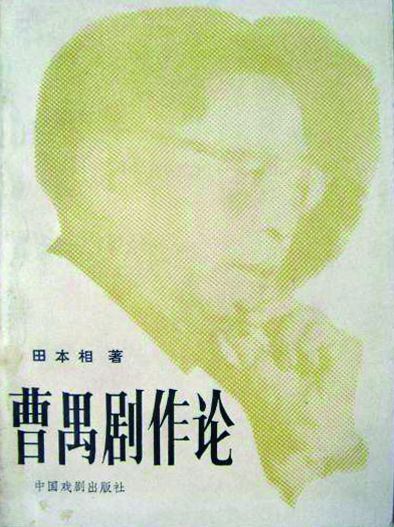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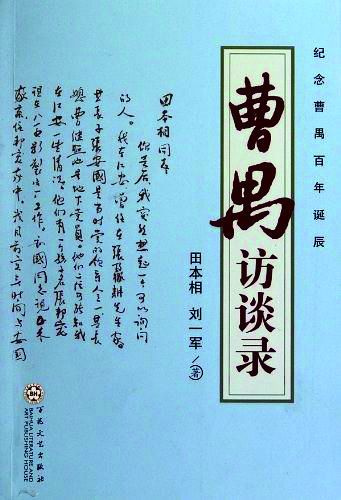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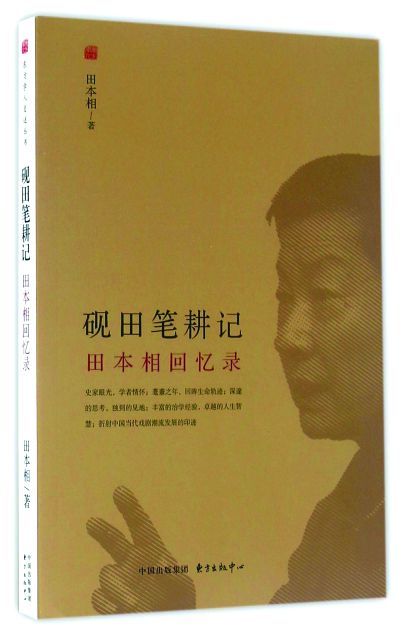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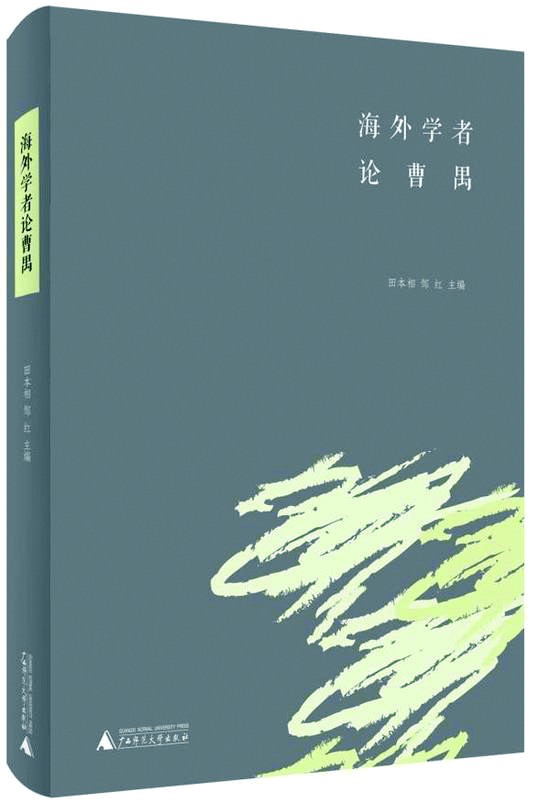
一 很长一段时间,我自认为对田本相先生是比较了解的。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一是我们相识已有20多年;二是我和田先生的一班老同学都比较熟,这些人有的又是我的老师,自然亲切;三是工作关系,20多年来学术文化的编辑采访工作,让我得以与田先生前前后后打过些交道,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都有帮助,自然,我对他也就有一些了解。
毫不夸张地说,田本相先生本人就是一部大书。
这部大书内容丰富,无法在短短几千字的篇幅中尽述,只能述说其中几个大的关节重点,而这对传主本人而言,则是人生几次大的转折与升华。一是从军,上前线。1949年3月23日,田本相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二分团,这个四野南下工作团中,当年还有汪曾祺。那一年,田本相17岁,他怀揣着激情与梦想,先是随大军南下到武汉,后入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再调入中央机要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田本相被派往前线,到19兵团任机要组长。他亲身经历了这场大战争,经受了炮火洗礼、生死考验。几年的军旅生活,他收获的不仅仅是三等功和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还是成长与成熟、正直与坚强,还有,一个“勇”字。
学者文人,先从军后从文的,比较出名的有黄仁宇。而田先生的南开同学中,我知道至少也有两位有从军的经历,雷声宏先生和陈慧先生,这两位后来也做出了大学问。可见,从军对青年、对做学问,确实有不同寻常的影响。
二是上南开。南开8年,几乎就此确定了他今后的职业方向,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格,也为他日后不凡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田本相此后的人生轨迹。他的学术风格就此打上了鲜明的南开印记。他后来在总结人生经历时说,在南开大学的学术环境里,他的学术趋向和志趣都形成一种“癖好、习气和毛病”。
田本相的南开经历,与他的同学略有不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父母也是与田先生同一年上的大学,而且同在天津。那个年代的大学,没有几天正经上课读书的。一天到晚不是政治学习,就是劳动锻炼,全国都一样。据田先生说,当年上了5年大学,有3年多是搞运动。不过,在南开这样的老学校里,好歹还能有几位老先生、真学者,当时的老先生有华粹深、许政扬、马汉麟等。学生多少还是会受到一些熏陶。虽然这些老先生也往往沦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南开毕竟是南开,学术氛围还是有的。中文系当时在李何林主持下,学术活动也较多,据田本相回忆,李先生就请过方纪、何迟、蔡仪、杨晦等人来南开讲座。据家严回忆,他们也曾在南开听过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报告。就是说,在南开,读书的氛围、学术的空气还是有的。加上田先生本人爱读书,于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5年读书时光。
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南开呆了8年,本科5年之后,又接着跟李何林读研究生3年。多读的这3年,就决定了田本相与他大多数同学在学术上的差别,那就是系统的、正规的学术训练,包括系统的读专业书。就差这3年,完全不一样。我认识父辈和晚一两辈的很多人,已经在高校里待了二三十年,却仍然不知论文为何物,以为搞科研就是复述教材,或者就是跟着一些时政话题发表一点看法。虽然当时各种运动连绵不断,但在研究生教学这个小范围内,读书还是主业。而且,田本相在写论文过程中,得到清晰严格的训练,在研究和写作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
三是到北京,先后在几家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20年,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几个不同的学术科研机构工作和研究经历,又使他获得了更广更深的知识储备。在广院,他一边教学,一边研究新兴的电视文化学,对这种区别于纯粹文字的艺术形式有了深刻理解。在中戏,他更是直接接触、研究戏剧表演、舞蹈、美术等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并且写作、完成了《曹禺戏剧论》。这些都为他以后以更综合的眼光研究话剧准备了条件。而最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他学术成就的集成之地。
回过头来看,他经历的这些炮火洗礼,学术训练,好像都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他自称,在北广和中戏做了20多年的“边缘人”,但正是这些“边缘”时光,给了一个学者充分的沉潜时间。他终于走到学术与人生的一个新阶段。1987年10月7日,田本相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报到,接任葛一虹,任话剧研究所所长。这一天,不仅对他个人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话剧史研究,对于中国话剧研究,也是值得记入历史的日子。
二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基础性研究。田本相在所长的位置上,把话剧史这一基础性研究确定为研究重点,全面彻底地推进开来。这就是田本相在学术组织方面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感,当然,也体现了他的勇气。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田本相就明确意识到,中国话剧史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当年,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都还在酝酿写作之中,尚未问世。1984年,田本相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时,发现堂堂中戏,竟然没有中国话剧史的课程;而一些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对中国话剧史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一些所谓“大腕”声言,中国话剧的历史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田本相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构想。进入90年代,陈白尘、董健的《史稿》,葛一虹的《通史》,还有田本相的《比较戏剧史》相继问世。这三部史,由于准备时间都较长,也注重充分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可代表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史研究的水准,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建立与阶段成果。而其中,田本相因为有着曹禺专门研究的根基,他的成果就更富有个人色彩。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集大成者。研究中国话剧史,必研究曹禺。就如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必要研究鲁迅一样。即使不是专门研究鲁迅,也要对鲁迅做基础性的研究。而在曹禺研究这一点上,田本相是下了别人没有下过的功夫,取得了别人没有的成就。他的成果,为学界所重,嘉惠后人。他的《曹禺剧作论》《曹禺访谈录》《曹禺传》,形成一个系统的、纵深的成果。《曹禺访谈录》《曹禺传》是田本相在曹禺的直接支持下,采访大量当事人,发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
田本相的成果远不止于此。概括地说,田先生本人的成果,一是丰富,涉及话剧史、话剧理论的各个方面,研究了许多关键人物,提出了许多引领学术的问题,而且,还有关于现代文学、电视等多个领域;二是宏大,尤其是在话剧研究方面,无所不研,研无不精,在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较早地具有了世界眼光和现代观念;三是贯通,不但是上下贯通,而且贯通话剧中的各个方面,并把戏剧批评和戏剧史、戏剧理论三者打通,把戏剧和文学贯通,在此之上,田本相建立了自己的话剧史理论体系;四是基础性,他本人的研究,还有他所主持的诸多研究,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田本相担任话剧所所长之后,为了把中国的话剧成就传播到世界,也有一系列的大动作,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就是连续举办了几届“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从第一届1991年8月在南开大学召开,到2010年的第五届。这不仅有力推动了曹禺研究本身,还大大扩大了戏剧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与中国话剧在世界上的影响。
三 田先生在离休之后,几乎同时,一边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一边撰写《中国话剧百年史述》,两书前者已出版,后者也交稿给了出版社。但是,田先生仍然觉得这部书未能实现他的想法,自认为它们只是在局部或者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他直白地说,“我之所以再主编九卷本的《中国话剧艺术史》,是不满意《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和《中国话剧百年史述》”,“不是一点不满意,而是有着诸多不满意”。他的设想是,第一,对百年来的中国话剧史作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梳理,使之成为一部具有百年总结性质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著。第二,这部史著,较之以往的中国话剧史著之不同在于:一是使之真正成为一部中国话剧史,把过去忽略了的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都包容进去。二是在内容上,真正写成一部话剧艺术史,彻底摆脱运动史加话剧文学史的模式,使它成为一部体现话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的史著,把舞台美术、导演和表演包容进来。第三,吸收近20年的话剧史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创新的理念下,使之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代表国内最高学术水平的话剧史著。第四,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史著,把重要的历史图片收入,使之成为一部形象的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史。
看起来,似乎与《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原来的设想也差不多,只是从三卷本增至九卷本罢了。但是,它与《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和《中国话剧百年史述》确有着某些质的区别。田先生简要地概括是:四个区别,一大关切。四个区别是:第一,还话剧作为综合艺术史的本体面目。戏剧毕竟是综合艺术,究其根本是表演艺术,导演艺术、舞台设计、化妆艺术,以及戏剧文学,都是环绕表演而运作、而展开的。因此,竭力还话剧史以综合艺术史本体的追求,是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的灵魂。第二,单独立卷的价值和意义。根据历史分期单独立卷,似乎还是传统的做法。但是,这样的单独立卷,将每段历史,更独立地加以审视和评估,不仅内容丰富了,而且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更深化了。第三,把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仅仅概括为战斗传统是不全面的,最能体现它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成果的,也是中国话剧的独特性的,是一批我们称为诗化现实主义的剧作。第四,图文并茂的设计。上千幅照片,使话剧史作为综合艺术史的面貌更为真实生动。一大关切则是对中国话剧命运的关切,具体说来,是对中国话剧危机的关切。中国话剧的危机首先是思想的危机。
此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2016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很高评价。
最近六七年间,田本相先生在撰写评论文章的同时,还有一系列专著和重要成果出版,其中,两种大型史料集有特别的分量,即由田本相主编的38卷本的《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2014)和由他倡编的100卷的《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2017)。2014年,他和邹红合编《海外学者论曹禺》出版,还编辑完成《田本相文集》(12卷)出版。2016年,田先生所著《曹禺探知录》《砚田笔耕录——田本相回忆录》出版。2017年还由他主编出版了《新时期戏剧“二度西潮”论集》。
田先生确实有一种对话剧史研究的迷恋,有一种穷追不舍的劲头。他老当益壮,老而愈勇。九卷本出来,他还不甘心,还想把中国话剧史的精华提取出来,于是产生两个想法:一是在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之际,写出《论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曹禺——话剧诗化之集大成者》等;另一方面,是向话剧史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进军,如《话说“话剧皇帝”石挥》,《论中国话剧表演艺术理论的发展轨迹》,这些都是他撰写的《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史稿》的有关章节。同时,田先生也开始组织有志于此的学者,撰写《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和《中国话剧舞台美术史》等。他的想法是,这些研究不仅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写出更为精彩的《中国话剧艺术史》准备了条件。
四 现在这本《砚田无晚岁——田本相戏剧论集》,集中了作者最重要的一些理论思考。比如,田本相曾经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有一个评估,认为它有两个特点,两个潮流,一大弱点。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移植性、模仿性和实用性;一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经验性。两个潮流,一是诗化现实主义的理论潮流;一是实用现实主义潮流。一大弱点,是学院派理论的孱弱。其中,“学院派戏剧批评”是田本相近年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何谓“学院派戏剧批评”?田先生认为,它首先意味着一种精神,即独立的、自由的、讲学理的、具有文化超越的远见和胆识的批评精神。这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化的戏剧批评和商业化的戏剧批评的第三种批评。这可视为田先生对于戏剧批评的一个贡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田本相先生出任话剧所所长,首先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话剧的传统问题。他当时就想,中国话剧难道就是“战斗的传统观念”所能完全概括的吗?难道真像所谓“大师”和“先锋”所说的,中国话剧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东西吗?此文集中,就有几篇文章论述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和“诗化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和提法,不妨看做一个大概念。这是田先生多年研究中国话剧的一大发现。他提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诗化传统。《诗经》《离骚》之后,赋、词、曲皆由诗演化而来。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来的话剧,进入中国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也为这个强大的传统所融合,就不可避免为这强大的“诗胃”所消化。
“中国的诗化现实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田汉,30年代形成曹禺、夏衍的诗化现实主义主流。它是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学的诗性智慧和中国戏曲的诗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更在奋起抗战的民族大觉醒之际,最终构筑成中国话剧的宝贵的艺术传统。”“这样一个传统是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中国话剧的希望也在这里”。
这是田先生对于中国话剧传统的一个总的命题。在这个总命题之下,他还有许多精深的研究,如,他提出“诗意真实”概念,所谓“诗意真实”,“首先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捕捉、感悟、提炼和升华”。 他发现,焦菊隐也一再强调舞台的“诗的意境”。心象、意象,这本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戏剧艺术所要创造的即是戏剧意象。焦菊隐反复强调的是,没有演员富有创意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就不能产生“心象”。
如果说田汉、郭沫若是中国话剧诗化传统的开拓者,那么,曹禺不但是中国话剧诗化传统之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国话剧诗化之典范。对曹禺研究极深的田本相先生,是首先研究发现这一点的人。他认为,曹禺是自觉地把话剧作为诗来写的。首先,曹禺的话剧诗化特别强调“情”,把主体的“情”注入对现实的观察和现实的描绘之中。曹禺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其次,曹禺创造了一种“诗意的真实”。田先生在有关曹禺的论著中对曹禺的真实观曾作过概括,即“诗意真实”,他善于发现污浊掩盖下的美,以及腐朽背后的诗。其三,在曹禺的诗化的戏剧创作中,几乎所有的中国诗学的审美范畴均化入他的作品中,这些对他并不是理念,而是在中国文学诗化传统的熏陶中形成的。
五 我与田本相先生相识,准确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至少应当在1996年8月之前。1996年8月7日《中华读书报》第5版,有我采访田先生的一篇报道,此可为证,标题是:从来没有完整的《雷雨》——田本相谈《雷雨》的改编。文章不长,但信息量不小,对一般读者了解《雷雨》还是有点儿帮助的,不妨录下:
原来,《雷雨》从1935年4月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开始,就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原剧本演出过。但是,这并没有使《雷雨》的光彩从根本上减损。
近日,记者再次就《雷雨》的改编问题采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田本相先生。田本相介绍说,《雷雨》在日本的首演,是杜宣、吴天和刘汝醴担任导演,演出时删去了《序幕》和《尾声》,杜、吴在致曹禺的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曹禺对此十分惋惜和不满。可是,全本演出《雷雨》要长达4小时,观众显然容易疲劳,删节剧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解放前的演出中,《雷雨》几乎没有过序幕和尾声。田本相认为,后来的情况表明,曹禺对这一事实也渐渐采取了认同的态度。而学界认为,这样的《雷雨》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雷雨》了——尽管它仍然很打动观众——而是一个在社会接受过程中变化了的文本。
50年代初,曹禺对《雷雨》做了较大的修改,强调了阶级斗争、阶级冲突。“文革”之后,这一点缓解了一些。在后来夏淳导演的《雷雨》中,更强调戏中原有的人情、人性。丁小平的《雷雨》,则加了序幕和尾声,但不是原来的。1993年,王晓鹰的《雷雨》中去掉了鲁大海,又做了小剧场的处理,对此,当然也有不同意见。
田本相认为,任何名著都意味着一个被不同时代接受、诠释的历史。“为什么说一部作品是经典,就因为它具有可以为不同时代和导演诠释的可能性。好的剧本会给导演很大的创造余地,可以发掘它的内涵,发掘以前没有被人认识的东西。但是,改编不是胡来的,不是任意的。改编确实是一种创造,改了它,但又是它。改编名著不是轻而易举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我满意的《雷雨》。”
田本相最后说到现在的一些名著改编,特别是影视改编,商业气和匠气太重,少有曹禺改编巴金的《家》那样成功的例子。
现在单看这段文字,好像也不少,但当时放在版面上,并不大,连一个巴掌的面积也没有,占全版面积的1/14左右。当时的版面用的是六号字,字数较多,一个整版排满字,将近有一万六千字。
这一版上,还有我采访万方的一篇,题为《爸爸说:“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作家万方谈曹禺和〈雷雨〉》。另外一篇评论,《曹禺对〈雷雨〉不成功的修改》也出自我的手笔,但因为是评论,所以就用了笔名。正好,当时《雷雨》改编电视剧颇受关注,又赶上《曹禺全集》出版;而《雷雨》改编,也引来一些不同意见,有争议,就有文章做——学术上的主要支持,自然就得靠田本相先生了。
当时,曹禺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版面上配了一张曹禺和万方的合影,是曹禺在病房里。1996年12月,曹禺就去世了。
第一次见田先生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是在恭王府,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就在那里。话剧所是在最北边一排房子。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如约来到。我站在院子里待了一会儿,田先生从走廊另一边信步走来。这个形象就这样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田先生的目光探寻着历史、打量着现实。他批判的锋芒,总是挥向戏剧中的丑,挥向学术研究中的劣,直指戏剧批评中的伪和俗。如此说来,他便有了鲁迅先生和李何林先生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