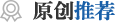《生如夏花》高众笔下的医者良心
“医学理论和实践不是我所要说的重点,我只想利用我从一名普通人成长为一名医生亲身经历的过程,从人文的角度来试图叙述我所观察到的和疾病与死亡相关的场景,进而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程,到底该受到怎样的关爱,这是我的本意。”高众在他的作品《生如兰花》开篇引言中如是说,给本书叙说“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辩证历程”予以准确的定位,让读者能迅速聚焦本书既不是纯粹文学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不是医学理论与实践的散文化堆砌,而是一个接一个真实生动的病患者的故事次第绽放,这样收放自如的表述,正好说明了高众身上兼有小说家讲故事和散文家随笔惟美交辉相映的文学才华。
生命对于任何个体来说,就像深山幽谷的兰花盛放一样,散发着浓烈的香味,清冽而迷人,没有人不珍视自己的生命,但也正如山谷幽兰一样,大自然许多致命的外来因素随时都可以摧毁“这一株”的生命,这种“摧毁”的惨烈其实就是生命与疾病抗争的过程:高众自小即患绝症,四处求医,其间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曾令家人四处求医问药、寝食难安,个中滋味实不可与外人道。这段病情的磨难如今在高众笔下娓娓道来,却少有悲伤与哀怨,更多的是凄美与惊艳,猪宝救命的巧合成就了高众内心深处的医者良心。多年以后的高众成为救死扶伤队伍中的一分子,在他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窒息”“压迫感”“濒死感”这种特定的场景与个体打交道,他始终秉承“医者良心”四个字来面对他的病人,在他看来,精湛的医疗技术不一定是主要因素,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予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或者是鼓励病人面对死亡。当然,人文关怀不是一句空洞的词语,而是需要用心去体察。于是就有了他与功勋卓著的病号“老顽童”关起门来撸羊肉串、喝啤酒的故事,接下来就有了替“老顽童”写“悼词”的资本;就有了与“高血压病小患者”小高的沟通交往,要求他提前进入CCU实习的宝贵经历;有了目睹年轻军官生命渐行渐远的恐惧与无奈……“生命如兰,春天萌芽,冬天凋谢,死亡只是生命的下一个驿站。如何让生命与死亡背后的轮回不再悲怆、怨恨甚至歇斯底里,在这华丽转身的背后更加坦然、包容、尊严”,是高众作为医生良心的最大亮点。在他行医八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用高超的医疗技术、浓郁的人文素养与悲天悯人的宽广胸怀服务各式各样的病患者,让他们明白了一个深刻而又简明的道理:生命舞台上的帷幕总会在某一个季节的某一个时刻悄然落下。同时另一扇大门会徐徐打开,里面黑暗无比。也许,这黑暗只是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另一个充满光亮的世界。
“从患者的立场看,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和亲情的温暖,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战胜疾病或者是坦然面对死亡的主要因素,这同时需要自身精神和具备一定的医学和哲学知识去支撑。”高众如是说,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从医的八年当中,他认为治疗得最成功的病人之一就是一位沂蒙老人,可就是这位称高众为“好把式”医生的病人后来竟然因为他出长差而不愿去别的医院治疗:
我在出差期间,曾经接到过这位经常坐在丝瓜架下老人的孩子的电话,没说什么,只是问我什么时间能回来。当我问起老人病情的时候,他的孩子说老人的状况不太好,等你回来再说吧。我说千万不能等,赶紧送医院。那边一声叹息后挂断了电话。
我回来的当天,老人便送进了我所在的医院。他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呼吸很微弱,当我给他采取急救措施之后,我抓住他的手叫他的名字,他没有睁开眼,只是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
读到此段文字时,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为高众的“医者良心”所震撼,一个病人如此相信医生,甚至是以命相搏,只能证明医者的伟大。是的,无论平时多么强悍,病人只要进了医院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旦碰上“从不训斥他的病人,相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的好医生,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其实,夕阳每天都会西下,黑暗每次都会如约到来,但是朝阳每天都会升起。这样的轮回不会被密布的乌云所阻止,不会被狂风暴雨所推迟,也不会随着一些人的逝去而改变,但是,活着,就应该好好珍惜。”高众如是说,他也是这样做的。八年来,面对无数的病号,他微笑、自信、坦诚、调侃乃至善意的谎言,赢得了多少病人信任的目光,我们无法去统计。但我认为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他直面父亲患癌的痛苦与陪伴父亲治疗过程的艰辛,此时此刻的他刚刚离开医疗岗位,他所面对的对象又是自己亲爱的父亲,急不得,恼不得,玩笑不得,往日面对患者的善意谎言此时已经无效,不仅无效而且还要面对接下来各种无法预测的结果,巨大的精神压力仿佛一夜之间要把高众压垮,但高众凭着“医者良心”过硬的精湛专业技术,运用与社会、人文、心理甚至哲学的相关知识,对父亲予以正确疏导,使父亲在治癌、抗癌的道路上得到了医疗、关怀、心理等治疗过程中所需要的全方位服务,最终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医者,病患者之父母也;良心,一副博大、善良、正直、伟岸的好心肠。从《白衣江湖》的横空出世到《生如兰花》的精彩亮相,是一位医者到写作者的华丽转身。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在图书封面上写下了“一部直击病人、医生、家属灵魂深处的白皮书,一把解剖疾病、健康、死亡背后轮回的手术刀,一首弹奏人性、生命、尊严纠结心理的交响曲”的广告词,以示我对高众的敬意。
医生这一伟大的职业历来被认为是最近距离接触人的人性及躯壳的,这使得医生与作家之间产生了某种不约而同的契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从肉体苦难和精神苦难当中解救人类。有人说,正是因为医生工作的特性,成就了一些弃医从文的伟大作家:比如契诃夫、毛姆、柯南·道尔、约翰·济慈、渡边淳一、布尔加科夫,还有家喻户晓的鲁迅,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也出身于牙医。“这两本小书算是对自己八年医学生涯的一个交代”是全书最后的一句话,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高众身怀一颗医者良心,就算以后的日子不再捉刀行医,他依然会以笔作刀,解剖世俗红尘里的种种痼疾与顽症,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更深刻的文字。
 更多
更多

阿来:文学首先是建设自己
“作家就是跟限制做搏斗的,写作的乐趣在这儿,难度在这儿,挑战性也在这儿。”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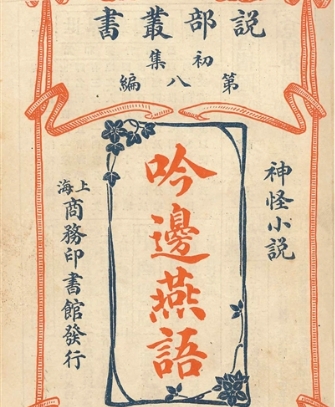
他把莎士比亚译成《聊斋志异》
几乎所有中国莎学史的书都会提到《吟边燕语》,它也给林纾带来无尽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