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让孩子的世界里有“光”
梁鸿的新作《要有光》有个感性色彩强烈、颇具文学性的开头,“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这或许可以概括许多为人父母者在亲子关系中的处境。他们感知到痛苦,但缺乏足够的自省意识,付出时间、金钱和努力,却未曾理性反思与孩子相处的方式。是否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有没有换位思考孩子的情感取向和精神需求?现实是,越来越多身在青春期的少年因为种种情绪问题离开课堂,深陷失学、抑郁境地,这已成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作为曾写出《中国在梁庄》系列非虚构佳作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梁鸿在这部新作中将关注的视角投向那些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少年。她在三年时间里走进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乡村的学校、医院、教育培训和心理咨询机构,与众多孩子、家长、教师、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深入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迷茫、焦虑与痛苦,思考青少年心理问题背后来自家庭、父母乃至社会层面的诸多原因。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等等,而是想找到那样一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它或者它们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重要时刻”,这样的节点,这样的时刻,在我们尚未察觉的日常言行中改变、伤害着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爱与信任。
这部新作出版后的一两个月,梁鸿频繁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新书发布会、文化沙龙、网络直播和播客节目中,这是这些年她的新书宣传力度最大的一次。在北京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面色疲惫但热情满满的梁鸿说,这么做当然不只是为了卖书,“只为了销量也不用花这么大力气。我希望青少年心理问题能被更多人关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讨论能令人们有所触动。你说一本书能改变什么?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吗?或许有一点点吧,改变一些家庭内部的交流,拓展一些思想空间”。她认为这本书是写给家长的,也是写给孩子的,“写给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每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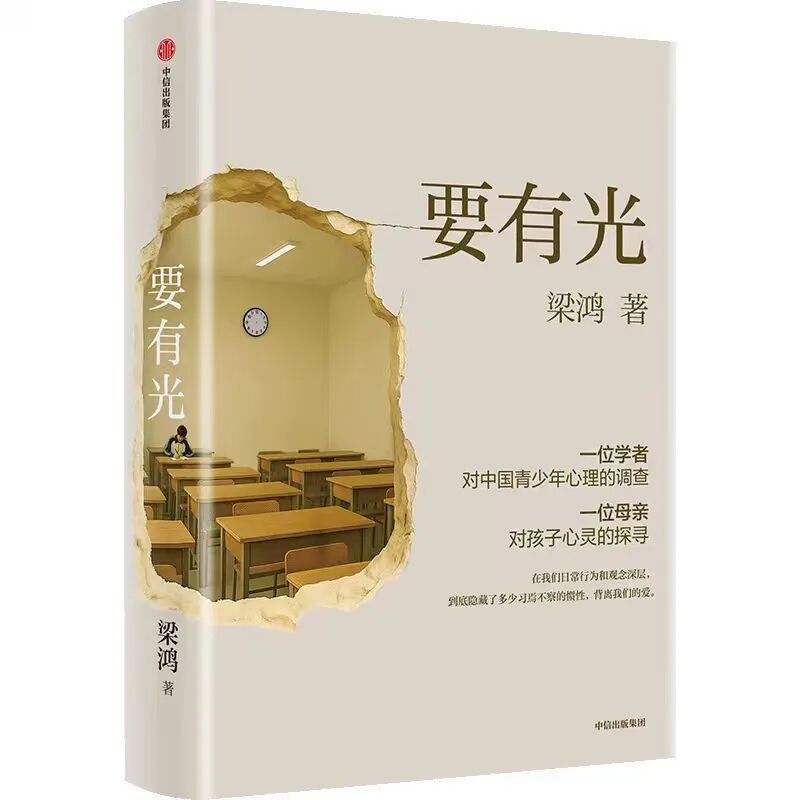
《要有光》,梁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第一版
中华读书报:“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要有光》前言中你表达的这些感触是写这本书的缘起吗?
梁鸿:写《要有光》首先源于巨大的冲动,这个冲动带来的写作无意间和青少年心理问题这个社会热点暗合。我自己也是母亲,我的孩子也在慢慢长大,我们同样有很多痛苦和迷茫。不管是我还是我身边的其他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业顺利,能成才。自己的时间、金钱、家庭的关注点都放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反而身体和心理出了问题,进而休学,这是非常大的反差。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痛苦?怎么尽可能避免这种痛苦?作为作家,我有自己的敏感度,会觉得这不只是孩子进入青春期所要面临的迷茫那么简单,有些孩子心理出问题了,有些孩子突然休学了,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这让我产生一种冲动,想通过采访和写作去探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我在写这本书,会对这些更关注,总是听说谁谁家的孩子不上学了,谁谁家的孩子在服药。原来觉得这一切离我很遥远,现在发现问题就发生在我身边。以前,我们听说某个孩子心里不舒服,会觉得过一会儿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现实中,很多孩子已经休学超过一年。我身边这种例子很多,有很多家长和孩子是不愿意说的。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在世界还没变得更糟糕的时候,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最初的写作虽然源于冲动,写着写着,也就有了责任感,好像看到了事情的本质,看到孩子的表象、内里,就去探讨家长该怎么爱孩子、爱社会、爱自己。这是特别重要的话题,值得书写和讨论。
中华读书报:从产生写作这本书的想法到最终完成想必是个漫长的过程?
梁鸿:这本书背后不止是写作的过程,还包括漫长的生活积累过程。我自己是孩子的妈妈,认识很多家长,也会读一些育儿、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跟几个妈妈有交往,之前可能没想到写作,但是会了解一些她们孩子的情况。这些日常和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是在为这本书的写作慢慢积累,也可以说动笔之前的准备时间很漫长。当提起笔来,就会知道,这些积累非常重要。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国在梁庄》系列,你更多是与故乡的亲友、乡亲打交道,沟通起来要容易些,而《要有光》中涉及到的家长、孩子都是深陷某种困境,是某些问题的“受害者”,在交流过程中,您如何让他们打开心扉、乐意讲述?
梁鸿:在和那些孩子、家长的沟通中我没怎么遇到完全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当然被拒绝也很正常。最初我在网上发布了信息,问哪个孩子愿意就这个话题聊一聊他们的经历,然后书中那位“雅雅”就跟我联系了,她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我就赶过去,去了滨海市,在那里陆续遇到了阿叔、敏敏。真正的采访调研,从滨海开始。我是作家,不是纯粹的社会学者,没有专门去规划、采样,那不是属于我的工作方法,我的采访也不一定要达到专业范畴的样本数量。其实,就是一些孩子和家长的生活来到我面前,那我就跟着这样的生活走吧,这是生活原本的形态。文学本来就是要记录、书写这些,我尽可能地把接触到的个案写好,它们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一些普遍性。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确定基于滨海(普通城市)、京城(大都市)、丹县(县城)这三个规模不同但颇有代表性的地点展开采访和叙述的?
梁鸿:这三个地方的选择很偶然,是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写《中国在梁庄》系列的时候,就是一次次回老家,和这个聊聊天,和那个聊聊天。写《要有光》也一样,先是去滨海,后来又去丹县。偶然认识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他在丹县乡下的卫生院工作,那边有个精神科,里边也有未成年人,我就过去了,之后就遇到了书中写到的娟娟和花臂少年,一聊,觉得还可以。当然我也去了其他地方,只是书中没写那么多。
在前往各地采访的过程中,我脑中慢慢形成了这本书的大致概念。要写什么,要怎么写,结构是怎样的?之前一点预设都没有。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写作,要摆脱原有的思路,要以崭新的状态进入。在滨海,采访是沉浸式的,是生活化的交流,几乎是和采访对象一起生活。我那时每天和学生、家长聊天,人来人往,谁来就和谁聊,我一直就在那儿等着。我把《中国在梁庄》那几本书放在桌上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接下来想写什么。他们说,呦你是个作家啊,就坐下来聊。我说我将来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会隐去你的名字,不会暴露你们的身份,这样对方的心理压力会小一些,交流起来就更放得开。他们觉得我是个真诚的人,就会比较信任我。
中华读书报:书中第一部分《滨海市》中阿叔这个人物是很特别的存在,他是一家补习班负责人,也是心理咨询师,他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孩子的问题,同时他的情绪管理包括解决方式并不都能让人信服,他甚至不乏情绪化、非理性的表现,您具体说说这个人物吧?
梁鸿: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读起来可能有点费劲,读几页就要折回去看看叙述者是谁,而这是我想要的效果。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书中呈现的是连续的生活场景,大家都在一个空间,学生可以学习、可以咨询,也可以和父母聊天。这样的空间对那些出了问题的孩子和家长来说非常重要,很多家庭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气氛冰冷而窒息。孩子们在阿叔这样的地方能够敞开心扉,家长能够和孩子对话。
阿叔作为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典型人物并不完美,在采访中我跟他吵过好几次架,他的很多想法我也不认可。书中我没有把他写成伟光正的人物,而是以相对客观、丰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我心中,他是很正向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种赤诚,对孩子真心地关怀,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是很多家长都没有的耐心。家长把孩子送到他那儿,作为咨询师,他也需要收费,但阿叔付出的心血不是那些咨询费能够衡量的。以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论,他的有些职业行为可能有问题,比如,心理咨询师要避免和咨询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阿叔和他的学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每次去采访,会请孩子们吃饭,也有阿叔参与。孩子们对他非常信任,愿意听他的话,一些观念就会改变,隔阂就会逐渐消解,解决问题的出口就慢慢有了。他对孩子的耐心和理解值得很多家长学习,尽管他的方法不适合每个孩子每个家长。
对人性、生活复杂之处的观察和书写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并不只是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给大家看,我希望我的写作能触及真实背后更深远的东西,试图分析,把复杂的路径和场域、相互交织的观点呈现出来,有内在观念的思辨。
中华读书报:在现实中,我们或许觉得一些家长做得不够好,但到底怎么不好,家长的表现有多少种样态,通过这本书就能了解。
梁鸿:孩子的内心是最敏感的,他完全知道家长的表现是真诚的还是装出来的。中国的很多家长特别容易轻视孩子,而孩子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轻视。这可能是我们文化结构中的一点,小孩是无知的,他不是独立的生命。我们要控制他,以我们的方式塑造他。但是现在的孩子自我意识非常高,他不像以前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给他吃饱穿暖就满足了。现在的孩子看到的信息、理解的世界,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你那样应付他、轻视他,会产生巨大的问题。很多孩子根本不跟父母说话,我采访时遇到过,他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所以拒绝跟你交流,除非你真的换一种态度。每个有问题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有问题的父亲或者母亲。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带给读者启发和触动,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您自己受到怎样的影响?
梁鸿:写作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个成长过程。接触到那么多案例,采访了那么多孩子、家长和心理咨询师,读了那么多心理学的相关资料……这些让我的内心变得疏朗了,作为家长,我也在变得更健康。我会反观自己的过去,会重新审视我跟孩子的关系,反思该怎么做家长才能做得更好。
中华读书报:我知道您和书中那些人物一直有联系,也会关注他们后来的情况。这本书的第四部分叫《时间……》,他们的故事其实没有结局,是开放式的,很多问题也不可能都得到解决。你说写作的时候没有具体的计划,但内心隐隐还是有些期许吧,从书出版到现在,曾经的期许实现了吗?
梁鸿:这次写作对我鼓励特别大,书出版后的反响超出我的预想。媒体报道的很多内容是我自己说的话,我反而很少看,我更想看读者的评论留言。有很多家长看了这本书之后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这让我很受触动;也有很多年轻人留言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也会说说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们真的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梳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有的读者留言说读完书哭了好久,我觉得哭是一种抒发,哭完了反思一下自己也很好啊。哪怕这本书不能改变什么,但他们读了之后开始正视自己,并且愿意把这些写到留言中,这已经是一种疗愈行动。
中华读书报:你在《要有光》后记中写到,这本书的故事是真实的,出于某种考虑,被采访者的名字、所在城市、学校、医院都进行了匿名处理,作为写作者和采访者,你是相对理性、严谨的,而作为一位母亲,和那些孩子、家长的交流又很难不让你情感波动,写作时这种理性与感性的分寸把握不容易吧?
梁鸿:是的,这方面处理起来很艰难。采访时我在场,写的时候又不想让“我”出现。一开始我还是按照《中国在梁庄》的叙述方式那样写,写了两三万字之后,觉得这种写法不适合这个题材。本来某个孩子、家长的讲述是直接面对读者,结果“我”出现了,显得碍事。所以我决定放弃这种写法,虽然在写法上转换人称、重新设置采访对象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很艰难,但调整之后感觉文本的流畅程度和阅读感觉一下子好了很多。读者可以直接面对敏敏、雅雅这些人物,会更有共鸣,有设身处地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接下来,你会继续写与《要有光》相关的话题?
梁鸿:我现在还没想过是否一定要把这个话题写下去。和书中人物在生活中可能会保持长久联系,所以也不排除之后有什么契机我会再写。对我而言,花几年时间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读者中慢慢发挥作用,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如果我是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那可能会持续关注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我是写作者,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放下,去写下一本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