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电影《鲁迅传》的一波三折 ——兼议新时期屏幕上的鲁迅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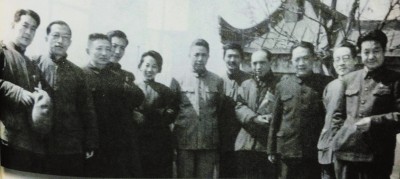
1961年,赵丹、于蓝、谢添,导演陈鲤庭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随《鲁迅传》剧组在绍兴
把鲁迅形象拍成电影属于传记片的范畴。在国际影坛,传记片原本是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的片种。电影诞生于1895年,1905年由欧洲引进到中国,经历了由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银幕、从平面到立体的技术变革过程。在欧美,像左拉、马克·吐温之类的作家早就现身于银幕。1940年,费穆自编自导的传记片《孔夫子》也受到了好评。1951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读者程庆图、李琮、高书平的联名信,呼吁摄制电影《鲁迅传》,因为“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给予人民的教育是亲切的”。
1960年底,《鲁迅传》摄制组正式成立。应该说,参与筹拍《鲁迅传》的单位和个人都是一流水准。虽然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但影片的前期投入也相当充分。上海天马制片厂摄制过《红色娘子军》《红日》《舞台姐妹》等五十二部故事片和戏曲片,知名度很高。导演陈鲤庭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蜚声文艺界。他创作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可以说家喻户晓。1942年他执导的话剧《屈原》轰动了国统区。2007年,陈鲤庭被授予“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参与剧本创作的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等,个个赫赫有名。执笔者陈白尘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代表作有《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宋景诗》等,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创作《鲁迅传》时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陈白尘对鲁迅作品相当熟悉。1980年把鲁迅的《阿Q正传》成功搬上了话剧舞台。主要演员赵丹、于蓝、谢添、于是之等,无疑都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至于各级领导的共同关怀和支持,更是其他影片很难得到的特殊待遇,结果电影《鲁迅传》历经五年,由“轰轰烈烈筹拍”,到“冷冷清清落幕”。
有人在回忆录中用很多笔墨描写了《鲁迅传》摄制组内部的矛盾,包括导演跟编剧的纠葛,编剧之间的分歧,主演跟导演吵架,以及剧组出现了作风问题、经济问题,等等。我想,凡有人群的地方,这些是是非非都很难完全避免。作为局外人,我们也难断是非。我曾走访过天马厂的一些老领导,觉得《鲁迅传》摄制组最根本的分歧,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对《鲁迅传》(上集)电影剧本本身的看法。
一
什么叫传记片? 我的理解,应该指真实表现历史人物的影片。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杰出人物,平凡人物,抑或反面人物,都必须真实存在,客观再现。虽然可以进行合理想象,适度润饰,有所取舍,次要人物也可以根据剧情需要虚构,但都必须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比如《林则徐》《聂耳》《董存瑞》都成功被拍摄成了传记片。但表现神话、传说(如《哪吒》《刘三姐》《阿诗玛》《杜十娘》《唐伯虎点秋香》)等这类虚构人物的影片则属于艺术片,不属于我们讨论的传记片范畴。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把传记片与艺术片分出高低雅俗,恰如不能让以真实人物为题材的影片跟《哪吒》《哈利·波特》一类影片一决雌雄一样。
把鲁迅的形象搬上银幕,比摄制其他传记片更为艰难:鲁迅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家,凡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从中小学教材中熟知了鲁迅的名字,每一个读者心目中往往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鲁迅,或难于跟他人交流或共享。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对鲁迅的认知各不相同,这也符合接受美学原理。因为读者在文艺欣赏过程中是有主动性的,文本一旦变成了作品,读者就会从阅读和欣赏中获得审美主体经验。这就是所谓一百个读者心目中会产生一百个哈姆雷特,而无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潜意识中沉睡的那个自己。
既然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有个体差异,再现文学家的形象更需要鲜明的个体性。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受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提倡一种集体创作的做法。其实集体创作古已有之,不少通俗小说或史诗民歌都是不经意间集体创作的。歌剧和电影《白毛女》就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但文艺创作的基础终归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劳动,集体创作必须与个人独创精神相结合。集体创作的效果取决于参与的个体之间能不能有效沟通。所以,集体创作并不适合于普遍提倡。电影《鲁迅传》之所以夭折,显然跟集体创作的方式有关。
据我所知,现在我们看到的电影《鲁迅传》剧本经历了五次修订,《人民文学》杂志1961年1、2期合刊发表的是第三稿,1961年《电影创作》发表的是第五稿。作为《鲁迅传》顾问团团长的夏衍修改的是第四稿,手稿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迄今未公开披露。1963年3月,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上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单行本出版,实际上是陈白尘1962年8月修订的第六稿。虽然执笔者在该书《校后记》中声明“这个上集的本子依然远难令人满意”,但初版本三万册顷刻售罄,1981年又加印了六千册。在不断修改过程中,编剧之间的分歧、编剧与导演的分歧、主要撰稿人跟顾问之间的分歧、演员跟编导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鲁迅这一光辉形象认识的分歧。对于通过电影表现手段展示人物的生活细节、生存环境、思想发展,不同编创人员各有自己的理解,最终难以统一。所以,有关部门对这部传记片“决定暂停投产”,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二
编创人员对《鲁迅传》电影文学剧本的第一个分歧就是框架。陈白尘把他执笔的《鲁迅传》上集比喻为“四间房子”。“第一间”(即第一章)起始于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此前经历从“旁诵”带过,终止于1912年5月初,略去了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那三个月。主要表现以鲁迅、范爱农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者跟封建复辟势力代表章介眉及辛亥革命后逐渐变质的光复会成员王金发之间的矛盾冲突。“第二间房”(即第二章)始于1913年春天,终于1921年冬天。主要表现鲁迅在十月革命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下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的对立面是在“不谈政治”口号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第三间房”(即第三章)始于1921年以后,终于1926年8月,略去了鲁迅在厦门大学那五个月的教学生涯。这一章写了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鲁迅的对立面是段祺瑞、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他们代表了北洋军阀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第四间房”(即第四章)始于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到达广州,终于1927年9月下旬。这一章主要表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支持指引鲁迅的是以陈延年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立面是祝家骅(即朱家骅)等国民党右派人物。以上“四间房”平分秋色,是执笔人陈白尘的创意。但是,也有人主张下集干脆从左联成立开始,上集写鲁迅的“成长”,下集写鲁迅的“斗争”。如果这样处理也并不是绝对不可以,问题是鲁迅终其一生都是在“斗争”中“成长”,只不过是前期斗争的环境与对象跟后期有所不同,斗争的特点和方式有所不同。陈白尘并非彻底否定这一意见,只是觉得把他精心设计的“四间房”拆掉,即使改得好,他本人还是不习惯,进屋摸不着门路。我以为,这其中还涉及到对鲁迅思想发展的理解问题。这一点在鲁迅研究界始终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就增加了拍摄的难度。
对《鲁迅传》电影文学剧本的分歧,还表现在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历史大厦是靠历史细节支撑的。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作为具有直观性的影视艺术,更需要通过真实的历史细节反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营造历史性氛围,揭示鲁迅思想。传记片的细节失真,观众就可能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顷刻之间产生幻灭之感。陈白尘对《鲁迅传》追求精益求精,几经修订,但这方面的问题仍然无法尽免。作为艺术创作,对于鲁迅生平史实进行前置或后移并非绝对不可以,但终究应考虑其合理性。根据小说《故乡》的描述,鲁迅跟中年闰土的重遇是在1919年底,其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职科长和佥事,所以闰土称其为“老爷”,杨二嫂也说鲁迅“你阔了”。剧本将这一场景前置于鲁迅去教育部任教之前,已显牵强,但是还能凑合,但让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期间“进行氢气试验”,就更显不合情理。因为鲁迅在这所学校担任的是博物教员,主要讲授的是植物学,而进行“氢气试验”发生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期间,那时鲁迅教的是化学和生理学。一个教植物学的老师,是不可能在课堂进行“氢气试验”的,虽然这个情节颇有画面感,也极有戏剧性。
剧本中还有若干违背历史常识的细节,如章介眉为了政治投机,“向军政府献了三千亩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绍兴,还没听说有拥有三千亩良田的大地主。周氏家族三房的公田只有七十二亩。鲁迅父亲的田产只有四五十亩。剧本描写鲁迅与挚友许寿裳同坐骡车,在教育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鲁迅的同时代人说,那时北京人出行几乎无人坐骡车,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车。许寿裳是教育部参事,鲁迅是佥事,两人差一个级别,不可能在一起办公。剧本为了表现鲁迅帮助扶植青年作家,专门设计了一个画面:“未名社的招牌。招牌旁边贴着一张《莽原》周刊出版的广告。”但《莽原》周刊是莽原社的出版物,社址在锦什坊街(现金融街一带),跟未名社应属两个文艺社团,相互关系不融洽。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也是发表在未名社的出版物《莽原》半月刊,而不是《莽原》周刊。这些细节,对不熟悉历史的观众是一种误导,在熟悉相关历史的观众眼中则是破绽。
三
创作鲁迅传记片的最大困难是对鲁迅其人的总体把握。凡杰出的历史人物,其性格必然有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但一定又有其多面性、矛盾性、复杂性。所以鲁迅认为评价或再现人物要顾及“全人全貌”,同时因为他仍然是人,所以即使是战士,身上也会有“缺点和伤痕”。鲁迅传的电影剧本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然会留下那个时代的历史印痕,即把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过于政治化,特别是《鲁迅传》属于集体创作,作为执笔人的陈白尘也不可能避免这种历史局限。
我这样讲,无意于反对鲁迅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提法。我历来认为,思想家是指那种关怀人类、求索真理而不受金钱和指挥刀指挥的人,其思想具有深刻性,思维具有辩证性,思想影响具有广泛性,而不必一律要求他们去构筑模式和建立体系。如果革命可以分为文武两条战线,那么将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作家称为革命家也不能视为“神化”,更何况鲁迅语言宝库中的“革命”二字相当于“变革”,而变革的方式与手段并不限于武装斗争——虽然鲁迅认为在旧中国进行改革,大炮比诗歌更有力量,但他进行变革的主要手段还是用文学来改造人生和国民劣根性。鲁迅的确不是政治家。他反对维持现状的政治,将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和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鲁迅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杂文)除了艺术欣赏性之外,还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他跟中国现代革命政党和革命人士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问题取决于如何恰如其分的表现。
在电影《鲁迅传》剧本当中,李大钊出场约二十次。如李大钊多次去鲁迅家拜访,谈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工农运动。钱玄同约鲁迅为《新青年》写稿成为了受李大钊所派遣,就连鲁迅南下广州也成了李大钊的指示。鲁迅认识李大钊,认为他朴质、儒雅,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但个人之间的交往或政治上的交流有限得很。1933年5月7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信中写得很清楚:“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解,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鲁迅初到广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鲁迅自然成为了国共两党同时争取的对象。直到“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作为革命人道主义者,鲁迅的立场才明确站到了被屠戮、被镇压的革命者这一边。鲁迅在中山大学的确接触了像毕磊这样的共产党人,但他跟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具体接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说鲁迅、许广平到上海是为了找陈延年,更是没有任何根据。《鲁迅传》上集的结尾是:“轮船在大海中航行。鲁迅掏出报纸,一条新闻被红笔圈了起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消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鲁迅是否在由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就从毛泽东的革命业绩上受到了鼓舞,这从鲁迅作品和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中都找不到证据。
在《鲁迅传》电影剧本中,对其他次要人物的处理同样存在过于政治化的倾向。1960年8月20日,许广平给《鲁迅传》编创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把许广平说成与李大钊相谈,与毕磊相识,似乎把许列入革命队伍中人,太不合事实,是否也修改一下?”许广平的这一意见决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对史实的尊重。难以处理的人物还有一位周作人,因为他后来的汉奸身份,所以在剧本中渺无踪影,只有一位三弟在鲁迅身边出现。此外,电影剧本中的反面人物,如胡适、陈源、朱家骅、傅斯年等,编剧在当时也只能将他们脸谱化、漫画化,无法表现他们本身以及跟鲁迅关系的复杂性。从以上的情况来看,陈白尘执笔的这个电影剧本即使当年拍摄完毕,今天回放也肯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四
2005年,上海电影集团、张瑜影视文化公司和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又新摄了一部电影《鲁迅》,执导者丁荫楠,曾获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凭借《孙中山》《周恩来》等人物传记片获得了盛誉。主演濮存昕是众所周知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他们联手在银幕上塑造鲁迅形象,又得到了张瑜的资金支持,观众期待能弥补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影《鲁迅传》夭折的遗憾,然而这位在摄制其他影片时“过五关斩六将”的名导,在拍《鲁迅》时却走了“麦城”。
我用走“麦城”形容这部影片的拍摄效果,依据是两个:在电影市场掌声寥落。上海以团体票房为主,似乎只过了百万大关;让编创人员更为受挫的,是这部影片在文化界也没获得好评。也就是说,既没赢利,也没收到掌声。
据介绍,传记片《鲁迅》把时间段压缩到1933年到1936年,也就是鲁迅临终前的三年。由于当今社会思潮的影响,这部影片把重心放在揭示鲁迅的情感世界,比如表现鲁迅的亲情、师生情、战友情……“无情未必真豪杰”,自古作家最多情。写情当然没错,但鲁迅临终前这三年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我认为用“愤懑”二字概括比较妥帖,代表作有两篇:一,《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前文跟《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样,表达的是对国民党“权力者”的“愤懑”;后文跟《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样,表达的是对同一营垒内部错误倾向的愤懑,所以鲁迅当年战斗的姿态是“横站”。但要通过电影手段将这一复杂的环境和心态通俗化地表现出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主演尽管想演出一个“会喘气的、活生生的鲁迅”,但影片中的鲁迅虽说“会喘气”,但并没有真正在观众心目中“活起来”,甚至不明白影片到底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鲁迅给观众看。
将鲁迅一生完整在屏幕上再现出来的是电视片导演史践凡。他跟我同年出生,也曾有过合作关系,成名作是《鲁迅》《鲁迅与许广平》。但我年迈多忘,很多具体情况记不准确。我用微信问他。他回复说:“哎呀呀,你是我拍鲁迅的顾问呀! 鲁迅少年时期拍了四集,鲁迅在南京拍了两集,鲁迅在日本拍了四集。上述十集先后在1981年、1983年、1986年完成。1999年接拍《鲁迅与许广平》,共二十集。连改本子带送审,修改后再摄制,直到2000年算是用电视剧的形式拍完了鲁迅伟大一生。虽然存在不少缺憾,但我们创作始终是认真严肃、崇敬而严谨的,更可贵的是全部是实景实地,这恐怕是空前绝后了,也更具历史价值。今后研究鲁迅的人都可以从这三十集电视剧里得到些许形象的感悟吧。更有你这鲁迅研究专家的斧正把关之功。这是绝对不可忘却的。”我接着问播放的情况。史导回复说:“全部都在中央一台及浙江电视台多次播放过。写少年鲁迅我是执笔者之一,剧本发表过。《鲁迅在南京》《鲁迅在日本》是我单独执笔,发表过。《鲁迅与许广平》二十集请了两位编剧,但我跟夫人奚佩兰导演修改过,得以通过并被充分肯定,剧本未见发表。但只有后二十集才有你这顾问的大名。”
事隔几十年,手头无剧本,我实在无力对电视剧《鲁迅》作总体评价,好在这部电视连续剧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特别奖、导演特别奖及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特别奖。这代表了业内及观众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是对史践凡导演二十多年执着追求的一种褒奖。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年,更何况是风华正茂的岁月?
我对史践凡导演有三个最深的印象。一,他196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78年开始进军电视。导演系和电影文学系应该是两个专业,但史践凡能写能导,是个全才,这在导演群中并不多见。二,他有一个戏剧界的家庭,其父史行,是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学生。妻子奚佩兰,是史践凡的大学同学,因导演《女记者的画外音》成名,能导能写还能画。女儿史兰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因在电视剧《围城》中饰演唐晓芙被观众熟知,在电视剧《鲁迅与许广平》中饰演许广平。我清楚地记得,在北京鲁迅故居拍的一场戏中,史兰芽一条过关,现场的奚佩兰情不自禁地说:“腕就是腕!”
史践凡给我留下的第三个印象最深,那就是他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都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电视剧《鲁迅》一开头的画面是借鉴了我在《民族魂》中的提供的一个细节:“鲁迅出生时,按照绍兴的习俗,家人依次给他尝了五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要备尝酸辛,经历磨难,最后才能品味到人生的甘甜。”我这一描写取自于许羡苏的回忆,而许羡苏的回忆又得知于鲁迅的母亲鲁瑞,当然绝对可靠。无怪乎曹禺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开头就拍案大声称赞:“好! 开头好呵!”拍鲁迅从上海赴日本留学这一集时,让史践凡感到苦恼的是找不到当年那种老式的日本客轮,难以让观众重返当时的历史情境。这件事最终如何解决的我就不知道了。拍摄鲁迅到陕西讲学时也遇到了类似难题。跟鲁迅同行的孙伏园有一篇著名的游记《长安道上》,描写当年黄河上的船夫“是赤祼祼一丝不挂的。他们紫黑色的皮肤之下,装着健全的而美满的骨肉。头发是剪了……五个脚趾全是直伸……他们的形体真的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史践凡当然也煞费苦心去找类似的群众演员,但是他很遗憾地告诉我:“现在的船夫都长得太胖,肉囊囊的,那种类似于伏尔加纤夫的人已经找不到了。”一部剧拍了二十年还留下些遗憾,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与鲁迅相关的影视作品还有一些,有的是纪录片,其中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先生鲁迅》请了不少专家学者出镜,各谈自己对鲁迅的感悟,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观赏性。还有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电影,影响较大的有桑弧导演的《祝福》,水华导演的《伤逝》,岑范导演的《阿Q正传》等。吕绍连导演的《药》和张华勋导演的《铸剑》也征求过我的意见。
鲁迅形象也被搬上过话剧舞台,但不属于本文议论的屏幕范畴,当待有机会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