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循的历史观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为了《天著春秋》的写作,我研读上古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都是从“我的历史观”这个基点出发,寻找那个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两种状态,是我写作的基座。 王树增:寻找古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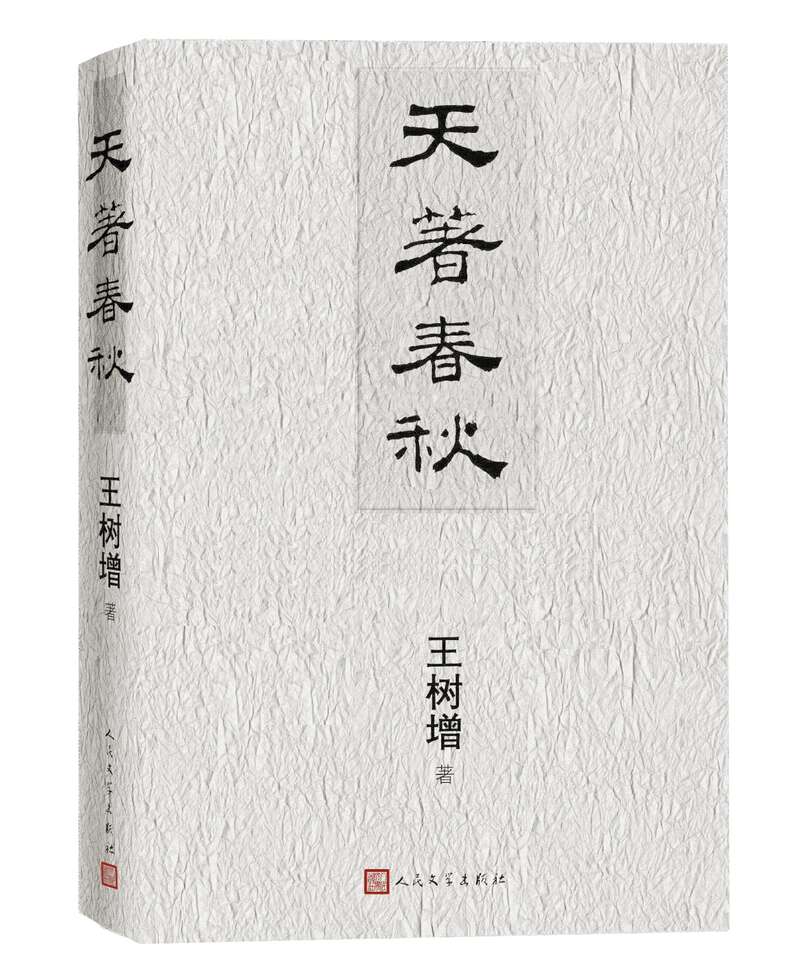
《天著春秋》,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年前完成《抗日战争》后,军旅作家王树增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潜心搜集、整理典籍,专注于《天著春秋》的写作。他甄别史料,也多次寻访古战场、古遗迹,终于以高品质的历史书写,完成了这部既是古代战争史,也凝注华夏文化、文明回望的大作。
除古代战争的丰富内容外,《天著春秋》将夏商周三代到春秋五霸的辉煌与挑战,文明的兴盛与延续,政治的复杂与权谋,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既可以从中看到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哲学理念、传统礼俗、文化心理等,品味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智慧,又因作者从个人史观和文化观切入的精妙解读,为我们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据不完全记载,春秋时期的大小战事达500多次,100多个诸侯国曾被兼并或亡国,超过50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死。战争在霸权更替、推动历史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书写战争,不是为了揭秘,也不止于梳理,王树增希望以重要战争为脉络,讲述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1901:一个封建王朝的背景》和《1911》、“现代战争三部曲”(《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朝鲜战争》,您所选择的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天著春秋》也不例外,起于夏商终于春秋战国,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走到了尽头。您在完成《抗日战争》后曾透露书写古代战争的设想,为何选择从春秋时期切入?这一阶段战争对军事思想形成有何特殊意义?
王树增:人类文明史,几乎伴随着一部战争史。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狩猎和农耕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人口繁衍加速,各部落之间的生存竞争愈演愈烈,战争行为便成为生存需求之一。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春秋时期是战争密集发生的年代,梳理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史,春秋时期是重要的源头。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古中国的兵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的文化依托,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灿烂辉煌的篇章,中国的兵家文化,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完成《抗日战争》的写作之后,踏着响彻这片土地上的连绵不断的战鼓之声向遥远的过去寻古溯源,是我心怀已久的写作夙愿,因为我知道,要彻底解析人类的战争行为,不亲耳聆听上古战场上的鼓乐齐鸣,几乎无法自圆其说。
中华读书报:为撰写《天著春秋》,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史料研读与田野调查,能否分享最触动您的发现或细节?
王树增:我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无论是《史记》还是《左传》,和《诗经》一样,都应该归于文学范畴。理由是:无论近现代考古学如何发展进步,人类历史的所谓“客观真相”,依旧是个谜团。所有的《史书》,都是编纂者站在个体立场上的“创作”。因此,对史料的研读,最大的功课是透过狭窄的缝隙最大限度地寻找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毋庸讳言,得出的结论也距离“真相”尚有相当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史料的研读是干枯艰辛的,绝少有撩拨心绪的时刻。而走访古战场,却是另一番风景:大河两岸,沃野千里,山隘险峻,沟壑幽深,大河还是那般流淌,春草还是那般婀娜,历史上一场又一场的血流成河没有任何留痕。于是不由得仰天诘问:那些帝王将相们呢?那些甲士兵卒们呢?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战争? 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在面对亘古山河的那一瞬,这些诘问涌上心头,催发了我的写作欲望。
中华读书报:从现代战争史转向古代战争书写,研究方法和叙事视角有哪些突破性调整? 您认为这种跨时代解读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王树增:无论是写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都是对文化的解读。所谓研究方法和叙事视角,实际上是文化解读和视角。因此,古代战争的书写,首先是对中华文化的回溯与瞻仰。但是,无论是《史记》《左传》《诗经》《楚辞》,还是孔墨老庄,研读都有相当的难度。这个难度,不是今人对古文字阅读的障碍,而是要摈弃以今人的思维和视角去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首先努力使自己成为“古人”,此乃难度之最。
中华读书报:《天著春秋》中对“一鼓作气”“卧薪尝胆”“退避三舍”“秦晋之好”等典故的解析令人耳目一新,如何在保证史学严谨性的同时赋予文学感染力?
王树增:如今“非虚构”类文学写作和阅读,似乎有热起来的趋势,我理解的“非虚构类”文学写作,至少有两个特征:一、非虚构,即严格遵循考证的原则,事件、情节、人物等等均不得虚构;二、是文学而不是史学,后者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梳理历史的前因后果,得出历史的规律性结论,前者是遵循“文学即人学”的原则,主旨是写历史中的人,梳理人的精神发展脉络——所谓“文学感染力”,即从这里而来。因此,历史事件仅仅是个依托,我想介绍给读者的,是“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和“一鼓作气”中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的思维和行为,才是写作和阅读的精华。
中华读书报:书中描写了很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历经千年,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德和智慧,同时也处处充满哲理和辩证,比如权力和人理之辩。比如书中既呈现“血流百里”的残酷,又描写“君子好逑”的温情,这种双重性是否暗含您对战争与人性的思考?
王树增:单纯的、纯粹的东西和事物,世间根本不存在,因此,我喜欢“双重性”这个词。毫无疑问,对文明的摧残与破坏,对生命的蔑视和杀戮,莫过于战争。但是,人类的战争行为的双重性是:战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国家形态的完善和进步,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哲学、美学和宗教,产生了人类的英雄崇拜——可以说,没有战争,人类文明的脚步便无法前行,这个结论残酷无情,但符合人的本性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君子好逑”的同时又“血流百里”,不正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么?
中华读书报:这种双重甚至多重性的比照在作品中无处不在。比如表现《诗经·郑风·东门之墠》时,您写道:“东门外美丽的花园呀,茜草沿着山坡生长。她的家离我近在咫尺呀,人儿却像在很远的地方……”以现代语言传递出民歌风情,反映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激烈残酷的战争相互映衬,更显出您在历史书写中深切的人文情怀。《天著春秋》不仅仅是战争史,而是以战争为线索的、以战争为脉络的上古时期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这部书的资料多出自《左传》《史记》等,但您的解析和判断客观而真实,史中见实。您在写作中秉持怎样的理念?
王树增:我无法做到“客观而真实”——《史记》是司马迁的“真实”,《天著春秋》是我的“真实”——司马迁秉承着怎样的理念,不得而知,我遵循的历史观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为了《天著春秋》的写作,我研读上古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都是从“我的历史观”这个基点出发,寻找那个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两种状态,是我写作的基座。我写了帝王们,但是,我力求在我的笔下,让帝王们回归到“人”的精神层面——只有将这种层面写透彻,才有当代读者的心领神会。
中华读书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能体会到您的良苦用心。作品以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长勺之战等十场古代大战串联千年历史,筛选标准是什么?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似乎“麻隧之战”相对冷门?
王树增:十场战争的选择都基于一个原则:导致欲望的破灭和国运的改变。“麻隧之战”是晋国树立大国地位的开端,也是秦国国运处于低谷的时刻——有趣的是,不久,不可一世的晋国解体了,秦国却成为霸主——这就是历史。从这个角度上看,此战不“冷门”。
中华读书报:《天著春秋》既写出了历史的大脉络,又写出了其中的人和精神。您以战事的视角切入,对历史、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呈现和解析。诸多君王、重臣、将领、游侠、谋士不再只是单一的符号,更是有血有肉的个体。非虚构写作中如何刻画人物,您的观点是什么?
王树增: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实际上是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个塑造除细节之外,还是细节。我的非虚构写作的体会是:大历史框架和丰满细节,两者缺一不可,谁将两者融合得恰到好处,谁就是大家。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李敬泽称本书为“精神的寻根之作”,您希望读者从中获得哪些超越战争本身的理解?
王树增:所谓“精神的寻根”,或许这是所有优秀文学作品共有的追求,只是《天著春秋》的精神溯源更为久远。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天著春秋》中,不仅仅读到了古代战争,更重要的是,读到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自然的春华秋实、生命的毁灭再生和兴亡的周而复始,从而使得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纷繁更加理性、心胸更加开阔,使我们面对自己的人生和生命时,积极坦然,从容快乐。
中华读书报:书中对兵器、仪式的考据极为精细,这类细节对普通读者理解历史有何助益?
王树增:《天著春秋》的写作,考据最为繁复的,是古代战争的样式、阵型、兵器、战法、部队编制、指挥系统、后勤保障,以及战鼓的尺寸和敲击处不同鼓点的含义、战旗样式和颜色具有的不同等级和指挥权限;甚至战场口粮的营养成分和各国军装样式的设计理念等等,史料珍稀,如同瀚海拾贝。但是,这类细节的丰润,是作品成败的重要前提,也是读者的期望之一。
中华读书报:莫言评价您“主观地解读客观的战争”,您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中作者主观性与历史客观性的边界?
王树增:莫言指的是虚构类写作和非虚构类写作的区别。如果“客观性”指的是历史本身的话,作家的独特解读,就是所谓的“主观性”。在优秀的非虚构类作品中,有一个必须的特质:对历史的独特的理性解读。写作的动力和灵感,正是这个“主观性”,读者阅读的目标,也正是作家的这个“主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