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穆旦,窥见复杂的时代面影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句来自穆旦名作《赞美》中的诗句,被2025年高考作文(全国一卷)用作写作材料,使得诗人穆旦再次引发关注,而且,这次影响的范围更为广泛,受众群体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者和穆旦诗歌的热爱者。梳理近三十年来的穆旦接受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中将穆旦置于全卷之首,穆旦其人、其诗开始渐渐广为人知。这之后,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的变迁,穆旦的经典化程度也得以大大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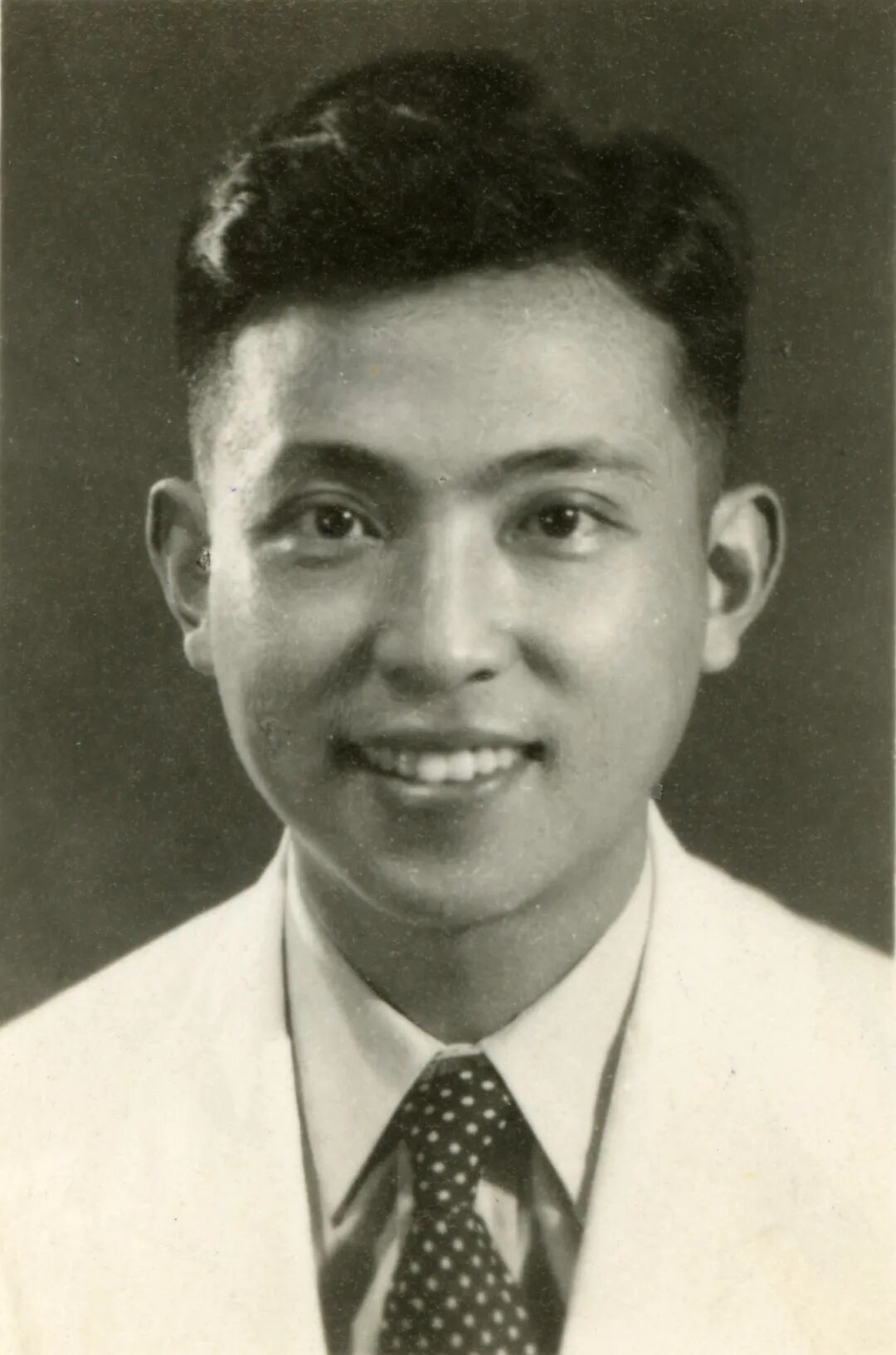
穆旦1949年3月在泰国曼谷
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易彬关于穆旦的研究,与这一进程紧密相关。自本科时期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他开始接触穆旦诗歌,到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以穆旦为选题。纵观易彬二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历程,穆旦是他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的文字已成系列:《穆旦年谱》处理的是编年问题,《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是史论的路数,《穆旦诗编年汇校》着眼于版本,《一个中国新诗人——穆旦论集》是专题论文集,《穆旦研究资料》(上下册,与李怡合编)是研究文献的汇编。
而在今年上半年出版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由《穆旦评传》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而来,则属于综合性的写法。“与同时代的重要作家相比,穆旦的自我阐释类文字明显较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可理解为穆旦无意于对自身形象的建构,但在客观上,尽管有少量残存的日记、书信等史料,穆旦人生中的某些重要节点,对后世而言,仍存在诸多晦暗不明之处。为解决传记写作所面临的难题,易彬自认是以穷尽的方式去搜集穆旦的各类相关文献。此书被称作是“一部以文献丈量生命的传记”,易彬希望能尽可能通过第一手或直接相关的背景文献,贴着穆旦来写,去查实每一个历史节点的内涵;同时,也致力于“提供一种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在他看来,20世纪的文化语境盘根错节,复杂难辨,传记(也包括年谱)类著作很有必要突破传(谱)主的单一性文献的局限。突破的力度越大,越能呈现出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也就越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面影。希望读者在进入穆旦并不顺畅的人生故事的同时,也能读出历史本身的复杂含义。

易彬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版
一个风格独特的“中国新诗人”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位长期研究穆旦的学者,您认为为穆旦作传最大的必要性和独特性是什么?与其他诗人传记(如郭沫若、徐志摩)相比,穆旦的生命史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提供了怎样一种独特的样本?
易彬:1994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学·诗歌卷》,将尚不广为人知的穆旦推为新诗第一人,引发学界的热烈关注。二三十年来,穆旦的文学史地位已然确立,而他那更为丰富的生命形态与历史内涵也已呈现。实际上,随着近年来新文献的批量出现,我也深感2010年版《穆旦年谱》、2012年版《穆旦评传》等著作已有修订和扩充的必要。关于《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的独特性,我觉得出版推荐语:“一部以文献丈量生命的传记”是很好的概括。在我看来,文献的准确与翔实是传记写作的第一要义,传记作者应该有穷尽相关文献的意识(虽然事实上不可能将其全部运用到写作之中),知晓文献的边界和那些实有的、可能的生命形态。因为文献不实(或没有仔细查阅,或简单袭用各类二手文献乃至道听途说)而产生的认知偏差不在少数。在不同的场合,我都谈到过希望通过尽可能翔实的文献,展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也更贴合历史的传记形象。也谈到书名“幻想底尽头”,是想强化对于穆旦生命形象的展现。其中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尽头”。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穆旦都有过热烈的、美好的“幻想”,却往往遭到挫败。放眼20世纪中国,类似的遭遇很多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穆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那不断燃烧的生命热情(投身于战争、办报等大事件)、对于祖国的挚爱(1953年排除重重阻力从美国回来)、对于文化所寄予的希望(希望翻译带来“中国诗的文艺复兴”),以及对于诗歌艺术性与个人性的守护、对于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着意寻求(秉持“良心”办报、在困厄的年代里持续翻译等),这使得他虽遭受不断的失败、挫折和磨难,而依然坚持自己的工作(翻译);终至走到“幻想底尽头”,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声音。
中华读书报:诗歌评论家谢冕将穆旦比喻为“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非常形象恰切,也非常打动人心。您如何评价新诗史上的穆旦?换言之,您心目中的穆旦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易彬:在谢冕老师的评价发出的时刻,穆旦确实还是一颗“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放眼新诗史,穆旦是在20世纪40年代崭露头角,50年代隐失,80年代被重新发现,90年代之后,逐步获得广泛的诗名和文学史高位。1996年列入“二十世纪桂冠诗丛”、将谢冕老师的《一颗星亮在天边》作为序言之一的《穆旦诗全集》,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今日所获具的文学史地位,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穆旦当年是很有影响力和非常受欢迎的诗人,实则穆旦生前不过是一位声名比较微薄的写作者,是一位小人物(主要身份是小职员),他在时代的激荡下成长,在语言和人生的双重涵义上探索、磨砺自己的诗歌风格。他原本也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诗歌声望,但被剧变的时代强行扭断。在留学归来直至去世这二十多年里,穆旦在很多时候保持着沉默,而无论是被时代风气所鼓动所写下的、还是历经磨难而残存的诗篇,都保持着自己的声线。而那些为数巨重的翻译行为,也有着诗歌使命和诗人形象的内涵。这就是这部传记努力去勾描的诗人穆旦形象。
中华读书报: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旦因其诗歌风格的异质性,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实,同时期的诗人受到的影响大同小异(比如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战乱岁月等时代因素等等)。在您看来,穆旦身上哪些特质使得他成为如此独特的个体?
易彬:首先还是要考虑时代的因素。传记的第二章植入语文教育的视角,是想强调在新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之下,穆旦相比于此前的诗人,所呈现出来的新的代际特征。穆旦在中学阶段进入着力培养“具有‘现代能力’之青年,使负建设新中国之责任”的南开学校,又逢教育部颁布新的、明确强调现代语言能力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这种“现代”教育环境形成了穆旦成长的总体背景。而穆旦中学阶段的写作即已表现出一种持重的品质,和对于语言、对于写作题材的敏感。随后他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染,则是进一步加固了中学阶段所接受的知识与教育。英国诗人、理论家燕卜荪的教导被认为是关键性的,让“沉浸于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穆旦也通过写作实践和诗文翻译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体悟与技巧研习。
文学教育之外,现实的磨砺也非常重要,也可能更为重要。抗战爆发之后的大迁徙、特别是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的三千里路途,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战场上的生死经历,直接改变了穆旦的人生方向,而穆旦也将这些个人经历内化为切实的诗歌经验。
穆旦在语言和人生的双重涵义上成长:不断去探索现代汉语的潜能,赋予其诗以独特的语言向度与艺术魅力;而又充分熔铸个体经验,其诗歌有着可以触摸的现实底色与生命质感。个人性、时代性与艺术性的这种平衡,使得穆旦最终成为一个风格独特的“中国新诗人”。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中华读书报:穆旦的人生经历中,早年的“破落户子弟”出身和长其近40岁的鲁迅很相似。您指出,鲁迅作为“家道中落”的“孩子”最终成长为“毁坏”“铁屋子”的启蒙者,同样“没落”的查良铮却没有以类似的方式“长大成人”。这一对比视角很有意思,也很具启发性。请您就此简要谈谈。
易彬: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这本书封面“幻想底尽头”五个字用的是鲁迅体。责编在封面设计时跟我交流,说这本书一开始就展开了与鲁迅的比较,中间也有线索,到最后鲁迅还是穆旦的精神支柱,用鲁迅体也正相宜。实际上,关于穆旦与鲁迅,我之前写过一篇《杂文精神、黑暗鬼影与死火世界——穆旦与鲁迅的精神遇合》,其中只有少许事实的勾描,如穆旦不同时期的诗歌、书信所涉及的鲁迅,更多地是藉助文本的内在线索展开。穆旦与鲁迅在写作行为与精神气质上有相似之处,如对于时代语境的敏锐感知,对于个体心灵的担当,但在现实人生、时代语境及相关文学命题方面,彼此所采取的担当路径还是多有分途。因为少有实证层面的线索,可见以鲁迅文学遗产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已经内化为写作者的精神资源。不过,限于写作体例,传记没法多展开这方面的话题。
中华读书报:“丰富的痛苦”是穆旦诗歌的内核和精神底色。您认为这种痛苦的核心来源是什么?是来自现代主义诗歌技艺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张力,是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内心挣扎,还是其个人性格与命运使然?
易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自1942年2月写下的《出发》,曾被用作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的书名,编者应该是想藉此来展现这位诗人的精神特质。穆旦总是能敏锐地察知到个体与周遭世界的紧张关系,这源于他的敏感心性,中学阶段的诗文作品即有流露;也跟他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有莫大的关系,穆旦笔下“那些表现自我的残缺、分裂、被动以及描绘‘我’与世界的敌对和隔绝的诗作”,不仅仅来自现代主义诗学资源,还可以往上追溯至柏拉图哲学理念和基督教精神(李章斌观点)。个人遭遇以及战争环境之下的动乱时局,也加剧了穆旦诗歌的精神向度。穆旦1940年代期的一些诗篇,比如,有着强烈的现实讽喻与愤慨的《饥饿的中国》,也内蕴着对于个人境遇的省思,“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传达了一个渺小的个体在充斥着“苦难”与“死亡”的现实世界里所领受到的“虚空”与“耻辱”情绪,对于黑暗、对于行将被毁灭的自我的敏锐感知,以及对于幸福的遥遥企盼。这大致可视作穆旦早期诗歌形象的一种归结。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穆旦最大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对于当今面对另一种时代复杂性的青年知识群体和写作者,穆旦能提供怎样的启示?
易彬:穆旦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所遭受的磨难,或非今日读者所能想象。他所遭遇的语言环境,比今日更为博杂、更多传统的阴影和政治负压。而他对于祖国的情怀、对于文化的热忱以及对于(翻译)工作的韧性,也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今日的青年知识群体和写作者而言,面对时代的复杂性,如何找到自己的“岗位”、保持自己的声音,又如何在个人性、时代性与艺术性之间寻求写作平衡,穆旦的写作与人生是能提供启示意义的。
打开新的问题空间
中华读书报:通过这次深入的传记写作,您对穆旦的诗歌是否有了一些全新的、不同于纯文本批评的理解?能否举例谈谈?
易彬:在穆旦这里,知人论世的批评还是更具效力。新发掘的文献、各种时代因素的深入勘察以及对穆旦写作行为的细致爬梳,都可能会带来对于穆旦诗歌的新认识,打开新的问题空间。一个非常恰切的例子是新发现的穆旦关于从军的文字,特别是语调悲怆的《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为解读穆旦的那些跟战争有关的诗篇,特别是《隐现》《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提供了更恰切的视角和事实的支撑,能让读者更真切地感知从战场归来的诗人何以全无“英雄主义的坏趣味”或胜利者的喜悦,而是以庄严的诗剧体式来反思现代文明,书写死亡和“遗忘”的主题。另一个显在的例子是藉由对穆旦写作行为的考察而获得的认知。穆旦是非常勤于修改的诗人,不同于别的传记的是,这本书中贯穿着穆旦诗歌版本与编年的线索。希望读者不要把它看作简单的考据或学究式的操作,我把它看作一种写作的需要,若没有这条线索,穆旦写作的某些秘密,特别是生命末期的境遇将很难得到清晰的呈现。
中华读书报:您从1994年大学时期开始注意到穆旦,硕博论文也是以穆旦为题,在其后的20多年里,编著有《穆旦年谱》《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一个中国新诗人——穆旦论集》《穆旦研究资料》等一系列作品。请您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20多年的投入,穆旦其人、其诗、其研究之于您个人,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易彬:想想也是很奇妙的事情,一颗偶然间埋下的种子,日后长成了大树。最开始是直觉,也有重要事情的触动,如2002年采访杨苡、杜运燮等四位穆旦友人,后来慢慢地成为一种学术自觉,会有意识地搜集穆旦的各类文献,也会去延展各类相关线索,比如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学、大学教育的文献,关于抗战特别是中国远征军的文献,关于新中国前后留学归国的文献等;也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在天津、北京、长沙、南岳衡山、昆明、蒙自等地。在这些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和一些有趣的人生交往故事(后记写到了一个故事)。二十多年已不是人生的短距离,一个人由青葱岁月到知天命的年纪,这个系列研究实证了我作为一位研究者的成长与存在意义。个中甘苦已无需多言,有一个朴素的感受愿与大家分享,那就是研究是一种坚持和耐性,它会让你穿过时间的长河,深入时代的内部,发现事物的秘密,从而展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会让你找到应对世界的方式,往大处说,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务必保持开放的学术视野。所以在穆旦研究的同时,我也做了为数可能并不算少的其他研究工作,也会从中去寻求视野的对照和工作边界的拓展。
中华读书报:与此相关,也请您谈谈这20多年来穆旦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生态变化。
易彬:穆旦属于被埋没而又被重新发现的诗人,穆旦生前身后的起伏遭遇,在不少写作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这类现象可谓文化语境不断蜕变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和纵深发展的重要表征。在1990年代中期,穆旦被推为新诗第一人,看似突兀,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现代性为主导的现代文学研究语境来看,实际也可说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发展结果,是现代性思维的一次夸张的展现。在引发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议之后,相关研究工作朝着更为学理化方向持续推进,随着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对于古典的再发现、对于文学场域各类因素的重勘、对于各类写作和文本的辨析,现当代文学研究视域更为开阔,文学经典化的格局渐趋稳定,穆旦已被公认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有必要提及的是,随着近年来数据库建设日益勃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对于文献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穆旦相关的文献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一项。这个风格卓著的“中国新诗人”的生命形态与丰富的历史内涵,已经能够得到更翔实的文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