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与台静农
编者按:日前,文史作家张守涛出版新作《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中国现代英俊》(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该作是一本梳理鲁迅先生人际交往,研究鲁迅对当代文坛和文化人影响的通俗著作。作者从知识分子人生和作品文本出发,结合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史料,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书写了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尤重鲁迅对其影响。经作者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本次发布的是第三章《“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与台静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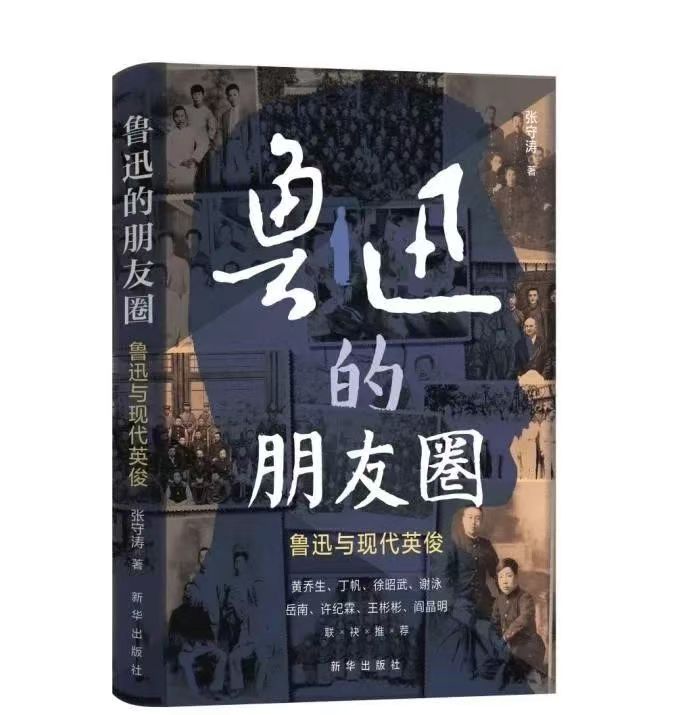
《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中国现代英俊》,张守涛 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
“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甘当“梯子”对青年寄予厚望,对众多青年作家热心培养尽力指导。中国众多现代作家与鲁迅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深受鲁迅影响,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等未名社成员就是其代表。
一、“台君为人极好”
台静农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他与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皆为小学同学。他虽然幼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但后来阅读严复的西方译作而萌发先进思想,中学时与同学合办《新淮潮》杂志以相应五四运动。1922年,台静农成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旁听生,旁听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对鲁迅有了初步认识。1925年4月25日夜,台静农在张目寒陪同下第一次拜访鲁迅,鲁迅当天日记纪录道: “夜目寒、静农来,即以钦文小说各一本赠之。”[1]
1925年,在鲁迅的提议、支持下,鲁迅与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曹靖华发起成立未名社,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为主,使得这五位文学青年正式走上文坛。其中,鲁迅与台静农交往非常密切。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鲁迅甚至曾在致台静农信中“吐槽”家庭负担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2]在鲁迅任教厦门大学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台静农单独或与友人一起拜访鲁迅多达29 次。
鲁迅对台静农极为欣赏,台静农的第一篇小说《懊悔》即由鲁迅审阅后交给《语丝》周刊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也由鲁迅审定改名为《地之子》出版,鲁迅称赞为“优秀之作”[3]。在选编《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鲁迅选了台静农的《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四篇小说,与鲁迅自己的入选作品数目相等同为作品最多的作者,可见他对台静农的赞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更是高度赞扬台静农作品道:“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4]
鲁迅对台静农的人品也极为肯定,说“台君为人极好”[5]。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时,曾多次与台静农会面,其中一次到了深夜。鲁迅多次赠书及《北平笺谱》等与台静农,还在1932年元旦手书《二十二年元旦》赠台静农:“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申年元旦开笔大吉并祝静农兄无咎。迅顿首。”1934年鲁迅“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6],又赠送台静农一首《报载患脑炎戏作》:“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祥,无如臣脑故如冰”。临终前,鲁迅还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寄赠给台静农。除参与集资刊印此书的人外,鲁迅只给台静农和许寿裳两人赠过此书,可见他对台静农的感情。
“投桃报李”,台静农对鲁迅也极为感恩。1926年,台静农将1923至1926年四年间报刊评价鲁迅的文章汇编成集,取名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出版。这是第一本有关鲁迅及其著作的评论集,书前有《鲁迅自叙传略》,书后附有许广平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应鲁迅的建议,台静农将国外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论删掉,而加了一篇陈源致徐志摩的信。台静农选编此书目的是“只想爱读鲁迅先生作品的人籍此可以一时得到许多议论和记载,和自己的意思相参照,或许更有意味些”[7],主要原因是他爱鲁迅那种被陈源骂为“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8]
1927年刘半农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便由台静农转达,鲁迅也是通过回信台静农拒绝。虽然鲁迅拒绝了提名,但此事可见台静农对鲁迅的尊重及两人关系的亲密。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视母亲,并应邀在北平作了五次公开演讲,时任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兼校长秘书的台静农全程陪同。台静农还陪同鲁迅到范文澜家,邀请鲁迅到自己家,以及会见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回到上海后,鲁迅特意给台静农写信感谢道:“廿八日破费了你整天的时光和力气,甚感甚歉。”[9]鲁迅还给许广平写信道:“我到此后……台静农、霁野……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都是看不到的。”[10]台静农还多次为鲁迅代买汉画像石拓片,如《鲁迅日记》中记载,1934年7月1日“得静农所寄汉画像等拓片十种”[11]。“在《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从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台静农通过友人替鲁迅拓印了南阳汉画像共231幅。”[12]
二、“谈到鲁迅时特别有感情”
1936年鲁迅去世后,正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台静农悲痛万分,他立即给许广平发了唁电,还寄去100大洋作为奠仪费用。唁电中写道:“周师母鉴:顷见报载,中央社电豫师去世,惊骇万分,然关于师之起居,向多谣言,颇以为疑。但记载甚详,似果真不讳,山颓木坏,世界失此导师,不仅师母之恸也……生静农上”。1936年11月1日,山东大学文学社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台静农在会上介绍了鲁迅生平,沉痛悼念鲁迅。据徐中玉回忆:“鲁迅逝世那年台静农老师正在山大,我们举办的追悼会上他带病勉强参加了,伤痛之意极深。”
为纪念鲁迅,台静农还手抄鲁迅诗作39首分送友人,如将其中一个长卷送给了舒芜。“台静农‘困居危城’钞写‘鲁迅师遗诗’长卷是寻找精神寄托;而将这长卷赠送给‘不知何年’才能相见的好友舒芜,显然是希望用这一份珍贵的礼物来维系彼此的友谊,互相勉励,永远以鲁迅为楷模,永远奋进。”[13]台静农还精工装裱了鲁迅给他的书信,后经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有43封。后来,台静农将保存的鲁迅信件和文稿几乎全部交给许广平,只珍藏了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稿即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以及保存了鲁迅送给台静农的《二十二年元旦》《报载患脑炎戏作》等诗幅。后来,台静农和好友魏建功、李霁野、舒芜等人相聚,也经常谈及鲁迅,“静农先生谈到鲁迅时特别有感情”[14]。
1938年10月19日,重庆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台静农在题为《鲁迅先生的一生》的演讲中说:“我们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得学习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抗战时期,他还著有回忆鲁迅的《鲁迅先生的一生》《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等文章。在任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时,台静农还曾讲授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1946年台静农到台湾大学任教,本欲“歇脚”(台静农将自己台湾居所命名为“歇脚庵”)的他阴差阳错从此定居在台北,成为台大中文系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奠定了该系自由活泼兼容并包的学风,被台湾学人誉为“新文学的燃灯人”。因为当时鲁迅名字在台湾极为敏感,鲁迅至友、台静农同事许寿裳便因在台湾宣传鲁迅而不明不白地被害,台静农从此不再公开谈论鲁迅纪念鲁迅,乃至后来被李敖批评为“愧对鲁迅”。对此,他曾对林辰解释道:“承续为豫师写回忆录,虽有此意,然苦于生事,所忆复不全,故终未能动笔也。”
但也许,台静农只是将对鲁迅的怀念深藏于心。据陈昌明教授的《温州街》一文记载,1989年台静农搬家时,台静农亲自将一尊鲁迅塑像抱在怀中搬到新居,“我看到台静农老师缓缓起身以双手抱着鲁迅的陶瓷塑像,步履庄重而沉稳像《仪礼》中的祀典,一步一步走向二十五号的宿舍。那是一种极慎重的态度,一种精神仪式是不能假手他人的,当我回家后还感受到这股神圣而隆重的气氛。”据梅家玲文章《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考证,这座塑像是来自香港的大陆走私货品,1980年由李昂买下送给台静农,台静农一直将其珍藏在里屋。“这尊鲁迅塑像鲜为人见,却俨然成为台老师多年来始终心念鲁迅,对其敬之重之的见证。它穿越无情的政治风暴,为那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有情的印记。”[15]
另据施淑教授回忆,台静农1990年弥留之际,他要读鲁迅作品,还特别想看《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其中有《鲁迅和台静农》一章。“最是难忘少年狂”,台静农晚年写了《酒旗风暖少年狂》等怀旧散文,虽然没有直接怀念鲁迅,但他对青年时期与鲁迅等人的交往终究难以忘怀。如施淑教授在《踪迹》一文中所写:“他一生悬念,至死方休的就是鲁迅与北京未名社的那些往事了。”
三、“皆师法鲁迅”
如上所述,鲁迅对台静农非常欣赏尽力培养,使得台静农成为了著名作家、大学教授。鲁迅对台静农的具体影响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台静农创作的影响。台静农本不愿意写小说,是鲁迅主编《莽原》杂志的索稿对台静农起到了直接的催稿作用,如台静农在《地之子》后记里所写:“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为了《莽原半月刊》按期的催逼,我仍旧继续写下去。”“晚年,台静农曾接受陈漱渝的访问,‘他承认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他原来爱写诗,参加过‘明天社’,后来读了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又读了一些莫泊桑、契诃夫的作品,才把创作重点转向小说。’(陈漱渝《丹心白发一老翁》)”[16]鲁迅曾直接和台静农说道:“直至我读了你的小说,我才发现了你的小说创作才能,你应当多写小说,多写乡土小说。”“鲁迅以自己的创作体验指导台静农应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开掘,多读外国小说开阔视野。台静农便埋头苦读当时能找到的外国小说集,而使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的还是鲁迅翻译的岛武郎写的《与幼小者》。”[17]此外,鲁迅对台静农作品的高度赞扬,无疑也会极大地鼓励台静农的创作。台静农的小说主要创作于认识鲁迅之后,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由未名社出版,台静农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影响。
二是对台静农作品风格的影响。台静农早期小说内容沉重风格沉郁极具“鲁迅风”,被认为“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尤其是《地之子》颇得鲁迅乡土小说风韵。香港文学家刘以鬯甚至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后来台静农虽然不再创作小说,但如学者孙郁所言:“先生崇尚汉魏文风,文字与书画,流着逆俗气息,一看便有狂放色彩。一个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人,由创作走向书斋,不仅无丝毫老态,且气韵生动,于旧学之中散出宏阔的气象,便也证明了其不失鲁迅遗风。”[18]甚至学者王德威认为台静农的历史著作《晚明讲史》是学习了鲁迅的《故事新编》,“他的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写作《故事新编》的鲁迅。”[19]《晚明讲史》也像《故事新编》一样借故讽今表达作者心声,充满洞观世情的清冷智慧和悲悯众生的温暖情怀,叙事方式也都比较“油滑”。
三是对台静农人生的影响。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早年也是“战士”,他除了发表战斗“檄文”外,还曾任“北平左联”常委,曾广泛接触左翼人士,因此三度入狱。抗战胜利后,为抗议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被解散,台静农还主动辞职,并为学生题诗道:“观人观其败,观玉观其碎。玉碎必有声,人败必有气。”可“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定居台湾后,被监视的台静农从“战士”转身为“醉心”于书法与古典文学的“隐士”。这正是鲁迅一直所痛惜的,这或许也是台静农不愿再公开提及鲁迅的原因之一吧,他内心或许的确感到“愧对鲁迅”。但鲁迅也曾劝台静农潜心治学,如他在1933年写信给台静农说:“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即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20]鲁迅与台静农后来的通信也大多关于学问,即台静农后来的潜心治学也未尝不是鲁迅的希望。
四、鲁迅与未名社
除了台静农,鲁迅对未名社及其其他成员也都很关心。鲁迅出资一大半发起成立未名社,在北大上完课后经常来到未名社,关心编辑、校改、印刷、经费等事务,南下后也依然非常支持未名社。李霁野在文章《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据李霁野统计,在《鲁迅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载多达七百多条;在现存鲁迅书信中,致未名社成员的信函多达212封。到1932年未名社解体时,未名社先后出版发行《莽原》周刊48期、《未名》半月刊24期,出版发行书籍33部,其中包括鲁迅很多作品,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有重大贡献。鲁迅曾肯定未名社译作道:“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观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水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21]
其中,韦素园因为身体不好不便外出而具体操办未名社社务,故被称为未名社的“守寨人”。鲁迅曾推荐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编辑,在南下后让韦素园接手《莽原》杂志的编务,与韦素园平时交往也很多,《鲁迅日记》中提及他的有130多处。后来韦素园病情加重,鲁迅非常关心韦素园的健康状况,多次写信询问病情,如曾细心叮嘱:“兄咳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22]1929年,鲁迅回北京时三次抽空来未名社,还专门去医院看望韦素园,他后来纪录道:“素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来许多闲天……接着又感到他终将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23]1932年8月1日,年仅30岁的韦素园去世,鲁迅亲自为韦素园书写了碑文:“君以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934年7月16日,鲁迅又写了文章《忆韦素园君》纪念韦素园,高度肯定了韦素园的贡献:“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24]
鲁迅与未名社另一骨干李霁野关系也很密切。李霁野早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便从《新青年》杂志上看过鲁迅的文章,到北京读书后更是仰慕鲁迅的风采,“鲁迅先生的文章表现着鲜明的人格,读时使人觉得亲切得很,仿佛作者不仅是一个可以教导自己的良师,也可以成为推诚相见的益友”[25]。后来,李霁野在张目寒的引荐下见到鲁迅,其翻译受到鲁迅很大鼓励,并在鲁迅资助下考入燕京大学读书。之后,他也与鲁迅经常会面谈话、通信,鲁迅致李霁野信有53封,“每次和先生的谈话,我都觉得爽快,仿佛给清晨的凉风吹拂来一样。”[26]鲁迅去世后,李霁野陆续写了一些纪念鲁迅的文章,并于1956年出版了《回忆鲁迅先生》一书,记述了鲁迅对他等文学青年的培养情况,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谦虚、朴素、慷慨、忠贞,和新兴阶级的优良品质——英勇、刚毅、乐观、坚定——融合成鲁迅先生的独特风度。”[27]李霁野还保存了鲁迅《朝花夕拾》的手稿,台静农保存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上最后一则题跋也出自李霁野之手,他题道:“毛锥粒粒散珠玑,奠定文坛万载基。墨泽犹新音容杳,怆然把卷徒唏嘘。”1984年4月6日,天津市文联和作协召开座谈会庆祝李霁野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李霁野在《答谢词》中回忆道:“在我的青年初期,我有幸亲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教诲,我的文学活动是在先生的领导下开始的,若是取得些微的成绩,那同先生的教导和鼓励分不开。”晚年,李霁野还倡导在天津设立了鲁迅文学奖,写了《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被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称之为“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
鲁迅作品《阿Q正传》由曹靖华介绍给俄国人王希礼翻译到俄国,这是鲁迅作品传入苏俄的开始。由此,鲁迅和曹靖华密切交往,曹靖华成为与鲁迅关系最亲密的人之一。据《鲁迅日记》记载,两人书信来往多达292封,曹靖华是鲁迅通信仅次于许广平的人。在这些信中,两人互相关心对方的家人家事、身体状况,甚至相互代寄药物和食品,鲁迅还将自己的各种心事、难事“交代”给曹靖华,可见鲁迅将曹靖华视为自己至交。鲁迅约曹靖华翻译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名著《铁流》,亲自校订此译作并写后记,又自掏一千大洋出版此书。他不断鼓励曹靖华积极翻译苏联文学,使得曹靖华后来成为我国翻译介绍俄苏文学的大家。鲁迅还为曹靖华父亲书写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这是鲁迅除了给韦素园之外写的唯一碑文。鲁迅临终前三天写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高度评价曹靖华的为人和译著,说为曹靖华写序“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还说“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一个,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28]第二天,鲁迅又给曹靖华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这是鲁迅生平的最后一封信。鲁迅去世后,曹靖华收到鲁迅给他的信时悲痛失声,此后也一直悼念、感激鲁迅。他在中法大学追悼会讲演中哀悼“鲁迅死得太早”,称鲁迅的死“失掉了我们的灯塔”,并写了《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鲁迅》等文章。晚年,年近九旬的曹靖华,还坐在鲁迅故居的书房中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对于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鲁迅本来也很关心。在鲁迅鼓励下,韦丛芜创作了爱情长诗《君山》。鲁迅读后很赞赏,特请画家林风眠为此诗稿设计封面,又请版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十幅。受此鼓舞,韦丛芜又创作了小说《校长》,鲁迅则将此小说推荐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但后来主持未名社社务的韦丛芜生活腐化,和未名社其他成员产生矛盾,导致未名社解体。鲁迅也因此声明退出未名社,“韦丛芜以后进一步堕落,鲁迅先生在书信和谈话中表示很深的惋惜,并处处可以看出他对韦素园的情谊。”[29]后来,韦丛芜著有《合作同盟》,“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并送此书请教鲁迅。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对此说:“立人(韦丛芜)先生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30]几十年后,韦丛芜从《鲁迅全集》中看到鲁迅的这封信而感慨道:“鲁迅先生寥寥数语,说得多么中肯,多么令人感动!”他为此写有诗歌《忆鲁迅先生》:“五十年来一觉醒,先生有怨我心惊!”
五、“为青年开路”
对于和未名社合办《莽原》的狂飙社,鲁迅原本也非常关心尽力指导。狂飙社领袖高长虹当时平均每月到鲁迅家六次以上,两年时间内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对于高长虹个人,鲁迅也特别关照,破例给予高长虹编辑费用。鲁迅还选编高长虹的散文和诗集为《心的探险》,亲自设计封面,编入《乌合丛书》,为此都累得吐了血。他还和高长虹一起选编自己老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并请高长虹为集子写序。这是鲁迅唯一一次请青年作家作序,可见鲁迅对高长虹的器重。即使后来鲁迅与高长虹以及狂飙社失和,鲁迅依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高度评价了高长虹和狂飙社:“1925年10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31]原本年轻气盛的高长虹后来在1940年8月发表的长文《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感慨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后,有过一番争论,不过以后我们都把它忘了。1930年以后,他的光明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他认为鲁迅是位天才作家,承认鲁迅“为青年开路”,赞扬鲁迅的作品鉴赏力。
鲁迅对其他很多文学青年也给予了力所能及地指导、帮助,与众多青年作家关系密切。如鲁迅与自己学生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上密切合作,选编老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写下《悼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悼念柔石、白莽等“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对青年期望很殷,培养很勤,但是他既不虚夸,也不姑息。他对青年的要求很严格,无论在言行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32]除了本文所述外,受过鲁迅培养、直接影响的青年作家至少还有冯雪峰、丁玲、胡风、巴金、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萧军、萧红、黎烈文、唐弢、萧乾等人,鲁迅关心、帮助过的其他青年人就更多了。
鲁迅原来相信进化论,“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33],而原本对青年寄予厚望。因此,他虽然认为青年不必“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34],但他自己很乐意当青年“导师”,非常关心、培养文学青年,指导了狂飙社、未名社、朝花社、沉钟社等文学社团,在北大、女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与学生也密切交往。
但狂飙社领袖高长虹对鲁迅的反戈一击,尤其是“四一二”事变带给鲁迅的冲击,以及后来创作社“小将”对鲁迅的攻击,让鲁迅对青年逐渐失望。他认为“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35],“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36]
所以,后来鲁迅对一般青年不太密切交往,只对胡风、冯雪峰、黄源、巴金、萧军、萧红等信任的文学青年交往多些。但鲁迅“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37],也还是尽可能地帮助青年,甘做“梯子”。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曾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38]
“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原本对文学青年充满关爱竭力培养寄予厚望,后来虽然对青年逐渐失望,认为仅有青年的进化是不够的更重要地是社会的进化,但他依然甘做“梯子”尽力帮助文学青年。“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鲁迅的“润物无声”,让台静农、曹靖华、胡风、萧军、萧红、巴金等大量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像一声声惊雷一样震惊神州大地。这正如鲁迅自己的诗所言:“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注释:
[1] 鲁迅: 《日记·十四〔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2页。
[2] 鲁迅: 《书信·320605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3] 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4]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263 页。
[5] 鲁迅: 《书信·331219 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520页。
[6] 鲁迅:《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三月》,《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7]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页。
[8] 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页。
[9] 鲁迅: 《书信·321130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10] 鲁迅: 《书信·321120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343页。
[11] 鲁迅: 《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七月》,《鲁迅全集》第 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
[12] 商金林:《生而不有 为而不持———台静农对鲁迅的敬慕和追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3] 商金林:《生而不有 为而不持———台静农对鲁迅的敬慕和追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4] 舒芜:《忆台静农先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15] 梅家玲:《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16] 汪修荣:《不尽往事尽风流:民国先生风华》,团结出版社,2024年,第38页。
[17] 陶方宣、桂严:《鲁迅的圈子》,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8] 孙郁:《鲁迅遗风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
[19] 王德威:《亡明作为隐喻——台静农的<亡明讲史>》,《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
[20] 鲁迅: 《书信·331227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533页。
[21]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 页。
[22] 鲁迅: 《书信·270108 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23]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24] 鲁迅: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 页。
[25]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页。
[26]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9页。
[27]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55页。
[28] 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29]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2页。
[30] 鲁迅: 《书信·330628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页。
[31]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258页。
[32]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22、23页。
[33] 鲁迅:《序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4] 鲁迅:《导师》,《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35] 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
[36] 鲁迅:《序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7] 鲁迅:《序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8] 鲁迅: 《书信·300327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