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沈从文致陈琼芝书信考释 ——关于“鲁编室”工作,兼及作家的复杂心态
2023年,在中国嘉德拍卖“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中,发现有1977年沈从文写给陈琼芝的一封书信。在《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全集·补遗卷》等著述编纂以及相关论著研究中,都未曾见到这封信或提及这件事,初步判断应为佚信。现呈示如下:
琼芝同志,您给我的信已转到,深谢厚意。我名分上还是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事实上因年老体力衰退,已多年不去馆中:住处原在历博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宿舍,因去年地震,家中人不放心,转住小羊宜宾胡同五号(在东总布胡同附近,原人民文学编辑处),只间或回东堂子取取书,所以尊信是十月里才见到,迟迟作覆,实深抱歉,望能原谅。有关鲁迅先生的作品,我缺少应有知识。特别是他的杂文,针对性极强,不是当事人,不大懂内容,十分显明。所以去年传说注《野草》时,有人问文学所,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说“不懂”。据个人私见,鲁迅博物馆有不少专家,遇疑难处向他们提出,或可迎刃而解。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处理我早期作品有关。因为我算得是第一期“职业作家”,每月依赖稿费过日子,在北京时,既从不参加过什么“座谈”或“聚餐”活动,到上海后情形相同。(闻、梁、潘、罗、等人一部分后来还在学校同事多年,生活上却无过从。)每期涉及政治论文,我就不看,也看不懂。我的主要目标,便是在短篇上求进展,创纪录,才有出路。依稀还记得在某一年“编委”还有我一个名字,只是事后相告,内情不知,也从不过问。也频、丁玲,算得是熟人了,也只限于一九二四—一九三〇一段时间中的一部分生活和工作,此外即近于无知。您一时如还不即离开,欢迎您们来谈谈天,随便谈谈家乡新旧不同处,也许比谈文学更有意思。解放后,我已真正改业,在午门楼上坛坛罐罐间,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主要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对于如何“古为今用”,充满兴趣。越学下去,越感觉主席提出的四个字寓意深远,所以工作努力重点,就是求落实这个伟大指示,来为以千万计的生产第一线的纺织、陶瓷、染术、牙……工人服务、打杂、作后勤,虽劳不怨。至于过去的文学创作,还在学习阶段,并未毕业,就在社会变动下告了结束。所有习作早被书店全部毁销了,曾得到正式[1]通知说“已过时”,代为帮忙付之一炬!正如古人说的“破甑不顾”,业已摔坏的陶甑,实在值不得回顾,更不想提它,或因人提提即“自我陶醉”。历史只前进,不会后退。近些年来虽发现新改的业务,也作不了什么,也许还得重新安排考虑,把有限余生,转用到更切实些又为新社会所需要方面去。但年纪已过了七十五岁,即或情绪上在某一时还不缺少童心幻念,事实上,是不大可能作得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出色工作了。“上湘西人”有它的性格上的局限,有的简直近于悲剧性弱点,在某些方面,像是能“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另一方面,就十分不中用,显得异常脆弱,处处吃瘪。吃不开。对家乡过去存在的人和事,我似乎还能看得出问题,但处理本人时,就一例沉陷到“习惯”泥淖中,无从由情绪束缚中摆脱,作出对客观现实灵活的适应,在找不出更合适名辞以前,就说是“夙命性的悲剧性格”,也说得差不离。六十年以下受过近代教育的同乡,大致是不至于如此的,日子会过得幸福得多!并候诸位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十七
住处有传呼电话,为555964来时先能通个电话免得失迎。
公共汽车乘九路应在过了火车站的一站下车,不多远可到。
信封:虎坊路十五号 鲁编室请转陈琼芝同志启
小羊宜宾五号 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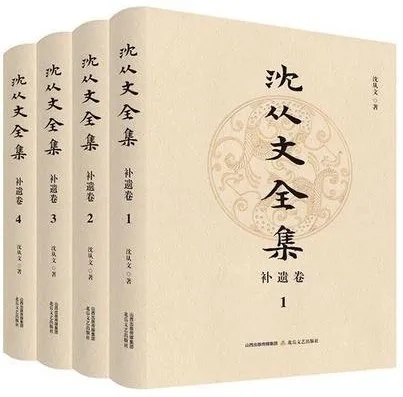
《沈从文全集·补遗卷》,沈从文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
一、陈琼芝寄信时间考证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小羊宜宾胡同住处山墙部分倒塌”[2],7月30日,沈从文寄信给儿子沈虎雏说:“小羊宜宾灾难大些,妈妈住屋山墙下坍,大几方砖瓦正好压在大的新翻修小间上,顶住了。若顶不住,也许几人均完事了。”“东堂子房子完好,只是两边人家大墙倒了,左边堵塞了出入道,右边把王家新翻新作新的X房子砸坏了,大致只有重翻一次不可。”[3]“因担心他长期住抗震棚健康受损,亲友们劝他和张兆和到苏州暂避。”[4]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苏州。因此,从这封信中沈从文叙述的“因去年地震,家中人不放心,转住小羊宜宾胡同五号(在东总布胡同附近,原人民文学编辑处)。只间或回东堂子取取书”来看,陈琼芝应是将信寄送到沈从文原住所东堂子,而沈从文偶尔回去取书顺便查看信件,才看到这封信。通过信中所言“所以尊信是十月里才见到,迟迟作覆,实深抱歉,望能原谅”,以及信封上沈从文的落款处地址“小羊宜宾五号”,可以初步还原当时的场景,即1977年10月,沈从文回东堂子,看到信后将信带回小羊宜宾胡同的住所,又隔了几天才给陈琼芝回信。因此,陈琼芝信件的送达时间是在9月乃至更早。由此推测,陈琼芝寄出信件的时间应在1976年7月地震后至1977年9月之间。又根据信中的“十月里才见到”这句话,推测陈琼芝寄信时间应为沈从文写信的同年。更进一步,沈从文在信中提到,“去年传说注《野草》时”,当时,《野草》的“征求意见本”即为注释本,其出版时间大概在“一九七七年一月”[5],考虑到这项注释工作完成到出版还有一段时间,因此,“注《野草》”的时间应为1976年,与沈从文所言“去年”对应下来,写信的“今年”为1977年。
1974年冬,沈从文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通过阅读现存1977年沈从文书信,陈琼芝寄信时间得到进一步确认。1977年4月4日,沈从文寄送给汪曾祺的信中提到,“这星期中任何一天都可以在东堂子相候。(以上午九时到十一点半,下午二时半到五点半为合适。来时先给一电话好些,免得答应别人或另有约会。)材料是在东堂子,可以来东堂子谈谈方便”[6]。随后,5月10日寄送王㐨[7]的信中提到,“约定十三号星期五下三时”找当时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到古绸缎织绣研究者陈娟娟“来东堂子谈谈”[8]。5月16日《复姚雪垠》中提到,“弟即可在指定时间内去东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9]。可见,在1977年5月之前,沈从文时常在东堂子,寄送的信件也能及时查收,即使沈从文曾对徐维[10]说过,“年前南行,住下半年才回来,回来后,长在小病中,手和眼都不大得用,各方面友好来信多不作复,十分抱歉”[11],也不存在他在5月或者更早之前已看到陈琼芝来信却不回复这种可能。1977年6月21日,沈从文寄送给儿子、儿媳的信中写道:“我和妈妈大在小羊宜宾住下,已成习惯,经常已不过东堂子,工作也只在这边继续进行。”[12]因此,根据现有书信推知陈琼芝的寄信时间应在1977年5月至9月之间。限于目前能够查阅到的陈琼芝书信较少,无法确定更为准确的具体时间。
二、沈从文、陈琼芝通信内容及《二心集》相关修改细节
陈琼芝在延边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受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简称“鲁编室”,下同)“主持《二心集》(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工作”[13]。1976年,鲁迅《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出版,俗称“红皮本”,其中“本书注释者”为“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浆厂工人理论组、延边大学中文系”[14],将“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浆厂工人理论组”置于“延边大学中文系”之前,主要“以显示工农兵管上层建筑的权威”[15]。除此之外,“征求意见本”的“编印说明”[16]指出: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视工作进行情况,陆续将各书注释初稿先行排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恳切希望同志们就本书各篇的题解和注释的内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据以修改。修改意见请径寄我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十月[17]
当时,许多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参与到对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讨论中。例如,叶圣陶1976年11月8日的日记记载,“昨收到鲁迅著作编辑室寄来《而已集》之注释样本,当夜即开始看之”[18]。同年11月13日记载,“上午有鲁迅著作编辑室之同志倪墨炎偕同《且介亭杂文》注释组之五位同志来看余”[19]。12月5日,“《而已集》注释以今日上午看完,即寄与鲁迅著作编辑室”[20]。12月15日,“北京师大有一个组,担任注释鲁迅之《集外集》,尚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先以油印本交来嘱余看之”[21]。12月23日,“今日将《集外集》之注释看完,即写信与注释组,请派人来取去”[22]。
依照上述材料钩沉和佚信内容,同时联系到鲁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指出:“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23]陈琼芝在信中很可能询问沈从文对杂文结集《二心集》注释工作的建议,诸如介绍其对鲁迅杂文的理解,以及新月社的相关情况等等,还可能涉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交往细节。然则,需要注意到,沈从文的这封回信并没有提到陈琼芝或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寄送《二心集》等书的文字内容,在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信中也未曾与亲朋谈起过修改或者阅读注释等信息。或许由于地震留下的安全隐患,沈从文连陈琼芝的信都是很晚才看到,《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可能没有收到,抑或陈琼芝并未寄书。更进一步说,陈琼芝是否同时寄送《二心集》已不重要。
如果陈琼芝的信于1976年10月(即《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出版时间)之前寄送沈从文,那么在信中询问“有关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杂文,以及“有关新月社派内情”等问题,则是在编印《二心集》“征求意见本”期间所做的相关调查。朱正先生回忆说:“在延大中文系,承担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琼芝和她的学生章新民。动手之前,他们先到北京等地作了些调查和访问,访问了冯雪峰、冯乃超等好些相关人物,还把收集到的材料编印了一本《二心集研究资料》。”[24]根据相关材料证实,朱正所说的《二心集研究资料》实为《鲁迅〈二心集〉资料选编》。这本资料选编的“后记”中提到,“我们从七四年起先后参加这项工作,曾于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化费了不少功夫和气力从事资料搜集工作”,“参加本书编选的是通辽师院中文系王保林、蒋镇,通辽市教育局罗炯光,延边大学中文系陈琼芝、章新民等五位同志。吉林师大中文系郭育新等同志曾参加过选目讨论”。[25]
通过对比《二心集》“征求意见本”(俗称“红皮本”)和《二心集》1980年版(俗称“绿皮本”)的注释,不难发现与佚信内容相关的注释受到修改。“红皮本”《序言》的“注释12”为“新月社”,陈琼芝等人在编著此处时,指出“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梁实秋、徐志摩等”[26]。而“绿皮本”则在“注释10”中将这段文字修改为“新月社”是“由胡适、陈源等人组成的文学和政治团体”[27],并在后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注释2”《新月》月刊团体(即新月社)中补充道,“新月社”是“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28]。除运用词汇更加严谨以外,仍要注意“绿皮本”对“新月社”主要成员的排序问题,修改后的排序将徐志摩置于陈源(即陈西滢)之前,又新增了罗隆基。联系到沈从文在信中提到“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处理我早期作品有关”可知,“红皮本”出版后,陈琼芝等人与诸如沈从文等相关人员通信、采访,再进一步查阅资料,“送请上级领导审定”[29],于是在“绿皮本”中对“新月派”主要成员的排序进行了修订。而沈从文信中所言“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则是《二心集》中沈从文相关注释得到更正的关键证据。1976年版《“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注释11”提到沈从文、凌叔华“都是‘新月派’成员”[30],1980年版则改为“沈从文、凌叔华,小说家”[31]。陈琼芝等人在保持公正、客观态度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沈从文的感受,联系到彼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对沈从文的积极评价,不仅将沈从文和“新月派”区分开来,而且还认可了其小说家的身份。
有研究者考察195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注释,发现没有沈从文的注释词条,“只在其他注释中出现了两次名字”[32],一次是在第五卷的注释中提到“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33],一次是在第六卷的注释中指出“炯之即当时的小说家沈从文”[34]。转而,到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在第四卷的注释中标识“沈从文 湖南凤凰人,作家”[35],这也是“《鲁迅全集》历史上第一次为沈从文出注,承认沈从文的‘作家’身份”[36]。对照“1976年下半年,鲁迅研究室部分同志分赴全国各地,采访鲁迅生前好友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搜集和抢救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资料”[37],由此或许可以进一步补充类似注释的修改细节。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王仰晨曾在《文学编辑纪事》中提到,1976年5月,注释体例(草案)修订后的条文内容要求:“注释人物时,应按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本文中涉及的程度,有选择地注明其生卒年代、别名、朝代、籍贯(外国人国籍)、基本政治倾向、身份、简历、主要著作等,一般应以本文所涉及的时期、与本文有关的情况为重点,如其后有重要变化时,也应略作说明;并不重要、在作品中偶尔出现的人物,可不注。”[38]这一做法,在由“红皮本”到“绿皮本”的修订过程中得到沿用。1977年12月,林默涵、秦牧等人与“鲁编室”“就注释、整理与出版工作中有关方针性的问题以及注释体例等重新进行了反复的讨论,进一步明确……注释力求做到简明易懂,不发议论,避免繁琐;特别要注意思想性、科学性、准确性和严肃性、稳定性。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社团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做到公正、客观,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39]。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注释词条极其简单,做到了“简明易懂”,但也意味着在“本文中涉及的程度”不太重要。然而陈琼芝等人却依然严谨地修正诸如此处等微小的语词,为后续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问世而尽职尽责。
关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迅著作的编写,由“红皮本”“绿皮本”到最终成型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李何林与胡乔木、林默涵等人围绕“题解”是否保留展开争论后[40],1981年版《鲁迅全集》保留一部分必要“题解”,其他均被删除,最重要原因便是“鲁迅杂文之谜”[41]。沈从文在“佚信”中也说,不大懂鲁迅杂文的内容,“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说‘不懂’”。1979年沈从文也表达,“涉及鲁迅文章,我毫无研究,少发言权,实在无可奉告”,“鲁迅先生既有主席指定为五四以来唯一硬骨头作家……”[42]除谨言慎行的考虑外,的确也如学者所论:“鲁迅的杂文之谜,关乎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的评价,而且牵连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理解。”[43]
三、由“佚信”而进一步理解沈从文的心态
沈从文在佚信中提到,“有关鲁迅先生的作品,我缺少应有知识”,“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处理我早期作品有关”,“也频、丁玲,算得是熟人了,也只限于一九二四—一九三〇一段时间中的一部分生活和工作,此外即近于无知”。从“佚信”中谨小慎微的言辞,可看出沈从文“夙命性的悲剧性格”,及其对于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心态。
其一,佚信直观展现出沈从文对鲁迅作品的复杂态度。1940年9月16日,《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沈从文的《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指出鲁迅的作品“近于恨恨的咒诅”,“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作品的出发点”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44],“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说明的倾向即“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45]。而在这封佚信中,沈从文似乎又不经意地说道:“去年传说注《野草》时,有人问文学所,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说‘不懂’。”由此可见,沈从文即使从事着历史博物馆的专业研究,却仍然关注着与鲁迅切实相关的《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
其二,佚信进一步表达了沈从文对学界认定其是新月社派成员的否认态度。一方面,沈从文认为,将自己归为“新月派”是一种“侮辱”。1980年7月,沈从文在给邵燕祥的信中提到,“过去人骂我是‘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回到北京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还加上个‘小京派头头’,到云南后又是‘战国策派’,事实上什么却都不是。说是典型‘单干户’倒差不离”[46]。另一方面,沈从文虽然不认可自己是新月派成员,但却与新月派成员徐志摩等人相熟。其年谱记载,1926年10月3日,沈从文“出席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47],1928年“3月10日,由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月刊出版,沈从文成为这个刊物的经常撰稿人”[48],《沈从文全集》记录沈从文于1928年1月初到上海,“3月起在刚创刊的《新月》连载长篇童话体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此后他成为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月刊文学作品的经常撰稿人之一,也因此被批评者列为‘新月派’一员”[49]。佚信中也说:“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处理我早期作品有关”。1929年“6月起,为缓解经济困境,经徐志摩推荐,接洽去中国公学任教事。8月,胡适校长破格延聘他为国文系讲师,开设新文学和小说习作课程”[50]。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就徐志摩的作品发表看法称:“徐志摩作品给我们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莹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从作品上看徐志摩,人可年青多了”。[51]1949年后,沈从文在公开场合对徐志摩的评价较为严谨,例如他在与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的通信中说道:“大致是相熟友好,居多年事较长,社会地位不同于上海一般青年作家,彼此间忌讳又较多,追悼文章见于报刊的即较少。特别是关键性人物,关键性事件,对志摩先生之死,即有深刻悲痛,亦绝不会在一般性追悼文章有所表示。甚至于在客厅或聚会中,也竭力避开此问题不谈。但事实上则在志摩先生死后,收集整理遗文、遗信、日记等等事情时,在较熟习的廿来当事人中所引起的种种感情,比南方友好追悼文所表示的内容丰富得多,也切实具体而重要得多。就尊著看来,这部分问题,接触到的似不多,因此在年谱中这方面分量似乎也略感薄弱。弟因此在反复阅读时,随个人见闻记忆所及,略作补充引申……”[52]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志摩全集》,由沈从文作一小文,其又称徐志摩“为人心怀坦荡,毫无机心,一团火一样热的心,且特具感染力,影响到不少当时年纪较轻的朋友熟人,我就是其中之一”[53]。沈从文对《徐志摩年谱》《徐志摩全集》等著作的态度也与对鲁迅文章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1928年《新月》第一卷第八号《编者余话》中提到,“沈从文先生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共分四卷……沈先生的小说我们还有得读,因为他答应以后在本刊上每期都另写一篇短篇小说,这是我们可以预告的”[54]。这段话也显示出沈从文作为《新月》长期供稿人的身份。
其三,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之间的交往不只限于佚信中所说的“一九二四—一九三〇”。1925年,沈从文“因稿件在《京报•民众文艺》发表,结识编者胡也频,随后认识其女友丁玲”[55]。三人逐渐成为好友。1926年8月之后,“他们三人一同住在北大附近的汉园公寓里”[56],1929年“1月10日,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主编的《红黑》月刊问世”,“1月20日,《人间》月刊创刊。该月刊为人间书店委托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合作编辑”。[57]1931年1月,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互相拜访,随后“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被捕。他多方奔走营救,几次往返沪宁,并把丁玲及其幼子接来和九妹岳萌同住。2月7日胡也频牺牲后,他以武汉大学教师身份,掩护陪伴丁玲把烈士的遗孤送到湖南常德丁母处寄养。因4月才回到上海而失去武大教职”[58]。同年,“6月23日,丁玲致函沈从文,告诉自己办杂志的计划(即后来的左联刊物《北斗》),向沈从文约稿,并请沈从文代向冰心、凌叔华、陈衡哲等人约稿”[59]。丁玲被捕后,其出版《记丁玲》《记丁玲续集》,随后多年偶有信函和面交,期间还有些许误会[60]。据《丁玲年谱》记载,1978年7月18日,“根据中央1978年11号文件精神,老顶山公社党委通知丁玲摘去右派帽子”[61]。而几个月前,沈从文给杜运燮写信说:“不久前,有鲁迅研究室工作同志问及丁玲山西住处,我因记忆力不佳,且怕增加不必要麻烦,故于回信中告他们直问其女儿或较省事也。”[62]因此,1977年的这封佚信中说“此外即近于无知”,可能还是考虑到丁玲身份的问题,避免舆论影响的说辞。然而,1980年3月,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文章的发表“等于公开宣告了她与沈从文旧日友谊的破裂”[63],从此,沈从文经常在书信中谈到此事,称不予置评,令人唏嘘。
早在1948年,沈从文就预感到未来写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会面临转型,他对一位青年写作爱好者说:“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6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把笔搁下”,持续专注于文物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偶尔写作短篇。他总是在书信中提到诸如“我这卅年能维持下去,工作信心未丧失,体力情绪也比不少熟人还健康,主要也像是从总的方面学会了最妥的自处之道,即用个‘社会主义公民’的资格严格律己。凡事先想国家和公家,再考虑自己,所以永远不至于灰心丧气……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65]。其实,这也正呼应了佚信中的“我已真正改业”“学习为人民服务”等话语。
四、其他相关史实考
除了以上的史料钩沉,佚信中还有一些信息值得加以注意。
其一,“鲁迅博物馆有不少专家,遇疑难处向他们提出,或可迎刃而解”。“不少专家”是哪些人?1976年2月,鲁迅博物馆“新任馆长李何林到馆。鲁迅研究室从速筹建”,这一年鲁迅研究室“聘请曹靖华、杨霁云、唐弢、戈宝权、孙用、林辰、常惠、周海婴为研究室顾问”[66]。朱正曾言:“‘鲁编室’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属于出版系统;‘鲁迅博物馆’属于文物系统,他们之间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两个单位的人员有很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67]因此,“不少专家”应指鲁迅研究室聘请的顾问们。
其二, 1983年,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一段时间中,虽短期与胡也频夫妇同在当时萨坡赛路204号得租一房子,并无冯雪峰在内,始终还未见过冯雪峰。当时熟人有戴望舒、徐霞村(现代社方面的);徐志摩、丁西林、袁昌英、罗隆基、潘光旦、胡适之、高一涵、郑振铎(新月与中国公学的)……”[68]在与其他史料互证后笔者得出,佚信中“闻、梁、潘、罗”应是新月社成员,同时也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国立青岛大学(山大)或者西南联大的同事。[69]因此,这四人应为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
其三,沈从文在佚信中提道:“依稀还记得在某一年‘编委’还有我一个名字,只是事后相告,内情不知,也从不过问。”根据信件上下文分析,“某一年”应指的是“一九二四——一九三〇”上下的某个时段。不仅如此,沈从文担任“编委”的这本刊物亦与新月社成员“闻、梁、潘、罗”有密切关联。查询《新月》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出版)至第四卷第七期(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共41册(43期)[70]的编辑者名单,未发现沈从文,不过,在《新月》第三卷第二期(1930年4月10日)封底发现一则《诗刊预告》,预告提到,“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创作当然最注重,理论方面的文章也收,看看新诗究竟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已经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孙子潜,饶子离,胡适之,邵洵美,朱维基,方令孺,谢婉莹,方玮德,徐志摩,陈梦家,梁镇,沈从文,梁实秋诸位,盼望陆续更有多多相熟与不相熟的朋友们加入。第一期定于一九年内出版,新月书店代理发行”[71]。又根据《沈从文年谱》记录,1930年4月10日,“《新月》刊出《〈诗刊〉出版预告》,宣布有几个昔日《晨报副刊·诗镌》的旧友打算再出一个《诗刊》,沈从文参加了《诗刊》的编辑出版工作”[72]。相关学者研究中附有“沈从文主编参编的报刊一览”统计数据,其中记录“上海《诗刊》(1931年参编)”[73]。此外,从现存《诗刊》来看,沈从文并未撰文,这与佚信中所言“内情不知,也从不过问”相符。因此,佚信中提到“依稀还记得在某一年‘编委’还有我一个名字”中的“编委”,应是指《诗刊》的编委。
其四,有关“上湘西人”的含义。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称:“我住的‘酉西会馆’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钱建立,为便利入京应考进士举人或候补知县而准备的,照例附近还有不动产业可收取一定租金作为修补费用。会馆约大小二十个房间,除了经常住些上湘西十三县在京任职低级公务员外,总有一半房间空着,供初来考学校的同乡居住。”[74]联系到佚信中“‘上湘西人’有它的性格上的局限,有的简直近于悲剧性弱点……对家乡过去存在的人和事,我似乎还能看得出问题”,沈从文在信中自称“上湘西人”,平时又经常称自己为“乡下人”,如此称呼而已。
总体而言,这封佚信不仅反映了沈从文与作为“鲁编室”编辑的陈琼芝之间的交往事迹,而且有助于回归《鲁迅全集》的编辑现场,回到“鲁编室”工作的艰苦岁月和复杂选择。与此同时,信中透露出沈从文历经时代沉浮、人到晚年的悲凉心境。这种情绪既根植于沈从文个人的生命经验,也体现了一代老作家的时代特质;而其中对人生困境的感慨与对理想的执着,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能够触动不同时代读者的心弦。这封佚信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可以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也就具有了文本价值。史料研究除了从史料本身分析,把史料当作纯粹的材料之外,有时候其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学文本,显然具有双重的文学史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活研究”(项目编号:20BZW14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正式”原信作“正知”,疑为沈从文笔误。沈从文在书信中经常提到“开明书店正式通知”作品已过时。参见沈从文:《19800615 复孙康宜——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沈从文:《19810124 复马逢华》,《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2][4][47][48][56][57][59][63][72]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549页、42页、54页、42页、70页、113页、585页、86页。
[3] 沈从文:《19760730 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71页。
[5] 《编印说明》,鲁迅:《野草》(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 沈从文:《19770404 致汪曾祺》,《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7] “王㐨常写作王序。考古学家,当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见沈从文:《19770124 复王㐨》,《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8] 沈从文:《19770510 致王㐨》,《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9] 沈从文:《19770516 复姚雪垠》,《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10] “徐维,通信时在天津地毯研究所从事地毯研究与设计工作。”沈从文:《19770816 复徐维》,《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页。
[11] 沈从文:《19770816 复徐维》,《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页。
[12] 沈从文:《19770621 致沈虎雏、张之佩》,《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13] 《陈琼芝逝世》,《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
[14] 鲁迅:《二心集》(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5][24] 朱正:《陈琼芝和〈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
[16] 《编印说明》,鲁迅:《二心集》(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7] 不同“征求意见本”的“编印说明”大致内容相似,但出版日期不同,该处为《二心集》“编印说明”时间。
[18][19][20][21][22] 乐齐编:《叶圣陶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341页、348页、352页、354页。
[23][26] 鲁迅:《序言》,《二心集》(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6页。
[25] 延边大学中文系、通辽师院中文系合编:《后记》,《鲁迅〈二心集〉资料选编》,1979年版,第308页。
[27] 鲁迅:《序言》,《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V页。
[28][31]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20页。
[29][38][39] 王仰晨等:《文学编辑纪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21—22页、25—26页。
[30]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8页。
[32][36] 黄海飞:《两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变迁与作家的重评——以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为例》,《中国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3期。
[33]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3页。
[34]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8页。
[35]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
[37]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北京鲁迅博物馆四十年》(1956-1996),北京鲁迅博物馆1996年版,第53页。
[40] 参见黄海飞、邵小莉:《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过程中的“题解”风波》,《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
[41][43] 汪卫东:《鲁迅杂文:何种“文学性”?》,《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42] 沈从文:《1979 复伯海》,《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页、469—470页。
[44][45][51] 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266页、259页。
[46] 沈从文:《198007 复邵燕祥》,《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49][50][55][58] 《沈从文全集》编委会编:《沈从文全集:附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11页、7页、14页。
[52] 沈从文:《19761007 复陈从周》,《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页。
[53] 沈从文:《〈徐志摩全集〉序》,《读书》1983年第5期。
[54] 《编辑余话》,《新月》1928年第1卷第8号(1928年10月10日出版)。
[60] 参见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1] 王周生:《丁玲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62] 沈从文:《19780116 致杜运燮》,《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64] 沈从文:《19481207 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65] 沈从文:《剧变前夕家书》,《泥涂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0页。
[66]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北京鲁迅博物馆大事记》,《北京鲁迅博物馆四十年(1956-1996)》,北京鲁迅博物馆1996年版,第71页。
[67] 李杨:《鲁迅的传记写作与史料考证研究——朱正先生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4期。
[68] 沈从文:《19830807 复小岛久代》,《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69] 参见沈从文:《19791015(1) 复孙玉石》,《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70] 1929年第2卷第6期和第7期、1930年第3卷第5期和第6期均为合刊。
[71] 《诗刊预告》,《新月》1930年第3卷第2期,封底。
[73] 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74]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