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日:新闻史视角下的记忆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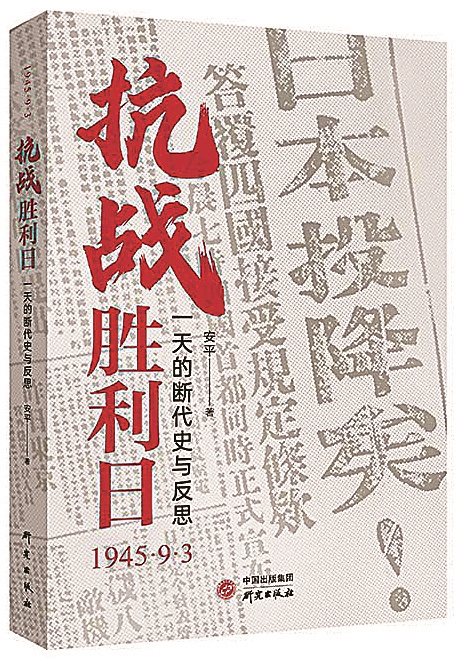
《抗战胜利日:一天的断代史与反思》,安平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1月
1945年8月10日,重庆。一个路过黄家垭口菜市场的女学生在日记里记下一则东北人“道德绑架式”的劝酒场面。然而,无论是劝酒的东北人、被灌酒的路人,还是她自己,都没有认为这一行为有什么不妥,反倒是为之泪流满面。
那一天的重庆充满“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氛围,杜甫的这句诗也出现在各大报纸关于“日本投降”的号外和社论中。商店里的鞭炮卖光了,街上弥漫着经久不散的硫黄味,餐馆连续几天免费开放。报社门口等待新一期号外的民众,把大门都捶出了裂缝……山城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彻夜狂欢,迎接抗战来之不易的胜利,“今日不饮,更待何时”。
渤海大学教授安平兼具新闻人、历史学者等几重身份,他将这些情绪饱满的瞬间都集结进了《抗战胜利日:一天的断代史与反思》一书中。这本书聚焦于“一天的断代史”,其核心魅力正在于捕捉胜利日的情感脉搏,重现了一个鲜活流动、饱含情感张力的历史现场。
国际范围内书写“历史转折日”的断代史作品,珠玉在前者有拉莱·科林斯与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合著的《巴黎烧了吗?》。它以1944年8月巴黎解放之时是否被焚毁这一历史悬念为轴,从政治博弈、道德挣扎、民众反应的层面切入,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近年来,以精缩时间单位呈现战争史的作品,为大众所熟悉的还有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敦刻尔克》,它展现了多线并置时间结构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在中文写作的视野下,还是在历史写作领域,安平这种聚焦单一历史日的微观断代史写作,仍属颇为少见的尝试。
作为一位有着新闻史、日本现代史研究背景的学者,安平将国人的喜悦、日本的崩溃与战后的记忆、争议和反思浓缩于抗战胜利日前后的时间容器中,其目的并非是为拼凑一本“日记体的编年史”。《抗战胜利日》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文学式历史调查,它以“节日”的面貌呈现不同意识形态场域,并以新闻的形式承载历史的诸多细节,让1945年8月15日从一个被纪念的时间节点,转变为可供大众重新审视、反思的叙事窗口。
全书分成三个篇章:上篇“狂欢中国”,中篇“疯狂日本”,下篇“胜利日的反思”,分别对应“抗战胜利日”中不同阵营、不同人群的状态和心理反应。
在上篇的“狂欢中国”中,首先呈现的便是“陪都”重庆普通民众、学生、知识分子在迎来胜利消息时的狂欢氛围;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军民通宵达旦的庆祝庆典和中央军委会议紧张的工作部署同时进行,身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中共中央在这一时间作出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也赢得了国外一些友好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字投降,《大公报》记者记录下麦克阿瑟将军为签字仪式准备的六支派克钢笔,并率先将日本投降的新闻传播到全世界……
中篇“疯狂日本”是对日本民众心理、日本军部抵抗机制的集中书写。从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日本的拒不投降态度,到裕仁天皇的“圣断”广播;从日本败将的剖腹自杀到“诏书”文本里的文字游戏,再到普通日本民众的漠然、愤恨与疯狂的“自杀式”攻击……安平在这一部分展现出了对日本史的熟稔,通过文献史料、士兵口述、战犯记录等翔实材料,将日本人眼中“最长的一天”描绘得如实且冷峻。
下篇的“胜利日的反思”,是全书中最具问题意识和深度的部分。安平重点提出了几个问题:“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吗?”“一亿总忏悔论的真相是什么?”这些问题直指日本战争责任及未尽事宜,其反思深刻而犀利。
在《抗战胜利日》一书的新版序言中,安平写道:“记者,记录者也。”在他眼中,见证历史瞬间、记录历史事件、参与历史进程是记者之天职。然而,记者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者,更应是发现者和思想者。因此新闻也不只是历史的旁白,而是其结构组成部分。《抗战胜利日》中使用的史料,大量引用了报纸社评、图片新闻、广播文本。这是多年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安平擅长的视角和语言。他在以直观史实内容还原昔日情境的同时,也着意于呈现舆论语言的语调、态度,以及版面头条、版式设计等细节内容。如书中提及:重庆《大公报》放出特地刻铸制作的铅字特大号标题——日本投降矣!这并不多见的头条标题使得《大公报》一出现在街头,便引发读者争相购买。
在《抗战胜利日》的附录部分,安平收集了艾青、梅兰芳等各界人士在胜利日创作的短文、社论与随感。这些新闻、文学、政治文本在同一个“节日”场域中相互映照、彼此阐释,凸显了本书史料来源的复合性特色:昔日的报刊、广播稿、口述史,乃至部分经作者严格筛选的网络文献资料,都被纳入其史料范围。
在当下的学术写作中,网络信息仍普遍被视为“不够严肃”的材料,特别是其中涉及主观表达或未经充分验证的部分。但安平作为新闻史研究者,深知媒介变迁下“历史的边界”早已扩展,网络平台本身也是媒介史的一部分。因此在《抗战胜利日》中,网络资料也被纳入研究视野,经过新闻人的专业加工与严谨注释,转化为具有史料价值的文本。这一策略不仅拓展了史料的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读者传统的文献认知。
作为一部在通俗与学术之间游走自如的断代史佳作,安平的历史写作用“节日”的象征性重建了胜利日,让我们重新思考“谁讲述了这段胜利”以及“我们又如何被讲述”。这本书提醒我们:新闻——这一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文本类型——蕴藏着历史的真实温度与痛感。作为经历过苦难与屈辱历史的中国人,我们不该只在一年一度的特定日子追忆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更要在阅读中理解历史的复杂,铭记历史。
(李蕙萌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志伟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