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想象的卡尔维诺图书馆
意大利“卡尔维诺实验室”(Il Laboratorio Calvino)自2023年起与卡洛奇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包括评论综述、文献学研究、接受研究、各类新诠释和新调查等在内的系列专著。在首批出版物中,实验室主任劳拉·迪·尼可拉(Laura Di Nicola)教授所著的《卡尔维诺的理念:批评释读与实地研究》(Un’idea di Calvino: Letture Critiche e Ricerchesul Campo,2024,以下简称《卡尔维诺的理念》)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关于作家的图书馆、他与书籍的关系及其自传性书写的宝贵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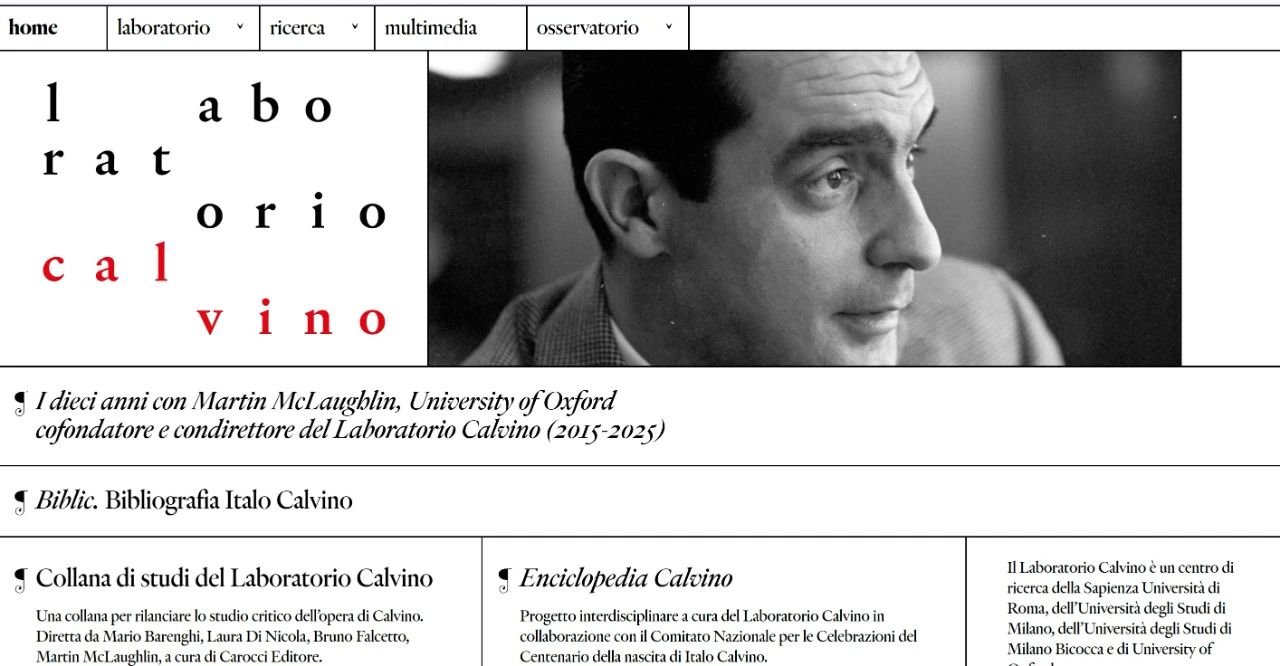
“卡尔维诺实验室”网站,图片由作者提供
尼可拉的工作始于卡尔维诺去世20年后,她从2006年起定期访问作家生前的最后住所——罗马战神广场的一栋公寓,与作家遗孀奇奇塔一同检阅卡尔维诺的开放式工作室,对有序摆放在4个大型书架、175个隔层中的7674本书进行编目。此前奇奇塔一直小心维护着卡尔维诺的私人图书馆的秩序,使之保持了作家离世前的原貌。2020年,工作室内的所有书籍、文件及家具被移交至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并在那里按卡尔维诺寓所的陈设布局建了“卡尔维诺厅”。这既是一个向公众开放参观的作家展厅,也是一个可供研究者勘探的学术空间,如尼可拉所言,“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图书馆不仅是一个作家的实体图书馆,还是一种辅助工具,可以用来揭示他笔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来源,从原初的角度理解他如何工作,并识别那些他为了写作和叙事而阅读和研究的东西”(Idea: 13)。尼可拉的著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示范了一条进入这个图书馆的路径。
《卡尔维诺的理念》全书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男读者,女读者”通过分析卡尔维诺两部代表作中理想读者的形象,阐释作家笔下阅读与写作的同构关系;第二部分“自我,他者(别处)”梳理卡尔维诺思想史中的自传问题,剖析作家在书写自我与隐藏自我的矛盾张力中所蕴蓄的身份认同;第三部分“图书馆,书架”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详述卡尔维诺私人图书馆中书架与藏书的构成样貌,在与作家遗作《美国讲稿》的对观中勾勒作家的文学理念轮廓;第四部分“卡尔维诺如何工作”为案例分析,重点评述了卡尔维诺对几部特定藏书写下的旁注。本文聚焦于前三部分的主要议题,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解读尼可拉对卡尔维诺图书馆的开创性考察,并提示未来可能的研究进路。
01 理想读者:隐性自传的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起,卡尔维诺作品中的读者角色开始成为意大利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如伊索塔·皮亚扎曾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作家笔下的读者形象能像伊塔洛·卡尔维诺的那样如此强力地介入批评性思考与文学构设。”读者对书籍之爱贯穿卡尔维诺的创作生涯:《懒儿子》(I figli Poltroni,1948)中的青年皮埃德罗、《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ampante,1957)中的柯希莫、《烟云》(La Nuvola di Smog,1958)中供职杂志社的主人公、《观察者》(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1963)中的共产党员阿梅里戈、《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1979)中的男读者与女读者、《帕洛马尔》(Palomar,1983)中的同名主人公……在卡尔维诺笔下,读者由不同作品中的人物担当,其书籍之爱亦随着作者/主人公年龄的增长、阅读兴趣的扩展和日臻成熟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可以说,这些读者角色在时间轴上体现了卡尔维诺阅读理想的演变,“构成了一个可借之观察作者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以及读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的参照点,也广泛地展现了卡尔维诺的诗学”。
基于以上背景,《卡尔维诺的理念》一书从读者的角色开启。第一部分标题为“男读者,女读者”,聚焦于卡尔维诺笔下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读者形象——柯希莫和柳德米拉,即《树上的男爵》(后简称《男爵》)中的男性读者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后简称《旅人》)中的女性读者。尼可拉之所以选取这两个角色来论述,是因为他们分属于卡尔维诺不同的创作时期:童话寓言时期与后现代创作时期。两个角色的阅读品味一个更多朝向过去(18、19世纪),一个更多朝向未来(20、21世纪)。他们所阅读的书籍最终都与卡尔维诺本人阅读与写作的历程交织在一起。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卡尔维诺早期作品中的读者形象主要反映了作家本人年轻时的杂食性,易被文字世界所诱惑,那么到了50年代末的成熟期,他笔下充满批判性的理想读者形象则强调保持阅读与现实的边界。
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敏锐地指出,这位审慎的意大利作家“在过去四十年间,除了一些并不重要的尝试,甚至未曾创造过一个不是自身变形的角色”。而柯希莫的特殊性恰在于他可在多个层面被视为卡尔维诺在幻想领域的分身。尼可拉从这一角色的自传性特质切入,认为柯希莫这个高踞于树、孜孜阅读的传奇人物是卡尔维诺在特定时期的自我投射——“或许从柯希莫身上,卡尔维诺首次在他的诗学里发现,他可以通过文学来表达将自我及生活置于梦想之上和生活之外的重要性。”(Idea: 24)在小说的各种幻想机制中,尼可拉着重关注主人公构建自己“图书馆”的方式——柯希莫为了在树上存放书籍“经常搭建各种悬挂式图书馆”,并“根据自己一段时期的研究方向和阅读喜好不断变换书架的位置”。他与书籍的动态关系——“他认为书籍就像飞鸟,不希望看到它们静止或被关在笼子里”(RR 1: 653);最重要的是,尼可拉从柯希莫的书单中归纳出三条阅读选择线路:
1.古希腊与拉丁经典(维吉尔、奥维德、塔西佗、卢克莱修、塞内加、普鲁塔克);
2.“当代作品”,即18世纪的法国、英国小说(勒萨日《吉尔·布拉斯》、理查逊《克拉丽莎》、菲尔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圣皮埃尔《保罗与薇吉妮》、卢梭《新爱洛依丝》);
3.以《百科全书》为代表的涉及哲学、政治、历史、人类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树木栽培学的各类综合书籍(他最大的书架上陈列着“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RR 1: 654])。(Idea: 28-29)
尼可拉指出,柯希莫从一个分支到另一个分支,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位作家到另一位作家的“移动”均指向隐于其后的作者,他与经典的联系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追求。(Idea: 26)小说中,“书籍的引文系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按标题、作者,通过显性、隐性、直接、间接、互文、影射、回溯、联想的方式,但从不进行具体的引用”(Idea: 28),但这些书籍在互文参照中构建起了“理想的书架”(Idea: 29),成为叙事的一部分:柯希莫在树木间行走时,这些书也像飞鸟一般在他的空中书架上来来去去,持续不断地为他提供新的知识,并赋予了他“讲述新故事”的能力(Idea: 29)。更重要的是,他逐渐从读者蜕变成了写作者,撰写了《树上理想国宪法草案》。
在阅读与写作的同构中,柯希莫的图书馆即卡尔维诺的图书馆,卡尔维诺的书架上遍布柯希莫的足迹。尼可拉对卡尔维诺图书馆的检视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其笔下人物思想的来源:在卡尔维诺的藏书中,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社的“浪漫主义丛书”(la Biblioteca Romantica)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书系”(La Librairi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显然与柯希莫的阅读密切相关;而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书籍(1957年之前的版本),与主人公在小说第19章中的署名“柯希莫·隆多,百科全书的读者”(RR 1: 696)相呼应;此外尼可拉还补充了两部在小说中未被引用,但很可能对卡尔维诺的创作起到指导作用的文本:卢梭的《植物学》(1802年意大利语版)、《〈忏悔录〉与〈孤独漫步者的遐想〉》(1951年法语版)。尼可拉强调,即使在《男爵》出版后,这些作者的再版书籍(即1958年后的版本)依旧可以在战神广场公寓的书架上找到(Idea: 41),这无疑意味着一种长期的热爱,也显示了柯希莫/卡尔维诺所朝向的18世纪不止是一场奇幻历险的背景,其拟追溯的启蒙思想的遗产更值得认真看待(Idea: 37)。
卡尔维诺在后期作品《旅人》中更深入地讨论了书籍、文学、阅读的关系。《旅人》是他对阅读主题倾注最大关注的一部小说,其中“读者”成为小说的主角,“既是作者的对话者,也是现实读者的投射”,与卡尔维诺这一时期想要与公众建立新联系的愿望密切相关。这既是一部关于阅读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写作的小说,作家在其中精心构设了一个多重嵌套的复杂机制:“书中的匿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主角读者,后者又进一步转变为作者,而作者同时也是其自身的读者。”(Stile: 146)该作自1979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大量关于元叙事、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的讨论,被奉为后现代小说的典范,但正如尼可拉所指出的,其复杂性亦“使批评陷入了叙事和认知陷阱的悖论”(Idea: 46)。尼可拉此项研究的开创性恰在于拂去各色批评流派为它贴上的纷繁标签,另辟蹊径,将这部看似最非个人化的小说还原成一部充满作家个人印记的作品。在最直观的层面,小说讲述的是一位男读者与一位女读者的故事、一对夫妇的故事;已有论者指出,它“带来一条简单的爱情信息”,然而在本质上它是一部“关乎爱欲的不寻常的自传性告白”(Stile: 145)。这无疑是个新颖的视角,因评论界普遍认为卡尔维诺大多数时候“是一个藏在面具后面的作者,他掩盖自己的身份,避开自我和内心世界的表达”(Idea: 58),但随着意大利学界对卡尔维诺自传片段的挖掘与重组,部分敏锐的评论者开始关注卡尔维诺书写自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如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在为卡尔维诺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所说:“他在支持并论证以‘抹除作者的自我’为特征的文学主张的同时,并未脱离自己。他呈现于幕前的是一个希冀向所有空间敞开的‘自我’,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随时准备牺牲自身存在的轮廓。”(RR 1: XXXI)
不容忽视的是,卡尔维诺藉其笔下理想读者所表达的爱的主题,除了文学与书籍之爱之外还有两性之爱,二者相互交织;而后者如前者一样,亦可从自传性的角度找到印证。《男爵》中柯希莫的爱人薇莪拉有着明确的现实原型,可将之视为卡尔维诺本人的一段爱情自传,这在学界已是共识,而《旅人》中柳德米拉这一角色,以及男读者与其的爱情该如何读解则尚无定论。“为什么要有一位女读者和一位男读者呢?或许是妻子读者持续散发着欲望的魅力,而丈夫读者总是被她所吸引?或许是夫妇二人通过书籍的语言,促成了对圆满婚姻的渴望?”在《男爵》中卡尔维诺将自己化身为柯希莫:“我认真对待他,相信他,与他融为一体。”(RR 1: 1214)而在《旅人》中,卡尔维诺显然没有将自己投射到无名的男读者身上,相反他将女读者赋名为柳德米拉,视其为“真正的主人公”,并在一次采访中称“柳德米拉就是我”。柳德米拉无疑代表了卡尔维诺的阅读理想,但在其他层面似不足成为一个自传人物,这也造成了阐释的困境。
尼可拉提出的论点起到了补全拼图的作用。她认为,卡尔维诺对柳德米拉的投射性认同是基于融合的渴望:“对他而言,柳德米拉是(妻子)奇奇塔,他渴望与之共同存在”(Idea: 53);“《旅人》也是卡尔维诺对妻子的献词,一种言说对方和自己的方式”(Idea: 52)。尼可拉对卡尔维诺私人图书馆的检视,在与小说文本的对照中提供了线索的印证:《旅人》第二章,男读者首次邂逅女读者时,后者正在书架间查看“企鹅现代经典丛书”(RR 2: 638)。尼可拉提请读者注意,“柳德米拉对企鹅经典作品情有独钟并非巧合,它们同样呈现在奇奇塔的书架上。正是得益于她,如今卡尔维诺的作品才被收录进著名的企鹅经典系列”(Idea: 53)。无独有偶,男读者在第七章走进了女读者的家,仔细观察她的书籍及其排列摆放的方式:
目光接触的第一印象,至少从那些你放在最显著位置的书来看——对你来说书是用来即时阅读的,既不是作为学习或查阅的工具,也不是要构成像图书馆那样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的藏书。也许你有时会尝试赋予你的书架某种表层的秩序,但每次分类的企图都会很快被异质性的内容所打乱。……然而,你总是知道如何找到它们,因为书的数量并不多(其他书一定是被你留在了其他住所,你人生中度过的其他阶段的书架上),也许你也不需要经常找一本你已经读过的书。(RR 2: 754-754)
对书籍存在方式的描写是绘制柳德米拉肖像的重要一笔。尼可拉指出,柳德米拉不多的书籍(尚不足以构成一座个人图书馆)仍与奇奇塔相关——卡尔维诺夫妇从巴黎搬回罗马后,他将妻子的书籍据为己有,放置在自己的图书馆中(Idea: 53)。《旅人》的故事处处与卡尔维诺和奇奇塔的故事交叠在一起,这种交叠亦影响了小说的架构:尼可拉在检视卡尔维诺的笔记本时发现了其中记录的“奇奇塔提供的开头语”,通过对照原文本,她指出这些句子“或许触发了某些微小说的重要机制,甚至是10个最终片段的整体构思”。(Idea: 51)在《旅人》中,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跳跃由柳德米拉的阅读欲望所驱动,而卡尔维诺的这则笔记为柳德米拉与奇奇塔的对位提供了证据。
卡尔维诺一方面追求写作的匿名状态,这一点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从自身经历广泛汲取叙事素材,这二者间的张力是如今意大利学界重建其“未完成自传”的根基。隐性的一线并不总是能立即被域外读者所识别,但前文所述的隐藏在作品中的碎片式自我无疑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勘探路径:“卡尔维诺式的‘我’因被赋予了‘植根于自我的特质’而具有典型价值,为重新定义其存在和想象机制提供了契机。”(Idea: 62)随着意大利本土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起系统性整理出版卡尔维诺遗作文集,批评界在新千年后更加关注卡尔维诺思想史中的自传问题。尼可拉的著作不仅从两个理想读者的角度作出了自传性解读的尝试,还在总结学界现有进展的基础上提示了三条可供追踪的路径:1.叙事作品中的自传性;2.散文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自传;3.明确的自传文本。(Idea: 62)由于卡尔维诺的创作跨越诸多体裁,且其非虚构作品经常入侵虚构作品,因而这三条路径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其中有大量丰富的素材有待学界继续挖掘。
02 作家的图书馆:记忆的分层
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学界对当代作家私人图书馆的兴趣和研究开始逐渐成形,衍生出一种批评范式。一些学者意识到,作家图书馆能够为那些有兴趣深入研究作家文学世界的人提供多种材料,对其进行恰当的研究和分析,不仅能再现其所有者的个性、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还能反映出他所生活和工作的整个文化背景。在2007年由毛罗·格里尼主编的《图书馆学:分类指南》(Biblioteconomia: Guida Classificata)中,曾任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20世纪文学收藏负责人的朱丽安娜·扎格拉(Giuliana Zagra)首次对“作家图书馆”(Biblioteca d’autore)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一种私人且个性化的书籍收藏,通过单部的文献及整个收藏的内部特征,能够为其所有者的智性活动、关系网络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佐证。”《卡尔维诺的理念》第三部分“图书馆,书架”详细记录了尼可拉在卡尔维诺生前最后一所公寓内实地研究的成果。
卡尔维诺的作家好友,同为“乌力波”成员的乔治·佩雷克曾在《关于整理自己书籍的艺术和方式的简短笔记》中写道:“每个图书馆都回应了双重需求,这通常也是一种双重癖好:一是保存某些事物(即书籍),二是以某种方式整理它们。”这也是研究者面对作家的图书馆时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作家收集书籍的方式(需追溯其不同的来源);不同藏书间的联系(需描述其系统的建立)。但二者往往都意味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图书馆是一个随着时间而成长和变化的‘活体’。……它缺乏一种历时性的深度视角”。鉴于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往往是作家晚年的图书馆,其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层层累积而形成,即它是作家于不同阶段不断收集的结果。而卡尔维诺留下的图书馆完美契合了这一点——尼可拉指出,卡尔维诺的所有书籍“都是与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居住的寓所、经常访问的图书馆、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与记忆图景的一部分”(Idea: 104),她详细勘探了构成卡尔维诺最后一座实体图书馆的藏书的三大来源:
1.来自圣雷莫梅里亚娜别墅的书。卡尔维诺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积攒了人生前25年的书籍,可大致分为文学启蒙类和继承自家族成员的书,前者从吉卜林的《丛林之书》到科洛迪的《匹诺曹》再到卡夫卡的《美国》;后者则包括卡尔维诺的农学家父母自己撰写的植物、园艺学著作和日常阅读的文学读物以及她的化学家叔叔订阅的蒙达多利出版社“浪漫主义丛书”。
2.来自都灵圣茱莉亚路80号的书。卡尔维诺自1941年起定居都灵,该处的藏书与他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担任的编辑工作有着密切联系,但由于寓所空间有限,卡尔维诺在挑选和舍弃书籍时越来越严格。(Idea: 109)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作者有:帕韦塞、维托里尼、帕索里尼;康拉德、蒙塔莱;博尔赫斯、科塔萨尔。
3.来自法国夏蒂永广场12号的书。这是卡尔维诺1967至1980年的寓所,他在阁楼顶层的工作室中陈列了约五千本书,他还经常持借书卡查阅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在新的文化坐标中,他经常阅读的作者包括:格诺(及乌力波小组)、傅立叶、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蓬热、瓦莱里。
需注意的是,三个“子图书馆”的顺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递进,而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彼此平行。正如卡尔维诺在197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的:“然而,我却从未有过一个能把所有书汇集一体的完整图书馆:我的书有些在这儿,有些在那儿;当我在巴黎要查阅某本书时,它总是在意大利;当我在意大利要查阅某本书时,它又总是在巴黎。”(RR 3: 106)作家如候鸟般在不同城市间辗转,他的书桌“仿佛一个岛:既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RR 3: 103)。也就是说,卡尔维诺的“完整图书馆”只有在1980年搬回罗马后才得以实现,他在战神广场公寓内汇集了那些源于其他住所、其他生活阶段的书籍。但这里的“完整”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并不能准确衡量卡尔维诺各阶段藏书的实际规模。因为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部分书籍被作家舍弃,部分遗失,还有部分被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在保留下来的书中,亦有必要区分“活跃”的部分与“死滞”的部分,后者中的一些可能会在作家下一次“修剪枝叶”时被剔除。
“图书馆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方面:首先是空间问题,其次是秩序问题。”厘清书目来源问题后,尼可拉的下一项工作便是描述这些书籍在卡尔维诺图书馆中的呈现方式。她指出,卡尔维诺搬回罗马后,面对大批书籍,他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放置系统,在不断的挑选与弃置中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知识体系。如今要对其作出界定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能找到书籍的系统”(Idea: 133)。她的开创性工作在于对4个大型书架(其中一个作为隔断的书架是双面书架)共计175个隔层进行了忠实而详细的编目,绘制了5张图表,使读者能够直观获知卡尔维诺每一隔层所放置的书籍的主题(按国别、文化或语种),进而想象其背后的逻辑方式与内部肌理。
其中最大、最显眼、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书架占据了客厅的一整面墙(含87个隔层,共放置了4355本书),是卡尔维诺知识地图的代表,提供了管窥作家理想图书馆的最佳观测点。从尼可拉提供的图表可知,编号为VI.D的隔层占据了书架的中心,放置的是卡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的作品。加达缘何成为卡尔维诺图书馆的中心?鉴于其对意大利域外读者来说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甚至算不上一位与卡尔维诺有明显亲缘关系的作家,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加达是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Lezioni Americane,后文简称《讲稿》)中用以开启“繁复”一章的作者,但要理解加达对卡尔维诺的意义,还应追溯此前的两篇书评《世界是一颗朝鲜蓟》(1963)和《卡洛·埃米利奥·加达:〈梅鲁拉纳街上一场可怕的混乱〉》(1984):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现实是繁复、多刺、层层相叠的。就像一颗朝鲜蓟。文学作品对我们而言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像剥不尽的朝鲜蓟一样不断翻阅它们,并从中发现阅读的新维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今人们所谈论的所有重要杰出作家中,或许只有加达才配得上伟大作家的称号。
加达曾阐释了一种将世界视为“众多系统的系统”的观点——这源自人们在他去世后在其遗稿中找到的一个哲学笔记本(《米兰沉思录》)。这位作家从他喜欢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出发,构建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每个单独的系统都与同一系谱中的众多系统相连;每一元素的改变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形。
两篇文章跨越了20年的时间,从层层相叠的朝鲜蓟到有着众多系统的世界,最终以《讲稿》中关于“繁复”的想象定格在卡尔维诺1985年图书馆的中心。在深层意义上,“卡尔维诺从加达那里继承的遗产是独一无二的:这不是一种风格遗产,而是一种思想遗产”。卡尔维诺看重的是作为系统的世界和亟待发现的事物之间的无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意义:每一个易被忽视的节点都可能衍生为关系网的中心,而沿着每一条线索追溯,愈来愈复杂的细节最终会包揽整个宇宙。带着这样的眼光去检视卡尔维诺图书馆的其他隔层,才能更深切地体悟到其所展现的作家智识系统的延伸。
从加达这一代表“系统之系统”的中心散射开去,卡尔维诺的图书馆亦是一个复杂的、包含了众多系统的系统,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开始,朝任何方向前进。尼可拉花了大量时间去探索卡尔维诺的书籍系统,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起点:左侧第一列底部编号为I.F的隔层就像一棵树的根,摆放着但丁、彼特拉克、卡瓦尔坎蒂等意大利文学的奠基者;从这一隔层往上走,有薄伽丘(I.E)、阿里奥斯托(Ⅱ.E)、莱奥帕尔迪(III.E);这棵树按时间顺序伸展枝叶,最终在顶部到达20世纪意大利文学(I.A-VII.A,7个连续的隔层,按字母顺序排列)。从顶部往下,各种分支扩散开来:语言学、符号学;自然科学(物理、数学、天文学);人文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国别文学(有法、英、美、日、俄、拉美作家的单列,也有东方文学和波兰、挪威等小语种国家的集合)……如朝鲜蓟般瓣瓣叠加、如晶体立面般层层折射的书架形成了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勾勒出整个20世纪的认识论基础。
作家的图书馆是阅读与写作交遇之处,研究者需依据主人的个性洞察其间的独特秩序。安娜·多尔菲曾从卡尔维诺的文论随笔《作为欲望表现的文学》(“La letteraturacome proiezione del desiderio”)中识别出一个具有博尔赫斯风格的图书馆理念——图书馆不仅被视为单本书籍的集合,更被视为一个相互交叉的组合系统。尼可拉则进一步描述了卡尔维诺的图书馆系统,将其界定为三层嵌套的同心圆系统:第一层,每个大型书架都有一个重心,与其他重心进行对话,并在知识领域间形成星座;第二层,每一隔层都有一个重心,与其前后的书籍进行对话;第三层,每本书都有一个重心,与所有作品对话。(Idea: 136)最终,图书馆就像一个“洋葱”或“朝鲜蓟”,可以不断剥开,从中发现阅读的新维度;而其中的书籍“可以像铁路时刻表一样被检索,从而确立思想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系与交汇点”(Idea: 137)。在这一意义上,图书馆亦是一部关于作者的百科全书,其内部层级及肌理与作家的智识历程形成同构。
03 一份知识地图:真实与虚构的向度
1984年6月6日,卡尔维诺接受哈佛大学的正式邀请,前往担任1985—1986学年的“诺顿讲座”的主讲人。1985年1至9月,他几乎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讲稿的写作中,直至猝然离世使得这一计划中断。最终,这些他“准备随时收入行李箱中带走的打字稿”经其妻子和美国编辑整理出版,成为如今广为人知的文论《美国讲稿》。众多学者已探讨了卡尔维诺这部遗作的重大意义,如意大利文学史家、卡尔维诺资深研究者阿尔贝托·阿瑟·罗萨(Alberto Asor Rosa)曾评价:“这与其说是狭义上留下的遗产,不如说是一份‘见证’,作家在公众面前展现了他最深刻的文学与诗学信念,以及他多元且矛盾的世界观。”(Stile: 67)尼可拉则认为它“不仅是一部文学观念的奠基之作,一份谈论其作品的目录,更是他的图书馆、他一生中的藏书的最美记录”(Idea: 119)。
在研究者们对这份讲稿的大量引用中,其“经典性”已被确证,其“未完成性”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未完成性”首先体现在总标题上,其次体现在6个篇目关键词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可能的版本的差异上,以至于如罗萨所言,“对于这样一位习惯让作品付梓前经历无数道详尽审查工序的作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如何使用这些‘讲稿’”(Stile: 65)。
强调“未完成性”,意味着将《讲稿》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意识到卡尔维诺留下的这本书不过是一张定格于特定阶段的“快照”。尼可拉恰切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未完成”的意义上将卡尔维诺的两份遗产联系到了一起。她写道:“卡尔维诺1985年去世时,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图书馆,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彼此映照:一个是由书籍构成的‘世界图书馆的理念’(战神广场的图书馆),另一个是‘世界思想的图书馆’(《美国讲稿》)。”(Idea: 115)前者通过层层的分类系统定义了书籍的地图,后者则通过翻阅自己内心想象的记忆来构建,卡尔维诺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位于两者之间:必须识别出那个点,即所设想的图书馆与实际的图书馆不重合的地方,找到它在文学和生活世界中的位置。(Idea: 115)
《讲稿》的一项显著特质在于,其中交织着大量的文学引用:“卡尔维诺提到了约90位作家,这对一本只有104页的小册子(子午线版)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Stile: 109)这是一本辑录“作者之书”的图书馆,从巴伦吉到罗萨再到后来的大量学者都曾尝试过从中提取一份详细的书单,以确定它们在卡尔维诺知识谱系中的位置。而尼可拉对卡尔维诺实体图书馆的开创性研究则展示了另一种观看与探寻的方式:可以把握近与远的关系(难以取及的书籍、触手可及的书籍、靠近书桌的书籍);有序与无序的关系(反常的书籍、偶然出现的书籍、待重新放置或可能与更微妙的思想线索相联系的书籍);满与空的关系(遗失、减少、空缺的书籍,或经筛查、淘汰、精选的书籍);先与后的关系(出版时间上——过去与现在的书;空间放置上——在前与在后的书)。(Idea: 103)换言之,这是一个潜在的文献库,书籍在其中的摆放秩序构成了文本的镜像——将书籍并列放置(如同页),将它们放入书架之中(如同章节),依据精确的顺序将它们排列在概念和想象中的地图上(如同结构)——从外部生成性的角度映射出作家“思想剧场”的空间。(Idea: 115)
真实与虚构的两座“图书馆”形成了引人入胜的交叠。卡尔维诺在写作《讲稿》时,穿行于自己的书籍之中:“我开始翻阅我图书馆中的书,寻找轻盈的意象。”(Saggi: 645)尼可拉告诉我们:“卡尔维诺用于撰写诺顿讲座的书籍并未被存放在特定的位置……它们散布在各处,在需要用梯子才能到达的书架上,或者是在后面的阵列中(这意味着他可能需要移动所有前面的书来放置它们)。令人不禁设想,卡尔维诺是凭记忆引用这些书籍的。”(Idea: 201)如果说《讲稿》这一巨大的精神图书馆是从作者一生中阅读的所有书籍中进行选择,那么“在卡尔维诺罗马战神广场图书馆内的约8千本书中,他只选择了极少数”(Idea: 123-124)。这也意味着,两座图书馆都存在显性的部分——记忆与选择;隐藏的部分——遗忘与弃置。
相较而言,显性的部分更易识别,只需对比《讲稿》中重点提及的作家,以及实体图书馆中显要位置的隔层即能获悉其大致的轮廓,但研究者仍有必要进一步辨析其中的首要层级与次要层级。如罗萨曾在对《讲稿》的研究中指出,从卡尔维诺的大量引用中可区分出两类文本,一类是单纯的只供他阅读的作品,为支撑或印证某个特定论题而引为论据;另一类则是在显性或隐性的意义上被他视为真正“模型”的作品。(Stile: 105);尼可拉在划定卡尔维诺实体图书馆范围时也使用了这样的二分法:“每个书架上都有活跃的和死滞的。后者是卡尔维诺甚至没有翻阅过的书籍,但他决定把它们留下来,放在那个特定的位置。”(Idea: 133)尼可拉将两座图书馆描画出的两幅地图进行了详尽的对比,指出二者间“存在惊人的巧合”(Idea: 124):在现实图书馆中,加达、格诺、卡夫卡、巴特四位作家享有单独的特定隔层,他们在《讲稿》中亦出现在同一讲中;而佩雷克和博尔赫斯在同一个书架上,在《讲稿》“多重性”一讲中亦然。且两座图书馆中都有一批重要的作者被反复提及,仿佛无处不在:康拉德、瓦雷里、莱奥帕尔迪、但丁、莎士比亚、卢克莱修等人的作品在卡尔维诺的实体图书馆中没有固定的位置,散落在多个书架上;卢克莱修、但丁、莱奥帕尔迪、博尔赫斯、瓦莱里五位作者则在六份讲稿中的三份中均占据了席位。这些名字构成了卡尔维诺图书馆的首要层级,是具有“模型”意义的典范。就像尼可拉在图表中为卡尔维诺书架的每一隔层都总结了一个主题,她在对《讲稿》的重新梳理中也为每一讲(六份备忘录,在其同构的意义上就像六个书架)确立了一个“引力中心”。这在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必要指引的同时也进一步铺垫了新发现的可能,她提醒道:“从这里开始,我们应该重新出发,重新组合一切,并创造出其他的路径。”(Idea: 130)
隐性的部分不易被立即识别及作出确切的定义,但对解码图书馆的“未完成性”而言甚至更为重要。例如,尽管卡尔维诺在《讲稿》中援引了大量文本材料,但部分敏锐学者已讶然发现一些重要名字的缺席:“像阿里奥斯托、康拉德和斯丹达尔这样的经典作家,在卡尔维诺的文学履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他们在作家的‘理想图书馆’目录中的缺失(完全缺失或几近缺失),意味着他更注重自己晚期的读物和偏好。”(Stile: 109)想象的图书馆与现实的图书馆并不完全重合,这也体现在尼可拉对卡尔维诺实体图书馆的发现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放置含伽利略在内的科学散文的书架并不容易触及(在较高层的书架上)”(Idea: 134),而“日本文学在卡尔维诺的书架上占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核心位置——在书架的核心,放置加达的隔层的正下方”。由于卡尔维诺的两座图书馆都在各自的意义上吸纳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作者,在书籍的摆放秩序和写作的素材库中建立各种自由的联系,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捕捉其中隐性的“联想游戏”,这些联想“与作家的多重个性、精神和品味相契合,并非总是易于理解”(Stile: 105)。
譬如,在《讲稿》“快”一章的结尾,卡尔维诺讲述了一个“庄子画蟹”的中国故事,但这是一篇伪作,其伪装性不仅难被欧美读者所识别,中国读者亦很难立即辨出其中端倪。卡尔维诺是否真正读过《庄子》,究竟是他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创造性转换,长期以来难以定论。但卡尔维诺的实体图书馆至少为前一个问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我们可从尼可拉提供的表格中勘探到他对东方文明的兴趣:其中编号为I.C、IX.F的两个隔层放置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原书标注:I.C:印度、日本、阿拉伯、波斯、中国、佛教及《一千零一夜》;IX.F:宗教文本、东方国家文学)。实际上,卡尔维诺的图书馆中不仅确实存有庄子相关著作,甚至还拥有不同时期、不同语种的两个《庄子》版本,它们在出版时间上相隔近30年,也从侧面印证了卡尔维诺对中国道家典籍的长期兴趣。卡尔维诺在何种意义上汲取来自异文化的养分,将之转化为自身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并在写作中发挥效力,这些现实文本的存在或可作为一把解码的钥匙。
然正如克里斯蒂安·德·文托所提示的,“一个私人图书馆更多地让我们能够勾勒出一种智识的轮廓,而不是精确地识别其所有者一生中所阅读的内容”,尼可拉在著作中亦将重心放在了前者,而没有对一些单独的特定作品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隐性联系作出详细的阐释。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卡尔维诺书架上一些特定隔层的书籍的讨论,正在由尼可拉所领导的卡尔维诺实验室“卡尔维诺百科全书项目”(Enciclopedia Calvino)持续推进,旨在从不同学科、不同国别的视角对作家的图书馆进行研究,重建卡尔维诺与广泛学科和知识网络的复杂联系。
从对卡尔维诺笔下读者形象的检视到对实体图书馆中不同时期书籍的溯源,再到与《讲稿》这一精神图书馆的比对,尼可拉对卡尔维诺真实与想象的图书馆的研究最终回落到对其中所蕴蓄的对“自传性”的强调上——与其重要对话者博尔赫斯一样,卡尔维诺的图书馆完全是“他人之书”的图书馆,其中并没有放置自己的作品,但这个“缺席”的自我仍以间接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面向一排排书架,他在不同篇章中反复提及的“经典”作家,“他把作为读者的自己置于镜前,发现其中映射出作家卡尔维诺的形象”(Idea: 139)。卡尔维诺的图书馆,就像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一样,是宇宙间无限可能的集合,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就像书签一样,藏在他图书馆的每本书里”(Idea: 16)。但藉尼可拉的贡献,这张知识地图正在新一代读者面前徐徐展开。就像卡尔维诺那些充满挑战性的小说一样,他的图书馆也为读者提供了无数个可能的入口与出口,其秘密无法穷尽,但我们至少可以“在阅读他、研究他、热爱他的过程中,领悟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Idea: 131)。


